来源:798艺术 文:李旭辉

“HOLZWEGE” 香格纳西岸新空间开幕展 2016年
在一味追逐经济发展的城市丛林里谈论反思现代性其实是件超现实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人们一边要追求架构在现代科技和金融基础的现代都市飞速发展,但一方面又要忍受自然资源的萎缩和污染,城市个体的疏离和焦虑,以及精神信仰的虚无糟糕处境。对于上海香格纳画廊而言,20年后选择用哲人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作为自己画廊经验积累的回答,但在巨大的英文标题《Holzwege》“林中路”中,香格纳也用中文“殊途”加以提醒另一重现实。
回望40年前的文革美术,艺术家往往必须依照统一的政治题材来创作作品,这种命题作文式的创作方式,曾经渲染了一个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红光亮时期,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无疑中国的艺术都是处于这种模式之下,80年代中期,受惠于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少数艺术家开始跳出原有的创作方式,开始模仿或在借鉴中寻找自己的文化方式。要回望过去,香格纳展出了老一辈艺术像余友函,李山,梁少基,丁乙等艺术创作能窥见当时艺术家的创作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吕佩尔茨,伊门多夫等人的创作也给予西方创作方式一个背景影响。

余友涵《5个女人》
展览中的《5个女人》余友函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此之前他从早期的风景,到中期的抽象,事实上也是循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路又夹杂着自我文化里的一些实验慢慢走过来,按照余有函的说法这些是在象牙塔里面的东西。但到1988年他开始创作“毛系列”,这也是在85‘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艺术家对社会有了个体积极性后创作的,余友函的“毛系列”和王广义的“大批判”都是在波普艺术影响下的结果,但相比较下,“毛系列”更重视的是日常经验的累积,作品里运用了很多民间的版画和纺织布上的图案,这些东西构成余友函少有的一段绘画色彩艳丽的时间。但时间不长,9年之后“毛系列”受文化管控,余友函开始创作《啊,我们》系列,开始对普通人的描绘,他利用杂志图像和写生图像来创作,《5个女人》属于系列中的一组。从形式上看,余有函将伟人头像的尺寸赋予了这些无名者,但却将人像以灰暗的色彩描绘出来,她们年纪,神态各自不同,或沉醉,或自恋,或忧郁,或喜悦,但都处于艺术家营造灰黑色的画面当中,事实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媒体总会将社会中的成功者美化,而这种美化的妖柔造作又是从早期神化政治偶像的手法中继承下来的,余友函一改日常经验的处理,而在一次访谈中也谈到缘由:“我心中有些感伤,所以画面颜色不是灰的,黑的,就是咖啡的,像烂泥一样。好像我们的民族,衰败成一堆垃圾,一堆泥土了,但是偶尔里面也有生动的发光的东西。这就是《啊,我们》基本的方向。”

张恩利《土红和深绿》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张恩利的近作《土红和深绿》就有了对照的关系,依然是脏色,在巨大的画面中反复涂抹,从早期人物,到中期的风景,静物,张恩利经历一个个提炼的阶段,线条是他的最爱。张恩利的线条从早期的表现主义的狂乱,到日常风景和静物的宁静,琐碎,疏离,逐渐形成一套自我对‘线’的自觉系统,就像古代书法家一样线条要获得自由,首先要形成对现实独立的认知。实际上西方也有诸多用线大师,像马奈,劳德累克,毕加索,德库宁,汤伯利等,而在张恩利这里我们看到其对话的对象不仅是针对西方艺术,也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2015年同名个展中,张恩利创作了很多不同的树干,这些枯萎但又妖娆事物,似乎已经死去,但又是生灵活现地在画面里扭姿作态,而在2014年《头发》个展中,张恩利绘制了很多满构图的新作,线条密集地演奏着华尔兹,并第一次尝试用拼贴的方式制作。这些《头发》系列就像散乱的树叶一样与《弯曲的树》构成共鸣,而在《土红和深绿》中,看笔触被打散了,但实际上,在涂抹当中艺术家提供一一两种色彩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而这个界限从底稿中就已经有。这是张恩利2016空间绘画中最大的作品,笔触上延续其作品《the box》的方式,但在看似无序中,某种能量和秩序也在逐渐成形。

马库斯·吕佩尔兹《梳妆(梅尔基斯 )》100×163cm布、框上综合材料2014 年
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情境,其实70年德国也同样如此,经济腾飞、精神空虚。一些德国艺术家经历过东西德不同社会割裂和逐渐转变,也在其中反思其文化的方向。像吕佩尔茨的作品能够很好彰显经历过战火后现代德国人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时普遍的创伤感和悲剧感。当然艺术家也在用作品直接地批判现代人在空洞的繁华中信仰的缺失和对生命价值的遗忘。在整个《阿卡迪亚》系列,吕佩尔茨试图将传统文化中故事重新谱写。像其中《英雄》这件作品描绘在一个简单街景中两个相向而行的人碰面的情境,艺术家用厚重的笔触描绘了粗壮男子的上半身,而下半身却用干枯甚至接近消失的笔触来描绘,男子的头偏向一边。另一边的男子面目透露着冷漠,浑身缀满了黄色的点。这是艺术家2013 年的创作,这件作品中艺术家给予了英雄两重身份,一个是战火中遗留下来的残破英雄印象,一个则是在物质世界里显露有名的偶像。这种歧路的确是令人深思。与此同时吕佩尔茨的《赫库莱斯》的制作模型也在出现在展厅当中,《赫库莱斯》是艺术家自创做过的最大型雕塑,其在德国著名的鲁尔区城市盖尔森基兴的实体雕塑有23 吨重,净高18 米。而盖尔森基兴作为德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曾经在纳粹时期也是德国的工业中心,随着鲁尔区能源的枯竭和新兴能源的更替,盖尔森基兴逐渐从原来的“千火之城”逐渐转变为利用太阳能源的“千阳之城”,而吕佩尔茨的大力神虽然失去了一只手臂依然能屹立不倒其也彰显着城市经历战火摧残依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但吕佩尔茨显然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再重新树立一座偶像,与他的绘画一样,他总是通过摧毁偶像的方式塑造偶像,以摧毁绘画的方式重塑绘画。《赫库莱斯》虽然巨大,但也显得笨拙,目光也略感呆滞,敢以这种自嘲的方式进行如此自我审视,也显示出艺术家的胆量和天分所致。

约尔格·伊门多夫《每个人都是画家》130×110cm布上油画2005 年
与吕佩尔茨一道展出的还有伊门多夫的作品,这位以描绘公共空间而著名的德国艺术家此次带来两件不同于以往的严密而复杂的叙事性作品。《我会将之带回》是伊门多夫1981 年创作的,此时德国柏林墙尚在,东西柏林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上对立和抗衡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而事实中,由于东西德经济的不对称发展,使得东德地区由原来的红色理性逐渐转变为白色恐怖,画面中白色的星状物体被锤子和镰刀,及金字塔状物体钉在漆黑的背景当中,这也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受难。而其另一件作品《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创作于2005 年,这是伊门多夫受疾病干扰下创作的作品,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也是其老师博伊斯一直以来的所提倡的。而在伊门多夫这里,个人主义的实践和探索铸就了新历史和文化情景,虽然在此过程中个体是孤独和被疏离的,但在文化旅行当中依然是丰富多彩,画面中的人手里捧着受难的个体,而历史的幻影在身旁却被投射出来。

梁绍基《孤云》木头尺寸75×428×80cm 钢架尺寸245×114×114cm木、丝、茧、钢管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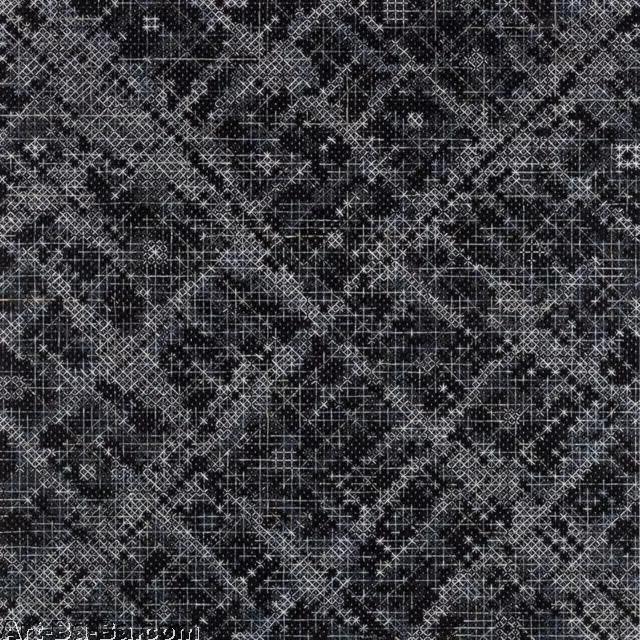
丁乙《十示2016-2》240×240×6cm椴木板上丙烯雕刻2016 年
当然展览不是一味的沉浸在表现主义的氛围里,丁乙和梁绍基的创作,让人们看到另一些坚定不移的艺术路线,在单一主题的繁复工作当中,艺术试图在破碎的价值体系中重构新的文化的线索,梁绍基将生物养殖和传统文化遗骸以及现代机械装置相融合,此次展览的《孤云》是将一块香樟木残骸外裹满蚕丝使其再生,而丁乙从80 年代开始用“+”和“×”构建其《十示》系列,二者虽然从方法和宗教倾向都有距离,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相同之处。

杨振中《如果你养了一只鹦鹉,你教他(她)说什么?》9'32"单路视频 , 装置 | 鹦鹉,老电视机2001 年
除此以外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和欧阳春、杨振中的装置从大小不同角度反观着今天现代性生活荒诞滑稽另一面,这种达达式表述方式似乎不像老一辈艺术家那样费心于营造某种庄严而凝重的文化情境,但这种借力发力的方式其实也使得艺术家从手工者的身份中脱离出来,而更加注重个体的思考和普通人的存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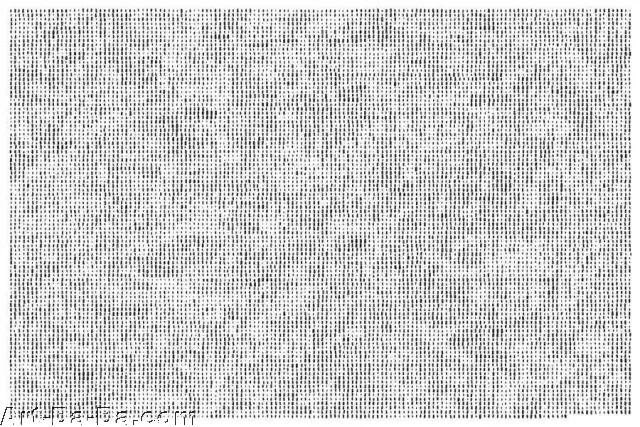
赵仁辉《试图记住一棵树》100×150cm(×2pieces)光泽亚克力、数码摄影、铝单板2014 年

刘月《为极限值得唯一 142015–2016( 选录 )》29×20.5cm(×370pieces)爱普生艺术微喷,哈内姆勒摄影纯棉硫化钡纸基纸 2015-2016 年
而出现在展览现场的80 年代后出生的艺术家,由于工作生活的网络化,数码化,很多艺术家都直接将目光投向网络生存空间反思和表述:赵仁辉的作品《试图记住一棵树》用摄影的方式将一颗树的每片树叶记录下来,然后排列成矩阵关系图像;陈晓云的作品《砍死你》用双屏影像的方式描述一个在黑夜的荒野中手持斧头向空气进攻的男子;刘月的作品《为极极限值得唯一》是其在2015 到2016 年间用手在无光处拍摄黑色图像的拼合。刘成瑞的行为作品《执行》是将一个巨大封闭的蓝色箱子从里面移动,而外面的合作者帮助其改变方向。林科的视频作品《我现在的主人02》将网络生产出的图像拟人化处理,并用语言描述其诞生,旅行的经历,最终将其放置在类似画廊的空间中完成再次重生。新的生存经验催生出新的艺术语言,而这些还在生长当中。
除去上面的艺术家个案,此次展览中还有很多其他艺术家采用着不同方式进行着探索,无论其连接的是个体经验还是历史文本,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社会。其所提示困境,所嘲讽的现实,所需要依靠精神基础却是实在的,在一个完美经济和科技为主要路径的世界里,‘殊途’无疑是必要的,它指涉着现实的诸多不完美之处,也给予了完美更多重身份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