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破报 文:苏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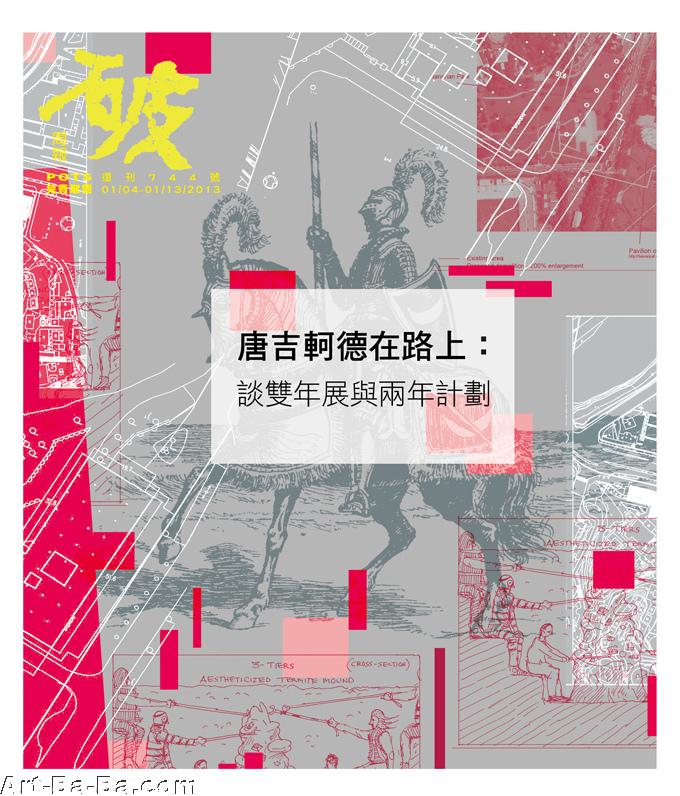
「曼查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着一位贵族。他那样的贵族,矛架上有一支长矛,还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马和一隻猎兔狗」——《唐吉诃德》
礼拜天下午跟「两年计划」策展人周安曼坐在咖啡店裡,听她谈了好久好久,从2010台北双年展以来、為反省双年展机制而开始的「两年计划」。由周安曼、林宏璋、提达‧佐赫德(Tirdad Zolghadr)策展、叶佳蓉、许峰瑞、叶杏柔、柯钧耀协助,与十位艺术家一起展开以两年為期的创作计划,经歷 2011年11月呈现进度的期中座谈,在本届2012台北双年展闭幕前,於1月5日即将展开《两年计划》终曲发表会。听着她谈了好几个预计实现的构想,以及好几个努力到最后得放弃的计划,还有一路以来策展人与艺术家的陪伴关系,记者突然觉得一群依循体制而生存的艺术家,站在自身也厌恶的双年展机制面前,简直像是拿着矛与盾的唐吉軻德。
对你而言,双年展代表什麼?
日本综艺节目「电视冠军」在节目最后,毫无例外由主持人询问比赛冠军,「对你而言,○○代表什麼?」。不管对方如何回答,节目都可以含泪带笑结束。清晰记得2010年双年展与台北花博同时进行,当时在场内质疑、场外引发的风波;2011年台湾艺术家在北美馆前,抗议特展环球策展公司的弊案;而前阵子北美馆公布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参展名单后,谁是代表「台湾」的艺术家,其评审机制出现争议。相较於身处艺术相关系所或长期在业界拼搏的人,记者对於台湾当代艺术的争论简直算是门外汉。这一次,记者只想询问国际双年展策展人,对他们而言,双年展代表什麼?

“两年计划”期中发表会(周安曼提供)
上海双年展1996年始由官方(中国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主导筹办。2012年总策展人邱志杰既是艺术家、也在美术学院任教。新浪网〈上海双年展更新处境难:艺术界被钱绑架〉报导谈到策展人面对资金不足的困境:「儘管『被钱绑架的脑残』不能作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要基调, 但多少从侧面展现了上海双年展面对『更新』时的困难处境」。邱志杰在「艺术中国」专访中指出「上海双年展依然是一个可以改变社会的力量,甚至依然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要素,它依然是一种里程碑或者是一种温度计,它能够测试出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它能够直接影响这个社会本身。......它依然是真实的事情,它还不完全是一场娱乐,它不完全是一种嘉年华」。
1995年开始的「光州双年展」,韩国政府在五一八武力镇压事件发生地,每年资助经费1200万美元办展,是许多策展人欣羡不已的数目。朱其却在《羊城晚报》上以〈六策展人难掩平庸〉為题,谈2012年光州双年展「时代是这样的平淡,艺术也就如此平淡」,以及全球双年展的疲乏情形:制度官僚化,致使除了国际重要艺术机构及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才有机会策展;好的艺术家数量少於双年展数量;当艺术家不断收到双年展邀请时通常不会拒绝,但也很难有酝酿许久的好作品。1895年开始的「威尼斯双年展」,於1907年鼓吹各国建筑国家馆。在吴金桃〈双年展在国际艺术体制中的位置与功用〉一文中, 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罗伯特.史托(Robert Storr)认為相较於美术馆涵盖不同时期、运动的展览,每两年而生的书年展是关於当下,也是大规模的团体展。他指出赞助者会给压力要求创造大型的公眾活动,「在双年展的概念裡,有一种奇观(spectacle)的元素存在」。他坦承「每个双年展有它自己的权利结构,而且不只一个」。没有艺术家完全没有政经事件介入,他说「关键在於艺术家如何处理这种情形,它如何影响到作品被接收的情况,以及你做了什麼样的妥协,而什麼是不能被妥协的」。针对「双年展疲乏」现象,他说「双年展是為那些来看展、但不是艺术圈的人而做的」。他认為双年展让特定地区的人们可以看到艺术作品,而如果双年展适当安排,能触及到学校、更多的人,超越平常对文化有兴趣的观眾。双年展常常被用来当作观光来行销,由商界或艺术圈来宣传,如果这仅是他们所触及的观眾,那是失职。
2007年塞尔文件大展策展人布尔格(Roger M. Buergel)在〈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报导中谈到,当文本作為与观眾的沟通工具,不会直接提供答案而是回应到群眾身上。观看作品时只要知道地理政治脉络、经验,事实上群眾会有自己的詮释。圣保罗双年展1951年由义大利企业家创立,作為拉丁美洲当代艺术指标。2012年圣保罗双年展策展人Luis Pérez-Oramas,在〈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地的〉专访中谈到,他相信所有艺术都是在地的,而当代艺术并不是国际形式,因為它只回应了世界某一地点与某一时刻的经验。在通讯科技发达的同时,他认為「艺术应该要抗拒所有看似要使我们的世界简单化的潮流」。

根据「亚洲艺术文献库」,全球目前83个国际大展分部各州,从1895年开始威尼斯双年展,以后每隔几年新增一个,80、90年代及2000年以后,以二、叁、五级数倍增。2011年初到年底有19个双年/叁年展在全世界举办。林林总总条列下来,看起来像是进入「世界(当代艺术)博览会」。双年展形式定期、大型、绝对是VIP限定、并且在多重权力结构中展演的当代艺术。世界博览会今天仍然在各国巡迴,从当初1851年英国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始,博览会作為工业革命后展现国家富强(或演变至今作為行政绩效的代表),在跨国贸易流通强烈趋势下促销產品的企图,展现了现代性、商品拜物教及大眾文化。双年展如何摆脱此阴影?要把权力批判弄进来、把评审机制打开来,或者更积极培养在地策展人或艺术家,将其视為难得且毫无局限的哲学思想交流场域精密操作,搞自己的小型艺术创作交流......艺术领域中,举办双年展这种类放烟火的行动,究竟是否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政府所应该担负的责任?这些问题绞在脑中没有答案。
记者想起,那天跟在任教高中美术老师的朋友,兴奋推荐2012台北双年展。她看完后表示没有办法带学生去看,现场展示的当代艺术太难懂,她说怕高中生会被吓到,然后觉得艺术都很难而產生抗拒心理。如果基层美术教育与当代艺术的讨论,甚至市立美术馆之间存在断裂,那麼所有艺术家跟作品试图对话、甚至反动的对象,是否仅限於一群熟悉脉络的知识份子?如果双年展是必要之恶,策展单位是否有一把恆常的尺,是在讨好舆论外需要尽到的基本义务?例如一直被忽略,美术馆或博物馆作為公共空间的社会教育意义,并不是硬体设备存在、贩卖商品或结合科技就等於推广。
「两年计划」的省思与尝试
针对这样定期、大型、多重权力结构间的双年展机制,所展开的「两年计划」,安曼谈到在2010年台北双年展时便跟艺术家一起讨论出来,与当中10位那时参展的艺术家合作,独立出来在双年展外开始两年计划。在当时的策展论述中,便以实验性的开放情境与展演方式,来谈双年展如何创造艺术。她说当时讨论到「每一次大家在做双年展,美其名是两年一次,可是大家都没有充足的两年期间在做展览,通常只有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準备。我们不如来做一个实验性的计画,把展览预备期间真正延长两年,所以才会有这个两年计画」。面对北美馆基於一年一次经费预算而无法支持策展论述中的「两年计划」,它在没有主办单位、经费还在边做边找的情形下展开。她表示,目前官方或民间可以申请的补助,仍然以大规模展览形式為主,没有实质东西的策展很难获得资源。从2010年台北双年展结束,一直到2012年台北双年展开展的两年间,安曼谈到当天闭幕,这些研究型的计划,最后的作品大部分不会有具体呈现,可能只是文件,大家的属性不同。她谈到参展艺术家提的计画,以原来参展作品為出发,有的做调整、有的做延伸。
 、
、
白双全《回家计划》
例如,白双全邀请观眾带他回家、延续两年友谊的《回家计画》希望出本一本书,安曼说。Lara Almárcegui则在2008年便来参加台北双年展进行《淡水无人岛保留计画》与《台北市齐东街旧屋拆墙计画》。Lara透过实地操作,如破坏旧屋墙面,彰显背后其实是一大片由政府认定的日式古蹟,在持续由资本推进、毁坏的日常生活歷史遗留与记忆,针对都市空间进行省思,并且透过书写、影像记录,重新叙述出另外一种城市发展史。她的两年计划则是根据之前对废弃老旧建筑物歷史背景与现况的田野调查,做出《台北废墟调查》。虽然此种具有完整概念与呈现的另类存在,其实未能改变居民、政府、建商叁者间并存共犯与矛盾的紧张关系。对於「看不见的空间」的挑战,则同时出现在Chris Evans的《台北市立美术馆腹地再空间计划》计画中。其实我们未能看见,文化生產空间在认知中有多少侷限。藉由2010台北双年展《家庭娱乐》,Chris在美术馆建筑顶端架了风向标,直指文化生產的可能方向,从来不在美术馆内。两年计划则是由建筑事务所工程师提案,表现如果美术馆想要打开,建筑物本身实体空间扩张的基本条件如何执行。很可惜,当记者听到安曼表示本来想找爆破专家,进行北美馆扩张,却考量到专业程序包括废气量跟建筑物距离等,因台湾建筑物太小,无法在想像中爆破北美馆。
当中突显个人介入传统知识与在地文化能动性,则是Mario Garcia Torres的《反转标準作业程序》,记者自己偷偷在心裡给它a.k.a.,「老外疯台湾之酿製苦艾酒」计画。风靡於20世纪初巴黎间而后遭禁的苦艾酒缘起不可考,而记者也完全摸不透参杂苦艾、绿茴芹、甜茴香与其他香草药材萃取出的苦艾酒,跟墨西哥艺术家Mario之间的关系為何。据安曼说他迷恋老旧文化的传承与记忆,而如何反转知识生產、参入个体,实际操作上Mario教大家他自己改良过的苦艾酒酿製方式,并且由台湾的四组艺术家团体,针对环境跟地方饮食条件不同有不一样的调配材料,酿自己的苦艾酒。另一个需要长时间酝酿的计画是《美术馆馆长报告书》。2010年因特展弊案北美馆馆长职位悬空,Christian Jankowski当时双年展提出馆长徵选计画,开放决策过程,质问美术馆馆长应有的特质為何。延续此概念,他的两年计划却有波折。本来预计透过人力资源公司或徵信业者,从外面人的角度来调查馆长职位应具备的能力。安曼表示,然而只从评量企业的观点,例如着重特展,则报告书无从评比起。她谈到当时碰到的困难,即是面对平常人普遍缺乏对於当代艺术的认识以及对文化的想像,因此「美术馆应该要做什麼,(大家)不知道」。这个坚持到最后一刻放弃的计画,似乎显现出艺术小圈圈可以自给自足良好无虞的荒谬。

“两年计划”策展人周安曼
回到跟年轻策展人安曼对话的咖啡馆内,原意是突破双年展机制中,每隔一段时间大量挑选、陈列当代艺术作品的循环。如果,那个两年不是花在行政操作,而是艺术创作上呢?那个重视时间而非空间的过程,似乎是当代艺术舞台上所缺乏的环节之一。她说,给予充裕时间做出来的成果,最后很多作品可能不会有完整呈现,「这是在其中一开始没有预料,但是后来也接受的方式」。安曼所重视的过程间,包括艺术家跟策展人之间,跟艺术家一起讨论、合作,谁是创作者的界线开始模糊。长期发生关系后產生作品,则是她在做完压力很大的10年台北双年展后的小心愿。她说在公部门的资源下,必须要满足很多期待,而且不许失败。以目前当代艺术市场的运作流程来看,包括安曼提到,艺术家被大展绑住,而没有当务之急的两年计划不会是工作重点项目,也不会实际在台湾待两年跟地方团体密切合作;或者因為没有展览期限、主办单位,所以具有独立性跟自由度,但回到现实面执行,没有机构资源支持,也缺乏资金、帮手跟联繫管道。如果说当代艺术生產,在製作「產品」的过程中,已经难以脱离大展形式的循环系统、地方官僚与行政体系,现代唐吉軻德们站在大风车前面,嘶吼吶喊的,似乎只是一个幻想出来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