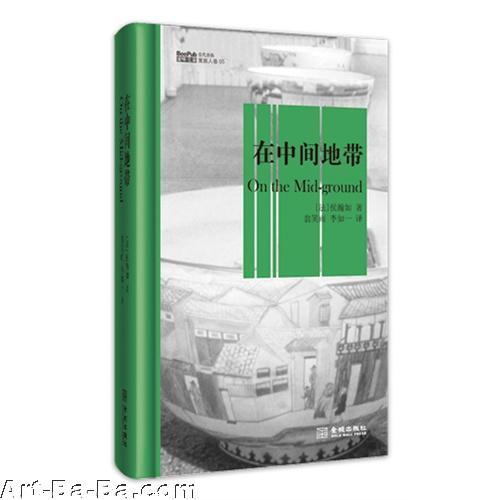来源:前线微信

杨福东《第一个知识分子》
艺术的赤裸形式
当今中国的艺术家必须面对这种赤裸的现实,这是他们工作的语境。
与19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运动不同的是,新一代的成长过程与这种赤裸的、结构性粗糙的社会和文化形成过程是同步的。与这样的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艺术往往直接与当下现实连接,与赤裸欲望的文化相呼应。往往通过直白的,甚至有暴露癖倾向的艺术创作,他们质疑这种堕落的、腐坏的、精神分裂的“文化状态”。将发财和成名的欲望用赤裸的图像表现出来也是“干预”赤裸现实的极佳途径,艺术的表达成为最赤裸的形式。
穿着打扮成为体现这样一种对物质成功欲望的最明显的方式,就像南京路橱窗里的广告一般。人们在现实里用时髦的衣服覆盖住肉体,却暴露出他们空洞的精神。穿着打扮于是也给许多艺术家提供了有趣的参照物,帮助他们理解现实、介入现实。施勇的网络计划是中国艺术家所创作的网上作品中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它以探寻穿着标准为中心话题。艺术家邀请参与者设计符合迅速现代化上海城市的理想市民形象,通过网络互动,公众可以投票选出最完美的衣着和发型。施勇讽刺性地揭露出一种肤浅的文化趣味,即一个社会的大众审美映射出其对好的、美的和时髦的理解。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共同自我暴露的过程,或者说一个“互相对裸”(mise-à-nu)彼此灵魂的过程。
许多艺术家的创作都表现出这种自暴癖,他们相信这也是获取成功最有效的捷径。与施勇具有讽刺和批判性的态度不同,许多其他的艺术家选择放弃批判性而使用最为玩世不恭的策略来取得名声。受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青年艺术家”(YBA)的影响,尤其是充满争议的“感性”(Sensation)展的影响,北京的一拨艺术家甚至称他们自己为“后感性”。达米恩·赫斯特(DamienHirst)将几头牛切成碎片然后迫使观众肉体地感受其残忍性,如果这样做就可以把自己变成巨星的话,那么一些中国的艺术家决定把他们的作品做得更残忍更极端。他们直接使用人体来“挑战”文化禁忌,因为“突破”了人性的界限。但同时,这些对所谓“突破禁忌的”残忍和造反过激而又粗暴的曝光实际上具有清晰的目的性,即为了赢取“国际”艺术市场的注意力。他们认为只要制造越多的绯闻和争论,“国际”市场就会对他们投来更多的目光。而其中的原因在于,这种做法可以使他们看起来更“中国”,而这种所谓的“中国性”也是“国际”媒体最想窥视的。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期间,许多展出目前中国实验艺术现状的外围展也频繁开幕,因为大家都知道前所未有的大量“国际艺术界人士”都将聚集在上海。其实这种借势宣传的策略也是许多展出的作品所共识的,尽管客观上,人们更希望这些活动能显示中国新艺术界的丰富性和活力。所谓的“激进性”是通过裸体、动物和生肉等常见“词汇”来表达的,一些艺术家甚至使用人类尸体来制造公众轰动性震惊效应。他们的行为艺术使用了从尸体中抽取的油脂,而另一些艺术家的行为居然是“吃婴儿尸体”,虽然这个“行为”仅仅是数码影像蒙太奇的形式。
尽管艺术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对作品进行了理论化的阐释,我猜想在这些粗暴的作品背后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易懂,即通过震惊效应来取得成功, 这也使它们显得 “普通”。与表面上反对社会和社会禁忌的反动者态度相反,他们实际上与社会现实自身亲密无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名誉、金钱、消费和欲望。为能震惊公众,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这也是在消费社会推销自己的最好方式,因为一切都是关于买与卖。绯闻也是最好的商标。
是的,赤裸欲望的表达与中国社会疯狂的城市扩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新的 “社会现实主义”,尽管这种“社会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社会现实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是不自觉地“反映现实”的,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具有工具性的。这些新类型的艺术的产生本质上是为了赢取一张进入“国际市场”的门票。一些艺术家尽管对这种趋势有所抵制但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影响,因而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批判,其中大多数都利用了现代化市场所能提供的新媒介:电脑、网络和数码图像等。他们往往是具有讽刺性的、嘲弄的、辛辣的,且往往带着一些自嘲的意味。周铁海是这种讽刺的高手,他将自己变成股票市场的指数,也许这是如今艺术家最关键的角色。就像他的“论坛”中提出的:“艺术世界里的关系跟后冷战时代国与国的关系一模一样。”这是为全球化提出的多么完美的标语啊!
是的,做好迎接“国际艺术市场”到来的准备是为取得成功所做的最为急迫与有效的方式。终于,我们迎来了2000年上海双年展,首个由中国机构组织的大型国际当代艺术活动。徐坦在他的海报计划中描绘出一幅有关于这种情绪的赤裸肖像,图中表现了各种场所“幕后”,在聚光灯打开之前做最后准备的景象,有几个女孩正在其已经粉饰的面庞上补妆。海报上还写着:“上海双年展欢迎您”。杨福东将这种情形表达地更为明显:在外围展“有效期”(展览的题目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中他展出了一系列展现妓女等待招客的摄影作品。难道艺术家就是这些三陪女吗?
是的,这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性时刻,只要放弃你的知性和理智,你便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当每个人都在说服自己知性已经一文不值的时候,也不能从一个恐怖的噩梦中醒来:我的自尊去了哪里?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历史失忆的年代,我们仍旧需要知识分子吗?谁能想象知识分子的样子?他一定是稀奇的人种。杨福东的回答是从消费主义天堂的废墟中重生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粗暴的人,充满了愤怒。站在通向最高楼房的大道中间,他扯破自己的西装领带,用一块砖头敲击自己的脑袋。为了思考,我们必须流血!
2000年上海双年展,谈判城市之空无
正版的,或者说,官方的2000年上海双年展海报上写着“上海精神”的标题,它显然没那么性感,而且颇具争议。
作为四个策展人之一,我一直企图在各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个人的束缚之中给当代艺术谈判一个“正常”的场所。我所谓的“正常”是指合法性、连续性、国际性以及最重要的,知性,这些特征赋予艺术以超越直接物质和政治兴趣的自由表达。这届双年展是中国官方机构举办的首个国际当代艺术展览,它的出现以及持续性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徘徊幸存于合法与地下之间、容忍与审查之间、个人自由与全球市场的压力之间。上海双年展的举办也第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当代艺术创造在这个国家也可以具有合法性,能在普通的展览场所展出。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重新发掘知识自由、独立思考、表达、质量、时间、空间、多元化、深度、复杂性和矛盾性等思维意识的契机。这些概念在公共话语和意识中不断受到压迫、抹杀,且被一种“结构性媚俗”的舆论所替代。策划本届双年展的责任和意义也就超越了仅仅做一个好展览的目的。它应该是一种对策略、协商和决心的长期实践,以达到彻底改变机构结构和思维模式为目标。它只有从最基本的、踏实的、日常的和普通的工作做起才能实现,从选择艺术家和作品到募款,从组织借展作品到运输到鼓动美术馆团队布展……当然还有收集整理信息,与政府官员、艺术界和媒体界谈判等。双年展的开幕标志着这样一种历史性过程的开端,尽管会有无法预测的意外和阻碍,但我们已无法回头。
一个国际性的双年展绝不仅仅只是聚集一些在国际艺术界最有名和最有影响的艺术家的场合。首先,它应该与“地方”现实产生关系和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双年展想要在“上海精神”(双年展中文标题为“海上·上海”)的标题下阐释艺术创作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的确,双年展的名单里包括了一大部分国际艺坛的“明星”艺术家,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艺术家的选择实际上着重强调了有关于城市的很多问题,包括后殖民谈判、移民和身份、传统和现代性、国际和地方,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上海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共同面临的。同时,双年展也鼓励艺术家创作场域特定的作品 (site-specificworks),为促进“国际”和“地方”的交流以及为艺术家提供特定的、重要的艺术表达时刻打开空间。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与地方性脱离的概念,它是地方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地方总是反映着全球的,它们是看待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张培力的作品《同时播出》是解释这种情景的最佳范例。在上海的一个美术馆里,观众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电视节目,当你每分每秒都在质疑这个世界的时候,看电视的经历也是这个世界所能够提供给你的方式。
毋庸置疑,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于有海外经历且已经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黄永砯和严培明是其中最著名的三位。此次双年展是这三位艺术家长年漂泊海外之后第一次返回中国展出他们的作品。为了突破狭小的艺术圈从而与更广泛的公众交流他的经历,蔡国强决定展出他在国外最近十年的作品的图片,将它们陈列在长条的陈列橱窗里。这些陈列橱窗与在中国各大城市街头政治宣传的陈列橱窗相似,独特地结合了内容和形式。这件作品显得异常有效,它不仅向来自中国的广大观众呈现了艺术家的创作,同时也与城市直接联系起来,反映了展览策划的理念。作品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打破了美术馆和城市、艺术和真实生活之间的界限:任何在街上的行人都能欣赏到艺术,而且还不用买门票!
黄永砯对城市的介入是以另一种维度展现的,他更愿意探寻城市的历史并揭开当下社会、经济和政治投机背后的历史性原因。在新装修过的上海美术馆展览大厅里,黄永砯树起了一个上海殖民风格建筑的巨大模型。这幢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 是首家殖民银行:汇丰银行。50年代,上海的殖民时代结束,随着外国资本的撤退,这幢建筑也成为上海的市政厅。到了80年代,它再一次成为银行,这次占有它的是浦东发展银行,也就是浦东新区的主要投资银行。这座建筑物的特殊意义是明显的:它与上海的命运紧密相连。但黄永砯作品的关键之处和艺术力量在于他的建筑模型是用沙子雕砌的,原本坚硬的石质立面变成了在展览期间不断塌陷的沙堡。它的生命在展览开幕时开始,并且以一种逆行的方式演化。它的生命力存在于自己身体的塌陷中,无论人们多么希望它稳定强壮和不可战胜,无常、流动和宿命永远是生命的核心。当然,我们也很快可以领会其政治隐喻。它是对这座城市上个世纪历史变迁的有力批判。与此同时,它体现了一种熵的概念,其建造完成与即刻崩塌之间的变换是今天上海和整个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写照。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梦想总是带着将自己推入灾难和毁灭梦魇中的风险,黄永砯的作品又一次暴露了城市的赤裸。
在他戏剧性的“建造-解构”装置旁边,黄永砯通过另一个姿态完成了他对城市历史与现实辛辣和深入的批判,而这件作品的轻松更能抓住人的眼球。在建筑大堂的边门上方,黄永砯将原有的灯罩换成了象征殖民者帽子形状的灯罩。这件作品将会在美术馆中陈列一段时间,因为艺术家将它捐赠给了美术馆。它仿佛在诉说着美术馆建筑的过去,别忘记它曾是殖民者的跑马俱乐部。
【注】《在中间地带》一书中《上海,一个赤裸的城市》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