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KLY 宋敏
《我憎恨人但我爱你》(I Hate People But I Love You),单频彩色有声录像,2017年;赛博格 - aaajiao 与刘晓光的Windows,编码开发自 Raven Kwok
文 宋敏 图 高征
编辑 宋敏
为了在Leo Xu Projects举办的新个展“用户、爱、高频交易”(5月27日-7月2日),aaajiao从柏林回到了上海——过去的一年多里,aaajiao在艺术工作之外一直忙于移居柏林的事宜。在上海生活了十年之后,他渐渐感到疲倦,柏林给他抽离与喘息的机会,“在移动中你能看清很多问题,你有两种选择,两种空间的跨度,可以不用在乎某一种空间里你不喜欢的事情,找到新的方式和它共处。”
Aaajiao是艺术家徐文恺的化名,更早亦作为他的网络用户名使用至今。生于西安,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并非出身于专业艺术院校的他,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曾经写过乐评、做过翻译、创办过数个曾颇具影响力的网站——conersound,soulseek的汉化版“嘘”,we make money not art的中文版——还联合创办过上海第一家共享办公空间“新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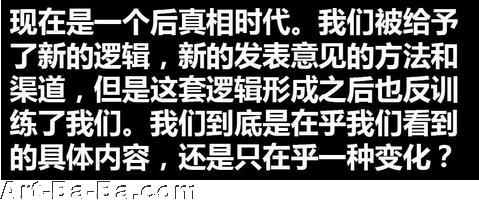
“现在的我或许可以大言不惭地讲我是一个艺术家,但在这样一个身份之前,我首先是以一个计算机和互联网用户的身份来定义自己的。因为除了作为人的一个属性之外,我觉得我的第二属性其实是用户。1999年我拥有了第一台电脑,是联想,在拥有这台电脑后的一年左右,我父亲就让这台电脑连上了网络,当时还是拨号系统,每一次拨号的时候我还会拿起电话听一下。这个回忆很美好,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今天又可以和世界连在一起、拥有一样的信息了。”
“用户”(user),这一数字科技和网络媒介赋予每个社会个体的全新身份和属性,不仅是本次展览,也是aaajiao多年来创作和研究的主线。从用户个人的自我设定,到社交媒体、移动科技中情感表达和人际交流,再到繁复的计算机算法和人际网络结构所改写的经济模式,“用户、爱、高频交易”捕捉了当代社会所处的特殊文化时刻——既重访了传统科幻电影对人机共融社会的幻想,亦再现了与之呼应又背离的当下现实,即社交媒体和数字科技对人类社会中情感交流和经济交易的改造。

Aaajiao在作品《404》前
Q:我们先来聊聊三楼的那件作品《404》吧。
A:我本来的想法是要去拍上海期货市场的机房,我有个同学是做高频交易的,答应了带我去,但他后来怂了不敢了。自2015到2016年的股灾和2013年光大乌龙指事件之后,这个事情就很敏感。失败之后我也考虑去香港拍,同样没有成功。这让我联想到404页面,作为一个“用户”,你的权限是受限的,你知道它的存在但触摸不到,它只能存在于想象里。
Q:很多人认为这件作品是对管控的一个回应。
A:对于管控的话题我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你不可以一直沉浸在一个被迫害的抵抗者的角色里,重复那种表达,“我是受害者,我需要获得同情和帮助”,但没有态度和观点,是毫无价值的。那然后呢?你作为一个受害者就不继续生活了吗? 现在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找到观点的时候。
Q: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A:个体面临的不仅是这个问题,而是你整体的社会身份变得更弱小。为什么要讲“用户”这件事,在互联网变得更结构化之后,整体变得更强大,每个人都被纳入到整体中,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在与整体共谋,个人进入了一种失语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需要去探讨,作为个体还有没有意义再发声?你如果只是用户不是管理员(administrator)是否还有机会发声?如果没有机会发声还能怎么办?

正在上海Leo Xu Projects举办的aaajiao新个展“用户、爱、高频交易”(5月27日-7月2日)
Q:你认为大部分人的角色都只是一个“用户”?
A:对。
Q:那你认为的管理员是谁呢?
A:管理员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单独的群体,而是因几个用户群体(user group)的制衡关系形成的虚化的形象,这很像《1984》里所描述的。
Q:《1984》对你有很大影响吗?恰好你也出生在1984年。
A:先哲们想的都很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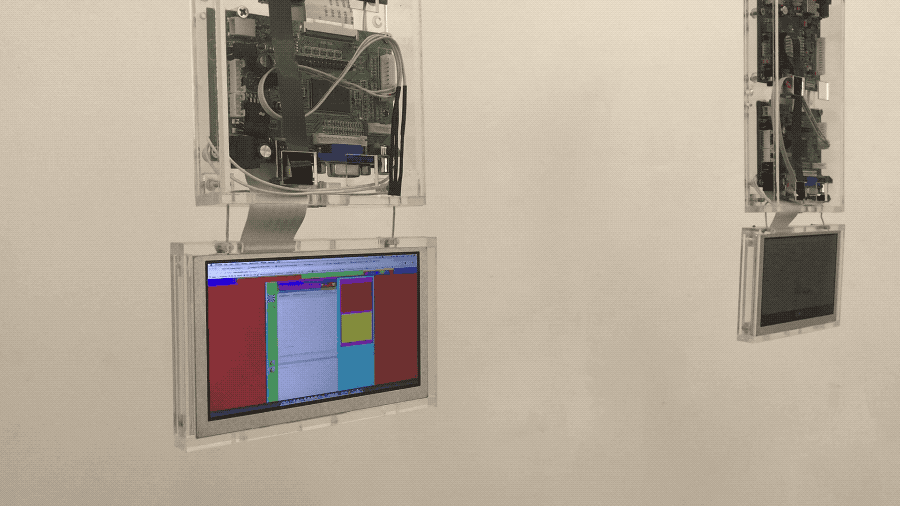 《糖纸》(Candy Wrappers),单频彩色录像、屏幕、线,2017年
《糖纸》(Candy Wrappers),单频彩色录像、屏幕、线,2017年
Q:你的这个观察和你体验到的互联网变化有关吗?
A:现在是一个后真相时代。我们被给予了新的逻辑,新的发表意见的方法和渠道,但是这套逻辑形成之后也反训练了我们。我们到底是在乎我们看到的具体内容,还是只在乎一种变化? 我认为现在很多人只在乎变化本身。一个信息带来了另外的信息,你到底关注什么?你的注意力让你已经没办法再保持关注。个体已经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处理这么多信息得到真相,不是说真相没有了或是在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都有,我们只是没能力看到真相了。
Q:这是信息爆炸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A:我们得到信息的渠道多了,以前可能一件事只有四种观点,你还能够分辨一下;现在有两百种,你怎么分辨?相应的可以说我们的权限变小了,以前我们是能看到全局的,现在永远只能看到部分。
 《头像》(Avatar),Gif动画、屏幕,2017年
《头像》(Avatar),Gif动画、屏幕,2017年
Q:看起来作为一个用户好像更自由拥有了更大权力,实际上权力却变小了?
A:对,由于生物结构所限,我们处理不了这么多信息,所以需要和机器共谋。比如说在高频交易里,不仅交易由机器来做,量化的部分也由机器在做。机器给了你足够的运算能力,你的思维和智慧依旧在,但执行需要机器去补足。
Q:在从前的互联网时代,你作为一个用户的权限更大吗?或者说从前你的身份是超越用户的吗?
A:从五年前起就逐渐转变为单纯的用户身份了,不过那时候不是很明显。转变的最大信号是真实和虚拟不再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当真实和虚拟的对立关系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身份变化完成的时候。只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理解这个变化。
Q:关于权限的缩小,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A:我认为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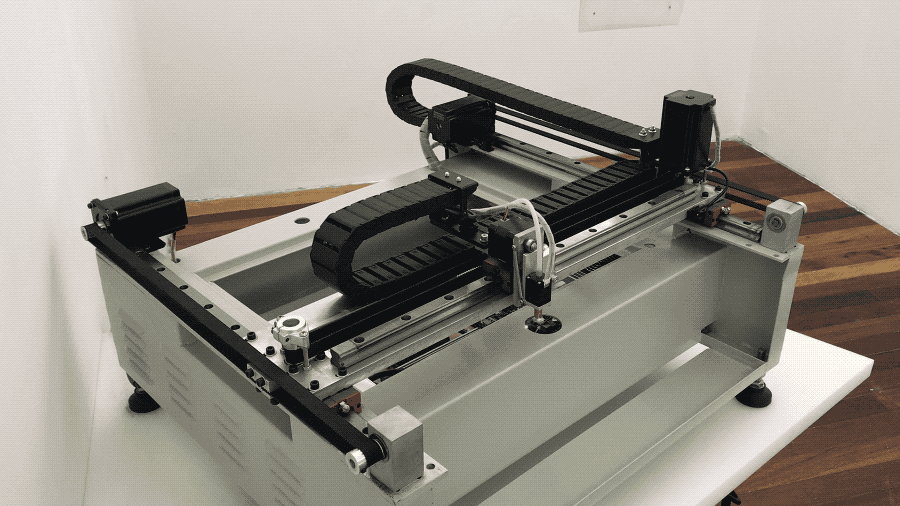 《所见即所得》(WYSIWYG),电路板、贴片机、金属和PVC结构,2017年;作品与马健和刘晓光共同完成
《所见即所得》(WYSIWYG),电路板、贴片机、金属和PVC结构,2017年;作品与马健和刘晓光共同完成
Q:那么你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还是正面影响更大?
A:恐怖之处在于短时间内来看好像正面影响更大。但如果从更大的时间范围里看,当人类真的有一天从人类中心论跳出来,去中心之后,可能是件很糟糕的事情。
Q:去中心是什么意思?你相信有外星人?
A:不是外星人的问题,是你最终构造出来的系统取代了你作为主宰。
Q:用户的身份和权限会受到空间的影响吗?你在柏林和上海的感受一样吗?在柏林时会觉得自己不仅仅是用户吗?
A:在柏林好像回到了十年前,回到了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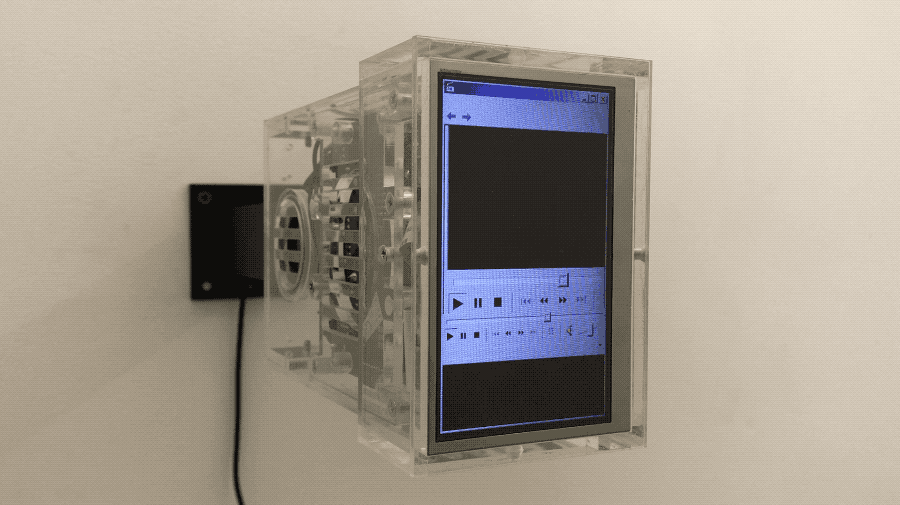 《进度条》(Progress Bar),单频彩色有声录像、屏幕,2017年;作品与张弢和声音艺术家谭硕欣共同完成
《进度条》(Progress Bar),单频彩色有声录像、屏幕,2017年;作品与张弢和声音艺术家谭硕欣共同完成
Q:面对信息洪流你如何应对?如何从纷杂的信息中获得真相?
A:重要的是心态,不要在乎你没看到的东西、错过的东西。真相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已放弃了寻找真相。 但这并不是说我要放弃思考,还是要保持一种自觉,不能简单地信或者不信。这种怀疑的态度可能变成了人唯一有优势的地方,自我怀疑和反思是人最有价值的部分。
Q:你的这些思考观众未必能体会到。你是希望他们能体会还是无所谓?
A:我从来都没有把观众的反应作为思考的一部分。专业观众看专业的内容,一般观众来自拍,我都无所谓。我并不反感观众自拍,他拍照肯定是若有所思,不管是单纯地觉得美还是联想到了什么。艺术教育这件事不是艺术家自己能做到的,需要更大的机构去做,我们能提供的大部分时候就是一种不可读和无意义,原因是你在生活中可读的东西和有意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Q:你对艺术的定义是什么?
A:艺术是在宗教之下的一种智慧。宗教在意识形态之下,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中最上层的,艺术是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外化方法。
Aaajiao认为他这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怂
Q:用一个词总结你们这代人的特点。
A:怂。
Q:展开讲讲。
A:怂是因为大的变化都赶上了,小时候玩泥巴,现在玩手机,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令人无所适从,你不知道该站在什么角度去理解这个变化,给自己一个定义,或者说是定义不出来,这时候你越想找到自己的内心你越怂。和“怂”这个字的写法一样,“从心”,希望有心的回归,那么多人去大理,搞灵修,变来变去都是想安放这颗无处安放的心。
Q:你安放这颗心的方式是什么?
A:不能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这颗心是移动的,在移动中你能看清很多问题。这不是说你不负责任,在这儿做点事就走了,你有两种选择,两种空间的跨度,可以不用在乎某一种空间里你不喜欢的事情,找到新的方式和它共处。 最怕的是从怂到绝望。
Q:所以“怂”不是个贬义词?
A:怂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负面评价。70年代人就不怂,他们是迷失的一代,迷失在物质欲望和乌托邦理想中。我们不迷失。
Q:下面的新计划是什么?会继续关注用户身份问题吗?
A:明年的展览是讲游戏研究的,用户接下来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玩家(player),在新的规则下进入一套新的体系,你可以积分,你可以所谓地战胜NPC,你可以打boss,这是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