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何蒨
从欧洲到中国:
关于“我们从未现代?” 的引述与重构
——写在布鲁诺·拉图尔北京行之后
加拿大摄影师杰夫·沃尔(Jeff Wall)在1992年完成的摄影作品《艺术家亚德里安·沃克尔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解剖学部实验室绘制标本》(Adrian Walker, artist, drawing from a specimen in a laboratory in the Dept. of Anat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似乎对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件作品也在不久前于中央美院举办的“新艺见”大师讲座期间、于拉图尔和与会的中外学者、艺术家之间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及。

“我们从未现代?——对话拉图尔”讲座现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2017年
图片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提供
围绕这件作品,拉图尔捕捉到了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投射——一件摄影作品呈现出了上世纪90年代法国学界争论颇深的西方“再现机制”(representation)的危机。然而危机何在?只能说,这场危机与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后现代生活与民主体验息息相关,最终以一场以当代艺术为隐喻的混沌之争不了了之。[1]然而,在杰夫·沃尔的作品里,拉图尔看到了学者们无法厘清的混乱,正以一种直观而清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西方现代性传统中的主客体关系,能够通过两种再现机制加以诠释,并恰好在这件摄影作品中同时在场。第一种即摄影术对置于台上的人类手臂标本的再现,这种再现可信无疑,信任感源于我们对标本确实存在的认知,以及摄影术忠实再现客体能力的认可。这里,摄影的本质更多地指向罗兰·巴特所解读的“曾在”(ça a été)。第二种再现机制为艺术家亚德里安对手臂标本的临摹,即画面中的素描作品。无疑,这种带有主观审美、又忠于客体的创作过程,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提出了艺术再现与真实的关系,即主体对客体真相的追认方式。然而,当杰夫·沃尔将这两种再现机制同时糅合在摄影媒介中时,好像脑筋急转弯一般,第三类再现机制悄然呈现,也即一种难以被西方逻各斯中心论所解读的“混杂再现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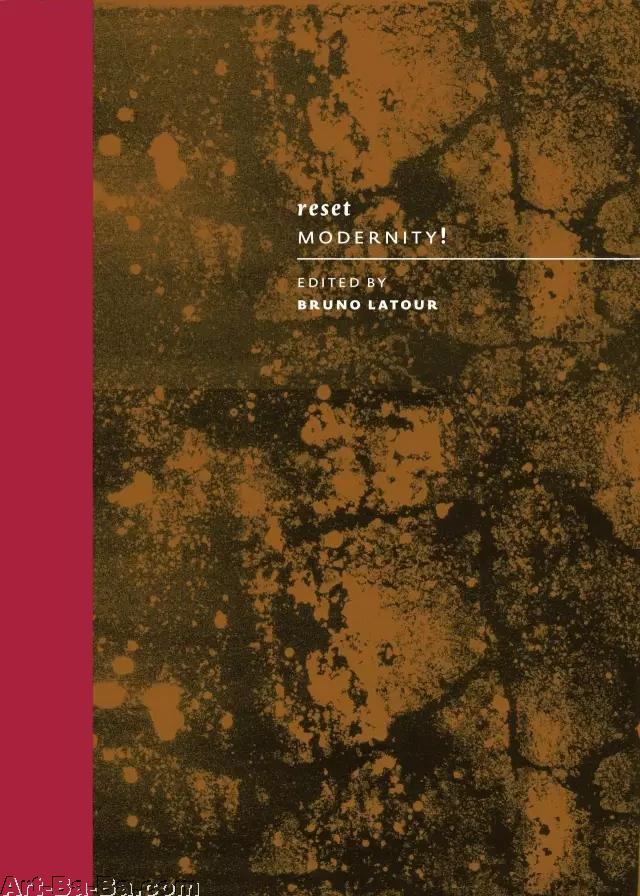
布鲁诺·拉图尔
《重置现代性!》(封面),2016年
*图片来自网络
在拉图尔看来,这件摄影作品在观众眼前再现的,是一个完美地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混杂真相”(mixed truth)。我们通常情况下理解的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在这里被艺术家的镜头打破。人体标本的“真相”与“艺术再现”被呈现在摄影术构造的“混杂真相”中,那么摄影术与这种“混杂真相”的关系又为何?这正是拉图尔要抓住的问题,也是他困惑的地方。有趣的是,我们的感官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这种关系的存在,但我们的逻辑却无法对之进行分析——因为西方现代性认知的整合性在这里发生了断裂。
这种哲学上难以言辨的认知困境,却在艺术家的手下轻易解决,前者之艰辛与后者之直观的对比,大概是拉图尔决定从艺术途径出发探讨其关心议题的起点。回顾他策划的三个展览——“Iconoclash,在科学、宗教及艺术的图像战争背后”(2002年)、“让一切变得公开,民主的氛围”(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2005年)、“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y!2016年)——我们能够从中捕捉到拉图尔思考历程中的连贯性,即他对西方现代性认知方法的质疑。这种质疑首先源自他对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挑战,并最终导向他对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再现机制”——的解构与调整。

“我们从未现代?——对话拉图尔”讲座现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2017年
图片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提供
“再现机制”已经渗入西方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象征领域的艺术再现到日常的民主政治。对于拉图尔来说,如果不能恰当地反思,这种“再现机制”势必造成“我们从未现代过”的困局。他在《图像战争》(Iconoclash)中就提到,“再现机制”是一种对世界本源的认知方式,即“相信真相与假象的绝对区分,认为存在着超验的、纯粹的理念世界,与之对应的则是人类所在的这个充斥着混杂、不纯粹媒介(mediator)的现实世界[2]”。在拉图尔看来,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恰恰在于对真相与假象的区分过于绝对,过分依赖媒介,同时又忽略了媒介在阐释能力上的有限性,从而导致真相与假象之间的“相对性”被长期忽略,最终使西方现代性走向了自身的死胡同。值得一提的是,在拉图尔的语境中,图像的内涵与外延超越了一般艺术史学者的见解,涉及符号、艺术作品、文字、以及一切能够扮演中介作用的有形或无形载体。
在2005年的“让一切变得公开,民主的氛围”展览中,拉图尔已然摆脱了图像(媒介)层面的认知困境,将再现机制的反思推进到主客体关系的重构上。拉图尔拒绝主客体之分,他更倾向于使用“物”(thing)的概念统合主体与客体之间被割裂的情感关系与意义延伸。拉图尔引用“thing”一词的词源学阐释,指出这个概念原本具有“聚集”(assembly)之意,即将人或物聚集到一起。这种聚合本身并不具备真假之意,聚合的事实仅仅意味着存在“议题”(issue),围绕这些议题产生了一致或分歧的观念,这种意见混杂的聚集才是“物”的本意。在拉图尔看来,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本应建立在这样的聚集观念上,却在现代性纲领的指导下,走向一种割裂主客体、无视真实意见分歧、把量化代表视为真理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正在经历着严苛的挑战。

“重置现代性!” 展览现场,2016年
德国ZKM艺术与媒体中心
2016年,时隔十多年,拉图尔才推出“重置现代性!”展览。所谓重置,即避免破坏和重建,不再走回“毁灭图像”的传统中去。对于哲学家拉图尔而言,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洞穴神话——正是引发先验世界观失误的源头,而人类内在经验的丰富性也被主客体的二元结构掩盖了。在这场展览中,拉图尔尝试重置人类的立场,无论是个体的渺小与大自然或宇宙空间浩瀚的对比,还是自然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政治现实改变,都是在打破西方自启蒙时期建立起来的“人是衡量世界的尺度”的人本位主义。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与伦理正义感,具有当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能够快速校准大众的注意力与体验发生机制,使观众进入拉图尔渴望营造的认知氛围中去。我们看到,拉图尔是在通过艺术的直观性及超越逻辑思维的能力,思考西方现代性得以建立的认知基础,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象征符号体系与社会制度。

“我们从未现代?——对话拉图尔”讲座现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 2017年
图片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提供
拉图尔的策展实践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气质,并且与西方社会中的个体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对“图像战争”的探索,立足于宗教、科学和当代艺术这三条对塑造西方个体的文化存在感知方式起重要的作用的线索。特别是拉图尔指出的西方社会对图像膜拜及摧毁的反复循环态度,指向了非常具体的文化体验(但这未必是非西方文化个体的真实体验)。通过这条历史沉积而建构的特殊“经验”路径,拉图尔提出了“物的民主”,呼唤西方社会中的个体产生新的体验方式(不再局限于“观看”),超越主客体的二元思维定式。因此,当拉图尔在谈及“重置现代性”时,这些前提条件——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如果被忽略,必然造成某种表面性的现代性趋同,却忽略了不同文明或社会在建构现代性时的特殊性。如此看来,拉图尔的策展实践实际上为他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注脚,即指出理论诠释的边界与极限。我们若忽略策展实践对拉图尔理论构造的意义与规范作用,可能会让误读挪用产生。
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与哲学家一起呼喊“我们从未现代”,并以此出发探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可能会忽视理论得以建构的现实经验基础。有趣的是,拉图尔在这次中国行中,或许期待获得中国学者或观众对他的理论与展览实践作出反馈,并让自己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行程成为一种经验样本,与他所在的法国社会(或曰西方后现代社会)做一个对比。但是,拉图尔对现当代中国的了解具有其有限性。在把他的策展模式引入中国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有效地构建一套可以理论化的感性经验素材,从中摸索出具有本土特殊性的现代性概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可参考《当代艺术的危机:乌托邦的终结》,原著(法)伊夫·米肖(Yves Michaud),王名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布鲁诺·拉图尔,《Iconoclash,在科学、宗教及艺术的图像战争背后》,德国Merve Verlag GmbH出版社,2002年,第16页。原文:Because we are digging for the origin of an absolute - not a relative - distinction between truth and falsity, between a pure world, absolutely emptied of human-made intermediaries and a disgusting world composed of impure but fascinating human-made medi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