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马

乌托邦时间与现实时间中的人民
王行坤 王原 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的形成与宗教信仰的领土化、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今天保马推送的帕沙·查特吉一文,作者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增补本中区分民族主义与族裔政治的尝试进行了批判。查特吉认为在这一区分的背后是安德森对现代时空的想象性理解,即将现代时间看作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线性地联系起来的空洞同质化的时间,从而为其创造关于民族与族裔的二元对立式的历史主义想象提供了可能性。而在查特吉那里,他拒绝由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主导的线性、抽象的历史主义,强调现代世界由数种时间共存的现代性的异质时间构成。该文为查特吉《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民主研究》一书第六章第一二节。感谢译者王行坤、王原授权保马微信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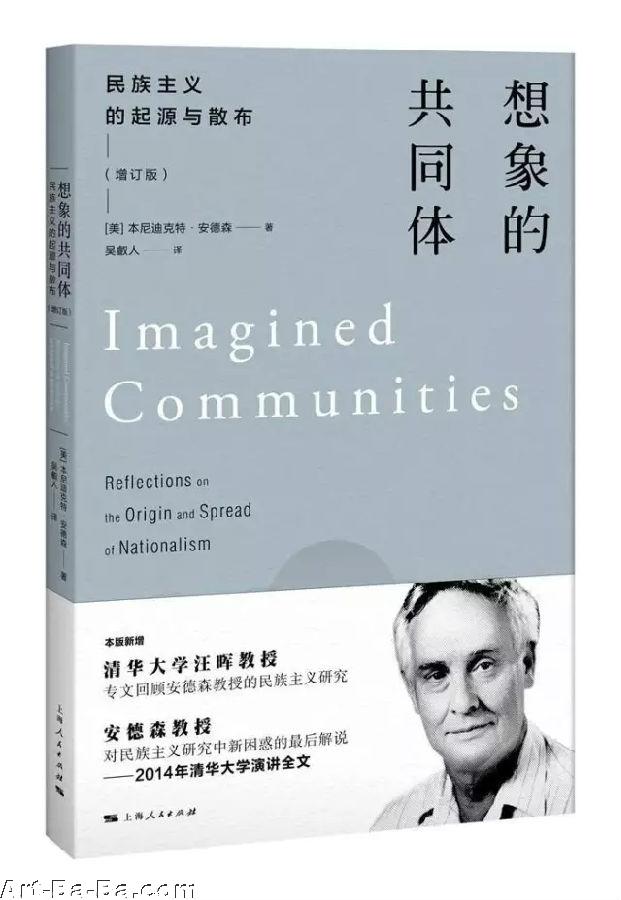
毫无疑问,《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是二十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1]在其面市之后,民族主义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世界事务中越来越麻烦、且经常是危险的“问题”。而在这一时期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继续对此主题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而往他这本受到高度评价的书里又添加了两个精彩的章节,并撰写了数篇新的随笔和讲稿。[2]1998年,其中的一些文章与关于东南亚历史和政治的一系列随笔以《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为名结集出版。[3]
民族与族裔
理论上说,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增补是区分民族主义与族裔政治的尝试。他是通过对两种由现代的共同体想象所产生的连续体的区分而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是现代社会思想的日常的一般共性的自由连续体(unbound seriality)——民族、公民、革命者、官僚、工人、知识分子等等。另一种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强制连续体(bound seriality)——由现代的人口普查和选举体系所产生出来的可以列举的人口类别的总和。自由的连续体一般是由印刷资本主义的经典机制——也就是报纸和小说——所想象和叙述的。他们为个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将自己假想为一个比面对面的小团体更大的团体的成员,可以决定站在这些团体的立场上采取行动,通着通过一种政治想象的行动来超越由传统实践所设下的限制。自由的连续体可能是解放性的。正如安德森所引用的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deya Ananta Toer)描述其笔下的一个人物角色所经历的解放时刻的文字所言:
现在,Is了解了她所进入的社会。她发现了一个比她兄弟、姐妹、双亲广阔得多的交际圈子。现在她在那个社会中有了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位女性、一位政府机关中的打字员、一个自由的个体。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人类,有着新的认识、新的故事、新的观点、新的态度、新的利益——也就是她设法从她的交际范围中撷取、收集来的这些崭新之处。[4]
相比之下,强制的连续体只能以整体来起作用。这意味着,一个个体对每个分类范畴来说都只能被算成1或是0,而不可能是一个分数,后者则意味着一切在部分意义上对某一类别的归属都被取消掉了。一个人只能要么是黑人、要么不是黑人,要么是穆斯林、要么不是穆斯林,要么属于部落民、要么不属于部落民,永远不能只是部分的或者随情境不同而属于某一类或不属于某一类。安德森认为强制的连续体是抑制性的,或许是有内在冲突性的。它们产生了族裔政治的工具。
我并不确定强制的与自由的连续体之间的差别就是描述安德森想要区分的政治形态差别的合适方式,尽管前者示人以数学上的精密性。为什么民族主义者想象的“自由的”连续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产出有限的、可数的阶级仍然不是很清楚。在解释自由的连续体的时候,安德森说它才能“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完全没有悖论的机构”。[5]当然,联合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都只能有有限数量的成员。而这是因为在获得成员资格所需的明确程序和标准之下,对国家地位的想象在这里已经退化成了治理术的制度网络。此外,如果我们在提到革命者的时候指的是那些革命政党的成员的话,那么一个国家之中、甚至全世界范围中革命者的数量也是有限和可数的(当然,这里要假定这些政党的党员资格存在清楚而明确的规定);通过同样的方法,人口普查号称能够给出——我们举个例子——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的人数。另外并不清楚的是,在何种意义上治理术的连续体是“强制的”。世界上基督徒或讲英语的人的数列在原则上是没有边界的,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数出的每一个总数在明天都会进一步增加。但是,这些类别当然跟正整数集一样是可数的,然而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上,这种所有基督徒或讲英语的人的集合总会包含有限个数量的成员。
数年前,安德森曾问我对黑格尔“恶的无限性”(wrong infinity)的观点有什么看法。我必须说,一个去世已久的德国哲学家提出的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观点从我这里得到某种道德回应,这种想法让我感到为难。在仔细地阅读了安德森的“连续体的逻辑”(logic of seriality)之后,我现在能明白他问我的到底是什么。对于安德森来说,可数而无限的类别(比如治理体系在人口普查等场合下所使用的基础计数方法——正整数列)与恶的无限性对黑格尔一样,都处于暧昧的哲学状态之中。通过有限量的序列(a sequence of finite quantities)的方法来描述变化或“形成”,只是使一个有限量和其余的量取得平衡,而绝对不是超越该有限量,这是由治理术的统计学逻辑所规定的。一个有限量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量中重新出现。“无限性的发展(progression of infinity)从来没有超越出对有限性之中矛盾的叙述,也就是说,它既是此物又是彼物(somewhat as well as somewhat else)。它不断重复地在这两个术语之间进行转换,一个词引用出另一个词。”这就叫做“恶的或者消极的无限性”。[6]对于那些试图通过这种有限数量的无尽发展的方法来领会某些事物的无限特征(好比时间和空间)的人,黑格尔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
在尝试思考这样一种无限性的时候,一般我们会被告知说,我们一定会耗尽心力。的确,我们必须抛弃无尽的沉思,但却不是因为这一工作过于艰深,而是因为它太过繁冗。要详述这种无限发展的思绪是很繁冗的,因为同一件事物总是在循环往复。我们设下一个限制——然后越过它——接下来我们又有了一个限制——然后永远这么循环下去。所有这些只是肤浅的转换而已,这种做法永远不会将有限的领域抛诸身后。[7]
相比之下,“真正的无限性”(genuine infinity)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一个有限来否定另一个有限(its other),它还否定其它的有限(that other)。这样做,它就“回到了自己”,而成为了自身相关的。真正的无限性并不会在有限的此世与无限的彼世之间划出一条鸿沟。确切地说,它表达出了有限的实质,对于黑格尔来说,那就是其理念性。它将有限的无穷变化性压缩到其理念性当中去。我并没有仅仅将这一晦涩的黑格尔主义观点拿来掩盖强制的和自由的连续体之间的区别,而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残余精华与族裔政治毫无改善的邪恶(unrelieved nastiness)的论述就有赖于此。相反地,我认为黑格尔关于真正无限性的思想是启蒙时代所特有的普遍主义批判思想的一个范例,而安德森希望维护的就是这种思想。而这正标识出了他的作品中真正高尚(我出于诚挚的敬意而选用这个词)而又合乎道德的地方。
正如我所说的,黑格尔的真的无限性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在康德和马克思(至少在对其标准的解读中)那里找到类似的例子。在面对不可置疑的历史冲突与变革,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确定一种一般的伦理概念(ethical universal),这种一般概念不会否定人类需要和价值观的差异、也不会将这些差异贬斥为无价值的或转瞬即逝的东西,而是会将这些差异整合到该一般伦理概念所建构其上的真实的历史立场中去。在十九世纪当中,许多哲学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呕心沥血:上述目的是否存在一个唯心主义和一个唯物主义的版本,如果有,哪一个才是更加实在的?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认真地看待这一争论。但是随着治理术的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传遍人类世界,这一至关重要的哲学思想被伦理普遍论(ethical universalism)和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问题所撕裂。在这一世纪中叶,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治不断增长的力量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尽管民族主义本身的成功也导向了一个荒唐的希望——文化冲突只是更加富裕、普遍的现代性的产生过程中出现的肤浅表象。然而紧跟着去殖民化脚步之后的是后殖民国家的危机,而文化战争与沙文主义、族裔仇恨和腐败并无耻操纵社会的政权画上了等号。从所有的方面来讲,民族主义都不可救药地被族裔政治所污染了。
安德森拒绝接受这份诊断书。他仍旧相信民族主义政治和族裔政治出现在不同的场所,吸收不同的营养,经由不同的网络组织,动员不同的情绪,为不同的目的而斗争。但是同西方学术界的许多人不同,他拒绝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油膏来治疗自由主义良心上的不适。他也仍旧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冷酷的“现实主义”的发展主义者,这些人为第三世界国家开出明显带有“道德给我们,经济给他们”色彩的双重标准的犬儒主义药方。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一书的结尾列出了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和令人感动的瞬间并对此做出评论:“在这一切当中存在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看上去可能会很奇怪……其中每一个都以一种虽然彼此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的国家是最最优秀的(ultimately Good),而无论这个国家的政府犯下何种罪行、无论现有的公民有多少会支持它。在这有限的几千年里,这种优秀能否被有益地舍弃掉呢(profitably discarded)?”[8]
唯心主义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尤其是我们知道在近年来安德森在文学和文化生产中的物质手段的研究领域有着比其他人更重要的影响,而正是这种生产使得在世界上的每个地区可能去设想现代的政治共同体。浪漫主义吗?也许吧,但是现代社会思潮中还有很多被浪漫主义所推动的优秀、高尚的事物。乌托邦吗?是的,而且我认为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这也是我对安德森持有异议的主要原因。

乌托邦的与现实的时间
在现代主流历史思想的想象中,现代性的社会空间分布在空洞的、同质化的时间中。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将其称为资本的时间。安德森明确地接受了这一来自沃尔特·本雅明的论述,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巧妙地用它来昭示由于同时阅读报纸或关注著名虚拟人物私人生活的体验所形成的大规模的、无明显特征的社交的物质可能性。而正是这一空洞的、同质化时间中的同时性让我们可以去谈论政治经济学中诸如价格、工资、市场等范畴的现实性。空洞的、同质化的时间就是资本的时间。在其领域之内,资本能不受阻碍地自由流动。一旦资本遇到了某种阻碍,它就认为自己遭遇了另一种时间——有些是前资本的,有些属于前现代时间。这种对资本(或对现代性)的阻碍总被认为是人类过去的产物,一些人们应该已经抛诸脑后但是却并没有实际做到的东西。但是通过将资本(或现代性)本身想象成一种时间属性,这种观点就不仅成功地将其阻碍打上陈旧与落后的标记,还确保了资本与现代性取得最终的成功,而无论某些人人的信仰或希望如何——因为毕竟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时间不会停下脚步。

E·P·汤普森
堆砌这类进化性的历史主义思想的例子会十分令人乏味的,因为这类思想散见于此前至少一个半世纪中的各类历史与社会学文献中。这里让我引用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例子,他因为反还原主义的历史能动性观点而得到了无可非议地称赞,而且还曾经发动了对阿尔都塞写作“无主体的历史”的计划的尖锐攻击。在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中时间与工作纪律(time and work-discipline)的一篇著名论文中,E·P·汤普森(E. P. Thompson)说到了所有工人都必须摆脱其前资本主义工作习惯的必然性:“没有时间的纪律,我们就不能拥有产业工人的坚持不懈的精力,而无论这种纪律是以卫理宗(Methodism)、斯大林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它都会降临到发展中的世界。”[9]
我相信安德森对现代政治有着类似的观点,即将其看成是一种正好属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性。参与、同情甚至信任那些抵抗其势力的努力统统都是无用的。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他记述了美洲、欧洲和俄国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模式形式,而俄国的民族主义后来成为了亚非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摹本。在《比较的幽灵》中,他常常提到“部分地在日常实践中得到反映、根植于工业社会物质文明中的标准化的政治概念——并非仅仅是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的令人瞩目的传播已经改变了世界运行的秩序。”[10]这样的一个政治概念需要将世界视为同一来理解,因此被称为政治的大众活动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就栖息在现代性空洞的、同质化的时间当中。
我不同意。我的理由在本书第一章已经解释过了,而我在这里将用不同的词句再次进行叙述。我相信这种对现代性的看法(或者实际上对资本的看法)由于其单面性而误入歧途。这种看法只看到了现代生活时空的一个维度。人民只能想象自己生活在空洞同质化的时间中,但他们并不生活在其中。空洞同质化的时间是资本的乌托邦时间(utopian time of capital)。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线性地联系起来,并为所有那些关于身份、民族、进步等等的历史主义想象创造了可能性;安德森和其他人介绍给我们的就是这些想象。但是空洞同质化的时间在真实空间中并不存在——它是乌托邦的时间。现代生活的真实空间存在于异质性的时间中:这里的空间是不均匀而稠密的。在这里,甚至连产业工人也并不都会将资本主义的工作纪律内化于心,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并不会按照相同的方式行事。政治在这里对所有人来说并没有同样的意义。我相信,忽视这一点就是抛弃了乌托邦的真实性。
很明显,我可以通过选取后殖民世界的例子来让我这些话更有说服力。在现代世界中,那里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几乎是一目了然地——显示出稠密的和异质性的时间。将这种情形称为数种时间的共存——现代时间和前现代时间——只是在重申西方现代性的乌托邦而已。我更喜欢将其称为现代性的异质时间。此外,为了进一步推进我这个会引发论辩的观点,我还要说明西欧与北美以外的后殖民世界实际上构成了人类居住的现代世界中的大多数。
请让我先简单地引用卡尔·马克思来澄清自己的观点。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抽象的劳动或者劳动力是一个平均值;它的价值是由其再生产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衡量的。他还说,“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数值。”[11]我们现在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科学这个词仍然指的是一套关于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中的各种定律,马克思做出了最早、最有洞察力的尝试,来阐明一种在社会现象中发现定律一样的一般规律的方法。他是通过在科学对照下的统计学方程之中导入社会事件的不确定性——他将其称为价值的偶然形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另外,通过用抽象统计学概念(比如平均数、正态分布和大数定律)来分析下述事件,哲学家伊恩·哈金说明了由概率内在决定的事件——诸如死亡、犯罪、破产、自杀等等——在十九世纪是如何(通过警察、公共卫生官员、会计、保险公司等)由政策的客体所造就的。[12]通过将抽象劳动的概念规定为一个与任何单一和具体的劳动行为无关,但是却存在确实影响的抽象的统计平均值,马克思对充斥着概率的商品世界做出了类似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对诸如工资、价格、储蓄率、增长率等抽象范畴起作用,就好像这些概念是立足于实际经济中存在的实体行为的基础上,而不去批判对以下事实的遗忘:这些范畴只不过是代表了社会平均水平的抽象统计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3]
马克思还说过,如果市场上的实际买者和卖者表现的就好像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而且其价值属性还排在其商品属性之前,那么他们就是在进行拜物教的实践。我不想在这里阐述虚假意识这一思想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但是我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并未将其解读为下了以下的断言——关于商品价值所掩盖的实际社会关系的科学发现将会清除令人疑惑的拜物教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遮盖了普通人的感知。实际上,他说的很清楚:“,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象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所独具的这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象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14]对这一话题我还有两点要说。首先,考虑到统计推理在二十世纪的所有科学学科和日常生活的公共言论中都占据主导地位,我并不确定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的拜物性和科学真实性之间所做的清晰区分是否都站得住脚。经济学或者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越来越多地通过诸如反馈循环的半自动(cyborg)机制,来将数学期望的统计学估计、自我调节技术、经济主体的那些据说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拜物行为吸收为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数据。[15]第二,我们从二十世纪中央集权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历史中可以知道, “好像”由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行为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从大地上冒出来的:即使在所谓市场经济中,它也是由新的经济体制的(通常是强迫性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种力量是由现代国家在管理和法律上的权力所支持的。这就是我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所做的区分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相关之处。
只有当其可以在一些有意义的方面上与资产阶级霸权区分开来时,诸如消极革命这样的政治形式(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再讨论这一点)才有意义。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认为印度共和国在各种意义上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都无甚区别,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而由于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就必须要描述出印度的统治集团使用权力的方式与西方民主国家中资本家们所采用方式的区别。关键的差异就在于劳动的社会形态(social forms of labour)。尽管我们可以宣称印度社会的绝大部分已经被普遍的商品生产所统治,有洞察能力的观察家(无论是资本家、官僚还是政治家)都不能也不会去承认这样一点:所有经济主体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按照抽象劳动的要求而进行各种行为的抽象主体那样。事实显而易见。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中生产相同商品或服务的经济主体在差异极其明显的条件下进行操作,以至于不可能说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能跨越不同社会形态的劳动。在所谓非正规部门中的主体可以在不纳税、违反安全或卫生规定、使用家庭劳动力的情况下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如果国家要对所有经济主体统一执行相同的生产条件的规章,许多或者说大多数非正式经济主体就会不复存在。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印度的政府机构并没有对所有人执行相同的规章。其中一些被当成了一般规定的例外。我已经说过,被当作例外来处理是一个谈判的政治过程的结果。市民社会才是规范要起作用的领域。规范在例外的领域被悬置了;这里是按照政治社会来处理的。
说到这里,我要回到安德森对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所做的区分。他承认治理术的“强制的连续体”能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而这正是族裔认同政治的食粮。但是这种共同体意识是虚幻的。在这些实际的和空想的人口调查中,“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数学方法、统一的实体都成为了同样的东西,并且连续地聚集成了幽灵般的共同体。”[16]与之相对,我们可以推论,民族主义的“自由连续体”不需要将民族共同体中的自由的个体成员变成一个整体。这种共同体意识可以设想民族从历史时代的黎明到现在为止一直以同一方式存在,而不需要对其一致性进行类似人口普查的验证。它也可以去经历一种假想的、同一时间上的民族集体生活,而不用去对其成员资格设置严格的、武断的条件。除了乌托邦以外,这种“自由连续体”还可能存在于哪里?
实际上,认同这种“自由连续体”而拒否那些“强制的”连续体就是在抛除现代治理术的情况下对民族主义进行假想。如果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数学方法毫无牵涉,我们能得到怎样的现代政治?似乎安德森所希望保留的历史瞬间就是经典民族主义的瞬间。他(可能是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行文中深刻的道德矛盾)将当今美国和其他古老的民族国家的族群政治称为“经典民族主义的迪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17]他严厉抨击爱尔兰裔美国人“远距离民族主义”,因为他们与“真正的”爱尔兰已经脱离关系,但是却忽视了这一事实:这个“爱尔兰”只是在乌托邦中才确实地存在着,因为这一政治现象的真实空间是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异质化空间。
所以,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和族裔之间对立(opposition)的论断可以追溯到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和治理术之间的差别,前者为经典民族主义的人民与民族的等式奉为圭臬,而后者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开始大放异彩。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对立呢?当成是好与坏的对立吗?还是当成应予保留的东西与应予弃绝的东西?或者我们应该说,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轨迹之后,人民主权和治理术之间的对立展示出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新矛盾,而这种秩序还要在在大众民主的大前提下维持阶级统治?
注释
[1]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中译本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收录于Imagined Communities(修订版), London: Verso, 1991。
[3]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中译名为《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2。
[4] 转引自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 41。
[5]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 29。
[6] G.W.F. Hegel,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Part 1, tr. William Wall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 137.
[7] 同前,138页。黑格尔详细地使用了他对真假无限性所做的区分来批判费希特对契约的法律正确性和道德正确性的论点。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 T.M. Kno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61.
[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 368.
[9]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Penguin, 1991), pp. 352–403.;中译本为《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352~403页(中译本第382~443页,篇名为“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
[10]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 29.
[11]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tr.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90),第六章,p. 275页。
[12] 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译本名为《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 Marx, Capital, vol. 1, ch. 1.4, p. 168.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91页。
[14] 同上,169页。
[15] 这里的“数据”和前文中的“一定的数值”,原文都是datum/data。作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的数值是一种带有决定论色彩的范畴;而现代经济学,或者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将各种动态的因素纳入其考虑范围,从而使其在解释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脱离了决定论。——译者注
[16]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p. 44.
[17] 同上,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