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午故事 文:黄昕宇
“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口述简史。“现在的摇滚可能都太要脸,应该再有一些不要脸的乐队出来,世界才能更美好。”

梅二:顶马十五年,哪年要过脸
口述 | 梅二
采访、文 | 黄昕宇
1
1995年,我考进上海大学文学院广告系,同班同学里有个人叫陆晨,我看他特别眼熟,一对,果然是小学同学,他是一班,我是二班,我们失散了整个初中高中后,竟然在大学又碰到了。
陆晨是他高中历年卡拉OK大赛的第二名。第一名永远是一个民族唱法的小姑娘。他唱的张国荣可以以假乱真,粤语,张国荣在演唱会中说的话他都能一模一样地说出来。那时陆晨听张国荣,至多到罗大佑。我高中就开始听摇滚了,听唐朝、黑豹、魔岩三杰,国外的涅槃、Radiohead等等,有一抽屉的磁带。有一天陆晨在我宿舍里打开了这个抽屉,就走上了一条通向摇滚的不归路。
在学校,我们老跟几个搞乐队的师兄玩,他们翻唱“枪花”、“涅槃”的歌,好像挺牛逼的。其中有个吉他手,绰号叫驴,现在是制作人,给“街道杀死奇怪动物”、“五条人”录音混音。驴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军队子弟,吉他弹得很好,留着中分长发,看起来特别酷。我们那时候中了《灿烂涅槃》的毒,无比热爱涅槃乐队,都穿格子衬衫,裤子上都剪一个洞。那帮师兄毕业后,驴一个人闲着,我们就和他一起做乐队,分配乐器,吉他手有了,我就去学贝斯,还有个同学,叫猪头,去学鼓。
当时上海有个美声乐器厂,它的附属艺校叫美声艺校,每周末在外滩的小学那儿办班,我们就去那儿学。鼓班有七八个人,吉他班有二十几个人,贝斯班在学校放体育器材的储藏室上课,只有一个老师和两个学生。
我买了一把三四百块的美声牌电贝斯,音质极差,巨重无比,背在身上站着弹会脑缺血。老师说,你不能用这把琴学,手会弹坏掉。我就跟父母要了一千九百块,买了把雅马哈250练习琴。老师送我们一人一盘磁带,有“小红莓”、“枪花”、崔健之类的歌,没有贝司音轨,我们就回去扒歌照着练。课上大部分时间,老师都在跟我们吹牛逼。
学校实在太烂,学了大概三个月,在一个教室里搞了一个毕业典礼,有人唱了郑钧,有乐队唱了METALLICA,然后大家就解散了。
1997年,我们组了乐队,叫七,Seven。起这个名字是因为看了《七宗罪》,觉得太牛逼了。正好有个蒙古族同学说,在他们民族,7这个数字很古怪。我们说,太好了,就叫七。
上海东北面是大学区,那儿有个叫“部落人”的酒吧,很多大学生和部队子弟在那儿混,我们也经常去玩。酒吧星期三晚上没什么生意,老板看我们是搞乐队的,每星期三下午给我们钥匙,让我们自己开门进去排练,排完吃了晚饭就在那儿演出,报酬是一人一大瓶青岛啤酒。我们每周三演完,就喝一瓶啤酒,骑自行车回去睡觉。
因为一开始排练就在舞台上,台下有观众,导致后来我们上舞台一点都不怵。
1997年12月31号,乐评人孙孟晋在上海在市青年活动中心搞了第一次摇滚大趴,把能上台的十几支乐队全都聚齐了。大家就知道有个Seven乐队了,开始叫我们去各种很怪的地方演出,有时在部落人,有时在华师大后面的啤酒吧,还有在上海影城的地下室,基本都是大学生乐队的群趴。
后来,在宝山区混的一个新疆哥们儿回到了乌鲁木齐,跟驴说他在乌鲁木齐能安排演出,让我们赶紧去。因为猪头没时间,我们三个就借了钱从上海坐了4天3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跟着那个哥们儿住进了他工作的铝厂,还找了当地的一个鼓手合作。晚上他带着我们去乌鲁木齐各种夜总会、音乐西餐厅,进去就找经理,说上海来了个乐队,想演出,经理就说你们试试吧,我们上去演涅槃,台下有陪酒的小姐跳快四步,我们才知道这哥们儿根本没安排演出,就带我们到处混而已。
1999年我们毕业了,都找了工作。陆晨一毕业就当了公务员,一直干到现在没换过。我进了广告公司,后来换了好几份工作。当时我们有一个搞乐队的朋友,在火车机务段工作,那儿有个地下室,他弄了一堆音箱和鼓,我们就每周末去排练,继续演出。
这时乐队就遇到瓶颈了,原来搞的是英式,后来越来越神经质,一首歌能写十几分钟长,和声特别奇怪。而且大家上了班,也没什么劲儿了。2000年,鼓手去英国留学,Seven乐队散了。

大学时期的梅二和陆晨

1998年,在乌鲁木齐。
2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陆晨的短信,说他和毛豆想做乐队,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可以啊。他马上回复:我们已经在你家楼下了。
我们就在楼下的小酒馆点了三个菜,喝了点啤酒,商量乐队的事。那时上海乐队挺多了,驴不在的话,我们三个的技术完全不能做出一个像样的摇滚乐队,于是我们决定不做原始的吉他、贝斯、鼓三大件乐队,要做就做很奇怪的东西。怎么怪呢?要么只有鼓,要么只有贝斯,要么只有吉他,总之要规避三大件。
毛豆是我们的诗人朋友,也弹琴,但弹得很烂,我们就让他当主唱。陆晨主要弹吉他,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弹贝斯。不过,还是视歌的情况而定,有的歌只有贝斯,就所有人都打鼓。后来我们又找了个会吹黑管的女孩。
我们的排练室在地下室。上海有很多地下室,都是文革备战备荒时响应“深挖洞,广积粮”号召挖的。好多人租地下室,墙上挂棉被,改成排练室。我们每周固定排练一个小时,然后去天山电影院旁的一个火锅店吃四个小时火锅,喝酒闲聊。大部分歌的想法是在火锅店里形成的,到排练室只是去实现而已。
有一天,我们觉得乐队得有个名字,就各自回家翻字典。最后在两个名字中选,一个是我提的“简明心理学词典”,我在家刚好看见这本书;陆晨提的是把卡夫卡的小说《马戏团的顶层楼座上》倒过来——顶楼的马戏团。我们三个人投票,二对一,顶楼的马戏团胜出。
如果叫简明心理学词典,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是个实验乐队,结果我们叫了“马戏团”。好像冥冥之中,这个乐队的气质一早就定了。
2002年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叫ARK的音乐演艺酒吧第一次演出。那天我们穿着对襟的唐装上台。有一首歌只有吉他,三把吉他在台上“吭吭吭”扫,我们还买了各种奇怪的民族打击乐器,在台上又拨又敲,跟做法事似的。演了几首歌,台下就一片“啊?”很错愕,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乐队。
乐评人老大哥孙孟晋那天也来看,他对我们印象深刻。第二年迷笛音乐节时,张帆找老孙带几支上海乐队来,他就推荐了“戈多”、“Junkyard”和顶马。当时迷笛音乐节还在香山迷迪学校的大草坪上。我们三支乐队坐1461次绿皮火车,硬卧睡了一夜,一到北京就坐了几辆黑车去了迷笛,晚上住在迷笛学校学生宿舍。当时的乐队都不想压轴,想先演——那会儿大家赶着回家,越晚观众越少。在张帆那儿,我们跟一个树村的乐队吵了半天先后次序,张帆说,让上海乐队先上。
那时北京的乐队除了“美好药店”,大部分都是树村的新金属乐队,上海却去了三支特别前卫的。戈多2001年就开始做后摇,第一天他们演的时候,台下观众也就听了;到了Junkyard,数学摇滚加实验噪音,观众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实在受不了,开始扔东西。Junkyard演着演着,“啪”一块砖头落在脚边。到我们演已经是晚上,我们的演出就显得更奇怪了。新金属的歌迷在台下瞎闹,大喊:“下去!下去!”
我们唱到最后一首《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主唱毛豆在台上喊:“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永远倔强,没有人能消灭我们!”
台下立刻哭成一片。
在迷笛音乐节这样一个很乌托邦的环境里,台下都是热血质朴的摇滚青年,那种感同身受特别强烈。张帆也很激动,拿着话筒上台说:“上海的哥们儿,牛逼!”
这次演出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批乐迷。那次音乐节之后,颜峻写了一篇很长的纪实乐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其中单独提到上海乐队。那是乐评人的时代,乐评人说什么都是最权威的,大家一看就记住了顶楼的马戏团。
那段时间写的歌收录在我们第一张EP里。那张唱片是用我的MD机接了个话筒在天山路的排练室一下午录出来的,音质奇差无比,我手绘了一个大象做封面,结果延续下来成了我们乐队的LOGO。

“顶楼的马戏团”首张EP专辑封面。
3
不久,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顶马被从摇滚乐队的范畴里划出去了。
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写词,因为主唱是诗人,歌词也比较诗意。乐队常在周末到各个朋友的办公室排练,渐渐就不用电声乐器了,想了很多很奇怪很实验的东西。人家会说,这不是个乐队,是个声音实验团体,很多演出也在美术馆或者艺术区。毛豆当时也有点疲倦,他还是喜欢诗意的东西,但我们渐渐觉得老热泪盈眶没什么意思,不喜欢了。毛豆就走了。
毛豆离开之前来了一个弹吉他的画家,叫顾磊。
上海有那种工厂修的老式新工房,一大片都是一模一样的六层楼房,按片区命名为XX一村、XX二村、XX三村,里面跟迷宫一样。那些新村都在比较偏的郊区,环境比较乱。顾磊就在上海西北角一个新村长大。他比我们大八九岁,身上有那种跟大学生不一样的、土土的流氓气息。顾磊是个一辈子都没工作的人,一直在画画,但好像一张都没卖出去过,他的吉他和弦摁法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没人能模仿。
当时,我们的排练室已经转移到陆晨家他的卧室,不能搞出太大动静,最后我们的第二张专辑《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就全是民谣。
当时我们已经很不好意思再唱《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了,觉得太矫情。第二张专辑完全是对诗意和艺术的反叛。那时候陆晨欣赏艺术家杜尚,他觉得把一个小便池放美术馆的做法特别牛逼,于是就把约翰列侬的《Imagine》填上特别低俗的中文词。另外一首歌《方便面》是这么来的:有一天我们在陆晨家排练,他跟他弟弟打电话,问他吃了啥,他弟弟说:“方便面。”我们就念叨,“方便面,挺方便的噢”,开始一路胡逼,“吃下去也方便,拉出来也方便,真呀真方便”,发展出整首歌词。
还有一首歌根本就是上海本土方言脏话教科书。当时顾磊教我们骂了好多特别土的脏话,我们一听就觉得,我操!太牛逼了!就把脏话垒在一起形成一首歌。实在想不出这么脏的歌要叫什么名字,就叫《陆晨》吧。
这张专辑基本就是这么胡来的。我们是业余乐队,自己出唱片没有审查一说,大家都有工作,也不担心被禁了不能演出、不能上音乐节什么的。我们完全无所谓,就到驴家里录了专辑。
第一张专辑是自己一张一张刻盘的,太累了。这张专辑陆晨在江苏找了个工厂,是免检单位,厂长说只要盘上印三个小字“非卖品”,不用版号也可以给我们压盘。我们压了1000张,连卖带送出了两百张。接着有关部门就把碟拿去审查了,先是一个小女孩听,听一半说,“科长你来听一下,这个光盘里怎么有驴叫?”其实那是我们从AV里录的采样。科长一听赶紧又找了个懂上海话的人来听整张专辑,那个人一听就说,这张唱片一定要禁掉。于是他们找厂长要求追回一千张唱片,否则吊销执照。
厂长开着车从江苏来上海请陆晨吃饭,说,“小陆啊,有个事很不好意思,你们唱片被禁掉了。我懂啊,你们这是艺术!我很支持你们!但是,不追回来我厂子要被吊销执照的,我请你们吃饭,请你们帮帮忙吧。”
我们赶紧把剩下800张还给他,然后一个个翻通讯录联系买家。第二天我跟陆晨打着车满上海收唱片,拿了就走,“不吃饭了不喝酒了,再见再见”。最后要回来100张左右。所以现在还有100张不知在哪儿的原版唱片存世,其他都被收回去销毁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被管束。作为一支摇滚乐队,被禁是最大的宣传。“顶马被禁”的消息一下子传遍大江南北,特别火。
这张唱片的第一次演出又在ARK。当时我朋友从北京带“AK47”乐队来上海演出,喊我们当嘉宾。我们唱了那首《陆晨》,台下一片哗然。有些观众怒不可遏,扭头就走,另一些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捶地大笑。ARK主办演出的女士跟我哥们儿说,你赶紧让他们下来。我哥们儿是北京人,听不懂,问发生什么了?她说:“我永远不要再在我的场地看到这支乐队。”
后来的演出就是各种闹剧。我们跑到大学里唱《方便面》,大学女生就往台上狂扔粉笔头和垃圾,大喊:“下去!”
我们胡搞,想干嘛干嘛,极尽搞怪,在台上跳大神,手舞足蹈。有一场演出,陆晨用鞭子抽顾磊,还有一回大家演着演着就从台上跳下去。我们觉得很爽,反艺术。没想到越反艺术,人家越觉得艺术。我们到北京,问“去哪儿演出啊”?——“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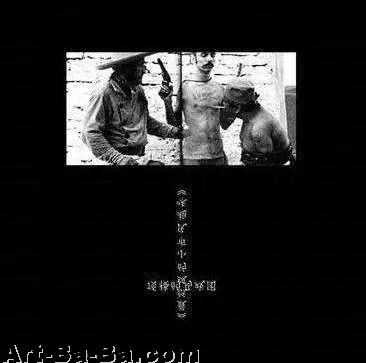
《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专辑封面。

顶马参加艺术家许坦的项目。左一为顾磊,中间坐着的是毛豆。
4
《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之后,我说,你们发现了吗,现在我们的歌又粗俗又难听,对观众意识形态冲击非常大,但是他们的身体没有反应。我提议做朋克,朋克是让人身体反应最大的一种音乐形式。那时候想做朋克先是受了台湾“浊水溪公社”的影响。一个台湾朋友给我们看了他们演出的视频,他们经常在台上把东西全部砸光,我们觉得这个好,就搞这个。
做朋克就要恢复三大件形式,我们把Junkyard的吉他手猩猩找来,又问另一个乐队的吉他手中科,你会不会打鼓?他说会一点。我们一看,很猛!可以!后来发现他打鼓也就猛一首歌,第二首就不太行,到第三首都要打不动了,但是他的打法很特别,一般的鼓手扒不下来。
2005年7月我们第一次演朋克,在上海的哈雷酒吧,连空调都没有,巨热无比,墙都在流眼泪。陆晨把头发弄成前后都是尖的,穿了条游泳裤COS阿童木,其他人每人穿一条内裤,屁股上挖两个洞,一边屁股一个字,依次写“阿拉顶顶朋克”(上海话,我们最朋克),鼓手戴了个红色的胸罩,打算COS林志玲。我们翻唱了几首歌,包括S.H.E.的《SUPER STAR》,把自己的歌也改成了朋克,还专门写了一首新歌叫《我们很愤怒》,因为朋克必须愤怒!
人家一看,啊?顶马又变成这样了!
后来我们排练时觉得,顾磊老师,吉他弹得真不行啊……我们刚开口,顾磊就说,“知道了知道了,我走了。”顶马就变成了四人编制。
2006年夏天,我们到杭州参加夏音乐节。天气实在太热了,陆晨演着演着突然脱光。主办方很快上来说,警察来了,赶紧走。我们就拿着包从后面溜走了,杭州警察出警真是不够快。
那是陆晨第一次脱光。当时他还想在台上拉屎,我问他为什么没拉。他说,这么多人拉不出来啊,别说拉屎了,尿尿都尿不出。他试了一下,没成功。
后来就成习惯了,除了冬天室外的演出,每次演朋克他都脱。观众也知道,看顶马演出就等陆晨脱光,不脱就开始喊,“脱!脱!脱!”——陆晨这是在向GG Allin致敬。
我们每天想怎么朋克起来。有一天吉他手说,要不要弄鸡冠头?大家一想,算了,没法上班。然后继续想,谁最朋克?吉他手猩猩就说,我知道一个人最朋克——GG Allin。一看他的演出视频,我们完全震惊了。吉他“哐”一响,一个全裸的主唱,浑身都是屎一样的东西,“嘭”地一拳打翻一个观众,然后薅女观众头发。警察直接把他带走了——太牛逼了!这才是朋克啊!
我们看了大量GG Allin的视频,研究他的歌词。根据他那种意识形态写歌,有向他致敬的《GG主义好》,也有用上海话翻唱他的《Bite It You Scum》,还有一首歌就叫《GG Allin》。
当时育音堂老板老张在万体馆那里的轻纺市场二楼开了一个排练室,我们在那里挥汗如雨地排了两个月,排出二十多首歌,其中19首做成一张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这张专辑从封面到制作都在恶搞鲍勃迪伦的《重访61号公路》。93号是我们后来排练的地下室的门牌号,蒂米是《南方公园》里的脑瘫小孩,不会说话,只会说“Timmy”,开心喊“Timmy”,生气也喊“Timmy”,通过语气变化来表达。《南方公园》里,他也做了个乐队,他是主唱,所有歌词都是“Timmy Timmy”。我们很喜欢蒂米。
在上海演了几场后,大家就知道我们现在是朋克了。喜欢pogo的人会特地去看顶马演出。那时候有个叫老杨的哥们儿在北京办演出,邀请我们去北京的老“豪运”办专场,我们就买了四套喇嘛服去了北京。为了更热闹,我们还特地叫了一个哥们儿故意上台跟我们打架,那时候已经不做乐评改做实验音乐的颜峻上来用电锯锯钢条,火花四射,但是那场演出的大部分观众都不是朋克。
那张专辑我们还写了首歌叫《朋克都是娘娘腔》,引起了雷骏等北京朋克的不满。后来一个叫冯然的北京人在上海搞了一次朋克音乐节,请来很多北京朋克,我们一起演出后又成了好朋友。
朋克音乐节的演出,我化装成白无常,陆晨化妆成僵尸,穿清朝官服,上海京剧院的一个哥们儿给他画了大白脸。吉他手猩猩走了,原本就是吉他手的中科又成了吉他手,他穿了一身喇嘛服,新鼓手晓零穿了一套睡衣,带着《惊声尖叫》的面具。后来,这种每次大专场或音乐节都定制演出服的习惯一直保留着。
当时我们已经有巡演了,也跑北京、广东做演出。在广东跨年我印象很深。30块钱一瓶啤酒,观众一下要了一打,往台上狂喷。舞台是玻璃的,我们在台上跳起来,一落地所有人就“哗”一下翻出去,陆晨又脱光了冲到人堆里,观众都很high。

第三张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封面

2005年,上海哈雷酒吧首演朋克。

2006年,1234海滩音乐节。

2007年,北京新豪运酒吧演出。
5
2009年年底,草莓音乐节的After Party邀请我们到北京演出。我有事没法去,乐队就找了另一个哥们儿苏勇去弹贝斯,后来他就加入进来。
那场演出,陆晨说,既然是party,一定要好好热闹一下。演出费顶马就不挣了,他用那五千块钱在北京请了个真的马戏团来表演杂技。马戏团带了个女主持,陆晨就穿着粉红色的西装在台上跟她一起主持串场。观众又疯了,来看顶马演出怎么一会儿顶缸,一会儿变魔术,还有翻跟头转碗?!一直到最后陆晨才唱了一首歌,翻唱《北京欢迎你》,改成了《上海欢迎你》。
不久,我们的地下排练室被拆了,我们就合计,把《上海欢迎你》改成《上海不欢迎你》,并且很快就在一场演出中唱了这首歌。现场有人用手机拍下来,放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击率就有几十万,引发了各种地图炮对骂,还有境外媒体跑来采访。我心想,操,事大了。果真没过多久,这些视频都被删掉,并要求我们把自己网站上的歌也撤下来。我们很配合,要保住工作嘛。
2009年底出了这事,没想到整个2010年顶马都不能在上海演出。
原先定在2009年12月24号MAO Livehouse办的新专辑首发演出,同时也是圣诞节演出,就这么黄了。当时好多媒体批评上海市民穿睡衣上街的现象,说这是不文明行为,引发很大的争论。我们办这场演出时特地注明:欢迎全体观众穿睡衣前来。主管部门跟场地方说,这个演出要报批,报上去后杳无音讯。到23号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演,只能紧急通知演出取消。好多歌迷还特地买了睡衣。
不止MAO,我们在上海所有场地都没法演,真是憋死了。于是我们跑去隔壁杭州演了一场。有三百多人从上海跑到杭州看我们演出。一个上海乐队在杭州演出,台下全是上海人。
还有个朋友在上海开了家小live house,看我们特别想演,就找了唱民谣的哥们儿,做一场民谣专场,括号:特别神秘嘉宾。大家私下就传开了:“你猜特别神秘嘉宾是谁?顶马。不要告诉别人!”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的Livehouse只有一个小客厅大,那天挤进来两百多人,站得密不透风。后面一百多人什么都看不到,就开始看世界杯直播。那场是德国队四比零血洗阿根廷,陆晨穿了件梅西的球衣。我们演着演着,还没到高潮,后面“哗”一阵喧哗,我们就停下来问,“怎么样怎么样,几比几了?”后来他们说,想让哪个队输顶马就穿哪队球衣。

2010年圣诞专场海报。

2011年乐队十周年演出海报。

2010年世界杯期间,在上海696 livehouse演出。
6
《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录了两天,陆晨两天唱了十九首朋克,把嗓子唱坏了。两根声带中有一根彻底废掉。
他说,哎呀,怎么办,再也不能唱朋克了。
我们最后一次演朋克是给二手玫瑰暖场。结束后陆晨跟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像摇滚明星了,一上台,大家就喊‘脱脱脱’,很套路,感觉不好。”我说,反正你嗓子也不行了,要不我们做后摇吧。他就去买了个键盘,又找了一位美国吉他手。
陆晨不唱歌很难受,提出申请:“能不能把键盘音量开大一点”。我们演了一次,做了个很大的即时贴,写着“后摇”两个字,往台上一贴,开始演。所有来看朋克的人都傻眼了,“他们怎么又开始搞后摇了?”,而且那么难听,键盘弹都弹不准还“嗡嗡嗡”声音巨大。
这不行。我问陆晨,你还能唱歌吧?他说,能,还有一根声带。
从2007到2009年,我们不知道做什么风格好,每次排练都很痛苦。其中有一年的“五一”我们去北京的迷笛after party 演出,索性翻唱了一堆《站台》、《我不做大哥许多年》这样的大俗歌,我们赤膊穿着劣质西装,陆晨戴着十个假金戒指,全场群魔乱舞,演出主办气得想拉电。当天我们还找了一个夜总会跳舞的姑娘来伴舞,唱《外来妹》的时候陆晨说这首歌送给五一长假还在发廊、夜总会、KTV坚持工作的外来妹,演出结束后那个伴舞的姑娘拉着陆晨,说“大哥你人真好”。
我大学时有个哥们儿让我听《流浪到淡水》,说“这是台湾的布鲁斯”,我当时一听,把磁带直接扔了,“去你妈的,什么布鲁斯”。台湾金门王和李炳辉是两个盲人,金门王的手烧伤了,套一个铁片当拨片弹吉他,李炳辉拉手风琴。他们都是在台湾音乐茶室里唱歌要饭的,唱特别土的台语歌,后来被伍佰发掘,出了两张专辑。2009年有一天,我在家又听《流浪到淡水》,觉得太好听了。几年间人的性格转变真是特别好玩。我和陆晨去卡拉OK点他们的歌,看MV,觉得好极了,决定就搞这种。
确定方向后,写歌其实很简单。顶马每次换风格都是如此,找风格需要一到两年,一旦找到,可能两个月就写好一张专辑。
《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这张专辑很平面地展示了十三种上海人生,都是快递员、白领之类的小市民,全是特别土的土摇。《是男人》那首歌,是我们走在上海泰康路上,看到有个人在那儿喊,“是男人,是上海男人,就喝!” 回来根据这个场景写了的。《上海童年》完全是上海七零后八零后的回忆。《苏州河恋曲》在中老年人中的传唱度比在年轻人那儿还广,甚至有歌迷找我要伴奏带,说他爸想在公司年会上唱。
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懒得自己设计了,就搞了个封面设计大赛让歌迷来设计,结果有100多个设计发过来,基本都不堪入目,但我们觉得特别好,然后决定这张专辑不发实体,反正也卖不出去,所有的歌和这100多张封面打包免费下载,你觉得哪个封面好,就用哪张做专辑封面好了。
《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有浓烈的地域色彩,描写的是市民生活,又都用方言唱,很容易让上海人有感触,我们的歌迷从原来的摇滚青年和朋克,一下扩展到整个上海市民阶层。
那时候我们的演出已经不脱衣服了,但是还是会专门准备服装,有的是向金门王李炳辉的《来去夏威夷》致敬,穿热带风格的汗衫短裤,还有一次草莓是支持同性恋,就穿了浴袍致敬张国荣。还有一年愚人节,我们举办了向自己致敬的顶马翻唱大赛,找了乐评人孙孟晋、张晓舟和电台的DJ来做评委。陆晨穿了女装晚礼服在台上扮演李湘,然后特别安排上海的“蘑菇团乐队”先被淘汰,再复活最后夺冠,特别复制了选秀大赛里励志正能量的桥段。
原来我们的演出也就来个一两百人,这张专辑出了之后,演出门票一下子卖出五六百张。2011年圣诞节,我们在MAO办十周年专场,警察都出马来拦人了,还是挤进一千多人。我们没想到歌迷规模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现场演出的感觉不一样了,有点明星的状态,还没上台大家就开始喊,一上台底下“哇”地叫成一片。比较无奈的是,我们都过了朋克时期了,观众还在喊“脱”。
以前,我们根本没指望挣钱。最早参加迷迪音乐节是没报酬的,只能报销路费。《金曲十三首》之后,草莓音乐节进入上海,顶马在爱舞台压轴,这才知道一个音乐节居然能给几万块钱。慢慢跑了一些全国的音乐节后,我们发现,原来搞乐队带来的收入比想的多多了。大家就开始考虑,是否做个PPT放歌词,让更多人听懂。
其实我们唱上海话,就是觉得好玩。没想到上海话让我们从全中国几万支乐队,全上海几百支乐队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出了有地域特色的专辑后,顶马变成一支有代表性的乐队。如果唱英文或普通话,知名度肯定不会这么高。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不到火遍全国,顶马在上海演出能来几百人,可能在天津就只有十个人。
后来,好多宣扬上海地方文化保护的人把顶楼的马戏团挂出来做典型。其实我们的歌里有很多嘲讽上海人的内容,很多人听了反感。有人在微博上一通骂,说我们是“沪奸”乐队,由一群“三校生”(中专,职高,技校)组成,文化素质极低。我们转了那条微博,就又来了一批“三校生”,质问道:“三校生”怎么了?

2011年,上海迷笛音乐节。

《上海市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封面之一。

《上海市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封面之一。

《上海市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封面之一,区区五百元先生设计。
7
很快又到了换风格的时候。我和陆晨商量,现在苏打绿、小飞机场很火,不如我们搞小清新。于是按照小清新的标配,找了会弹键盘的女主唱范范,一共凑了六个人。大家在陆晨家吃饭时民主投票——“搞小清新行不行?”立刻全票通过。紧接着所有人一起创作。上一张专辑是给老年人写的,这张小清新嘛,我们决定往年轻人的生活偏一偏,比如,写写年轻人开房。最后一共写了30首,都挺好的,所有歌都能大合唱,于是出了张双唱片。专辑有个特别长的名字:《谈钞票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钞票又伤感情》。
2013年,这张唱片给我们带来一大批九零后歌迷。
这个乐队渐渐从几个好朋友胡闹,进入了真正摇滚乐队的状态:演出,排练,参加音乐节,比较高的演出费出现了。大家见钱眼开,觉得挺好。我们找了职业经纪人帮我们接演出,谈价钱和演出条件。
排练越来越像上班,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对话,“这个和弦要怎么打”、“排练不能迟到”之类的,排完就散了。大家觉得喝酒没什么意思,就很少一起吃四五个小时饭了。三十五岁之后,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固定下来,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圈,慢慢就玩不到一块了。乐队变成一种合作关系,不再对彼此生活产生那么大影响。
2014年底,我们接了一趟某饮料品牌的巡演,跑了五六个城市,挣了点钱,但不是很开心。赞助商去现场看了第一场,很有意见,觉得这个乐队怎么满口脏话。经纪人就希望我们注意点儿。
我们真是憋得慌。以前演出时,我们跟观众的互动就是相互调戏,没那种状态,就没劲了。
从2014到2015年,我们几乎每周都有演出,音乐节和巡演接了不少,特别忙。原本大家还想尝试Ska,但陆晨说,他觉得很累,想休息一下。我们都理解。演出多起来之后,又上班又做乐队是很辛苦的。他在台上的表演又是很身体化、很激动的,比我们累多了。
陆晨已经不像二十几岁那样,台上台下一样疯了。以前所有北京乐队都知道,千万不要跟顶马一块喝酒。年轻时,我们每次来北京都跟小河、万晓利他们喝酒,喝的都是低等劣质白酒,猛喝,然后发酒疯,闹得特别厉害。年龄渐长,生活环境状况都变了,身体和精神状态也都往下走。以前喝个大酒恢复一天,现在可能三天都缓不过来。小河他们一个个都是戒酒协会会员了。
到后来,陆晨在台上台下完全是两个人,私底下其实很平静,只是他习惯了演员的身份,在台上会演出大家心目中的陆晨。他休息了一阵,大概觉得比演出舒服多了,就决定退出。我们确实也能体会到这个乐队慢慢发生的变化,那就散了吧。
其实,最早顶马组起来就不是要成为什么职业乐队,纯粹就是好玩。我们都有工作,能保障生活。单位的同事都知道我们是搞乐队的。这很痛苦!我以前在电视台,每年年会领导就说,你得唱个歌。我说,我是贝斯手呀。领导说,不行,你会弹吉他嘛,得唱一个。我很想跟他说,那我是法医呢?是不是表演一下解剖尸体。
陆晨的工作很清闲,也稳定,旱涝保收,他很清楚保障生活之后才能干想干的事。
原来在乐队,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当这样一个九十年代组起来的业余乐队渐渐职业化,想在市场里分一杯羹的时候,原来的玩法已经没办法适应现在中国的音乐市场了。
陆晨退出后,我们剩下的人组了个后摇乐队,起名“反狗”。
全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乐队,之前和我们类似的乐队有云母逼、耳光、驳倒、板砖等等,我们还凑在一起搞过一个小清新音乐节,这些乐队大部分渐渐都散了。我觉得特别可惜,这世界上除了蝴蝶蜜蜂蜻蜓,还应该有苍蝇蚊子,否则就不丰富了,影响了物种多样性。现在的摇滚可能都太要脸,应该再有一些不要脸的乐队出来,世界才能更美好。
题图:2014年,梅二、陆晨和勇哥。来源:世界中国。
所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