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

艺术家陈劭雄
据悉,2016年11月26日上午,“大尾象”工作组成员、艺术家陈劭雄因病逝世,享年54岁。生于广东汕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陈劭雄,80年代中期开始介入广州实验艺术界,生活、创作于中国最为繁忙的大都市之一——广州,对都市题材的关注正是陈劭雄早年与林一林、梁钜辉、徐坦在广州组成艺术小组“大尾象”时就开始的艺术实践,这些经历造就了陈劭雄对城市精神状态的敏锐洞察力。近30年来的艺术创作始终不断重新定义着观看与感知的方式,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折射时代对个体的投射。


艺术圈人士们沉痛哀悼
2016年10月29日,陈劭雄作品展“景物”与其近二十年回顾展分别于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及博而励画廊开幕。其中,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出了艺术家最新作品:大型互动影像装置《景物》及《集体记忆》系列作品。而博而励画廊则带来了艺术家90年代创作的多件重要录像装置及2005年以来的水墨动画系列录像作品。展览开幕当天,包括王璜生在内的圈内众多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前来观展,两个画廊一墙之隔,串联起了艺术家陈劭雄的过往艺术历程及其最新力作。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陈劭雄个展“景物”现场

陈劭雄 《集体记忆-泰特现代美术馆》,布面中国印泥 ,267×180cm,2016
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出的艺术家近十张《集体记忆》系列作品延续了此前的公共项目形式,邀请普通公众用中国印泥点按出世界各地著名美术馆建筑景观。另外,展览还将展出大型装置《景物》,这是该作品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展出后首次亮相北京。
陈劭雄表示:“《集体记忆》系列创作是将照片的数码还原成大小不一的像素点,然后邀请有着共同记忆的社区居民来合作,用他们的指纹构成一个图像,以代替冲印照片的药水,这是介于摄影暗房技术和绘画制作技巧的方法。是集体对其共同生活空间的追忆。”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陈劭雄个展“景物”现场
在本次新作展中,陈劭雄选择的场景是城市当中的公共文化机构——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古根海姆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这些机构本身就是极具表现力和激动人心的建筑。它们在城市文化生活中日益成为重要的场域,精英主义的起源被重新定义为拥有广大受众的“景点”和地标性建筑。被陈劭雄邀请来参与用指印创作的是学生与普通公众,他们在画布上用手指重现这些建筑景观,整个过程将图像摄影、软件处理与绘画等各种语言方式结合。这是陈劭雄近年来所专注的公众参与的艺术实验,在侯瀚如看来,这也“代表了形象文化和知识生产的民主化”

陈劭雄 《景物》,四频影像装置,2016


《景物》局部
《景物》是陈劭雄2016年创作的大型影像装置,四块弧形屏幕上变换的画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风景。艺术家在漫漫旅途中剪切下一个个时间和空间的片段,在周遭世界继续变化的时候让它们保持不变。栖息在树梢的喜鹊、推着自行车穿过铁路的人、冬日的荷塘、溜达的小狗……这些微小的时间碎片逃离了原本的存续命运被永远地封存,像是琥珀中的昆虫,成为陈劭雄的私人缅怀。在观众观看、审视、凝望的过程中,这个内心自由之景将触发多重的感知,与更多的记忆联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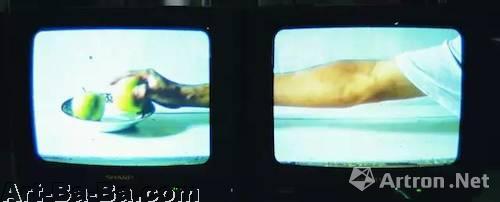

陈劭雄,《视力矫正器》3,1996,双频录像装置,有声,彩色,7’50’’
在博而励画廊的个展是艺术家继2007年的“看见的和看不见的,知道的和不知道的”,2009年“信则有”之后,艺术家在画廊举办的第三次个展。展览呈现了陈劭雄于90年代创作的《视力矫正器3》《风景-2》《警察与小偷》《改变电视频道便改变新娘的决定》等录像装置作品,以及自2005年以来的水墨动画系列录像作品。




博而励画廊陈劭雄个展现场

陈劭雄 《信则有》 2009-2015 照片 30X23cmX8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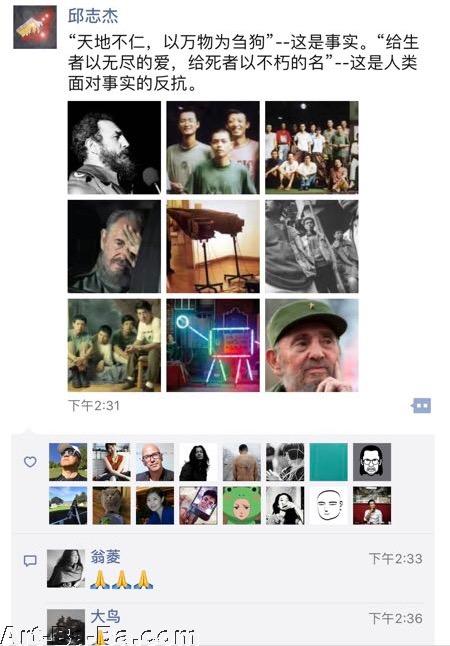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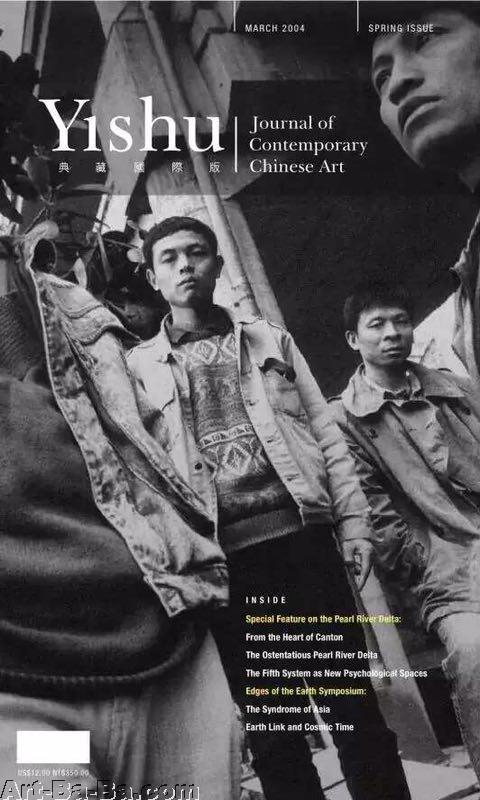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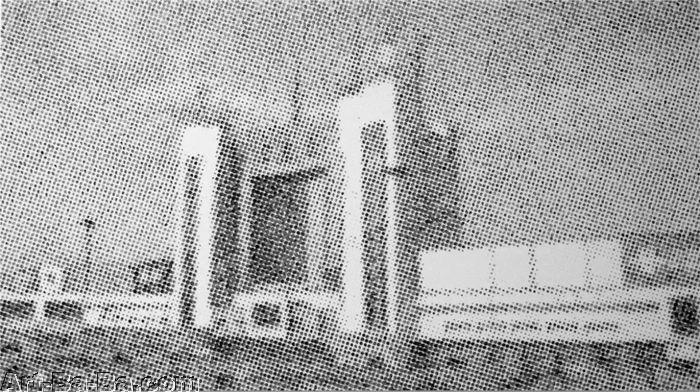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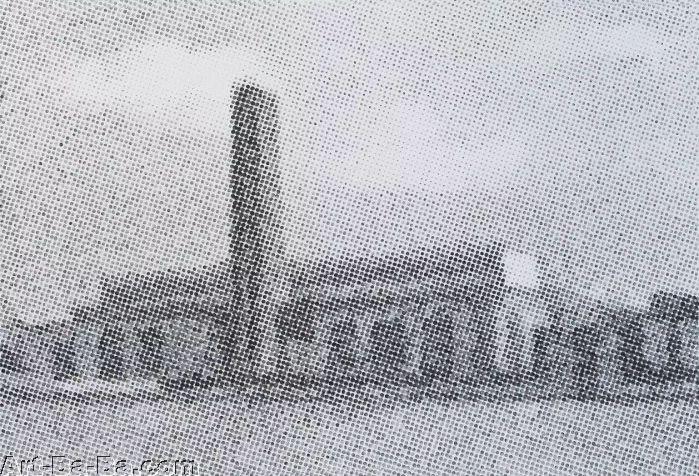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众友回忆送行
2016年11月26日上午10点,艺术圈传来著名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尾象”成员陈劭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的噩耗后(享年54岁),立刻引起其好友及艺术人士们的沉痛哀悼。为了缅怀陈劭雄先生,定于28日下午三点至五点,曾与陈劭雄一同走过艺术之路的爱人罗庆珉,陪同纷纷到场的亲朋好友,彼此追忆陈劭雄给大家留下的美好生活回忆和艺术的无尽反思。

▲ 陈劭雄追思会海报
11月28日,录像局、“大尾象”成员及陈劭雄好友,在征得艺术家陈劭雄爱人罗庆珉女士的同意后,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共同筹办了“陈劭雄追思会”,为追思陈劭雄的亲朋好友们凝聚出一颗共同悼念并难舍难忘的心。有近100位好友出席了当天的追思会,不论大家是怀着怎样一种沉痛惋惜的心情,毋庸置疑地是他们都留恋那份与陈劭雄一起经历生活和艺术创作、思考的岁月,甚至是陈劭雄对年轻一代艺术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和成长鼓励。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陈劭雄追思会”准时以陈劭雄的挚友侯瀚如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副馆长尤洋的主持发言开始,尤洋回忆到,他作为晚辈在前两年经常与陈劭雄老师相聚在一起,健身、谈论艺术。同时他也代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表示,在此除了一同思念陈劭雄先生,今后UCCA也会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去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和使命。尤洋也相信陈劭雄先生的精神能激励着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继续前行,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去珍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在鉴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支持,陈劭雄的挚友侯瀚如也感慨能有这样的机会让所有的好友与陈劭雄相聚,但遗憾的是此时并不是为了庆祝一件事情,而是为了怀念一位好友。在追思会中,大家都称陈劭雄为“劭雄”或“兄弟”,这种至深的感情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给这些好友带来了终身的快乐。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陈劭雄“快乐”的性格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活力和幽默感,这在今天的艺术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特别难得的一种素质。一方面,这是一种非常有批判性和社会意义的工作;另一方面,这又能够从快乐和愉悦当中获得对这种批判更加深入的一种认识,这是陈劭雄的作品所留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同时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参与到实验艺术、前卫艺术的工作中,是一位从业于当代艺术三十年左右时间的见证者和践行者。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陈劭雄爱人罗庆珉:
这几天,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一起追思陈劭雄。作为他的太太,我跟他一起共同面对:从他生病到他离去将近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在他旁边看到他面对生病时的那种态度,然后他又如何跟疾病对抗,我真的很佩服。如果换做是我,我肯定会放弃掉,但是用你们常用的一句话来形容:“他真的很爷们儿,太爷们儿了。”我只能在旁边协助他,也没办法去帮他解脱,所以我现在也很混乱,非常混乱。在这里我真的很感谢大家,特别是他在生病的时间里,每位朋友对他所作出的关心,我再次感谢大家。我接下来的工作会帮陈劭雄整理他的文章和他的资料、手稿,如果大家手里有陈劭雄的文字、图片等资料,我希望大家能提供给我,谢谢大家。
(由于“陈劭雄追思会”现场发言的内容比较多,“凤凰艺术”节选了部分好友的回忆内容,请见谅)


▲ 图片转自艺术家邱志杰
陈劭雄永远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艺术家,尽管他今天在身体上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在灵魂上还是在不断地给予我们去发掘今天和未来世界憧憬的新的可能性。他也是一位非常敢于去面对世界的艺术家。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国和世界的艺术进行一种非常抽象的比较和联系,而是通过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参与来改变这种关系,特别是他在后来近十年的关于“西京人”的工作,他和一位韩国艺术家、一位日本艺术家建立“西京人”这样一个长期的合作。
这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启示,就是他通过非常个人一种合作去面对一种非常宏大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面对的是超越艺术家个人创作的束缚,而进入一种集体合作的新的天地里。所以陈劭雄不只是在多媒体的语言里有一种创新,而且他在对“艺术的定义范围”里给予我们一种开拓,陈劭雄确实是一位世界性的艺术家。
在1986年夏天,我们准备做沙龙实验展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广州的大街上飞奔,那个时候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车辆,可以骑得很快。到了90年代一起做“大尾象”小组的时候,广州很少人理比较短的头发,然后陈劭雄理的头发就已经接近光头了,所以当时广州的警察看到后会以为他是犯人,以至于我们经常骑着自行车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非常尴尬,当然拦的不是我,是陈劭雄。有一次我们和北京的朋友坐出租车被特警查车,结果被特警拿着枪顶着背后查身份证。我觉得他现在到了一个好的地方,上了天堂,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查他的身份证了,或者说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用这身份证。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陈劭雄不仅是我们的战友,而且是我的老同学,我在广州美术学院时比他高一届。在我们刚刚做同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是一个很锐智,反应非常敏锐、快捷的人,有时候他讲话也特别幽默。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囧的事情,都会想到陈劭雄在就好了,因为他很快就可以化解掉这一些,这样的故事非常多。总的来说,陈劭雄在艺术上的思维非常耐人寻味,但他的人又很清澈透明,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艺术家里非常少有的。
当时读美院的时候,我到劭雄的宿舍看到墙上有一张铅笔画,大概有对开那么大,画的是海滩上有一些裸体女人,带着一点点变形,一点怪诞的意味,所以当时在美术学院我们都觉得这一种表现是很出格,很勇敢的,那是我对陈劭雄的第一次印象。直到1990年~1991年左右,大尾象第一次做展览的时候,我重新见到了他们,除了陈劭雄,像林一林、梁钜辉都没见过,他们像电影最后一个镜头的样子走进学院的大门。从那以后,我跟他们的来往就越来越多,这些年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也不住在同一个地方,我回顾90年代我觉得是我们非常美好的年代,我们一起在外面吃大排挡,聊作品,甚至帮着一起做作品。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今天我们坐在这都很沉重,其实刚才林一林也说,劭雄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怎么都快乐不起来,杨振中做过很重要的一件作品:他拍摄每个人说一句话“我会死的”,但是此时这不是自己说,而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真的离开你了,我觉得带来的都是一种沉痛和思念。我跟劭雄不是同学也不是同乡,我跟他最早认识大概在90年代初,我知道陈劭雄这个名字是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了他的作品,那个时候录像的作品很少,他做了一个“翘翘板”,而我刚好也做了一个“翘翘板”,我看到这个作品后,很惊!我觉得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冥冥当中觉得好像我们两个人是可以聊天的。后来不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展览,就认识了,应该是1996年在杭州的那次展览,应该那是第一次。然后真的很奇怪,我们就是一见如故的感觉,大家好像都没有距离感。他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
在最后的时间我们看过他几次,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很难想象,放在我身上会怎么样?但是我每次去看他之前我们都有很多担心,考虑该说什么?是安慰他还是怎么样?但是好像每次见到他都不需要,因为他很淡定,反而他都主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每次都是很沉重的进去,然后很轻松的回来。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不管陈劭雄带给大家多少快乐,此刻我的心情还是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悲伤。在得知劭雄这一消息的几日内,我在朋友圈推过两张照片,一张是1996年我们在杭州第一次做影像展,后来我又翻我的影集看我跟劭雄经历过的,一些做展览的一些照片。后来我又早朋友圈推了一张照片,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我们和培力一起去看劭雄,也巧合一算时间整整二十年:1996年到今天2016年。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机缘,这二十年我们一开始作为同行,然后到了特别好的朋友。
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我现在耳朵里一直记着劭雄的笑声,穿透力特别强——得了点便宜就会大乐。那种感觉一直让我难忘,我希望劭雄一路走好。
我刚才一直在看墙上他的照片,会让我想起来跟他在一起参加展览,出去玩的画面,有时候我们几家人一起去云南玩。记忆当中有很多欢乐的事情。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96年杭州展览的时候,从我的角度他应该算是老师辈的人了,但是他特别好玩,我们在杭州一起布展的时候,他总是跟所有人斗嘴,特别机智幽默,这么好玩的一个艺术家离开我们了,我觉得特别遗憾。

▲ 陈劭雄追思会现场
今天来的都是劭雄的好朋友,也是艺术圈的兄弟,我认识劭雄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年,自从他病了做了手术以后,有一天我跟颜磊、林一林说劭雄病了,我们想看看他请他出来一起吃顿饭,原来想象他病了应该是很严重的,结果那天见到他,他是坐轮椅来的,这是我很意外的一件事。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他一直很轻松,精神也特别好,照样谈笑风生,我觉得这是他很坚强的一面。上一次我们见到他是在他上个展览开幕式之前,去看了他,顺便也谈谈上海的展览和北京个展的一些事,结果这次看到他的时候和两年前又完全不一样了,他完全是躺在病床上,不能行动了,当然精神照样很好,我们谈了十几分钟,照样充满了活力。但是讲了十几分钟他就已经不行了,浑身发抖出冷汗,马上打吗啡维持他的疼痛。但是确实这十几分钟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讲的很清楚了,交流的很好。所以我们能顺利地把这个展览做下来,包括上一个展览,他的夫人阿罗确实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劭雄也是在病的过程中一直通过视频解决问题,去调整他展览的状态,我觉得这太坚强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帮兄弟和朋友很难得的一种精神的表现。
我从最早认识陈劭雄的时候,是在早期他参加大尾象小组的时候,当时我发现,家庭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非常重要,后来他们就开始合作。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有一年夏天他们做的一个项目叫“夏令营”,就是家庭的这个因素在他的作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实我从得到陈劭雄去世这一消息后,闪电般地想了想,完全是一些和陈劭雄的碎片。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若干年前,我和劭雄也是在一种突然的情况下送走大尾象的第一个成员,今天我们又面对如此快的打击。但是我更多地想是什么让我一直在记住这个人?其实最开始我记得他有一个作品叫《视力校正器》。当时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我和培力有共同一种感觉,这个时候你突然觉得,有一个人跟你不相识的人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而且他已经付出了行动。这个对我当时不论是从作品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有很多启示。其实我觉得今天不是说在回忆过去,我觉得包括大尾象和陈劭雄本人的很多工作,我们今天可能要谈一谈现在:他仍然没有被完全打开的那一部分。比如说艺术家自制,比如说对城市空间突然的占领,我觉得这种实践可能仍然对今天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也包括我们面对社会政治这种不断变迁的情况。我觉得大尾象也好,陈劭雄本人也好,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就是行动。
我跟陈劭雄、朱加、海峰我们工作室在一起用了差不多五年,但是海峰经常也不在北京,加哥也忙于公务,主要的物业工作就是陈劭雄和我。所以在这几年的相处当中,我就不说他的艺术了,生活上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严谨,而且任何事都想到之前,陈劭雄永远是第一个在工作室的,无论做什么样的作品,非常认真,然后不但要管自己的作品,还要管大家的水、电、气,真的是认真的一个人。另外这一次生病以后,我们去医院看他,陈劭雄还是一贯的幽默,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去的人都很轻松。他会说你们这个用药,用了吗啡怎么还不止疼啊?说你用的药是什么药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幽默。所以我觉得陈劭雄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是一种快乐的、幽默的、机制的感觉,这种画面是永远是呈现在脑海里的。
我其实也是96年认识的陈劭雄,但是一见如故,可能因为我是闽南人,他是潮州人,两个都是瘦猴,然后幽默感的方式比较相似吧。后来他来北京经常住在我家里,来了北京之后,反倒交往没有那么多,可能因为他来到北京,我去了杭州,之前他在广州的时候来北京还经常住我家里,经常通宵的聊。回忆过去,回忆不完,他是永远都很乐观。我在想那天接到陈劭雄的消息,我想起泰戈尔的话,“给生者以无尽的爱,给死者以不朽的名”,我想更多的是他这一生有这么多的好哥们,我们怎么来帮助他把老婆、孩子的事情搞好,让我们的资源,包括学生参与进来,把陈劭雄这本书做好,还有遗作。我们让陈劭雄继续参加几十年的展览,这是我们哥们一场特别想做的事情。
我跟陈劭雄基本上是性格相反的两个人,他的脑子我觉得特别快,我特别佩服。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他们在广州玩牌,一张一张需要跟一张牌,你要想翻一张牌要押钱,看着不行的时候就别跟了,然后不跟就等于赢,这是他说的,所以我觉得特别逗。总之他经常说这种特别让人吃惊又特别准确的表达,对我来说,他一直挺生动的,因为前两天我摸他的身体还有弹性,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是很生动的形象。
其实我之前早有预感,但是听了消息以后还是觉得有点不能接受。这两天更多的是回忆起我和他在一起的一些细节,我们认识的时候比较早,在02年、03年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来往,后来我们在一个学校做过同事。来往比较多的时候是我来到北京后,他也住在我们的小区,很近。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也很感激的,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经常来我家,说一起喝酒、聊天,那个时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包括我家女儿吃饭不爱吃,他就说你女儿到底喜欢吃什么?他就喜欢吃烤鸡翅,突然有一天晚上10点多陈劭雄送来了刚烤好的鸡翅给我女儿。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其实特别细腻,虽然他平时看起来充满了各种对抗、挑战,其实他心里面有特别柔软的这一面,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这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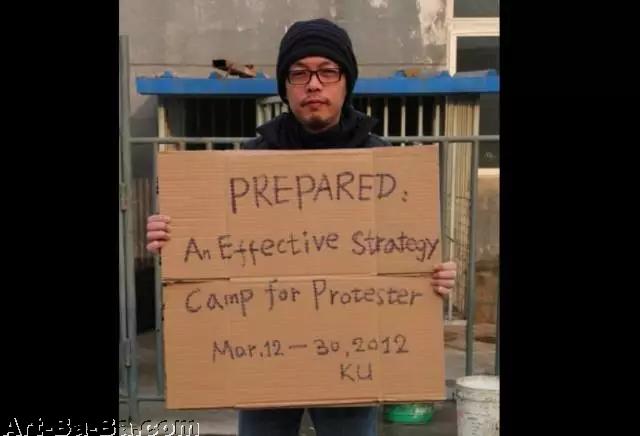


















▲ 图片由陈劭雄爱人罗庆珉女士提供
从北京,从外地,甚至从国外赶回来参加“陈劭雄追思会”的挚友们,都为了一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美好的回忆为他送行。我们也相信陈劭雄在天堂也会非常高兴,感到欣慰,仿佛他也永远活在每位朋友的心中。我们也希望陈劭雄对艺术所做出的贡献工作,以及他的人生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鼓励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