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 文:徐佳蕙
视觉之外,许多艺术家们的工作不再局限于,或满足于在视觉层面上的艺术实践,而是从其他感官的体验入手。基于此,本次专辑从人类的不同感官出发,旨在跳出传统的视觉艺术的范畴,探讨当代艺术在与科技的结合下产生的更多元的创作及体验方式。分别从听觉、嗅觉、触感以及全体感四个维度进行介绍,带来一场场“闭上眼睛”即可享受的艺术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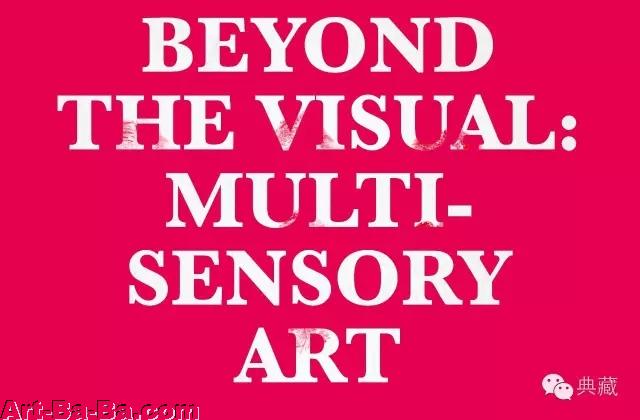
全感艺术:感知驰骋 官能幻境
18世纪,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Baumgarten,1714-1762)首次提出了“Aesthetics”,即美学这一专业术语,自此,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研究美的学科。
Aesthetics,源于希腊语,原意为对感受的感知,相比“美学”,“感知学”是更接近原词的译名。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美学不仅仅研究直观感受,艺术也并非单纯的感官刺激,不过这也提醒着我们艺术与感官感受的重要联系。
从古老的壁画、雕塑到新媒体时代的影像、装置,视觉在艺术领域几乎处于独尊地位,从“看”展览、“观”众这些表达便不难看出,视觉对艺术的权威统治已蔓延成为共识。但视觉能替代其他感官成为感知艺术的唯一渠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Chris Salter,《Haptic Field》,2016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感觉已被分为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可见感官感受历来的重要性,但也因感觉的复杂性和主观性,对感觉的研究始终伴随着争议与不确定。经验主义哲学曾把感觉提升到异常重要的地位,“知识来源于感觉”揭示出感觉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直接途径,颜色、形状、气味、触感等等构成着我们对物体的认识,感觉越全面细致,认识也相应地越正确。但我们看到的物体就是物体本身的样子吗?错觉并不少见,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相同事物的感觉可谓大相径庭,感觉的主观性与私密性必然使客观标准成为妄想。《庄子·秋水》中就曾提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不止是他者的感受,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到的他者是否是其本身都被打上了问号。
源于感觉的这种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身心二元论者倾向于把感觉贬斥为低等形态,肉体的、具体的感受和抽象的心灵思维站在了对立面。不过,随着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些感觉是通过各个感觉器官传输到中枢神经所产生的反应,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发展出的著名思想实验“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更是把感觉来源于神经刺激的理论推向极致(“缸中之脑”实验即把大脑从身体内取出,放置于维持生命的液体中与电脑相连,通过电脑向大脑传输、模拟各种感觉和场景,这种情况下还能否分辨真实与虚幻、是否有人愿意在这种条件下生存成为争议。)同时,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不同的感觉刺激导致不同的心理情感,不同视觉效果所激发的不同情感体验在艺术作品中早已有所表现,尤其以色彩心理学为典型。而在生活中,听觉引发的各异情感也尤为明显,鸟鸣令人心仪而噪音引发焦躁。

Chris Salter,《Haptic Field》,2016
目前,我们已经得知感觉与神经反应、心理反应相关,但各种精密仪器、心理学理论的介入并未解开感觉之谜,毕竟感觉无法与个体分离成为绝对客观的研究对象,每个人各异的身体条件和经历,致使我们仍旧像古希腊人一样,有着各种感觉却对感觉本身难以言说。
我们再回到艺术与感觉的关系,或许正是因为感觉的日常性、普遍性,很少有人把闻到花香、摸到硬墙壁这种事情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不过,像这种无法用科学理论言明、能引发各异心理情感且具有一定共通性的东西,还有比艺术更合适的表现方式吗?

Chris Salter,《Ilinx》,2014-2015
艺术研究对象和表现方式的持续拓展,加上前沿技术的跨界引入,视觉早已不是唯一的艺术欣赏途径,如今常见的影像作品就包含着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的共同作用。而视觉艺术(Visual Art)一词就已表明其他感官艺术的存在,听觉艺术、嗅觉艺术和触觉艺术都在发展,这些强调某一感官的艺术形式通常会创造出独特情境,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感官上,或是提供极端的感受体验,与日常感受相区别从而收获新的感悟与认识,而全感艺术则是多种感官艺术的集大成者。

Chris Salter,《Haptic Field》,2016
克里斯·萨尔特(Chris Salter)在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展示的最新作品《体感场》(Haptic Field)融合了触觉、听觉、视觉多重感官,打造出一方充盈神秘气息的净土。萨尔特作为蒙特利尔考迪亚大学新媒体、技术与感觉讲习研究员,对把多重感觉融入艺术作品情有独钟。《体感场》中,参与者首先要穿戴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输入设备与音乐互动实验室(IDMIL)研发的特殊装备——一种可无线震动、发光的装置,并带上将视觉模糊扭曲化的特制眼罩方可入场。进场时拉着墙壁上的一根细绳,沿着绳子的方向进入一片漆黑,而想离场时寻找墙壁上的细绳循绳而出即可。

Chris Salter,《Haptic Field》,2016
进入场内,由于特制眼罩的作用,视线一片模糊,隐约能在黑暗中看到点点闪烁的灯光,而在眼罩的处理下,仅留的视觉形象也被扭曲,灯光由正常的点状被模糊为团状,好似进入了高度近视者的世界。同时身上的设备不定时震动并发光,方才发现那些团状灯光应是其他观众,而全身多处同时震动的异常体验,则让人处在高度紧张和警惕中。放开绳子后,参与者摸索着进入场地各处,随着意大利艺术家兼音乐家特兹(TeZ)创作的气氛诡谲的音乐,在不断变化闪烁的光影中,空气、墙壁、其他观众都变成了重要的触觉来源,在如此朦胧混沌,甚至略带虚无性的场域中,参与者也只能依靠各种感觉以及提供这些感觉的他者确定自身。
如此极端异常的体验,无疑带来了复杂的心理感受,从进入黑暗的恐惧、震动与闪光引发的紧张,搞清状况后的放松与欣赏,直至离开时的沉思。多重感官体验混杂着情绪的频频变换,引发各异的联想与思考。这并非萨尔特首次在作品中调动多重感官,作品《JND》中,观众在黑暗空间中,通过传有低频震动和声音界面的频率变化,创造坠落及躺在不同质界面的感受。《Mediations of Sensation》则让体验者在特殊空间中穿越充斥红外温度与气味的黑暗隧道、品尝奇特液体等过程中保持知觉的敏感性。如今的感官人类学研究表明,各种感官可能并非独立作用而是相互影响,而在萨尔特的作品中这种弥合感异常明显。

Chris Salter,《Ilinx》,2014-2015
从《体感场》走出,科幻电影中的外太空、神秘不可测的海底世界、潜意识中温暖的子宫,这些都是观众体会到的不同的世界,但相同的是对自然的惊异好奇,以及对自身生活的反观。萨尔特在《交叉,替换与扭曲:惊异之感》中提到:“如果我们任想象驰骋,并设想感觉不仅有五种,那么我们的文化图景会成为什么样呢?”其实不用感官自身发展,技术的革新已经在不同程度延伸着自然感官,使人们的生活和艺术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不论怎样发展,带来奇特感受并引发思考是艺术文化的根本,而多重感官相结合的全感作品,无疑更擅长创造出迥异的空间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新奇并值得深思的。
图 |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
来源:典藏 文:李素超
专辑② | 触感艺术 :“触”摸世界“感”受艺术
在人类的五种感官中,“触感”(Haptic),即通过触碰(touch)、接触(contact)的方式对周遭环境的感应,可以说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感觉,绝大部分人全然没有意识到触感与触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英文术语“haptic”,源自希腊语“ἁπτικός”(haptikos)、动词“ἅπτεσθαι”(haptesthai),除了在该特定领域或工程实验等科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鲜少被提及和认知的概念。不过好在艺术领域,已经有艺术家及相关理论研究者意识到触觉作为最基本的生物特性,可以经由艺术表现被重新发掘,尤其在科技的辅佐下,以触觉为主导的互动式艺术项目及体验进一步延展了艺术的范畴,触感也成为一个创作的理念,一种构建内在自我意识的方式。

Stahl Stenslie的作品《The Blind Theater》(©Stahl Stenslie)
在探索“触感艺术”之前,有必要先对“触感”本身做一定的阐释,以期重新认识触感的本质,从而真正发现触感艺术在美学、心理学等多维度面向的独特之处。
由皮肤觉(cutaneous)、运动觉(kinesthetic),以及触觉系统形成的触感像空气般无所不在,也像空气般,状似不存在,却是所有生物存在的根本,而要透彻地了解它也绝非易事。有学者认为触感是最原始/原生(primordial)的感官,是一切感官之根本,并将所有感官体验归因于触碰(touch)的发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现代传播理论的奠基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在我们有意识的内在生命里,是我们所有感官的交互形成了触感”;芬兰著名建筑师及建筑理论家帕拉斯马(Juhani Pallasmaa)认为,正因为所有感觉器官都存在表皮,所以它们都与触觉相关,他说:“所有的感官,包括视觉,皆是触觉的延伸;它们都是表皮组织呈现出的特性,因此任何感官经验都具备触觉的形态,跟触感息息相关”。著名法国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早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提出了“知觉为先”的理论,把对触觉的讨论放在了身体作为一种“在世存有”的面向进行,身体在此被当作“与世界沟通的媒介”。触感远非大部分人眼中一种简单的行为或感觉,它实际上指向一种高阶的互动性、多样性(multiplicity)及互惠性(reciprocity)。

Stahl Stenslie的作品《The Blind Theater》(©Stahl Stenslie)
在人类出生之际,触感是我们的第一感觉,而且不同于视觉、听觉,它不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消逝,我们通过它使自己的身体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也发展出内在的自我,从本体论及现象学层面来看都是我们生存最重要的基石,然而触感却是一种难以描述的身体体验。如今电子工程学的发展增强了触感的能动性;最新的触感技术(haptic technology)使我们能够积极地感知到真实或虚拟的物体与环境的质感、重量和阻力,从而对其做出反应。通过触觉感应器及计算机仿真,使用者还能远程识别/操控/创造虚拟物体,这项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电脑游戏、网络购物、医疗、人机交互等诸多领域,也为艺术家们探索触感美学,创作以触感为导向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途径。
相较于占据绝对主流的视觉艺术,由触碰主导的艺术体验方式最显在的益处,莫过于给予失明和弱视者欣赏艺术的权能。它们常常结合了声音,以触碰和聆听的方式感受;比如英国声音艺术家James Bulley(1984-)曾专门针对失明和弱视者群体创作了一件作品《Tactus》。参与者通过触碰由纺织物编织成的音符来触发声音、谱写乐曲,每个音符都有其特定的声音模式,利用电容感应(capacitive sense)技术,使参与者在触碰到这些音符时,对应的声谱也随之而出。艺术家认为基于触感的作品给到了失明和弱视者群体最直观的艺术体验,该群体在触碰上的感知比我们更胜一筹,而这也往往被习惯依靠视觉的人们所忽略。
挪威艺术家Stahl Stenslie(1965-)的创作专注于实验性媒体艺术与交互体验,对我们惯常的看待/感知世界的方式发起挑战,唤起那些潜藏的内在知觉。在挪威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Oslo),他专攻触觉与科技(Touch and Technologies)领域并取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rsity)艺术与科技专业。Stenslie的研究及艺术实践多集中于虚拟触感、触感美学、触感享乐(Haptic Hedonism),结合运用可穿戴设备、触觉感应器等技术媒材,创造由虚拟触感所引发包含美学层面的、私密的,甚至有时带有性快感的身体体验。

Stahl Stenslie的作品《The Blind Theater》(©Stahl Stenslie)
《盲人剧场》(The Blind Theater)是Stenslie始创于2009年的一个艺术表演项目,首场在挪威当代戏剧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于挪威国家剧院(Norwegian National Theater)上演,参与者在黑暗的剧场里游走,身体在此成为这出剧目的舞台。作品将身体作为中心,探索有关身为女性的五种不同身体感官经验,五位艺术家——Shiva Falahi、Edy Poppy、Narve Hovdenakk、Veronika Bökelmann,与Kate Pendry因此受邀写下各自关于女性身份的内在的故事。
在进入剧场时,参与者被蒙上眼,穿上一件由电脑控制的电子穿戴外衣,这身外衣成为参与者全新的皮肤,它将有关女性身体的那五个故事“输送”至参与者的身体,通过触碰及双声道立体环绕声,将体验者带入故事的核心,让这个过程变为一场真实的、私密的演出,这些故事也似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参与者的身上。经由该作品,艺术家提出一个全新的剧场概念,其中参与者也是表演者,同时为失明者和未失明的人共同创造一场愉悦感官的、民主的剧场体验,在视觉主导的文化下,开启了一个为失明和弱视者观众开放的剧场。

Stahl Stenslie的作品《The Ichihara Touch Tales》(©Stahl Stenslie)
通过触感与声音的结合进行身体和心理的感知是体验Stenslie的作品重要的方式。他的另一个艺术项目《可触的市原传说》(The Ichihara Touch Tales,2014)向参与者诉说来自日本位于东京湾旁的市原市(Ichihara)的故事及神话;该市结合了城市、乡村及工业区,呈现出多元的日本社会面貌,围绕东京湾的海岸线布满工业时期残存的大量化工厂,从岸边乘坐电车前往市原市中心,沿途会经过平静安详的郊区、高尔夫球场,深入茂盛而神秘的竹林;这段70分钟的旅程恍若隔世,似一场精神之旅。
这种体验及市原地区富饶的生态,经由该作品被艺术家复制出来呈现给观众——作品主体是一件根据市原地形裁切的触觉感应桌子,上面的每一块感应区域(touchzone)对应一则日本神话故事,或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故事,又或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传说,亦或是这些故事的混合体,参与者通过触碰这些感应区,触发萦绕在该区域范围的声音,开启一场体感式(somatosensory)市原之旅。

Stahl Stenslie的作品《The Ichihara Touch Tales》(©Stahl Stenslie)
Stenslie的艺术实践不止于此,他对于触感的探索在对该技术深度的研究下,使之更多地指向艺术表现及感官美学。在触感艺术中,身体/皮肤既是媒介,也是观看/感知的“眼睛”,被削弱的视觉于此让位给其他感官,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遭受挑战,触感变得敏锐,被我们忽略的潜藏的意识与自我图像逐渐显现,由此唤起身体及心灵的“共情”,应是创作最终的方向。
图 | 艺术家官网
来源:典藏 文:李素超
专辑③ | 声音艺术:声韵艺韵 音波无界
当声源振动引起声波,通过空气传播至耳朵,经由内耳的环能作用使声波转变为听觉神经上的神经冲动,再传送到大脑皮层听觉中枢而产生主观感觉,听觉即由此产生。感受声音、辨别声音是其基本特性,也是除视觉功能外,被认为最具主导型的生物功能、最重要的感觉通道。现今,该领域已建立起广泛的研究与理论体系,从物理学、生物学、神经学上对声学特性、听觉机制、频率学说等的研究到心理学、哲学及美学上对听觉文化的探讨,对我们进一步感知/理解以听觉为主导,以声音为媒介的艺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底。

杨嘉辉,《室乐》,特定场域声音装置、音乐记谱,尺寸视场地决定(图片提供:艺术家)
声音艺术的范畴
听觉艺术(Auditory Arts)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本质上以听觉目的为创作重点的作品,主要表现为音乐;而诗歌,即语言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基于听觉的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上世纪90年代末,新的名词——“声音艺术”(Sound Art)的出现,在更广的层面诠释了当代的听觉艺术;它常常是对古典音乐、诗歌及视觉艺术的颠覆与延展,没有明确的定义,包含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是声音装置、声音雕塑、表演艺术、声音景观(Soundscape Composition)、声音行走、田野录音、电路扰动(Circuit Bending)、声音设计、互动声游戏(Interactive Sonic Games)、图案有形诗(Concrete Poetry)以及以音频媒材创作,以聆听为方式的实验性艺术项目。
正因为声音艺术的内涵如此之广,在创作的过程中,包括许多的艺术运动和实践者,都对其有不同的阐释。有人极力将声音艺术与音乐区隔开来,甚至强调二者的对立关系,而有人则把声音艺术看作是音乐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代音乐/声音艺术领域的先驱纽豪斯(Max Neuhaus,1939-2009)曾指出:“上世纪伊始,为了回应音乐界的保守势力,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èse)提出将所有有组织的声音都纳入音乐的范畴,以拓展音乐的边界。约翰·凯奇(John Cage)则进一步将‘无声’也归为音乐的一部分。而今天,即使处于谨慎的‘永恒的莫扎特时代’的余韵当中,我们也无法再对那些新型的音乐假装视若无睹,并把他们排除在音乐范畴之外。如果说,对文化事物进行分类和命名确有其缘由的话,那么就是为了对事物间的差异加以提纯。审美体验的目的则是深入体会这些差异的精妙之处,而不是以不同事物的公因子去拆解差异。就声音艺术而言,不同类型音乐的最小公约数就是‘声音’。”另一位当代著名作曲家劳克伍德(Annea Lockwood,1939-)则写道:“对我而言,音乐和声音艺术是非常不同的。这两者在观念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看来,能够被称为‘声音艺术’的作品与语言学无关,毕竟,所有形式的表演性音乐作品都是一种语言。随着人们对约翰·凯奇的创作理念和声音世界了解的深入,他的反语言作品也成为了一种语言。又或许,‘声音艺术’一词不过是博物馆策展人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而创造的,用来说明艺术界将声音接纳进来的新情况。”

杨嘉辉,《室乐》,特定场域声音装置、音乐记谱,尺寸视场地决定(图片提供:艺术家)
无论如何,听觉的艺术是个开放的概念,它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诗歌,可以是激浪派(Fluxus)艺术家约翰·凯奇及其追随者们的实验音乐,可以是源自达达主义的噪声艺术,也可以是在“后约翰凯奇”的当代,结合了视觉图像/功能的声音雕塑,或是以空间为基准的装置性的声音场域,或者任何以聆听(listening)为体验过程的作品。总之,其共通之处在于从听觉出发,始终把声音(sound)视为艺术领域里一项独立的、自主的媒介,并对声音文化、声音美学,以及声音技术做持续的、深入的探究与拓展。
声音艺术的当代“灵光”
当下的声音艺术,已从音乐(包括实验音乐、噪音)的范畴解放出来,被放进宏观的时空与文化语境中考量。当我们回头再看中国清代利用声学原理建成的天坛回音壁,何尝又不是一件堪称经典的声音装置!在欧洲,早在中世纪时教堂为圣歌而布置的一系列发声器材,同样也是件绝妙的声音作品。而今技术的发展为声音艺术实践带来了爆发式增长,也极大改变和多元化了声音艺术的创作/展示方式,声音艺术得以再度闪现“灵光”。
2013年,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开办了其首个完整的声音艺术展——“声音:当代记录”(Soundings: A Contemporary Score),展览几乎全面地囊括了迄今为止当代声音艺术领域的创作实践:艺术家维泰洛(Stephen Vitiello)录下的钟声、纽约人帕里奇(Tristan Perich)用1500个小扬声器制作的作品、格拉斯哥的菲利普兹(Susan Philipsz)重新编配演奏1943年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为被关押的音乐家创作的一段交响乐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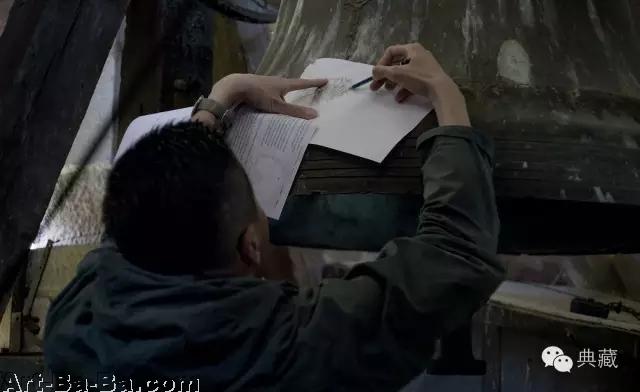
杨嘉辉《丧钟为谁而鸣:冲突的音频史之旅》(图片来源:www.wallpaper.com/)
来自香港的作曲家,声音艺术家,媒介艺术家杨嘉辉(Samson Young,1979-)在2007年因其视听项目《最幸福的一小时》成为首个来自香港获得彭博新兴艺术家奖的艺术家,更因2015年赢得第一届巴塞尔艺术展-宝马艺术之旅大奖(Art Basel- BMW Art Journey Awards)而名声大噪。2017年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杨嘉辉还将代表香港参展。他仍在进行的项目《丧钟为谁而鸣:冲突的音频史之旅》(2015-)是他赢得巴塞尔宝马艺术大奖后踏上跨越五大洲多个城市的旅程而开始的创作,记录下一路上各种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钟声,专注于这些钟声及其作为和平与冲突的象征地位。2013年,他受上海西岸双年展上的“中国声音艺术大展”(Sound Art China)之邀,在一个大油罐中特别制作了一件特定场域的声音即兴装置《室乐》(Chamber Music: Homage to John Cage & Mortan Feldman’s Radio Happenings)。作品基于古典乐里对四重奏的想象,通过数组细小的物件组成的装置以及弱音源和光线的变化来阐释四重奏中的句式结构,为声音本身增加了“亲密”“隐私”“形式主义”“物质性的纯粹”“平等参与”等理想化的想象空间;通过科技手法对这多种音源发出的声音进行重组,它们绕着墙体反射,并在空间中被不断延伸和扭曲,编织成一道声音的网络,在声音、空间和参与者之间构筑起一场私密的对话。
艺术家在古典音乐、电子音乐及媒体技术上的造诣,使得声音(艺术)在当代发展出其特有的“灵光”;正如杨嘉辉提及的:“即使声音艺术的定义持续缺席,它作为一种艺术系统与论述的语言,今天已发展出一系列毫不含糊、有力量又甚具当代性的故事和主题。聆听是如此熟悉的感官体验,声音作为创作的媒材面貌却又如此模糊,这反差正是声音艺术的迷人之处。”
来源:典藏 文:张亚庆
专辑④ | 嗅觉艺术:呼出自我 吸入万物
“我爱一切气味。香味让人身心愉悦,臭气使人敬而远之,气味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但人们对它却知之甚少。”
——西塞尔·道拉斯
当我们在地球上呼吸着第一口空气的时候,我们的鼻子就迈开了嗅觉工作的第一步。人类在每天的生活里平均需要呼吸23040次,随着每一次呼吸,甚至是酣然入梦之时,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也会在我们体内流淌,它包围着我们,进入我们,最终再散去。而在这种一呼一吸之间,渗入身体里的抽象分子,拉进了我们与现实的距离。它唤醒我们的欲望,触动我们的记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甚至构建我们未来的方向,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感知世界的新方式。那么,与我们有着如此亲密的嗅觉感官,我们真的理解过它吗?可能在生物学的领域,它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艺术领域,它着实沉寂了很久。

西塞尔·道拉斯作品《自我的肖像》现场(图片提供:M21)
嗅觉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艺术?这可能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不得不提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写于1986年的小说《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轰动文坛,书中讲述了法国嗅觉天才格雷诺耶为了收集世间“最完美的气味”,而不惜杀害少女提炼她们的体香,制成迷人香水的传奇故事。
当小说《香水》被确定制作成电影的时候,很多《香水》的书迷一度质疑:如何在一个视觉屏幕上表现出书中给予人们的那种带有抽象神秘的味道呢?最终《香水》的导演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还是做到了,他的选择是“用意象、声响和音乐的力量,营造出气味的氛围”。于是,小说和2006年上映的同名电影一时间掀起了一阵“香水热”,同时也将“香水的意义”捧上了一个神秘至上的高度,而“气味”这个抽象的概念也随之在大众流行文化和学术界传播开。

“嗅觉艺术:1889-2012(the Art of Scent:1889-2012)”现场(图片来源:madperfumista.com)
那么,作为“气味”里最为美妙的一道,香水可以定义为一种艺术吗?2012年,纽约艺术与设计博物馆(MAD)里展出的“嗅觉艺术:1889-2012(the Art of Scent:1889-2012)”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也是第一次名义上在博物馆级别的展厅中展出气味艺术作品。展览中,观众可以顺沿着一条长长的完美的弧形墙体前进,同时可以随意享受来自设计在廊壁上半弧形小洞里散发出的熟悉的气味。在这过程中,一切气味无关任何香水的品牌包装、标签、注解等等信息,但它们成为了这场展览的主导。
如何“读”嗅觉艺术?
我们该如何“读”气味艺术?是否看一件气味艺术的作品,就如同皇帝的新衣?如果不是,我们又该怎么证明它的存在,或美妙呢?难道答案只是“好闻”“不好闻”,或者“闻起来好像……”?的确,气味是无形的,抽象的。但是,它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它能够唤起人们情感、记忆,和各种主观及文化上的联想。特定的气味可以吸引我们,也可以令人厌恶。当气味环绕于我们周身,微小的气味分子经由鼻腔渗入体内,这种熟悉的气味可以将人们带回某一个记忆中的时刻:年少时母亲做的饭菜,在学校操场奔跑时流的汗水,热恋时爱人的气息……

西塞尔·道拉斯作品《自我的肖像》现场(图片提供:M21)
挪威气味艺术家西塞尔·道拉斯(Sissel Tolaas)甚至还编造了一部气味辞典——《NASALO》,试图找到一种学习味道的方法,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味概念变成可以分析、研究的量体。虽然这些词汇都是经由艺术家自己编造,但并非随意而为。如果一种气味被贴上了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这种气味的主观感知,因此气味辞典里的词汇是偏想象的。但是,纯粹的“气味”不能形成艺术,它只是刺激感官的一个环节。“气味”若要成为一种艺术,必须依赖于其他学科的辅助,比如说科技。在道拉斯《香味杂志》的作品中,没有文字、没有图片,只有12页“印”有不同气味的纸张。艺术家就是使用了一种叫“微包装”的技术(一种可以将每个分子分别包入微小胶囊中的纳米技术),使得读者只要用手轻轻摩擦纸张,就能闻到12种特殊气味。
出生在挪威的这位气味艺术家道拉斯是一位职业多面手,她有化学与艺术两方面的专业背景。生活中,她几乎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格雷诺耶”。从90年代起,她“开始了像狗一样工作”,搜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气味,包括衣服、奶酪、狗屎、灰尘、街边的垃圾、下雨后的泥土……在道拉斯位于柏林的气味档案馆里,存放着世界上超过7000种气味,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每一个放置在档案库里的气味,被艺术家通过蒸馏提取的方式密存起来,每一个封存的气味用相应的代码标记完好,同时注明相应的时间和事件过程,以此证明它们存在的意义。她甚至能清晰的告诉别人,在法国的蒙彼利埃街头一位路人的牛仔外套上,有17%汗、15%的猫、25%的万宝路烟、5%的龟甲万酱油,以及咖啡、口香糖、狗、清洁、煤油的气味。
道拉斯无时不刻都在用气味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把‘气味’这种无形的东西具体化,通过文字记录、科学分析和艺术展览,改变人们对它的浅薄认识。”不仅如此,她还尝试通过气味传达人类之间的情感体验和共鸣。2006年,道拉斯曾在全球各地举办“体味的畏惧”展览,她通过采集20个不同男人在各种畏惧之下产生的汗分子信息,经过纳米技术处理成微胶囊包裹的汗味融合在绘制白墙的透明涂料中,观看作品的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墙壁的方式来感受处在不同恐惧下的味道。而在上海民生二十一美术馆开馆展中展出的《自我肖像》,艺术家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自身与观者之间的交流。

西塞尔·道拉斯在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展览中展出的互动装置作品《上海嗅觉地图》(图片提供:西岸艺术中心)
大约在1998年,道拉斯除了展开对人类自身交流的研究,她还把目光移向人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当中,在各大城市里开始了“城市味景”的项目,其中包括巴黎、底特律、柏林、开普敦、伊斯坦布尔、广东、上海等。她希望通过气味重新发现城市的隐藏特质,对于道拉斯而言,气味意味着一切信息,它能告诉自己每一个城市发生着的不一样的故事。但是气味是复杂的,又一直处于不停变化的状态中。所有研究气味艺术的艺术家们也深知,希冀用气味穷尽宇宙的奥妙,只怕还是未知数。就连道拉斯也承认,“我也不知道我的气味档案馆在未来能有什么作用,但是它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基础,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只要我还在呼吸,这个旅程就将没有终点。”
也许,这也是嗅觉艺术未来之路的思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