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引]本文基于德里达对康德-谢林-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大学理念的解构,所以对这个“德国大学理念”的解构看上去才这么势如破竹。写的时候我自己是感到越来越深的无能和挫败感。这是用我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印证伟大前辈的远见。弄明白,已太迟:我想做知识分子和学术分子,但显然此路不通,或者说,人进来了,但根本与一个民工背着蛇皮袋进城没两样,绝望与希望搅在一起,什么都还不好说。
本文将从讨论大学排名的罪恶开始,来指出今天的大学已被鹰占凤巢,应用-实证的技术学科抢占了大学核心,我们所追随的康德理念下的大学已流亡到了大学之外。既然我们所呆的大学已得了尿毒症,那我们大学人如何自救?结尾处,本文提出两种安慰式出路,一是社会学家布迪厄说的大学人的“马奈的位置”,一个天天自我刷新的知识-学术研究人位置,天天写或画,永远做“今天”的英雄,为它献身。二是哲学家斯蒂格勒提出的对大学的药理性的主动使用,同时将这个有毒的大学当毒品和解药,正面地去迎接新的工业经济代谢和新的数码-算法国家的重建,将今天的大学问题看作是三代人如何重新一起学习,如何将小学、中学和大学一起搞的事情。但愿大家读后不会悲观。
上、对大学排名的控诉
康德在《系科的冲突》这个小册子里最早提出“大学的外围”这个说法。它指的是处于大学议会的哲学系科[1]和三大权利执行学科之外的应用科学、工业技术性学科。康德认为,它们应该作为大学的“外围”存在,才是合适的,如进入大学之内,就会扰乱哲学、大学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宪政互防之民主结构。各种技术或应用性科学应放在大学外围搭出的帐篷内,围着大学,作为“爱好者协会”,或作为各种“科协”存在,才是合适的,否则就会鹰占凤巢。大学的外围霸占了大学的内部之后,大学就会像白蚁那样吞食掉大学的核心,成为资本利用国家权力的盘剥工具,殃祸人民。
可以说,康德的担心真的在2016年的世界大学系统里成了现实!不光只有在中国!真的就是鹰占凤巢,大学被挤出了大学之外!大学成为资本力量动用国家权力压迫人民的工具的同时,那个大学的“核心”已无家可归,流落在外多年了!哪怕大学里那些自认为最风光的人,也不能幸免!全球大学排名是这种鹰占凤巢的必然结果:照各应用、技术学科的评估标准来评估大学内的所有学科。它甚至要给全世界的哲学系科来排名了,用分数!外围霸占了内部,核心也已沦陷。
这样一些爱好者协会或科协围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在这一点上,康德与谢林的看法有分岐。康德认为,哲学、大学和国家三者之间互防,构成“民主”,哲学应该在大学里永远当反对派,使大学成为不列颠下议院,通过系科之间的斗争,来使这种国家能够“民主”得比较健康。哲学系科领导各“数理科学”和“历史性科学”与大学“内”的知识-权力执行学科如神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天天你死我活地斗争,才能形成大学内的“民主”,这民主才能为国家内的民主作出示范,使后者不会太走歪。
而谢林则认为大学不应单设哲学系,反而应该将整个大学办成哲学系,大学生进校后的前两年,就只是研习哲学和写诗(是宏观上讲的哲学和诗),用这两者来讨论重大问题,校长应该从一、二年级的学生中选出。所有的大学教师都是事实上的哲学教师,处在不同学科,但都是在哲学地教、必须教得足够“哲学”。
照这个蔡元培想要引进的“德国大学理念”(今天应该理解成康德-谢林-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德里达眼中的大学系统),建筑系和土木系、商学院、环境学院等等,都应该放到大学的外围,作为某个科协或某个爱好者协会存在,才是对它自己、对大学和对国家最合适的。比如伦敦的AA就是一个著名的培养建筑师的大学“外围”。而一个建筑系被“综合”在一个大学里,哪怕很得势,也是可悲得很。不去好好办协会,吸引真正的爱好者来献身,最后肯定也是办得一地鸡毛,弄出一大堆名头大得吓人却狗屁不通的官僚学者来,“大学”这种吓人的名头常常就这样地将人人害得不浅。同时这也会搞乱大学,使它被鸡占凤巢,建筑系哪怕呆在里面再是风光,也仍是一样地被王宝强了,排名再是高,也仍是处身黑砖窑,肯定也是最迟悔悟过来的。
照康德对这个universitas的原初设计(architectonic),大学只是一个新知识的议会,是一本国家-本体-知识-百科全书,大学图书馆是其某一种表现形态,由大学师生来激活它,后者是其各个方面的知识保管员,负责不断给这一国家-本体-百科全书升级,从VCD升到DVD,再升到马上要到来的生物芯片之中。后来,海德格尔认为他的作为师生劳动-论争-战斗共同体的讨论班,就代表了大学,就代表了国家,就代表了人民议会内的论争,其小教室内的论争和战斗,就是在全体人民面前演示、保持和捍卫某种民族精神的火苗了。黑格尔认为他的那本《精》才是真正用得着上的大学,大学必须是这样由我们自找、自设、自办的。大学必须每一个人自办、自进,没有一个开着门的大学等着我们进去的!德里达说,国际排名下的鹰占凤巢后的大学已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它自己“之外”了。它作为自身的幽灵存在着了。我们原来以为的大学今天已妖魔附身。
所以,对于我这个普通教员,大学在今天已成了敌战区,我只能孤身野魂地与之周旋了。因为我反对排名,所以我还是大学排名的拆台者,我的劳动(比如我此时在你面前写的这些)因此不但没有帮助大学提高排名,反而是在降低它,所以,我说不定是目前的这种校长们所谓的大学的敌人了。而我在这里说,只是企图打回老家去,要从他们手里夺回地盘,早就没有胜算了。
对于大学的排名,我的看法是,在那个康德-谢林-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式的大学理念下,一个民族国家应该只有一所大学,就像它只能有一个议会。这还用说!按照上面说的这种德国大学理念,一国只有一所大学,镇里办一所,也属于那一所的;因为,国家就是大学。我们还是人民的国家呢,所以更是了!那么,如果只有一所,还怎么个排名法?像教育部搞的这种内部排名,是在分裂国家!在现有的专制-官僚统治下,大学被它给了不同的经费,被允许或不允许、谁先办谁后办某些专业,等于在预算时就根据排名来拔款了,那你还要再在国内另外搞出个排名来干啥,你反正都已排好了?证明你钱给得多的地方终于也排在前面,虽然它们一开始就是排在前面、最先在搞的?
每一个公民都有对哲学、大学、国家的权利,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替任何人筛选,去决定给谁而不给谁,给这而不给那。高考入学筛选,就已是对人民的这种“对哲学的权利”的出卖,是对国家权利的分赃不公。到哪里去上学,上什么学,都是人民在行使他们自己的“对哲学的权利”。[2]每一个人的对哲学的权利:国家、大学和哲学三者是在一个同心结构里,任何一个公民去上大学就是在上国家,就是在上哲学,就是去搞民主,这是德里达上世纪80年代对于德国大学理念的重要的解构成果(参见他的《对哲学的权利》一书)。排名是在离间、破坏这种同心结构。排名后的公立大学就像被当作洗脚屋里供客人挑选的不同价位的妹子了不是吗?
对于排名,我还有另一点是不吐不快的!在现有的排名下,我觉得我的个人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被低估了,本来我也不在乎,但在现有的排名系统里,我对排名的贡献等于是有负于我所服务的机构了,像欠了它的债,常被责备,被勒令要为之做贡献,这就让我有点急了。可我又认为,我自己已经是全身投入到自己的研究和教育的,其实也已全力贡献了,实在拿不出另外的小把戏再来为排名做贡献了。同时,在现有系统里,我的很多劳动和全部献身可能是无法被算进表格的;我哪怕献身了,他们也会说我献错了,不能算。不长期潜伏在里面,不混进著名实验室,不去著名杂志发表,参加他们的学术话语-权力分配游戏,我的劳动就永远无法被算在里面,打折也不行。这是最让我难受的地方,虽然当个学术民工,我其实也是很乐意,一直快乐地在当着的。
这听上去像是我的一面之辞,我想摊开这一点,来自辩,从下面这些问题入手:什么是我的贡献或韦伯说的我那“智性上的献身”?如何评估和折算它?为什么只有某些劳动是可以被选作排名参数的?为什么我的献身对于想要排名的大学来说似乎是献错了?献身还有好坏、高低和多少的吗?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努力做一个知识分子和学术工作者,其实最后与任何人一样,也掉进了一种严苛的劳动分工之中,路越走越窄,其实到最后也就没有办法,只好献身其中了。献哪里不好,要去献给了一个公立学校?要献也献一个体面一点的十字架啊!这就是我的苦难。我没别的法子。甚至都没法好好地挑一下供自己献身的那个十字架,就像一只青虫,就地在哪一条树枝上急急地献掉了自己。是的,就像一位小吃师傅,在我熟悉的献身领域,我其实是很“神”的!但是,社会学家韦伯在“作为志业的学术研究”中说,究底说,这种“神”,这条路最后仍是不通的:大学教授在实验室的小电工看来,是很吊的了,但是,不光99.99%的人成不了这样的社会劳动分工中的成功者,而且成功者的99.99%再是神气活现,最后也只是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时时如坐针毡,不知最后会怎么被炒鱿鱼。[3]等工资、等养老金,那就是彻底放弃反抗了。要知道,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能留给我的,最多只有这一时时时带危机感的献身位置,就像它能留给我的墓地位置也决不会宽敞一样。但是,哪怕看出了这一点,我除了献身,还有别的路可走吗?[4]
所以,我早就看到和领会到了,哪怕看上去很光鲜的欧美的导师们,大都也就只能这样“献身”罢了,最后只是为献身而献身,只有在这种献身里才获得了自己的一点点职业成就感,否则眼前就是一片茫茫,喊出去连回声都听不到的。而在没有别的路的情况下,不能这样地去献身,我自己就会很急的!我会急着想要把自己献掉。哪怕通过自杀!涂尔干认为,很多一起扬帆出发的船只中途要过同一个闸门,有一些注定是过不去的了,其中的有一些就这样先行自我解决掉了。而我还想要说,就算是冲过去了,也是像秋蝉那样急急地寻个地方去自我献出,本质上与自杀并没有太大的两样。社会劳动分工把每一个个人都逼到了这条窄路上和这个窄门前。[5]
大学里,从小的到老的,是人人都在寻找这样的献身机会,还苦于没有这样的献身机会呢。就只是想献身,不管怎样地无论如何地把自己先献掉,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也并不想换来什么,有时就像尿急寻厕所般地迫不及待了。大学教员典型的就是这样的已献掉或至少已献掉一半的人。半献掉的人,就像搞婚外恋,是很不自由,无法安心的。几乎可以说,献一半是不能算献的,最后一定会主动去全献掉的。
所以,我这就将自己看作是没有办法只好完全将自己献掉的人了。特征是:不再算计每天投入的小时数,每天大脑最清醒的几小时都献给了那个事,管它有多少的工资回报。哦,还另有一个指标,就是:做一个喜欢的事直到为此而严重受伤,最典型不过了,热爱而献身然后被自己所爱的东西伤害,仍乐此不疲。献出后,这一边和那一边分不清了,过不好日常生活了,心思都在“那一边”了。这就是我们为自己所投身的劳动分工所付的惨重代价。韦伯在“志业”中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这个的,必须把这逃不过,看作是我们个人的那么咪咪细的一点点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唉!大学教员都因此而上了这条很挤的通向某个闸门的船!
总之,像我这样的研究、写理论、教书只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最后路越走越窄,然而就没有了退路,只好献身,像蚕到了时间就要上草山去结茧,很果决的。然而,大学排名时,也要求我这个螺丝钉为排名作贡献。这就是要来衡量我这种献身值多少钱了,这就有点荒唐和残酷了。
你说,各种献身之间是可以比较的吗?穷人就一定比富人献身得不惊天动地吗?民工就一定献得比艺术家不彻底吗?人类学关于献祭的各种解释已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每一个人的献身是一样神和圣的。只要是献身,就都是一样神和圣的,不论来自哪个人,哪怕来自杀人犯或女巫。每一个人爬上自己选定的那个十字架后,都是一样神和圣的了。所有的展示,只要是展示,都是一样神圣的。所有的艺术展示之间,所以都是平等的。不能说我是著名艺术家,我花在展览上的钱格外多,我的想象、念头、裱糊好看一点,我的就格外厉害了,应该得到双份的奖励。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神会拿响雷来劈你的。
所以,我们还不得不说,来自一个普通教员的献身,是与来自一个生物学家的献身和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医学教授的献身一样神和圣的。每一个人的献身,上面说过了,那一定是全部和彻底的,而且你还不能说这种献身比另一种献身就格外彻底,各种献身之间我们还只能假设它们是平等地全部和彻底的。但是,大学排名时所用的参数系统严重藐视了大多数大学人的献身,给这种献身排等级,更是要遭来天杀的。但韦伯在“志业”中说,大学是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它是一定会用表格来这样计算你的献身的交换价值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
什么是用来排名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不顾我的总体献身,只从我的献身的过程里抽取一些能被某种标准比如著名实验室、著名杂志等衡量的东西。它抽样地测量出我们献身于一个领域和某个研究共同体后的一次次局部的献出物的象征(!!)价值。它假设了各种献身之间是有等级区分的。等级低的献身就不能折算成分数。
上面说所有的献身都是同样彻底的,但实际情况却总是,有的献出就是不能算,打折扣后再算也不行。具体来说,对于排名的贡献,我的校长可能是我的十倍或百倍,他发表的成果格外算数,而我的就格外不算数,虽然他也只是像我那样献身,每天的劳动时间也不一定比我长。但我要问:他的献身真的比我更彻底吗?他比我的献身神圣十倍或百倍是如何算出来的呢?他用了哪种很神的本事呢?他在研究像土豆品种改良这样的东西,总是不断有新的突破,成果就像地里的南瓜一样总是滚滚而来。但我的献身过程里就是没有这样的一系列的突破,和滚滚而来的成果的,如果有,也因为是低一级和好几级的,都不算数。照现在的排名过程,我的献身就只值他的献身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我本来倒一点不妒忌他,只是遇到排名的事怪到我个人头上来了,感到如此荒唐地委屈,才想到这个。他在排名的贡献上这么厉害,那他的献身就一定很神喽?
几年前有朋友来说,大名鼎鼎、手上握有几个亿现金的艺术家王广义特别爱看《乡村爱情》,必须在电视台首播当晚拿着小板凳跟着看,到如此虔诚的程度。你会说,看看就看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要说,他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献过身的,名声这么如雷贯耳,献身得一定惊天动地了,我也把他当成伟大艺术家了。但是,他的生活内容在我看来好像反证了他的缺,需要看《乡村爱情》来补上、来被安慰,显然是还没献身干净!献得不彻底!最后也就这样了!看着《乡村爱情》的王广义,就像是武林高手由于爱看连续剧而在沙发上遭坏人暗算,身上中了几十枪啊。王广义沉默十多年了,再给他二十年?我看是等不到他什么了。他是我书架上的VCD了!
问题就来了:如何保证我那如此神通的校长、大学里的各路能够让排名如此飚升的神仙们,晚上不会像王广义那样去偷偷看《乡村爱情》或什么韩剧或抗日剧呢?我在想,天天嘴上挂着“世界一流”、“追求卓越”、“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人,因为白天假话连篇得习惯了,毕竟也难受,晚上看看《乡村爱情》应该也很疗伤的!也就是说,我感到有些把大学排名指数弄得很高的人的献身,细细看其实也蛮假的!他们在献身过程中好像玩过很多猫腻,被权力、经费和关系左右,而成了傀儡。当上了校长和院士了,本来可以蛮神气的,教育部的那些十三点文件他总可以挡一挡的了。不会的!他第一时间就要将这些文件落实到广大师生头上。一个很听教育部文件指挥的校长他不就很窝囊了吗?都当了院士了,仍是这等上面说什么他就执行什么的没骨气。你就很难想象,是院士啊,行止却像一个腐败的接收大员,这是公立学校耶!而这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很信这种排名系统的,也是这种系统的优秀产物,头顶着这个系统给他的无数光环,他就是来鹰占凤巢了,还正春风得意呢,我们竟还指望他!这正是我要来写本文的原因!你所在的大学只要你细看看,往往也是落在这种动机不明因而更可怕的外星人手里的!
所以说,校长要的大学并不是我要的大学。我和他是奋斗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大学之内。我是死也不愿呆在他的那种大学里的。他宣称是在紧跟德国大学传统的哦!你去问问当了将近两届的校长什么是德国大学理念,或谁是提出大学建筑术的康德试试。他保证会很生气地反问:谁是康德?整这些没用的干吗?所以,下面写的这些也可以算作是写给校长大人的启蒙读物,提醒他一下什么叫做德国大学理念,也警告他一下我所向往的大学是与他正在办的这种大学是何等风马牛羊兔地不相及的,与他的这近十年的相处,可以说也从来都是同床异梦、鸡同鸭讲,今后也难有另外的指望。[6]我将继续坚守的我自己定义的大学精神,也决不会是他所理解和正在坚守的那一种,我也压根不会将他放进我向往的大学空间里,从来也只将他看成我的眼中的大学的捣乱者,正如他会将我看作是大学排名的破坏者。而我的大学、他的大学、大家以为的那个大学,有没有必要存在,还要看一国的哲学、大学和国家的宪政建制的现状,而且我们各个意淫着的这种种大学,当前也正在彻底地被新的算法系统扫描,不论你说得有多老卵,无论你所说的哪一种大学,它们也都正在被新的算法掏空,正在“分子般地消失”,哪怕表面被资本化妆得越来越光鲜。我们要的大学,真的还必须另搞!
所以,说清楚什么是大学的外围,才能说得清今天的大学排名的实质性危害及其这种大学之恶的真正来源。
下 什么是“大学的外围”?
从康德时代以来,这一大学的“外围”
一直是被限制在大学的边缘的。今天就没有这么确定、这么简单了。今天,无论怎么说,大学本身已成了原来的大学的外围的外围。至少,大学的有些系科是被贬底到了这一地位。
--德里达,《哲学的权利》,413页。
要么,我们就任自己被工具化、被改造为专家而不是学者,由此而使我们身上的学术功能越来越失去信誉;要么,我们(像德里达、福柯那样)躲进无条件的自治这样的无未来的梦中,妄图避开所有的药学,相信不进入药理过程也能够思考所有的心智事务,也就是想避开所有的心理-集体个人化,仍想在大学之内和外围一直这么做下去。
为了逃离这一假的选择,大学极有必要通过第三存留(短记忆物,如大数据)的理论和实践,与业余爱好者共同体合作,也就是说,通过大力发展贡献式研究,来发明出一种与它的外围的新关系。
--斯蒂格勒,《震惊状态》,328页。
我们在1968年5月发现的大学的问题,显然不在学生和教师身上。它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知识的传输、行政人员的训练、群众的欲望、工业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而且最后所有的这些在大学配置里绞在了一起。政府的改革者拿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方案吗?他们只是集中注意要将大学封闭到大学的结构和组织里面。
--瓜塔里,《心理圈》,143页。
今天的大学的核心已被它自己的外围组织霸占。大学里充塞着寄生物[7],其核心已流亡在外多年。大学本应该是由每一学科的爱好者簇拥的一种松散组织,但资本和企业的力量却凑了上来,伸出咸猪手,前来挪占、玩弄大学的权力印章和地盘,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顾自在大学内横行,欺压小学科,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们更是鹰占凤巢,技术学科则成为大工业麾下的傀儡。大学内的各技术学科也被巨大的外部资本,如来自医药业、军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国家和财团资金哄得团团转。正是这些巨大的资金投入,在决定着大学的国际排名,而越排名,大学就越会投向这些出资方的怀抱,成为它们在大学内的雇佣和走狗,养着一大群像张维迎、郎咸平这样的无耻之徒。大学的外围在今天已成了大学的煤黑的核心。
由康德、谢林、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所阐述的德国大学理念来透视,我们今天的大学的深度中毒主要表现在: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服务科学都将大学当作国家权力的印章,不去追求自己的科学性,反而想借大学的国家权力图章,来给自己的话语-知识添上国家权威,然后出租给各大财团和社会主导阶级,去盘剥人民。今天的大学就像被黑社会或贪官的情妇霸占了一样。是丁书苗通过刘部长在指挥铁道部了!
从这一理念来看,各大实验室和技术学科这些本应该作为科学爱好者协会呆在大学外围的机构和组织,现在像害虫那样寄生于、霸占了这个康德意义上的“大学”之核心了。这些学科的言行是不受大学内的反对党也就是哲学系科(广义上的)的监管的。它们为私利而盗用国家的名义,将自己生产的话语直接当作大学话语出租给各种资本力量。大学已中了木马计!原有的系科式议会被架空,执政党(权力执行学科)和反对党(哲学系科)之间的扳手腕本应成为大学和国家政治的清洗剂,现在,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哲学系科却落到了乞丐的地位,它们的存在,现在都要看那些技术管理学科的经费的脸色了(正如乔姆斯基所说,他的语言学的研究经费得依靠美国国防经费的增加,由航空力学系申请来,分出一点点给语言学系,才有)。我们的大学,已像一架严重中毒的电脑硬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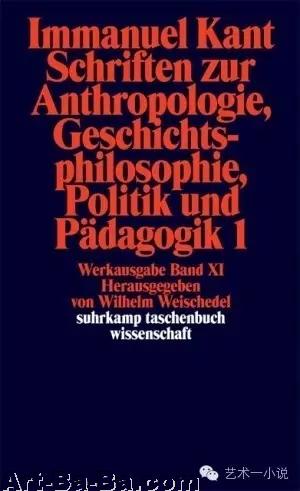
作为康德说的“理性的师傅”的大学文科人也常被这套看上去很光鲜的管理绩效系统吸引,忘了自己的本务,很贱地去学样。而原来,在谢林对大学的设想中,大学师生作为“自由艺术的师傅”,不光是向全国布道,也本身就成为magistri,成为国家、大学和哲学的新的“化身”。[8]新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人,就是新国家就是新大学就是新哲学。但是,今天,我们的大学或哲学腐败了,再也做不到这个。因为哲学系科是很快就会腐败的,施莱尔马赫因此甚至建议哲学系应该先私有化,以避免它这种必然的腐败。而谢林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有机总体是可以防止或清洗这种必然的腐败的。他指出,一种思想,如果不是在一种(大学式的)独一和总体(derEin-und-Allheit)之中形成,就是空洞的,须加以挑战;大学或哲学或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有机总体,自己就能清洗干净大学话语。只有经过大学学这一架独一和总体(l'uni-totalite,大学-总体)机器过滤后,知识才成为思想;否则就成了没有性别的蜜蜂(geschlechtsloseBienen)的劳作。[9]
但今天,总是大学的权力和权力执行学科在不用对任何一方负责地先拿着大学话语去颐指气使了。大学排名,和将这排名的责任压向每一个教员,就是这种欺压的一部分。而本来,哪怕哲学话语本身,也必须在大学的这种话语-议会的气氛的有机过滤下,才能健康。如果不能与大学的有机的知识总体接通,这些技术-管理话语是应当被大学的有机原则淘汰出这个会发芽的、活跃的总体的。[10]大学必须有机,这是比康德还高的要求。今天,大学内的技术-管理学科的话语却都没有受到这种监管,而直接就自诩为大学话语了。
康德意义上的“大学”外围的科学爱好者协会的典范,是普朗克研究所担任的角色。今天,这一构架正由开放软件等等带给我们的新的贡献-合作空间里涌现,各种新的业余爱好者协会会更多地涌现。而我们的大学系统正在走向这个技术时代要求我们、我们必须适应的新境况的反面。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被排名捆绑的大学系统在这个新算法统治时代里正在自取灭亡。
我们必须天天重新定义大学在这一刻对我自己昭示什么了。只有在这种重新定义中,我们才能用这架中毒的机器了。
3-小结:大学内的哲学空间之是改造大学的备用的游戏空间
在康德的系科建筑术中,生物化学和管理科学这样的搭不到一起的学科,本都应成为大学的“外围”,应以“科学爱好者协会”的方式,帐篷般存在于大学周边。可是,现在,它们却鸡占凤巢,成了大学的主角。它们不接受哲学反对党的监管,反而间接将哲学系科边缘化了。大学不大学了:它里面的知识被不断分割,永远不可能变成有机整体了,谁经费、论文拉得多,谁就更有理,排名就是建立在这一逻辑上的。
大学本是人民集体对国家主权的哲学式运用,但它在货币社会里必然败落,而走进合股经营,人称美国化。我们所说的德国大学理念其实从来没有机会被真正落实过。从康德的大学理想看,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存在理由是无法得到辩护的。大学是西方的纯理性对国家权力的系统术式的建构:不是国家给了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和管理学院权力基础,而是相反,正是这样的学院撑起了国家这个道具,为国家理性作了辩护!这种国家权力的系统术式的建构,也就是这种撑起现代国家这个拱顶的努力,是靠了在大学内根据技术图式和技术必然性来组织知识,形成一个国家-知识-本体百科全书,而做到。可是,渐渐地,连哲学系科自己也都忘了它的作为大学议会里的反对党的作用,而只是靠了社会所能付得起的成本,来提供豪华的、实行三保的意识形态本金而已。[11]也就是说,哲学系也被大学化了,也不是那只理性原则的牛虻了。因此,我们需要对新的大学启蒙的启蒙(les Lumieres d‘une nouvelle Aufklarung universitaire)了。这也就是说,再不能依赖哲学系的作为反对派的作用,因为它也只是其中的股东和功能了,必须也将其推进新政治,在新政治中来自我启蒙了。
思想,哲学,关于大学的思想和哲学,因此不可能是一个大学内的事件,不可能是一种学术因素,学术行为。那种教授治校式的大学内的大学式改革,只能是“重组了那种种姓、阶级或股东权力”,是再生产了大学内的等级而已。[12]康德认为,对大学之认识和改革,必须由哲学系科、并在一种哲学空间里来进行,因为大学自治是脱出、高于那种职业和专业分工的;哲学教师是建筑师,懂得系统术,他们的理论是最高等级的实践,而他们的力量也正出于他们的自我审查和自我限制方面的能力。他们是最知道自己的职业之deontologie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最知道自己的职业和专业权威是被悬置。他们最应知道自己的在研究中捍卫着的原则,也应在政治实践中加以捍卫。也就是说,不能像鼓吹教授治校的人那样,对外是要宣称去自治和法治,却给自己留出了例外,先得到一块自留地再说。哲学系科像船坞也像急救病房,是修理大学系统的预留空间。康德认为,哲学系科是进行公共论证时的最高审查机关( hochesten Orts sanktionierte)。对此,德里达解释说,成为大学老师,就是“不自觉地将哲学系和哲学教师当作潜在听众来发言”。每一个大学教师都应将自己看作哲学教师,每一个系科都也应立志成为哲学系。关于大学应往何处去,必须在这样的哲学式集体论争中来定夺。康德说,哲学系科是用来置疑被别的学科检验过的真理诉求的(Die philosophische Fakultat kann also alle Lehren in Anspruchnehemen, um ihre Eahrjeit der Prufung zu unterwerfen)。翻译成今天的话是:哲学系科用批判理论挑战科学,也从科学那里寻找其批判理论的最新边界。但是,哲学系自己检验过的真理,将由谁来置疑?康德说,由它自己。所有学科中,惟哲学握有这一特权。它如何来自己置疑自己检验过的真理?用理性!理性是一种用理性来理性的能力。哲学因此是用来让我们像哲学那样地来哲学的能力。这不是同义反复。这是人类理性的自我宪政。正因此,康德认为,只有哲学才能帮大学摆脱它必然涉入的危险。[13]
在迎接数码治理的今天,大学本身已被架空、且内部空洞化的情况,对大学内部的改革已是太轻描淡写的说法。今天,在大学内部,所有的知识都正在同时快速走向教条化和无产阶级化,而互联网而不是大学图书馆则已成为大学人的数码知识记忆存储的主要部分。我们需要一种矫枉过正术来同时治疗大学之病和学术人身上的技术中毒;我们不应该再培养学士,而应该培养出药士,治疗大学人自己身上不断加速的无产阶级化。大学人自己的知识组装正在变成VCD。
而在大学的外围,数码短记忆材料正在将我们的社会关系编入一种陌生的算法-语法:家庭、男女关系、劳动、商业、金融、政治、外交等等方面都正在被新算法架空,危险正来自此。大学的外围也越来越不是“大众”、“拜耳”那样的大公司而已。世界大学排名,就像国际小姐或世界小姐选拔一样,是这种新的语义错乱的一部分,是大学被带入最最非理性的它治的一个最新写照:它必须擦脂抹粉,甚至必须主动去站街,来在网上得到一个好的评分。大学的遭遇是比一个难民和流离失所更糟糕的处境。
4-尾声(1)一点点安慰:让我们成为马奈!
去世前不久,布迪厄在法广文化台的访谈和身后出的《自我分析之素描》一书中在一片绝望中深情地向听众和读者坦白:我很想要呆在艺术家马奈这个位置上!如果你们对我当真,那么也希望你们来体认我现在所处的这一位置,“能在我的位置上认出你们自己的经验、困难、责疑和苦难等等,现实主义式地认同于我的位置,不是忘情地投射,而是从中找到做你们所做、活你们所活之更好的手段,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们高兴的了”。[14]
那么,什么是布迪厄去世前如此执着的这一“马奈的位置”呢?就是真的像韦伯建议我们的那样,放弃那个学者或教师位置和荣誉的幻觉,去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天天去面对一个新的当前,决不停留在某一个位置和立场上!不是出一次风头,而是天天出风头,自己先天天变!接我们上面的说法,这是天天在献身,每天一献身。就只做艺术家,天天变!布迪厄是在说,这比献身在学术事业更让他向往,也希望我们都这样去天天做马奈!
在“文科的未来”一文中,哲学家凯特琳・马勒布重新评估了马奈对于福柯的重要性,并越过福柯,强调了马奈绘画中所表现出来的“造型性”[15]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勒布说,对于康德而言,“启蒙”就是我被当前绊住了,想去思考为什么我会被拖进这种思考之中,去思考那将我拖进这种思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启蒙,在她看来,是要克服阻挡着我们的当前困境,是我们的当代解决。我们一意识到“今天”或“当下”,就有了现代性;“现代性”也指:意识到我们陷于“今天”之中不能自拔后产生的自己改造自己(把自己当作造型对象)的积极态度。马勒布进一步指出,“启蒙”,就是现代人所要追求的自己的可塑性。她认为,这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就已被指出是“精神”的命运。现代人必须彻底打破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指称幻觉,[16]主动去逆来顺受,在塑造阅读对象的同时,主动接受塑造。阅读过程中,现代读者的造型和被造型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思想,就是现代主体主动愿意屈服于来自阅读的改造;在画画上说,就是同时去画,也被画。大脑里的源初模型或标准总是在被不断揩擦掉,读和写,就像马奈的画画。学习、获得新的技巧、得到新的记忆,这是我们身上一生都在做的事。我们一定已揩擦掉自己不知道多少次了。启蒙,不光是要找到新的参照,而且也还要换掉身体。[17]马奈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榜样:他在每一幅画里都达到了这种塑造和被塑造之间的平衡,哪怕冒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风险。
启蒙,就是在当代变形。我们的源头,也是不断在变的。在历史中,得放进去一点神话,我们这才能从中变出来。[18]
而我们在今天也许需要比马奈更主动地去辩证、破坏和解构,才能到达我们的当代!存在没有“之外”,我们无处可逃,所以只能变!我被变也自变。我的世界像一个舞场,我变,大家也都变,我不一样了,但大家也都不一样了。一切都似是而非了。人在此在之上变形。[19]
未来是可改造的![20]面对白板的未来,马奈一点不怵;他在画布上思想,在画笔下变形,天天自我造型,当作一件很出风头的事。在今天,我们更需要发扬马奈精神!天天发明自己!每天发布自己!天天自拍得不亦乐乎!今天,一种在今天还算靠谱的新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是:对我们的未来,我们应该还是可做点什么的!有时,我们是可以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正如马克思说,人造就自己的历史!
综合地说,康德加马奈的启蒙,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必须发明/捏造出自己的“今天”和“当前”;同时发明/捏造出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这是由待我们自己去发明的。

马拉美肖像
巴塔耶在评论马奈画的马拉美像时指出:他就画着一个艺术家,画马拉美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不再作出任何指称。也就是说,在马奈看来,做什么劳动分工,都是没什么意思的,就这样做艺术家到底,天天不同好了。[21]做艺术家,不是依着自己的内心孤独、死硬地使自己更加成为自己,不是去坚守,不是像学术研究者那样得意于自己的那一点小分工,而是天天以新的方式去成为自己、成为艺术家,天天化蝶一次。艺术家才是躲开了劳动分工的人。巴塔耶说,在马奈之前没有人这样去看过、画过一个人。
一个大学人的学术道路通向的是一个异化的位置,而马奈的位置,是一个天天自我变型的艺术家的位置。布迪厄想说的是,我们只有在马奈的位置上,才能摆脱大学这个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对我们的异化。
(2)斯蒂格勒:积极利用大学本身的药性
在今天这个新算法时代,哲学家斯蒂格勒指出,大学必须成为普遍而多样的关系网络。大学不该光喊喊抵抗就算。大学的未来必须奠基于新的工业模型上。改造大学,第一步必须是重建深度关注(与社交媒体拖着我们做的相反),[22]而那决不是教学法的问题。这要求我们直面这个后消费主义时代的新的“世界性”,对技术-科学知识的批判也必须与对新的工业力量的批判相结合,[23]以此去重建代际关系,汇合三代人,一起重新学习,小学、中学和大学一起办。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打开大学的未来。
从来,教育都是抛向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从柏拉图那时开始就是这样。在大学成为诺奖、《自然》和经费统治的黑砖窑之后,斯蒂格勒认为,我们必须重问:什么是大学的核心知识?答:它就是胡塞尔说的无数代人不分前后地构成的“几何共同体”所共同拥护的那些一代代重新被激活的知识。几何经验正是大学的所有知识的不言自明的地基。[24]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必须不断重申,学术知识是没有目标的。学术研究对象是无限的。几何、哲学、文学、历史中都没有最后的说法。大学内对于知识的追求,像伟大的登山过程,像伟大棋手之间的多回合较量,是几代人的共同升华的过程。
大学改革不好的,也用不着另起重做。大学是在迎接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的过程中在我们身上自我代谢的:
1)发明新的出版方式;
2)发明新的大学、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大学向中小学直接提供教学内容;
3)发明新的全球宪政秩序空间;使破败的全球大学系统在迎接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挑战时先成为一个“互联国”;这才是真正的“大学之外”;
4)大学人直接干预正在冒出的新的工业政治、新的精神的工业生态;
5)去鼓励每一个大学人去发明新的工作;
6)发明新的终极价值;走向逆熵。
(感谢钟立兄为我初步编辑了稿)
[1]康德这里说的“哲学系科”主要是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历史性认知学科,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教学、大文科、自然科学和经验知识科学;二是纯理性认知科学,指数学、纯哲学、自然之形而上学(今天的脑科学和量子力学等等改变我们本体论的那些学科)以及伦理学(见康德,“系科的冲突”,《人类学、历史哲学、琡和教育学文选》, 291页)。
[2]康德以后做哲学,我们与海德格尔一样地处于这一困境:我们必须破坏我们的观念赖以形成的机构,在这一机构里阅读和写作,但我们又必须解构,好象全部的读和写就为了推翻这一机构一样。这就是解构。它是一种自我破坏式的机构实践(德里达,《论哲学的权利》,88页)。我们身处康德的universitas,但我们的任务是要破网冲出。康德使我们身处的机构可能,但我们的任务是去破坏这一观念的机构。但康德教育学的核心不是去教学生掌握自然法则和先验原理,而是要教学生去分析,去做助产师,做纯哲学的工作:揭示、唤醒或说明,那只是将已经广为人知的东西教给学生。这一教育学不符合我们这个数码时代的政治要求了!对哲学的权利,这种人人具有的权利,德里达说,在法语里的字面意思,是“直接通达哲学”,取四边形的对角线的意思,而最初,康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就是以这一两点之间和对角线的直,来解释“权利”和“法”的。在我们时代,我们是不是又应该来拉直这条线了呢?哲学直接将权利塞到你手里,通过你直接通达哲学。
[3]原文是:“请同学们注意,在生命的关键问题上至少99%的教授都不可在你这个青年学生面前扮足球教练。”可被引申为:你们作为青年学生来大学,总是不把老师当作先知,就把他们当作领袖。但是,老师们如想要扮领袖,就应该到街上、市场中去发言,而不应在课堂内,在众人都闷声不敢反抗他们的情况下企图来影响大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就是说:学生以为的和老师想扮演的这两个位置,其实都不在。
[4]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中说:今天的科学也只不过是如此:它们也无非是在各种学科内被组织而成的"职业",任务是,去澄清和理解各种相关的事实。这只是一项职业,并是不是要你去当伟大的洞见者和预言家,去阐发神圣的价值和深知,也不是要你成为伟大智者和哲学家,去替我们沉思宇宙的意义。这是我们当前的历史情境的不可逃避的限定。他后又说到,个人想要在浨研究中找到志业,必须硬下心肠,接受这样的安排:“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一个科学或学术工作者,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总算有一次或许今生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地意识到,她做出了某一个会经久流传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决定性的、优良的成绩,在今天,总只是一定分工下的成就。谁要是不能把自己的眼蒙住,许我这样说吧,一心要认为她的灵魂的命运就要依赖于她能否在写稿时作出正确的猜测了,那她还是不要来弄学术的好。她这是永远不会得到所谓的“关于科学的个人经验”的。”没有这种奇怪的、被外人取笑的迷醉,没有这种激情,你是没法拿学术做你的志业的,还是去捣鼓别的更好。因为,激情地投身去做一件事,一个人才能最彻底地发挥出本色。这是因为,韦伯解释说,“我们时代的个人命运的特征是:理性化和智性化(知识化),而且,首要的特征,是“世界之被去魅”。再是终极和高洁的价值,也已从公共生活中退出,躲进了某些神秘生活的先验领域,或退入了直接和个人性的人类关系和兄弟情谊之中。一点不偶然的,我们能见证的最伟大的艺术,是亲密的,而不是高屋建瓴式的。”
[5]韦伯在“志业”的倒数第5至第三段里反复讲到的“智性献身”,就是指这个。献身后,我们才能在周围的种种先知和领袖面前保住我们的品格,“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和在我们自己的志业中,达互本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6]不过他最近在做完新生开学典礼后突然被教育部无情地撤换,再一次印证了韦伯的伟大的前见:再是气的明星科学家,哪怕他以为是这个体的鹰犬了,也就是这种最终下场。
[7]德里达,《哲学的权利》,417页。
[8]同上,385页
[9] 465页。
[10]465页。
[11]483页。
[12]496页。
[13]康德,同上,297 页。
[14]布迪厄,《自我分析之素描》,131页。
[15]见:http://article.yeeyan.org/view/465004/395923。
[16]马勒布,《海德格尔变变变》,243页。
[17]同上,95页。
[18]93页。
[19]322页。
[20]77页。
[21]巴塔耶,《马奈》,英文版,131页。
[22]大学的本质,是去获得这种关于长记忆的经验,实现知识的跨个人化。重建深关注(斯蒂格勒,《震惊状态》,276页)。大学是疗养机构,是要帮我们重新找到新时代(同上,282页)。
[23]今天的大学动员和组织其研究机体,无限止的创新加速,是以毁灭我们的未来为代价的(同上,328页)。大学系科要做的,是治疗式工作,但首先必须与大学内的数码短记忆装置作斗争(317页)。
[24]264页。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