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Jacob Dre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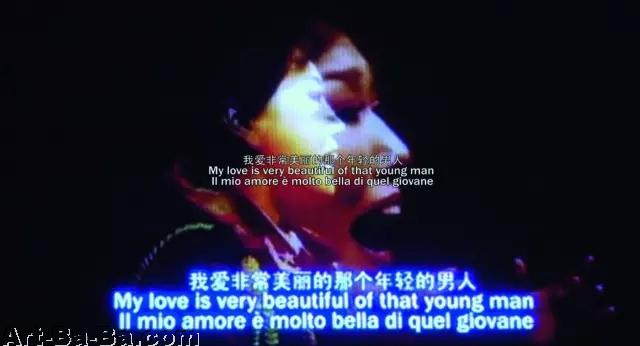
黄小鹏,《意大利咏叹调》(截屏),2009年,单频录像,彩色,有声,1.85:1,2分42秒
在艺术之前,在任何表现形式之前,我们作为生命存在: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上,被贴上自己无法选择的标签,并被这些标签界定。我们感受周遭的世界,并立刻做出反应:身体上的反应。而我们大部分的身份标签,就是事后对那些即时反应的合理化解释。然而我们依然对这些标签感到疏离:被我们的身体深深包裹的那个“自我”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出于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压力以标准化的、预先设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时,便离我们最深切的自我以及独一性越来越远。一个脱离阶级结构和主观性的自我的不可能性,或许可以解释真实的集体经验——这一推动着中国现代艺术、文学和哲学发展的乌托邦式的抱负——距离“我思”很远,就像我们身体的真相那样遥不可及。虽然我们还没有体会过一种无界限的海洋社会形态的快乐,但如果打破阶级、撕下面具和所有中国现代性的奋斗有意义,它可能是创造出一种流畅的存在形式,让我们能够表达真实的自己和我们对他人的感受。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学生们基于对精神分析学的独特解读,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在“情动理论”的广义范畴内把各种思考系统化,探索其在艺术、社会、历史和经济领域研究中的可能意义。按照这种体系的划分,我们的“自我”是庞大社会群众的组成分子,这种“自我”几乎总是根据与他人的关系而被定义,并且以预设的格式表现出来;这些格式,或者说“情动”,即“个体感受他人并且做出的反应”[1]。性别常常被认为是虚构的,种族也被认为是虚构的;这些社会认同的分类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都相当武断。或许在定义一群人方面有些用处,但是在理解个体方面作用不大。同样地,我们的身体语言也在传达、连接着社会的虚构情节,而这些虚构情节可以多变地适应历史和经济环境。与我们的艺术和文学类似,我们所选择的身份是一种基于我们身体的上层建筑,使得我们能够参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并且发挥作用。就像太阳一样,那个非理性的内心虽然每天都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它的全部—我们根本不具有那样的感知能力。客观地观察人类需要我们完全抛开已有的观念和利害关系。
人的一生就是在思考和表达之间徘徊

黄小鹏,《每天猜测爱》(截屏),2007年,单频录像,彩色有声,3.31:1,2分50秒
情感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社会的虚构。不过,我们选择表达情感的方式是由社会建构的。在英语中,“affected”(直译为感情化)用来形容人们故意表现出不自然的行为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也有“矫情、做作”的含义。随着亚文化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以及互联网虚拟现实的萌芽,自我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区隔不再那么明显;我们都在通过“矫情”表现自己。矫情不是一种情感、感觉或者情绪,而是一种面部的、身体的,甚至语言上的表达方式,直接表达我们的反应,甚至与自我无关。社会可接受的情感反应形成了一套有限的表达方式—与人类情感和经验的多样相比,KakaoTalk、Line或者微信的表情包只有8种或者16种情绪表现形式:喜悦、好奇、惊讶、愤怒、苦恼、害怕、害羞……每一类都基于特定的表情形态,可以方便地叠加到其他表情包上,例如气泡狗之类。我们正在把身份与自身的虚拟表达绑在一起,我们在微笑或者皱眉的时候更加直截了当:实际上,我们现在微笑或者皱眉的时候只需按下对应的按钮,这种表达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取代了口头或者书面语言。埃里克·肖斯说,“身体有它自己的语法,没法完全通过语言表达。”如果说“真实”本身完全没有经由社会集体经验的调停,那么它就可以在“身体”上被找到—只要任何身体反应可以被予以认知性地阐释,它就冲破了关联、规则、类比以及之前经验所共同构成的网络的束缚。如果没有思想,我们的情感表达就会粗糙而笨拙;但是如果没有“矫情”,情感表达就只是如爬虫般的、没有生命、没有激情的反应而已。
我们的“自我”是陌生人,是墙上的影子;我们只有通过收集有关我们自己的八卦、阅读领导给我们写的年终总结,或者更实际些—查看我们的银行账户、观察健身房镜子里的自己,才能够了解这些“陌生人”。对于德勒兹来说,“心灵源自对身体冷冰冰地、好奇地审视。它首先是一个见证人,然后受到影响,变得热情洋溢。也就是说,它所体会的并不是身体的直接影响,而是在身体之上并且裁判它的真正关键的独立存在。”[2] 我们表达的情感、我们选择定义自己的方式,凌驾于所有策略性的应对机制之上;这些我们所选择的方式是对周边环境的回应,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并以此证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东西就是“真实的”。
在我们这个社会,以再现方式存在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其前瞻能力:去表现期望中的未来,并激发其物质性。从艺术分析发展出来的再现理论,在解释人类身份本身的构建和表达方面很有意义。我们精神中不成熟的、神秘的部分也许都不为我们所知。既然用来表达这部分的所有语言都不准确,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在描述或外化这种感受之时丧失了其多样性。从本质上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遵循了一条乌托邦式的发展轨迹,个体、城市和地区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已经根据可预期的结果被计划好了。如果把我们的精神当做一种理论,那么我们的情感表达就是一种实践: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与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之间的那个部分,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我们的“情感的真相”。
假面的告白

黄伟凯,《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剧照),2008年,58分钟
一条城市街道上,可能是在东莞、上海、重庆或者巴黎第十三区,一个年轻女子对她的男伴说:“你好讨厌!”然后,他笑了笑。一辆摩托车撞上了一辆汽车,争吵开始了。明显在发抖的一个小伙子走出车外,他的表情从害怕转为装出来的愤怒,一群老人家围上来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显然,有一套复杂的代码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使用某些词汇或者面部表情来表达他们的感受—他们也许是从电视、微信图片或者地铁、电梯里的广告里学来的。最近爆出的社会丑闻中有不少“没人性”的冷眼旁观事件—看着婴儿被车碾过、老人在公共汽车上摔倒而其他乘客无动于衷—人们仅仅是因为害怕承担可能的经济责任。当然,要期望那些在无孔不入的经济大战中苦苦挣扎的人,假装合作地伸出援手,这也不公平。普通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他们牵涉其中的商业化行为都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最终,大众文化的主要目标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认为:心甘情愿地为集体奉献一生才是唯一的生命意义。如果说艺术是政治未来的理想化预测,那么表达或再现就是对迄今为止不存在的物质性的一种内在化的表现;所有的社会真实也就可以说是在虚构情节、种族、性别、性向、阶级以及其他方面达成的共识,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证明过了。身体是承载我们精神活动的不稳定的平台;在这块画布上,我们的精神不断扭曲,留下印记,与之“做”爱。

陈界仁,《试爆子宫》,1985至1986年,行为表演
自我表达在城市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艺术、时尚、媒体和公关领域相当有效。在这个意见领袖当道的时代,没有真情实感支撑的仪式化表达已经成为了常态。电梯里的显示器上正在播放一则巧克力广告:孩子蹦蹦跳跳地穿过房间,喊着“妈妈,我爱你!”我们视而不见—只顾着刷微信朋友圈;言不由衷地因为收到公关公司的礼物而表示谢意;给下午茶或者其他能显摆酒店餐厅里各种消费方式的照片点赞。在多种表现形式推动的城市经济中,情感被商品化了,就如同在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劳力被商品化一样。
这说明情感的表达具有巨大的价值(否则人们为什么愿意在这方面花钱?)矫情和感情是引导我们说服自己的路标。各种经历和因素组成了“心理”,它们看似随意地被物质需要绑定在一起,得以在社会中生存并且实现其价值。为了解释和统一这些不同的经验和要求,就必须选择一种简单的描述,并且就到此为止:一种可能是陈词滥调的表达。
这是我们的派对,我们想哭就哭

黄伟凯,《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剧照),2008年,58分钟
我们是如何得出情感的当代形式的?是谁发明了那些成天轰炸我们的陈词滥调?
在一开始,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把中国人多样而分散的经验整合起来,这就好比通过现代性建立起经济关系一样。康有为是近代中国首批乌托邦主义者,他把古代儒家思想纳入现代社会结构,形成了他称之为“大同”的思想。西方城市资产阶级的情感形式通过帝国主义经济体渗入了中国的话语,并且几乎立即进入了诸如鲁迅和萧红等思想家所提出的集体化、政治化的痛苦的形式,正如他们两人的个体经验—作为一名留日学生在电影院里看国人被杀的经验和父亲重男轻女的经验—成为了无法表达自我的集体痛苦的隐喻。今天,当《新闻联播》告诉我们某某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时候,这种集体痛苦又再次浮现出来。然而,它曾经在革命公社的“后延安”表达中被转化为极大的集体喜悦(50年代农村地区的集体生活可以说是实现了康有为和孙中山所设想的乌托邦,这种情感的乌托邦是随之到来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理想社会的前驱)。张爱玲和钱钟书所描写的肤浅的市民,梳着大背头,扣着整齐的白纽扣,戴着正圆形的黑框眼镜(也好像上周末展览开幕上见到的人),总能迷住周围一些看似情绪被动的人。他们被发配去向人民学习。对于那些打算抛弃自己的思想、用更适合集体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的人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当代文化之前的那段酝酿期研究甚少,尽管那是一个持续成型与嬗变的过程。
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似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立刻出现的,强行融合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尝试被抛弃了。从网络小说到热门漫画等流行文化让三线城市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讲述他们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同样地,“伤痕文学”和极端的行为艺术也让知识分子表达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体验,只不过是以阳春白雪的形式。知识分子们经历了种种苦难,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失去了机会,他们的家园被绷着脸的陌生人挤占了,他们虚度了青春……工人阶级也慢慢意识到集体虽然还是一种经济的实体,但他们已经没法进入其生产模式了。理想化的80年代见证了包容每一个人、一起向前迈进的集体主义理念的最后光辉;尽管这种集体主义理念已经渐渐黯淡,但在今天的一些消费主义愿景和电视节目中,依然能够看到它的痕迹。在深夜的卡拉OK包厢里,对着桌子上摆着的几碟瓜子,这个社会吟唱着它的痛苦,尝试着新的情感表达。
社会主义—或更简单、通俗地来说就是集体生活—的感召力似乎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们因为害怕孤独,所以挤在一起,表述和对比我们的经历是为了验证它,并以此抚慰持续体验新奇性所带来的心灵创伤,而这种新奇性就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名词。今天,我们重新学会了把自己当作一个个体、一个创业者,去面对上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无数可能性。尽管看起来选择很多,但其实不然;我们正在通过这些方式重新构建一种体系,重新定义经过一种激进的开放性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的新参数。那种开放性就像是一道伤口,极为痛苦。情感表达的当代模式看上去似乎更加个人、更加自由(即使没有笛卡尔主义的西方那么自由)。实际上,资本主体的经验就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保证和力量支撑的状况下忍受着集体生活的所有压力(当然,CEO或者艺术理论家之类的人,因为手中握有权力,他们即使承受着压力,也比那些妓女、四线城市的变性人这样的边缘人群承受的压力要小得多)。刚受伤的时候很痛苦,之后伤口就愈合结疤;现如今,它们在色彩鲜艳的纱布下面隐藏得很好,学到的教训也许就是:“已经都那样了就干脆不要管了。”我们与其继续装着敬而远之,不如开始考虑什么样的情感表达形式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那个我们期望许久的集体。今天,在过去三十年间出现的许多社会形态都在被重新评估和衡量,其中不少被重新定义为“腐败”。为了保持人和阶级之间的分界而重新出现的货币经济准则不能容忍任何挑战,但以混乱却生猛之势膨胀的欲望却表达着我们对理性的海洋—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的向往。我们希望世界大同,我们就有了大同坊;广大市民的脸上映照出了我们自己的疏离。
宝宝不开心了

黄小鹏,《爆炸是这一时代听到的声音》(截屏),2006年,单频录像,彩色有声,5分46秒
无力的人们试图以不那么让人癫狂的方式阐释着自己的脆弱,用语言让他们的无力显得可爱。媒体话语不断重申着女性(还有性少数群体、农村人口以及其他各种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劣根性,淹没了那些鼓励女性加入到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的充满弊病却真诚的努力。今天很难再看到萧红那样无畏而痴狂地开创“自我”形式的女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如果要写一本关于苦难的书,不仅要重新挖掘自身经历的奇闻逸事,而且要收集社会整体的经验,这种事或许是除了腾讯业务拓展团队以外还没有任何人尝试过的。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这个自己,足够有钱吗?这个自己,通晓艺术史吗?这个自己,住的地方还不错吗?这个自己,为自己做了多少?或者说,为了别人眼中的自己,是如何煞费苦心地塑造自身形象的?为什么你与你自己的关系看似受到了各种想法的影响?提到“矫情”及其含义,又会引出关于代表性和真实性的老掉牙的问题;至于说到我们怎样向其他人表达自己,其实我们对自己都不说真话。“矫情”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真或假的问题:它就是最基本的状态。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会微笑。这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它是一个表征,一种尚未出现、即将到来的真相的前驱。我们对我们在乎的那些人表现出情绪和“矫情”:例如,处于主从关系的一方,或者利害关系的另一方。城市生活的匿名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它意味着把人当作物件,因为那个人与你的物质命运无关。只有在彼此关联的情况下,澎湃的情感才能成为可能:彼此为敌的经济大战成为了一种大型批斗会,根据不同的主线对历史进行精神分析式的重述和重构。为了克服过去,我们抓住它,把它开膛破肚,让它的器官流了一地,然后我们轻装前行。我们将之称为“近代的超克”。我们尚未成功。
脚注:
1. 克莱尔·海明斯,《激发情动:文化理论与本体论转向》,《文化研究》第19期,2005年。
2. 吉尔·德勒兹,《批判与诊断》,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文/卓睿(Jacob Dreyer)
译/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