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来源:E演学刊
陈箴(1955-2000)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活跃在世界艺坛上屈指可数的华裔前卫艺术家之一。他对生活的热爱,社会的关注,尤其是他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教育和生活经历,造就了他对事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鞭辟入里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并使他得以创造出一种既丰富又独特的当代视觉艺术语言。他用这种语言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从而为中国文化艺术在当代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陈箴
陈箴的双亲,陈家伦和许曼音,是上海广慈医院医生。文革时陈箴曾随父母去农村接受“再教育”。1973年他进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攻读美术和牙雕专业,毕业后又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美术和布景设计。勤奋和聪慧的陈箴,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学习环境下,犹如海棉般地吸收着中国传统和西方艺术各方面的知识。熟悉他的同学们都觉得,陈箴继承了他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母亲敏锐的思路。在教师们的指导下,他不仅练就了一套过硬的绘画功夫,关心社会和时事,而且打造出了一颗敢于攀登世界艺术顶峰的雄心。不幸的是,在毕业前夕,他壮志未酬却得知自己身患溶血性贫血,并被预测活不过五年。心理上倍受打击的陈箴,并非因此而沉沦,则决意去巴黎创业。事后,陈箴在事业上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说明,他医生家庭的出生,早年在农村受到的“再教育”,青年时代在艺术院校受到的训练和熏陶,以及带疾病的身体条件,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成年后的艺术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很多大陆出国留学的艺术家一样,陈箴在巴黎的经历是从勤工俭学开始的。他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的同时,以在街头为路人画像而谋生。用他的话来讲,这就是“大丈夫能曲能伸”。“在巴黎,陈箴吃惊的察觉到,虽然大批移民正在创造法国现代史这一事实已众目可睹的,但是他们在巴黎的艺术界似乎并不存在。他感到,和国际艺术界相同,巴黎艺术界被白色的权力机构掌控着,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艺术家几乎毫无机会取得成功。”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巴黎当代几个艺术机构的艺术总监/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在他的文章“能源场”(A field of Energy)中回忆陈箴,“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西方是否有做艺术家的权力?’我回答他说‘你的机会与他人均等。’”[1](Sans,"A field of Energy",6)
安娜-卡非兹,希腊当代国家艺术馆馆长,在为《陈箴——身体的隐喻》所写的引言中提示:
陈箴认为,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一个文化中心,各种文化只是不同而已,在质量上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坚持这样的观点,当代艺术才有可能复兴。而这样的观点是和中国传统中所主张的宽容,共存,以及各种宗教和哲学门派之间的互动和协同是一致的。(Kafetsi,22)
为了在西方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呼出自己的声音,陈箴毅然决然地摒弃了传统的架上绘画,在工作室苦干了一年后,他开始用他的装置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巴黎的艺术舞台上。
据桑斯描述:
这些作品用视觉的语汇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桥梁。陈箴用了来到巴黎后两年的时间,消化并记录了他所经历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接踵而至的作品,是一种惊人的东西方文化参考物的对位。这种独特的语言为他之后的近十五年里所创作的既复杂而又难以归类的作品奠定了基础。(Sans,"A field of Energy",6)
纽约新美术馆的报道也对陈箴作品进行了分析:扎根于道教的精神和形而上学的思想,陈箴在他的作品中“采用了西方前卫艺术的战略去探讨当代人所关心的主题,例如,在全球性的消费世界里,自然和人为,传统和发展,历史的和当代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Field of Waste:Chen Zhen,"The New Museum Annual Report,1992-1994)

在之后短暂的十几年里,陈箴的作品曾多次应邀参加重要的国际性艺术展览,其中包括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加拿大蒙特利尔双年展,美国卡内基国际当代艺术展等。他的《圆桌》在1995年(联合国50周年纪念日里)被展示在欧洲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楼前,之后又被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他参加了世界各地一百多个美术馆和艺廊的展览,其中包括三十几个个展。除了法国各地之外,他曾多次涉足于德国,美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南朝鲜,英国,芬兰,瑞士,日本,加拿大,巴西,希腊等国家进行创作活动,并在瑞典,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摩洛哥,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展示他的作品。各种文字的报刊杂志不时有他作品的报道和评论,其中包括七篇《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当代艺术展的报道中,陈箴被指名为十来位“当代国际艺坛上最热门的艺术家”之一。在这十几年里,由于他的作品代表并带领着当代艺术的最新潮流,他曾得到国际上很多著名基金会的资助。同时,他的作品还被编入一百多个出版物,其中包括书籍,画册,画展目录和杂志等。(Chen Zhen,Chen Zhen:Invocation of Washing Fire,433-450)然而,正当他的事业走向高潮之际,他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
陈箴在2000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他入葬于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 cemetery)。巴黎的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以葬有众多艺术家,如画家毕沙罗,修拉,莫迪利安尼和德拉克洛瓦,作曲家肖邦,舞蹈家邓肯,剧作家莫里艾等著称。陈箴过世后,在陈箴遗孀徐敏的支持和帮助下,包括美国纽约的P.S.1当代艺术中心和波士顿ICA美术馆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美术馆和艺廊,纷纷举办了陈箴艺术的回顾展。
陈箴用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正如桑斯在追忆他的一文中写道:“陈箴虽然在2000年12月与我们告别了……但是,他犹如一个充满能量的磁场,将继续激励那些知道他的人,和那些将通过他的艺术发现他的人。(Sans,"Between Therapy and Meditation",Chen Zhen,10)
陈箴的“融超经验”和“游子的视角”
“融超经验”是陈箴发明的词汇。它既被用来指陈箴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的积累,以及他的创作理念,也被用来“描述经常流离于不同的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当代艺术家们的文化游牧状态。"(Anna Kafetsi,22)根据陈箴在《融超经验》一书中的描述,它是一种特殊的经验积淀和经验的融汇贯通。它意味着过去和现在、回忆和现实、西方和东方的时空交错;意味着用比较、分析、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意味着精神上的“出走”,走出自己的“茧"(Chen,Transexperiences,3);也意味着走遍世界和找到“自己”——自己的根,自己的路,自己的个性和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陈箴用“双交会”(double intersection)来描述这种经验。“第一个交会是我过去的与现时的经历之交会;第二个交会是我自己的过去和现时经历的总和与他人——如西方人——的经历之交会。”(Obrist,21)
从上海来到巴黎,陈箴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那就是“游子的位置”。他发现自己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把东方和西方加以比较;在看到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生态失衡的弊端,看到了它所孕育着的“贪得无厌”。他在保罗-塞尚经常作画的圣维多利亚山上,将人们堆积如山的弃物吊挂在树枝上——从电视机到电冰箱,从玻璃瓶到旧轮胎——把由于物质过剩而破坏生态平衡的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在纽约PS1博物馆展出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把由算盘和计算机搭成的经轮安置在地下室的通道口,由打算盘声,现金出纳机开关声伴随着经轮的转动,把当今“资本主义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富有成了每个人的梦”的奇特景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1995年,在国外飘泊了多年的陈箴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他已经“鸟枪换炮”了:不是因为他身上增添了几套时髦的衣裳,也不是因为他额头刻上了几道年轮的皱纹,而是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有了崭新的视角,有了更敏锐的洞察力。这就是一个“游子的视角”,一个能对过去和今天、东方和西方加以比较、分析与批判的“视角”。他不仅看到了一个高楼耸立的“新上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而且看到了一个在高楼的阴影下正在逐渐失去其魅力的“老上海”,一个和他一起长大的过去的上海,以及与这个“老上海”并存的“正在失去的”,“传统的”价值观念。(Heartney,16)他看到了,当今的中国,当今的东方是东西文化冲突的焦点。也正是这种新与老的对比,东与西的冲突,传统的和时尚的搏斗,激发起了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创作灵感。于是,《日咒》、《游戏桌》、《福倒福到/佛倒富到》、《催生》、《夜咒》等相继问世。
陈箴在他的“融超经验”一书中提到了“精神出走”的问题。多年的“浪子”生活使他体会到:只有勇于“走”出自己的“茧”;把自己置身于“他文化“的环境里,才能更清楚的认识自己本土文化(native culture)的特质和精神(Chen,Transexperiences,3);改变和运动是人生成长与成熟的必经之路,而“出走”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根的移植。“融超经验”是陈箴发明的词汇,他以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赋予了这个词汇以丰富的内涵。
陈箴装置作品创作灵感的由来和语言特征
如果我们说,陈箴创造了一种有助于东西方人沟通的艺术语言,而这种语言又不归属于任何的一种现成的艺术派别,那么,他的艺术语言有哪些特点?他的创作灵感又来自何方?
量体裁衣(Site Specificity):陈箴的装置作品大多都是为某个展览地点“定做”的,这类作品在拉丁文中被叫做in situ,在英文中被称为site specificity。无论是在传统的美术馆里,还是在非传统的展出环境中,每做一个项目,陈箴都要去实地考察。在作品构思的过程中,他不但会分析这个地点的物理空间特点,而且会把地点的人文、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地域政治的(geopolitical)语言环景都考虑进去。他把这种对展览地点所做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比喻为“记者的工作”(陈箴艺术笔记[2])。而考察和构思的过程对陈箴来说,是一个他与特定地点的“看不见的人文背境”(invisible cultura context)“对话”的过程。所以,如果说陈箴的“融超经验”是他创作构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那么,带着“融超经验”的他与特定地点那个“看不见的人文背境”的对话,则经常是陈箴创作灵感的发源地。这样的对话是一种能够迸发出火花的碰撞。陈箴用“短路现象”来描述这类“创作中处于最兴奋状态的”的碰撞。他说,“……艺术家每次与不同的背景因素相遇的时候,均会在不同的层次,范围,力度上产生冲突,对话,一种‘时空召唤’或互为转换,即‘短路’现象。”(Chen,Chen Zhen:Invocation of Washing Fire,162)
陈箴所提出的“与‘看不见的人文背境’对话”的理论,以及他那些把自己的经历与特定地点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深化了他in situ作品的内涵。此外,与一般in situ的作品不同,陈箴的作品还经常会把“特定地点”处理为更大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环境的缩影和典型,以此起到举一反三的隐喻作用,因为他经常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命题,如“精神和物质的冲突”,“战争与和平”以及“种族平等”等作为他作品的主题。他认为,隐喻“是一种表达哲学思想的方法。中国人喜欢用故事来引申出深刻的含义”(Heartney,16)而陈箴作品中的这些永久性的主题,使他的作品既出自于特定的地点,又超越特定地点的范畴,从而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例如,他的《绝唱——各打五十大板》,虽说这一作品,是陈箴对1998年中东危机作出的反响,是当时他为以色略特拉维夫美术馆定做的装置艺术。但是,作品中涉及到的“自我约束”,“待人宽容”等佛教思想却适合于化解小到家庭纠纷,大到种族和信仰的冲突,以及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各种类型的争端。所以说,他的这一作品既萌生于特定地点,其意义又超越了特定地点的地域范畴。


借鉴成品(Readymade):与今天不少前卫艺术家相同,陈箴无疑受到观念艺术的影响。他作品的原素经常是人们熟视无睹的日用品(ready-made),如床、椅、柜、桌等。他把它们进行解构(deconstruct),重新回炉(recycle),重新组装(reconstruct),并把它们放进新的结构关系和背景中(relocate),以使这些物体从它们本身固有的实用性和物质性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当今"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实质所在。观念艺术的鼻祖马赛尔-杜相(Marcel Duchamp)认为,在审美的过程中,为了使物体的美学价值(而不是其实用价值或其物质性)先入为主,艺术家必须改变日用物体的原有状态。陈箴在他的作品《圆桌》中把29只椅子镶嵌在一张大圆桌周围,改变了日常生活中桌椅间的关系;在《绝唱》中,他将动物皮绷在椅架和床架上当鼓面,改变了椅子和桌子的实用性;而在《日咒》中,他将马桶改装成编钟的形式悬挂起来,使马桶消失了它们日常的功能。这些观念艺术的实例都是艺术家“先发制人”的手段,用以使观众首先注意到艺术处理的人工味,从而,把日用消费品从“实用”升华到“审美”的高度。陈箴不但吃透了杜相理论的精髓,还在杜相的理论上又迈进了一步。在用成品创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同一个物体,在不同的作品中,由于它的用法,以及此物体和他物体的组合关系不同,可以引伸出不同的意义。以木马桶为例,在《日咒》中,它以古代编钟的形象出现,是中国“古老的”、“东方的”、“传统的”、“精神的”象征。它被用来和一堆代表“现代的”、“西方”、“时尚的”、“物质的”组合物作并置与对比,以表现中国改革与转形时期共产主义的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结合所引起的新旧价值观念的共存和冲突;在《瞑想椅子》中,它以耳机的形式出现,表现大脑的思考作用,及其被清洗的可能性;在《游戏桌》中,它被用来暗示陷阱;而在《会诊室》中,它又成了中药罐。陈箴经常在不同的作品中使用同样的日用品,而每一个“同样日用品”的真正含义,只有在其自身和周围物体与环境的关系中才能得以萌生。就这样,他用对成品的解构、重构和重新定义,来赋予日用品以崭新的艺术生命。
东西融合(Cultural Hybrid):陈箴的装置作品经常把中国传统的视觉元素和西方当代前卫艺术的游戏规则组合在一起——他把语义以视觉符号和语言结构的形式,精心的编入了这种他持之以恒地运用了十多年的组合——旨意使东西方观众在解读他作品的过程中,竭力去了解“另一类人“(the other')的文化。要读懂他的作品,东方观众需要了解西方当代前卫艺术的策略和游戏规则,而西方观众则需要了解中国各种传统符号的所指,其中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教教义和仪式的符号、(如《绝唱》中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教义和佛教仪式)、谚语(如他作品的题目《福倒福到/佛倒富到》)、成语(如他作品的题目《有钱能使鬼推磨》、和兵法(如他的《游戏桌》中所用到的“三十六计”)等等。自然,不知道“马桶”是什么的西方观众,是无法理解“马桶”在《游戏桌》这一作品中为什么会成为“陷阱”,也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游戏中,“你进球越多,就输得越惨”。同样,如果你不懂中国民间把“福”字倒挂是什么意思,你就体会不到陈箴在他的《福倒福到/佛倒富到》中,用同音异义的题目讽刺当今社会“拜金”现象的锐利触角和幽默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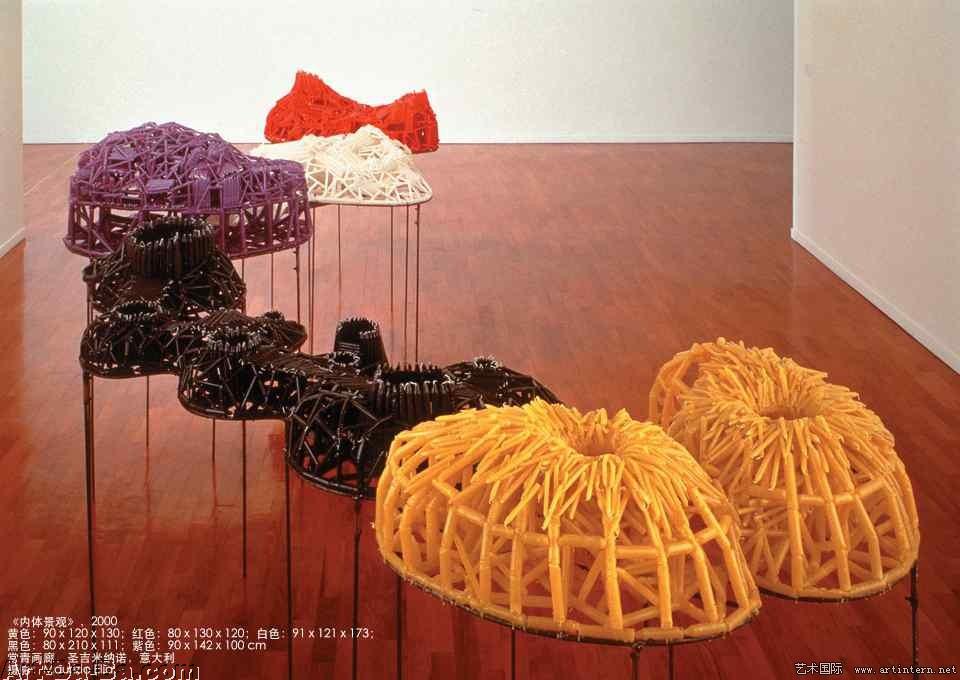
尽管陈箴的作品往往采用东西结合的视觉语汇,他认为,多元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多元文化是要在思想上高度的冲突(conflict)和融合(fusion),才能对人类有贡献。”(陈箴艺术笔记)
悖论(Paradox):悖论是陈箴艺术语言中常用的战术。和很多关心人类社会发展的艺术家一样,对“病态”的社会现象,陈箴会本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信念去暴光和批判。而陈箴在这方面的优势,是他对社会问题敏锐的洞察力,精确的艺术表达能力,以及顽童般的,带刺的幽默感。托尼-格雷罗(Tony Guerrero),当时在任纽约当代美术馆(MoMA P.S.1)展览及运营总监,原陈箴助手,在一次访谈中告诉本文作者,“陈箴非常善于发现问题,并善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陈明,访谈笔记)不仅如此,在用视觉语汇提出问题的同时,陈箴还会用“悖论"的手法,把锋芒隐藏在诙谐和幽默之中。使观众“吾”在震惊和嬉笑之间。在谈到创作过程时,陈箴曾经说过:"我工作中最兴奋的状态是当两件以前不搭界的事相遇,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对比,矛盾和对抗的关系。”(Heartney,16)他的《圆桌》、《游戏桌》、和《福倒福到/佛倒富到》都是运用这种悖论手法的实例。
就拿《圆桌》来说,这个作品是1995年陈箴为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日创作的。它以一张550cm中国式圆桌为主体形象,被安置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楼前。圆桌的中心是用工整的中国粗体字排列而成的联合国十四条主要章程。围绕在圆桌四周的是艺术家从五大洲收集来的29张椅子,用以代表联合国的会员国。在中国,圆桌是传统中“合家欢”和“喜宴”的典型形象,也是统一、和谐和对话的象征。在国际政坛上,它又让人联想到联合国“圆桌会议”,并意味着讨论、谈判、政治交易以及权力上的相互牵制。咋一看,陈箴的《圆桌》洋溢着一片和平共处、皆大欢喜的佳节气氛。然而,当人们走近圆桌,仔细品味时,其作品中的幽默感与悖论便油然而生:圆桌边有29张椅子,但是竟没有一张可以让人入座;因为它们都被镶嵌在桌子台面的周边。其中有一张椅子甚至“背道而驰”,它是一张来自教堂的祷告椅。它的椅背朝着桌心,而面对着联合国大楼,犹如一个虔诚的教徒,双膝下跪,在为和平“祈祷”〈Chen,Invocation of Washing Fire,159-160)。这种戏剧性的强烈对比,颇具“笑里藏刀”的效果。也正是以这种悖论的方式,艺术家一方面诙谐地披露了联合国作为一种权利机构,日常中所遇到的这种不协调、不统一的窘境,从而对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否真正沟通,达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提出责疑;另一方面,他又用每一个椅子在桌边“各守己位”的组合方式强调:由于利益的冲突、文化上的不同。真正的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存只有在各国互不干涉内政、共同遵守国际条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陈箴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家。他意识到,绝对的平等协商只是一个愿望,而不是现实。他鄙视非正义的行为,渴望通过自己的艺术为正义和明天的更加平等而呼吁。
和《圆桌》相同,在《福倒/福到-佛倒/富到》中,陈箴用倒挂的佛像和堆积起来的汽车/电器设备零部件并置在一个具有庙宇外形的结构中,以抨击扭曲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而作品的题目,又以同音异义的悖论手法,妙不可言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同样,《游戏桌》中的游戏规则“进球越多,就输得越惨”也异曲同工地在貌似玩笑的游戏中,道出了“谨防陷阱”的真谛。
跨学科和多媒体(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 and multi-media):此外,陈箴的装置作品不受媒体和学科的限制。比如,在《绝唱——各打五十大板》中的击鼓声、喇叭声、舞蹈和宗教仪式都走出了传统视觉艺术的框框。象《日咒》中洗刷马桶的声音和从电视、收音机里录下的“混合人声”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能还是戴奇艺廊的艺术顾问杰弗里-戴奇的话:


陈箴的雕塑不仅仅是给人看的;他是让人体验的。他最大胆一些的作品带有音响,节奏,香味,并邀请观众与作品进行互动……我有生以来对一个艺术品有着最强烈的体验和最深刻的印象是在我随着击鼓声走进哈拉尔德-塞曼安装好《绝唱:各打五十大板》的威尼斯军械库。三十个人在那儿欣喜若狂地舞蹈。他们倾心地打击着悬挂着的几十个床和椅子。这些床和椅子的框架被绷上兽皮成了可以敲打的鼓。在我所经历过的艺术作品中,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品能够和这个作品的物理的,音乐的和视觉的综合强度相匹配。"(Deitch,12)
对陈箴来说,跨学科不仅是对艺术家而言,而且是对观众而言:"跨学科的概念与观众如何去解译他们所看到的和触摸到的有密切关系。”(Obrist,23)
陈箴在美国创作的作品
《荒野》


Field of Waste: Chen Zhen, The New Museum Annual Report, 1992-1994
《荒野》是陈箴为纽约当代艺术新美术馆(The 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创作的一个装置艺术。这也是他在美国创作的第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反映了他观察中的两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处境。据新美术馆的年度报告,“在美术馆主厅的装置作品是一个月来艺术家驻馆创作的总结。这个项目,无论是在室内空间安排上,还是在美术馆所处的中国城和市中心服装区的成衣厂群的地理位置,都是为新美术馆量体裁衣的。”在了解和分析了由中国移民潮在美国引起的文化之间和种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化和共存关系后,陈箴通过这个作品,对移民的目的和价值提出的疑问。
在宽敞的展览大厅里,陈箴把展览厅的大空间用沉重而高大的铁丝网墙分割出一个如“集中营”一般令人窒息的封闭性空间。但是,铁网的大门则敞开着,通行无阻。在网外过道上行走的观众,可以通过铁丝网窥视网内的一切。在铁丝网内的一个尽头,三台缝纫机连带着一条通过东拼西凑织成的彩色布毯。在这条近20米长,蜿蜒地向纵身伸展去的布毯中,参错地夹杂着中国国旗和美国星条旗。布条的另一端,与之相接的,是又一条长达20多米连绵起伏的“纸灰山”。
在了解到成衣厂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的主要生存手段之一后,陈箴用燃烧过的旧报纸搭成“纸灰山”,来代表老一代的中国移民,并暗示其无组织性和无文化状态;他用彩色的布料织成的地毯,来代表新一代中国移民,并表明他们受教育的背景以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虽然,新一代移民似乎比老一代移民强,能和美国人共处,并在冲突中影响他们,但从整体上看,他们还是象他们的前辈一样,被埋没在这个一望无际的荒野中。和这儿所指的“荒”字不同,陈箴题目中的“荒”是打“荒废”用,而不是“荒芜”或“荒凉”的意思。
在谈及这个作品的构思时,陈箴写到:
象木炭一样乱糟糟的报纸灰,用衣服和旗帜七拼八凑缝制起来的地毯,围栏的隐喻性景观,以及安装起来的旧缝纫机和材料,构成一个触目惊心的环境:以示无计数人的生命包括精神和物质之恒周性的生产和毁灭。这是一个原始的,并再经利用的“荒野”。(陈箴艺术笔记)
在观看这个作品时,细心的观众也许会情不自禁的发问:既然艺术家有意表现令人窒息的环境,又为何把大门敞开。而敞开的大门也就是这个作品提出的问题所在。用铁丝网墙分割空间,使人不禁联想到集中营和监狱。然而,和集中营或监狱不同,敞开的大门却暗示着选择进出的自由,而随着移民潮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在去留上一般都有选择的自由。陈箴是用敞开着的大门,点石成金地发问:为什么能离开却不离开?"中国人和美国人无论在传统观念及政治和经济制度都代表了两个极端,"他们有可能共存和合作吗?什么才是移民的目的和价值?(陈箴艺术笔记)
《日咒》

步入展览厅,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貌似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编钟”的装置。与真正的编钟不同,在这个装置中,一系列内部装有扩音器的中国老式马桶,经过变异后,代替了“钟”的位置和发声功能。马桶被悬挂在一个三面封闭的厚重的木质框架上。扩音机里,交替地传出清洗马桶的水声和朦胧的“混合人声”。被封闭性框架簇拥着的,是一个用捆绑起来的电子电器设备构成的球体。这个作品是陈箴在1996年为纽约的戴奇艺廊创作的。
《日咒》可能是陈箴作品中最有争议的一件。首先,那些最明显的争议是由于他在这个作品中选用了“马桶”这个视觉元素而引起的。陈箴非常清楚这一点:
亚洲艺术家和西方艺术家对我的作品经常作出不同的反映。就拿去年我在纽约为杰佛里-戴奇做的《日咒》为例。在这个作品中,我用从上海运来的马桶做了一组中国的编钟。马桶现在正在逐渐消失,它象征着老城市,老文化,不发达地区等等……中国观众说,太可怕了,这些物件又丑又臭,绝对不适合在艺廊里展出。西方观众说,那些是美丽的中国旧物件,它们看上去很不错。但是,后来当它们意识到他们看到的是马桶,情况就不一样了。(Heartney,15-16)
陈箴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开放性建筑“(陈箴艺术笔记),不但允许别人对它们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意地”创造误解“,挑起“争议”。因为,他认为,只有“争议”才能使人们进入”思考的状态。”(陈箴最后的笔记)当埃莉诺-哈尼问他是否一直在玩“误解”的游戏时,陈箴毫不含糊地回答:
我不是在玩“误解”的游戏,而是在创造“误解”。这就是我思维的方式:我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一点。(Heartney,16)
在他的笔记中谈到这个作品的创作观念时,陈箴写到:
这个作品的主要制作材料是上海老式马桶。对我来说,它的魅力在于,首先它不是艺术作品,而是日常生活用品。中国人对马桶有两个概念:其一,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件丑陋的物品。其二,对那些相信迷信的人来说,马桶是“生儿育女”的宝座。它能帮人传种接代。这是一件隗陋但却有巨大价值的物品。这个物体的双重意义是和我想要在这个作品中找到并表现的内在性质十分接近。此外,于西方的城市政策相吻,马桶是一种被遗弃的物品,这种物品正在逐渐销声匿迹。所以,它和“西方”,“现代化”,以及“新陈代谢”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马桶”是陈箴制造“误会”的手段,那么他《日咒》中的“咒”字,则是他挑起“争议”的一种策略。“据他说,《日咒》的想法来自于他在文革期间的个人经历。他认为,每天清晨洗刷马桶和晨读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麻木(mantel insensitiveness),而这种麻木不仅历史上有,当今的社会中也有。(陈箴艺术笔记)
《日咒》中的“咒”字,因为经常被用于贬义,人们往往会忽视它褒义的一面。联系到陈箴这个作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他“文革期间的个人经历”,而“文革”又是一个人们“争议”的热点,他以“咒”为题去掀起“争议”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事实上陈箴这个作品中的“咒”包含着褒贬的双重意义,正如他在他的作品观念声明中指出:“‘咒’,英语叫‘incantation’,有褒贬两意。它可以打‘法术和语言魅力的编织’用,也可以打‘致命的诅咒’用。“他认为,“《日咒》的题目加深了这件物品的双重意义。”(陈箴艺术笔记)
也正是因为陈箴《日咒》的这种双重性,不同的观众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对这个作品进行不同的解译。
在上海正举办的“陈箴:不用去纽约巴黎,生活同样国际化”的陈箴艺术展的报道中,陈箴的《日咒》被理解为对物质社会弊端的抨击和嘲弄。在潘雨希看来:
展览中,巨大的编钟交替发出“水清洗马桶”和广播中的“混合人声”。他抓住了马桶“需要清洗的特质”,把它们和工业社会中“能发声”的电视机、收音机等并置在一起,用水的自然的力量来“净化”消费社会的“污浊”思想。(潘雨希)
陈若轻认为:
此件作品对当代物质社会、信息社会的内在弊端,以及潜在危机进行了“宗教唱诗般”的嘲弄。(陈若轻)
法国华裔艺术策划人侯翰如把《日咒》看成是表现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和冲突。他认为,陈箴试图通过《日咒》展现一幅多媒体的全球化画面: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是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并在这个画面里反映出一个栖息于东西方之间游牧人的批判性的眼光。
与侯翰如的看法不同,加拿大艺术策划人,蒙特利尔国际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克劳德-高瑟则认为:
陈箴的这个装置作品包含着从西方和东方来的物体,这并不表明它就是一个有关东西方关系的作品。这个作品更象是反映个人和社会群体在抓住一种躲避他们的文化时的那种痛苦,而这种文化是由他人领导的。这个作品是对那些在被社会机器剥夺了说话权利的地方的届时的和新的现象的一种查询。这个作品的表现形式——既沉重又脆弱——和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意义是再完美贴切不过的了……《日咒》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它刺激和要求一种觉醒。我们是否只是对交流之困难袖手旁观,还是积极的去保卫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去保卫一种文化?
陈箴的这个作品确实是一个“开放性建筑“。这个“建筑”为东西方的交流提供了“说话”的平台。而对他这个作品的解释——这种解释存在于艺术家的思想和评论家的思想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反射出评论家的视角及其所处的位置和语境。
《中空》


“大地中的宁静”是一个系列艺术展览计划。这个计划的策划人,美国的法兰斯-莫兰(France Morin),在1996年邀请了世界各地十位著名艺术家,去美国缅因州的震教村(Shaker Village,夏克农庄)体验生活,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艺术创作和展览活动。陈箴也是其中的一个。
缅因州沙贝斯戴湖畔的夏克农庄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住有幸存震教徒的社区。从奔走于频繁的跨洲艺术项目之间,急转到栖息于这片震教徒的净土,陈箴感到了文化冲击的力量。他在驻村体验生活的日记中写道:
吃饭既不是为了生活,亦不是象我一直认为的“要赶时间”,也不是为了享受。吃饭是一种礼仪。吃饭是一种让身体的需要与精神的需要同一沟通的时刻。或者说,一个让物质与精神均消失的空界状态。震教徒(Shaker)是这样活着的……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这样活着的呢?……好像我们没有时间概念。(陈箴艺术笔记)
而当他看到,震教徒在祷告时连电话也不接,他感慨的写道:“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可以有一刻,这一刻比电话铃更重要,比人,人对铃声的生理反映更‘迟钝’”。与震教徒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加深了他对他们的了解,也唤起了他年轻时在西藏与藏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精神上得到启示”的日子的回忆。
在现代社会中,“坐”谓何意?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人真去注意它了。今天,人们实际上已经不懂“坐”了……从震教徒的坐中,我们可以看到:坐主要是hand to work(让手去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赚钱谋生,而是与另一个箴言联在一起,那就是heart to God(把心交给主)。亦可说,劳动是祈祷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物化的,身体化的精神外露。而所有这些均从“椅子”上度过。(陈箴艺术笔记)
“在展览会上,有不少作品采用了‘虚空’这一复杂的隐喻;而陈箴的《中空》把虚空的空间视觉化了,那是一个他自己的文化与震教徒文化的对话”。莫兰在她题为“中国有一句谚语是这样的……"一文中接着描述到道:
在一个被从中国尼姑庵运来的一系列木质窗框围绕着的封闭空间中,悬挂着一个封闭性的圆形摇椅,以示一个大空间中的小空间。虽然,木架子和椅子的工艺特点使人联想起震教徒的设计,这个作品中围起来的那个受到保护的空间,又使人联想到禅宗中永恒的沉思那种静坐。观众只能从窗筛栏的洞隙中窥视这个椅子,却触摸不到它。在围栏的唯一开启处,悬挂着一个由中国家具做成的祭坛。祭坛上摆着一些类似盛水和放大米用的坛坛罐罐。这些日常用品一般不会被当作精神产品,虽然他们来自中国,在这样的语境下,它们可能被用来反映震教徒崇敬日常活动的神圣起源,而这个起源也是创造力的由来。陈箴构思了一个两种文化相交的空间,一个成长的空间。(Morin,18)
莫兰为陈箴在展览会中的作品做了一个比较详尽并有洞察力的描绘。可惜的是,她忽略了陈箴构思中的一个更大的封闭性空间:
在展览厅里,《中空》将被挂在四周墙上的另一个题为《夏克农庄日记》的27幅平面作品所环抱。如此,《中空》将以一种独特的,现场交换的方式面对着《日记》——这种现场交换,即把私人的(日记)通过人物头像变成了和震教徒以及观众公开的对话;而把公共的(椅子)则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如果说“涅槃的椅子”暗示着“圆寂”,那么与之相反,这些日记则反映了“日日度的生活经历”,它们使我想起了一句佛教中的格言:“生活意味着日复一日的经历。”(陈箴艺术笔记)
陈箴通过这个作品提出了,在当今这个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毫无“精神境界”和“片刻安宁”的世界上,我们如何去寻觅“自我孤独”,找到“一席空野”。(陈箴,《陈箴》,96)
常言道,时事造英雄。陈箴的装置作品和艺术理念出自于多元文化正处萌芽状态的全球化大环境里。无论是以文化冲突或文化融合的形式出现,它们丰富了多元文化并促进了它的发展。陈箴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六个年头,但是,他那自强不息地为东西文化交流而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艺术家,并被载入世界艺术的史册。
作者简介:
陈明,曾在上海青年话剧团和华盛顿市佛爵莎士比亚剧团工作,并先后在上海戏剧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肯尼索州立大学任教,现任肯大(College of the Arts,Knnesaw State University)终身教授、舞台美术设计师。
参考文献
陈若轻.“陈箴:不用去纽约巴黎,生活同样国际化.”凤凰艺术.2015.网络.2015年5月29日.
陈箴.《陈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6页.印刷.
陈箴.陈箴艺术笔记(unpublished)
Chen,Zhen.Chen Zhen:Invocation of Washing Fire.Prato-Siena:Gli Ori,2003.433-450.Print.
Chen,Zhen.Transexperiences.Kitakyushu:Korinsha Press&Co.Ltd.,1998.1-end.Print.
Deitch,Jeffrey."Sculptor as Doctor."Chen Zhen.New York:P.S.1Contemporary Art Center,2003.12.Print.
"Field of Waste:Chen Zhen."The New Museum Annual Report,1992-1994.1994.Web.30May,2015
Heartney,Eleanor."An Interview with Chen Zhen."Chen Zhen. New York:P.S.1Contemporary Art Center,2003.15-16.Print.
Kafetsi,Anna.Introduction."Chen Zhen:Metaphors of the Body.Athens: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2002.22-26.Print.
Morin,France."In China There Is a Proverb That Says……."Chen Zhen.New York:P.S.1.Contemporary Art Center,2003.17-19.Print.
Obrist,Hans-Ulrich."Conversation with C henZhen."Chen Zhen.New York:P.S.1Contemporary Art Center,2003.20-25.Print.
潘雨希.离世15年的陈箴在外滩美术馆与上海继续‘对话’”.艺术新闻.2015年.网络.2015年6月23日.
Sans,Jérôme.“A field of Energy."Chen Zhen.London:Serpentine Gallery,2001.6-7.Print.
Sans,Jérôme."Between Therapy and Meditation."Chen Zhen.London:Serpentine Gallery,2001.10-12.Print.
[1]本文中所有英文书籍的引言都是作者的翻译。
[2]本文作者有幸接触到陈箴遗留下来的艺术笔记和手稿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