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评Hito Steyerl的图像打破术
不能被话语-图像驯服的那部分,才是艺术。
--利奥塔《话语,具象》
应该重拍一切电影!
--朗西埃,《电影寓言》
[导语]
图像是资本对我们的身体的捕捉和捆绑。在展览中,艺术家的工作是:通过策略式地使用图像,使观众在图像面前获得自由。这自由的意思是:观众的身体在展览空间恢复全整,每一个动作都像舞蹈的一部分了,是主演了。图像政治的第一大原则,就是:在艺术工作去戳穿每一个图像背后的诡计,不让其去粘吸观众的目光和身体。艺术家将自己的方法全部裸露在观众面前,像在布莱希特在教育剧中所做的那样。
HitoSteyerl在这方面堪称我们的当代楷模。我们下面将通过分析她的艺术创作立场和一些作品,来看她的一些图像政治主张对我们今天有何意义。
1-基本立场
Steyerl将艺术当作一种占领的行动。艺术是一种占领与反占领之间的拉锯。我们的艺术地场总是已被资本和权力占领。所以,当代艺术的每一种行动总须从反占领开始。她一再举艺术机构的实习生作例子。研究生想要去艺术机构实习,还须申请!这等于是请求被剥削!如何从这一如此消极的占领(occupation最负面意义就是去占到一个位置、职位)进击,去占领?这问题等于是在问一个实习生如何搞当代艺术了!
像戈达尔那样,Steyerl反对一切视觉再现,同时也反对为了所谓批判而加以文化、政治再现,也就是说,反对下面这种常见的做法:站到某一立场上,去替某一部分人说话。她认为,我们(欧美艺术家)身处“后民主社会中”,艺术的功能只是这一社会的自我维护所需的话语系统的一部分。一个进步艺术家应该将自己看作罢工的工人,拒绝了社会劳动分工,像罢工的工人那样,要与这个制度耗到底,越悲壮,自己的行动和坚持才越有说服力,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像罢工到底的工人最终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一样。
因此,在后民主社会里(将艺术资金充沛的当代中国看作这样一个场地,我觉也未尝不可),艺术家做的是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这个说法来自中世纪,指年青人对各种立场和利益不作选择,宁愿作雇佣军,哪个国家的钱给得多就为哪个打仗,但没仗打时,自己也能完全维持自己的生活。今天解决自己的社保和劳保,是艺术家的工作的一部分,但须做得更多。这样,他们的整个生命才能都成为艺术的材料。
当代艺术场地内的矛盾 Steyerl这样看待艺术场地:The art field is a space of wild contradiction and phenomenalexploitation. It is a place of power mongering, speculation, financialengineering, and massive and crooked manipulation. But it is also a site ofcommonality, movement, energy, and desire. In its best iterations it is aterrific cosmopolitan arena populated by mobile shock workers, itinerantsalesmen of self, tech whiz kids, budget tricksters, supersonic translators,PhD interns, and other digital vagrants and day laborers. It’s hard-wired,thin-skinned, plastic-fantastic. A potential commonplace where competition isruthless and solidarity remains the only foreign expression. Peopled withcharming scumbags, bully-kings, almost-beauty-queens. It’s HDMI, CMYK, LGBT.Pretentious, flirtatious, mesmerizing.
艺术场地的内部矛盾,等级与剥削的两极,都要在促使艺术家去做雇佣军:也许其使命是使两者更快地火并。

“贫图像” Steyerl认为,“贫图像”首先是图像运动地过程中的状态,只是速度不当的拷贝而已。但观众对清晰度的期待实际也是有问题的。他们认同的那个图像等级,本来就是成问题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Steyerl认为,在我们的图像工作中保持数码不确定性,倒反而是能保留和利用到更多的真实。同时,越“贫”的图像,抽象程度就越高,使身体及其观看越活跃。同时,“贫图像”在我们的政治斗争中还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工具。连恐怖分子都很懂得如何利用“贫图像”来获得政治上的先进性。
而在某些时候,如威尼斯双年展上纪念卢旺达大屠杀的那些作品中,“贫图像”是对生命的更好的尊重,因为“贫图像”更能表达生命复活的过程。
而在私人领域,“贫图像”更能传达亲密和神秘,更能传达非-公共空间中的日常。
美术馆与工厂 美术馆里的政治电影像戈达尔说的那样,是一种妥协吗?Steyerl说,不是的。工厂电影这种状态在美术馆里会得到更好的考验和提升。针对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她指出:由于影像的时间长度、体裁、风格、观念、政治立场之百科全书般的汇集,原来适合工厂的政治电影,在美术馆空间里落下一个汇总后形成的多样的立场和观念的星丛,是一架好的乌托邦机器。

她认为,沃霍尔的工厂是今天的新美术馆处理影像作品的学习样板。政治电影的待遇,就是影像作品在他的“工厂”里的待遇:生产现场、展示现场和艺术-文化梦境的三者重合。因此,今天的美术馆应该成为工厂。而我们今天的新美术馆很多也正是由从旧工厂里改造过来。
甚至说,今天的美术馆里的确已成了观看的工厂。Steyerl引用艺术家Beller的话说,看也是劳动。她认为我们应该鼓励观众来做蒙太奇,并将观看到的破碎影像和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做进现场作品中去。美术馆空间里音响也不好,使观众容易走神,中途走开,也都不要紧。观众是联合策展人。他们来最后缝合。
2-斯戴耶(Steyerl)专门为Dokumenta12制作的视频《亲爱的安德莱娅》别开生面,展示了一种痛快淋漓的图像打破术。艺术家假装自己是20年前被拍的SM捆绑艺人,去采访问当时的摄影师,以假乱真,将所有当事人都绕进里面,彻底瓦解了我们观众对于SM业和纪录片拍摄和图像的见证性的全部预判。

她拿着色情杂志(她用做旧的方法PS上去的)去东京千辛万苦地寻访当时的摄影师(他其实是被陷害的),说当时我刚出道,这是你帮我拍了第一张,今天我来怀旧、寻根了。因为拍得太多了,摄影师也记不清了,就说算我拍的吧。在一阵尴尬之后,后者和捆绑师们就开始抱怨起来: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过去真的是好时光。那时警察追得紧,动不动要来查抄,拍捆绑,观众看了才觉得刺激,杂志看的人多,在人们眼里,我们也是像崔健和艾未未那样的英雄呢。如今警察也不大来管了,基本没有查抄了,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但看的人就因此觉得得没劲了,杂志不大有人买了。说着说着,大家就像同学会一样围在一起,不管到底在过去有没有过瓜葛,都顺水推舟地感叹起好日子早就过去来,很怀念二十年前的那些刺激岁月喏。
于是拍摄就开始走偏,采访起新入行的那位像当时的“我”自己那样的带路的皮绳女演员来了。
她认为,身体被捆绑了,有观众和读者仔细地来盯着看了,才能感到自由,否则,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完全松绑着,她们反而随时感到不自由。被捆绑,才自由!她们于是只能像来健身房一样天天来,变成一种必需,挣钱还是第二。她们只有在这里才找到了革命根据地,才有她们的解放区和党组织,大有在SM里终于自我实现,退休前可以写书卖鸡汤的味道,狠不得读MBA的学位进来做呢。



结果,这个助手和配角开始抢戏,成了这个片子的主人公。整个电影就这样被解构了。
这是艺术家刻意发起的一次很积极的自我捣乱!拍摄失控了。片子最后就像伍迪.艾伦的《来自开罗的紫玫瑰》的后半段了:演员、拍摄工作组、全体辅助人员、评论家和观众和围观者都摊开手,问观众:我们这是在为谁忙?人家投资要挣钱,我们就得这样替他们忙个不亦乐乎?我们自己的日子过不过了?老子今天不干了,我们狂欢吧!大家一起来!

到片子最后,制片问艺术家:我们这样拍你满意了吗?艺术家竟无从回答,傻眼了。
这个作品所以是一个反-作品。观众跟着导演出发,却找到了他们并不期待的东西。但是到后来,观众在电影里面只遭遇了与他们自己在早九晚五的生活中遭遇的一样的真实的东西。作品通向我们天天撞墙一样面对的真实!真是打开窗户说亮话了。解放每一在图像,同时解放图像周围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关系,艺术家在这个作品里硬是做到了!
但艺术家的手法却令我们惊叹。她找到一组图片,然后就伪造自己的身世,根据手里的照片弄出一大堆的史实和遭遇,去实地寻访。在寻访的过程中,这一组照片里的所指,全被像煞有介事地拖到了当代之中。作品中的内容,对于观众而言,仍只是可疑的证据,但全被艺术家当作猛料执意地去执行到现实中。在观众眼里,艺术家成了一个很二的侦探。实际上,整个作品在告诉观众,千万别信你在图像中看到的任何东西,你以侦探或卧底的眼光一看,就会发现,它们放那里给你看全是蒙人用的!

史戴耶的作品总是上半部分是破案,下半部分是面对现实时的唏嘘。到最后,艺术家和观众都从照片对于他们的专制中解放出来,浑身都轻了。图像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必须摆脱才好的。图像只是我们的死皮,必须快点将它揭掉。
艺术家弄的是一种图像摆脱术,在教我们如何摆脱图像对我们的粘缠。她脱身时,观众和演职人员在电影里开始狂欢了。
3-斯戴耶是典型的集艺术家、学者和活动分子三个角色于一体的混江龙(狄奥尼索斯式的)。她演示了一种批判,但很独特,完全是艺术家式的批判:不当真,先搞乱再说。她是艺术家里面的教练式人物。我们知道有的球员在踢球时就已很像教练,艺术家里也有这样的品种。这种创作是教学法式的:一边创作,一边奔着教人的目标去。这个方向上布莱希特是祖宗。
在最近到BANK画廊展出的《流动公司》中,Steyerl以写一部数码《资本论》的野心来拍一部论文电影(essay film),将流动性当作一切人事后面的真正动力。整部电影总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动画效果制作介绍:如何动画出好看的水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教学法式创作。


片子的故事都围绕水或流动性来展开,但所要揭露的却是:这种流动性在今天是可以人为地制造的,也许只是一种动画效果,做真来很容易。
与《资本论》不同的是,作者不是系列地揭露,而是在最细节处下刀,但很快就心不在焉、没心没肺地进入下一个话题,以为是离题了,结果不经意又回来补一刀。她是在一片嘻哈中心不在焉地完成了动作。
也许今天的批判型艺术家正经受这样一些高强度、高运筹的训练,才能达到批判的深度。批评的深度是由某时代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选择、快乐、抵抗和执着来构成。艺术家要不输给知识分子,就得在策略上下功夫。史戴耶在这方面有过人之处。
批判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两个作者之间所启动的两种历史之间和两个主体性之间的对话。批判者或批评家不应该是一个醉心于过去的真理的人,而总应该自我中心地滑向当前。它是当场上台去戳穿魔术的那个人。史戴耶的方法是:潜入记录过去的图像周围,想各种办法去颠覆它,像成功揭穿了一场魔术后那样,她带着观众凯旋。

在这一展于上海BANK空间展出的《流动(资本)公司》(Liquidity Inc.)中,斯戴耶的批判被拉到了很大空间里:金融危机与气候危机哪个重要?流动性短缺可以用印钞机来填充,气候黑洞如何来填补?如果我们来开一个提供流动性的公司,我们应该做什么业务?艺术家们的关怀和批判,不正是在许诺这样的关怀和批判吗?他们想过后面的连带责任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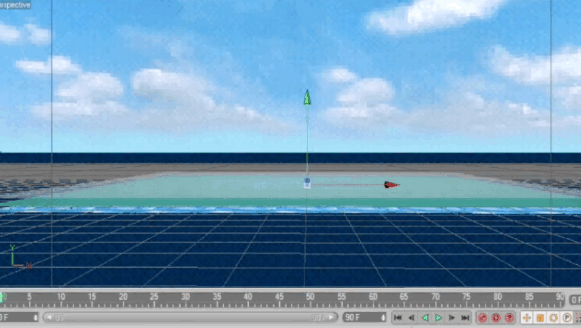
这个作品将批判拉到了生态、感性、审美领域,却仍能在对媒体理解和话题的操控上玩得转。要是抛给知识分子们手中的批判理论,这一大堆话题,是很难处理这样举重若轻的。这也许是欧洲艺术家的长处: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在与公共知识分子别苗头,在重大的生态-政治问题上,他们想平等地接过话头,来发表意见。史戴耶发表在e-flux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寄托着这样的大的关怀。
在BANK的同一展览中,她与《第四公民》的导演罗拉.柏翠丝的访谈,进一步揭露了斯诺顿事件的编造的成分。她几乎又像王海打假那样地揭穿每一次图像上的弄虚作假。令人吃惊的是,她自己的立场却是:必须虚构!在纪录片制造中,正常的编造是必需也必须的!这就引出了如何拍纪录片这一政治问题。是我们加进去的虚构,才使纪录片有意义。与其围绕图像去做我们的阴谋论,我们还不如主动潜入图像,去策反其中的现实,使一切重又暴露在当代的光天化日之下。她使纪录片拍摄本身变成一种步步论争的过程。所以也可以讲她所说的essay film理论成论说文电影、小论文电影。

4-朗西埃说,由于社会中总是共识太多,“当代艺术”就成了社会中的各种“异感实践(dissensual practices)”,各种反共识的刺毛话语和实践的庇护所。只有在这一块地方,大家仍认为,你我感性之间的冲突,责疑和重建已有的感性联系,是最正常不过。当代艺术是一个新政治的根据地。所以,艺术家是不是应该在其中当一个好客的趴体主人,张罗和鞭策前来扎堆艺术空间的各种异感实践,像一个乐队指挥那样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各种新感性扇得火狂,自己也就不用忙着去土法上马搞艺术了?史戴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她在艺术领域研制各种新政治的新战术…
关系美学向我们暗示当代艺术的两种矛盾态度:要么,艺术应谦虚地为社会重建被市场破坏的秩序,要么,艺术自己应该走进社会,在美术馆和社会之间躲猫猫,像孙志刚那样,用自己的遭遇,来让刺醒社会的觉悟。史戴耶玩的是后一种。她去扮受害者,但决不是为了夺回被剥夺的权利,而是将这个转变为一种教唆术,要大家都来学样。
艺术的操作里就有世界和现实在了。艺术活动的每一步,都在捣散原有的关于地位、位置、资质和边界的局面;做艺术,本身就在破坏和改造这个真实世界或现实,不必另外再去干预和改造。这在史戴耶的图像-政治实践里很明显:将图像的意指当真,深入社会关系,在一个点上揭露出全部的猫腻。

也许,根本用不着艺术家像要去月球或火星探险那样,身上配好所有装备,去关怀、去批判、去干预、去希望,反而应该成为他们的本份:魔术师?让正在发生的,发生得更壮烈更翻天覆地些。对于他们,没有已完成的战役,而只有一次次重新去“点开”?打破一切图像,来一个,破它一个,不被它摆布,像演员一样,在舞台上对着道具大叫:我再也受不了你啦,我只想要一个人好好地呆着!
每一个图像都是可疑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故事片。必须揭穿每一个图像后面的诡计。
5-Hito Steyerl是当前高度活跃于国际艺术展览和理论的艺术家。其作品用了最新的媒体生产技术,探讨的也是图像生产中的最尖锐的内部矛盾,构成对图像政治和当代艺术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高难度挑战。

附录1:请大家观看Hito Steyerl2007年的影片《亲爱的安德莱娅》及相关访谈
附录2:请大家观看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Hito《太阳工厂》观众偷拍版。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