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文:张璐诗 (发自伦敦)

相比哲学家的身份,“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如今更热衷于从事各种能帮助别人的事,比如说严肃地解读八卦新闻、开成人网站教大家如何去“爱”,当然将写作视为照顾别人与照顾自己的他仍旧在推出新书。(图:已多年没有写小说的阿兰·德波顿透露,最近刚完成了一本关于“成熟之爱”的小说《爱的轨迹》,形式与他 23 岁时令其一举成名的《爱情笔记》相似。)
已多年没有写小说的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透露,最近刚完成了一本关于“成熟之爱”的小说《爱的轨迹》(The Course of Love),形式与他 23 岁时令其一举成名的《爱情笔记》(Essays in Love)相似。

阿兰·德波顿以“英伦才子”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知,除了写作之外,他还主持在线视频频道、办网站、开演讲,可谓身兼多职
近日,《外滩画报》特约记者拜访了德波顿一家在伦敦北部的公寓。德波顿与太太夏洛特育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分别起名“所罗门”和“索尔”,都是昔日以色列帝王的名字。德波顿在玻璃杯里为我倒下矿泉水,特意告诉我他平日喜欢听巴赫,但如果是现代音乐,他偏爱“伤感的女声”,最近常听一队名叫London Grammar的乐队。
这位生于瑞士、8 岁移居英格兰的作家以“英伦才子”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知。而在英国,自 1997 年出版《拥抱逝水年华》(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以来,德波顿一直是“普及哲学”书架上的畅销作家,他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旅行的艺术》(The Art of Travel)、《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等作品甚至被英国人当作礼物馈赠亲友。2014 年,他的新作《新闻的骚动》(The News: A User's Manual)也被视为反思今日新闻操作方式的力作。
从 2008 年开始,德波顿在作家的身份之外又变身企业家。他是非盈利性的情商教育机构“生活学校”(School of Life)的大老板,在全球 10 个国家都有办事处,通过出书、拍网络短片等方式,教大家如何“聪明又健康地生活”。在与记者交谈时,德波顿还透露最近“生活学校”加开了一个成人网站,试图“让成人故事也有尊严起来”。
B=《外滩画报》
A=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哲学的高尚地位已不复存在
B:你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哲学家”扮演什么角色?
A:几乎什么都不是,“哲学家”基本上就是个笑话。你在大街上随便问人:哲学家是什么?你会意识到,这是个近乎无效的职业。在人们心目中,“哲学家”就像一帮从中世纪来的游吟诗人,骑着马边弹琴边吟唱。哲学曾经拥有的高尚地位,如今已经不复存在,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哲学家跟大夫、神父、骑士一起,位列最权威的职业。而在今天,人们失去了对于“智慧”研究的兴趣,与智慧相关的职业要不是显得装腔作势,就是显得不合时宜,令人发笑。如今人们的信仰是科学,大家深信科学知识能解释一切困惑。当人们希望获得“智慧”时,他们拐弯抹角将之称为“洞察力”、“知识”等等,而且只相信实验室的结果:比如人们想要了解爱情的真谛,大家会去做个脑部扫描,然后请社会心理学家去分析扫描的结果。相比之下,哲学家说什么都不重要了,都显得是拿不出科学证据的随口胡谄。
同时,大学学院里一直以来固守哲学的狭隘定义,这种做派在今天的英国大学生群体里,只能引起极少数人对哲学产生兴趣。哲学这门科目基本上是死掉了。这很令人伤心。学哲学的真谛本来应该是积累知识、帮助人们建立智慧人生的。可学院派并没有这个意识,没人能在哲学系里学到怎么维系一段感情、如何善良做人、怎么能无忧无虑去度假。很多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碰到的问题,都没能获得系统的学术研究。我自己对哲学的兴趣,就是来自我对大学机器这方面缺陷的不满,还因为看了很多写得很糟糕的书。古今许多智人并不懂得怎么把书写好:像康德、罗素,他们很有思想,但都是糟糕的写手,读了半天都不清楚他们到底想要说什么。我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人的思想提炼出来,重新整理写作,以做普及。我就像个厨子,将各种原料混在一起煮,煮好以后分给饥饿的人们吃。



德波顿算得上是多产的作家,而他的作品几乎全都有中译本,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
B:哲学家明星化会不会让人们越来越难去严肃地看待哲学呢?
A: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哲学是严肃的,问题是严肃的事情到底长什么样?比如我认为喜剧表演是很严肃的,喜剧演员的任务独特而重要。换句话说,想要让一件事物在社会上产生严肃的效应,并不非得要面目狰狞、怪诞而冷血。这件事看上去也可以是很迷人的。“吸引人”在今天来说特别重要。我们生活在消费时代,没有人再相信“精英”了。从前,书籍是文明发展的果实,小孩子一定要读这本书、读那本书才能成长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现在市场为先,最大的竞争是如何去吸引眼球。
今天西方社会之所以病态,就因为吸引人注意的事物都很有诱惑力、激动人心,但都跟现实生活无关。像一部电视连续剧,很好看,可里面讲的爱情关系在现实里根本不可能。网游简直让人上瘾,但那不会启发人怎么处理好跟他人的关系,还有色情片也一样。这时知识分子们就会说,这些人很软弱,很笨,没办法抵御“低级诱惑”,去追星、追流行歌、沉溺网游,这些都不是“好人”。法语里有一个词“bien pensant”,意思是“思想正统的人”,这些人认为自己情操纯粹而高尚。可这个词在今天其实已经成为侮辱,这样的人其实是蠢货。可是每个社会都有这样傲慢的bien pensant,他们极其反对流行化、粗俗化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们将这些事情视为堕落的象征,认为俗世肮脏而可怕,坚决与之划清界限。
我有不一样的出发点。我深信如果一个人对于某些思想充满了信念,那这个人就有职责去传播这些思想,哪怕这过程意味着自我破坏。我经常对于那些对我感兴趣的事物无感的人充满好奇,经常会去想:怎么才能抓住这个人的注意力呢?怎么才能去诱惑他们,让他们对原本毫无兴趣的领域产生好奇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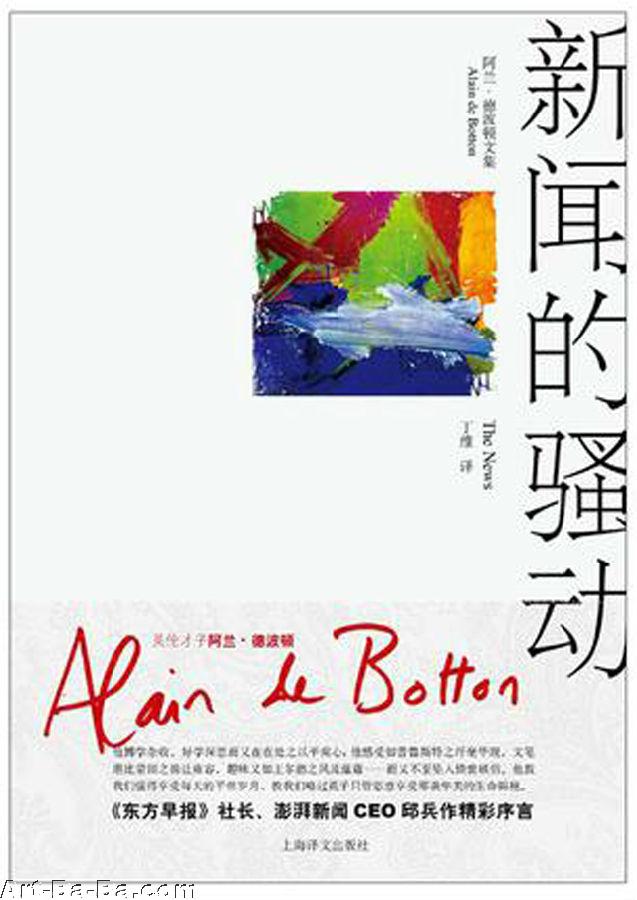
德波顿在去年出版的《新闻的骚动》中探索大众媒体处理新闻的方式
B:这种执念是怎么来的?
A:有可能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喜欢并且看了很多书,我对书的作者充满了崇敬。另一方面,我崇敬的家长却对这些作者和书毫无兴趣。这刺痛了我。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都很聪明,但他们对“智慧”不求甚解。这种“知识分子”与“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很没有必要。我自问:那么好的书应该是给所有人看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会孤独,都会焦虑,都在受苦,最后都会死去。这些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每个人都需要在生活里去面对。可我觉得,在西方社会的今天,对于个体灵魂来说很重要的“新闻”并不足够。
未来将是个体度身定做的新闻时代
B:这是你写作去年出版的书《新闻的骚动》的动机吗?
A:很有意思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读报,看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要是不随时看新闻的更新,就不能算是很严肃地对待生活。我不这么看。大众媒体对于我们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事”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些天,估计在伦敦看新闻的所有人都在想着叙利亚难民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处理新闻的方式从来是断章取义而且有局限性,这是个问题。
看看今天我们往前走的方向吧,我想,任何自称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不可能再回避人与人的沟通。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精英阶级主导的旧社会,我们生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

德波顿创办的成人网站 Porn as the Therapy 看着一点也不带情色感
B:可还是会有人自视为“精英”?
A:当然会有,但“精英们”对今日社会不再有影响力。你看,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剑桥大学文学系教授是谁?没有人知道。可是人人都知道默多克在《太阳报》上都说了什么。我们容许一个社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人人去聆听未必很聪明、很有趣的声音,这是消费与民主社会派生的问题。去思考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中有着怎么样的身份,是个挑战。
B:去年你开了一个“Philosophers’ Mail”的新闻网页。
A:那是一个实验,现在网页已经关掉了。当时我们想用讽刺手法去仿效英国一张八卦小报、也是最受欢迎的网络新闻端《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这张报纸每天都在八明星轶事,我们就用哲学的角度去解读斯泰勒·威夫特的大长腿、布拉德·皮特的假日,我们想颠覆大家的思维:没有什么八卦是不可以严肃认真去解读的。这么做是想去改变我们司空见惯的小报腔调。
B:你认为,什么是真正必要的新闻?
A:这并没有统一答案,得看每一个个体自身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现在也许还不成气候,但一两个世纪以后将是个体度身定做的新闻(personalised news)时代。最重要的新闻将是每一个人此时此刻最需要了解的新闻,以帮助自我成长为人格更完善的版本。有些人也许需要更多地了解移民形势,有些人也许需要更多地了解“谅解”,不一而足。今天大众媒体的问题就在于规定了所有人必须关注那几件事。而不少有心理问题的人都在利用大众媒体去分散对自我的注意力,以逃避现实,而生活在由新闻事件堆积成的虚拟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没有个人生活的方向、不需要责任心、不需要处理感情关系和人际互动,只有抽象的事物。
B: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
A:带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去消费新闻,这种个人化的读报习惯,有时候还意味着刻意不去读报。
B:你是要说,信息爆炸时代会消减个体独立思考的习惯?
A:肯定会的,信息爆炸频繁分散注意力,也暴露了人性中一些很糟糕的方面,比如说以牙还牙的报复心、毫无耐性地对他人做出草率的评判、愤怒等,这些经常见于社交媒体中。有时候看推特上满屏的戾气,觉得整件事就像一场严重的精神病。
B:因此社交媒体会影响到情商?
A:这确实会成为情商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B:但同时你也在Youtube上开了个频道:School of Life(生活学校)。
A:是的,我们还是得擅于去利用现有的武器。最近我们刚刚开办了一个成人网站(pornastherapy.com),我们自己拍摄小电影,去思考情色电影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提起成人电影,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恶心”、“羞辱女性”,但同时互联网上三成的搜索都指向成人网站。在人类的好奇心领域中,这是极为庞大的数据。对此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有些人倡导对成人网站“杀无赦”,最近印度就出台政策,打算全面封杀情色网站。但“生活学校”想做的是从人们的需求出发,想办法去升华这种需求。我们自己制作拍摄“更好”的成人小电影,“更好”不是指更纯洁、更激动人心,而是与人类高尚的追求相连接。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想办法连通“高级”和“低级”趣味,让成人故事也能有尊严起来。我尤其对古代的印度和古希腊成人故事很感兴趣,“肉欲”在这两个文明古国中是很严肃的事。阿波罗在古希腊神话中有着代表肉欲的外型,但他同时是智慧之神。性爱与智慧并肩,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寻常的。

德波顿说他明年将出版的新书《爱的轨迹》是对“时光里的爱情”的一次研究
写作就像在做自我疗愈
B:十多年前你开办了名为“活着的建筑”(Living Architecture)的现代建筑项目,其中一个动力是“看不惯英国人的保守和势利眼”,现在你觉得英国人对这个项目的反应如何?
A:长期以来,英国一直都在抵抗现代建筑,尽管英国本土培养了众多现代建筑设计师。促成这些设计师们成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他们没法在英国大展拳脚,被迫跑到国外去。像诺曼·福斯特、理查德·罗杰斯等人,在国外接的活都比在英国多。很多人到英国来,会惊叹这里全都是老楼。“活着的建筑”想做的是,为英国百姓展示一些高品位的当代建筑,希望培养起人们对新建筑风格的鉴赏力。我不知道这实现了多少,不过现在英国各地,尤其是伦敦存在一个问题:过去三四年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伦敦市长下令取消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伦敦因此出现了建新楼的大潮,也一下子出现了很多当代建筑设计师,问题是设计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更糟糕的是,有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我:“你看你那么卖力地推广当代建筑,可是瞧瞧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
B:既然说到了难民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
A:噢,我真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话来。
B:你还会写小说吗?还是觉得写励志书更能直接地帮助到人?
A:我并没有放弃写小说。写励志书还是写小说,还得看是什么题材。如果是想要写感情关系,没有什么比小说这种体裁更适合。我刚写完了一部新的小说,明年出版。小说名叫“The Course of Love”,故事跟着一对情侣生活了许多年,从最早相恋开始到多年以后,算是对“时光里的爱情”的一次研究。
B:跟《爱情笔记》有相似之处吗?写作动机来自哪里?
A:题材上不太相像,但都是夹叙夹议带着分析去写的小说。区别是:《爱情笔记》着笔于浪漫之爱,新的小说写的是成熟之爱。写这本书,其实还是在我长期感兴趣的那几个领域里兜转:爱情、工作。选择这些题目,因为我感兴趣,也因为我深受其困扰。我将写作看成是照顾别人和照顾自己的方式,我写下的所有题目也都是我想对自己说的,就像在做自我疗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