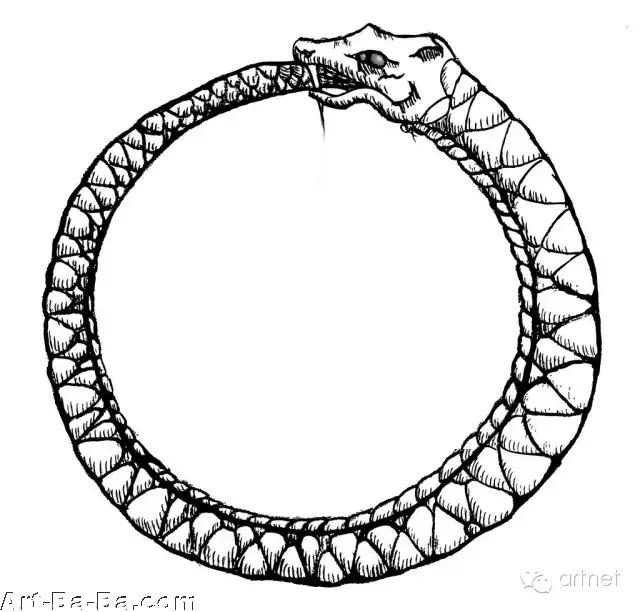来源:artnet


MoMA PS1的展览“大纽约"(Greater New York)——这个城市著名的年轻艺术家盛会自称放弃了对新晋艺术家的展示,而转向批判都市贵族化、非政治性艺术及艺术市场,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它至少显示出,博物馆策展人的心里还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刚进入展厅,你会误以为当下的艺术潮流已经不再被失控的地产景观和猖獗的商业主义所左右。然而,细心观看之后你就会发现:参展的157位艺术家和他们的400多件作品中,超过半数是在2000年之前创作的,而艺术家的年龄也都在48岁以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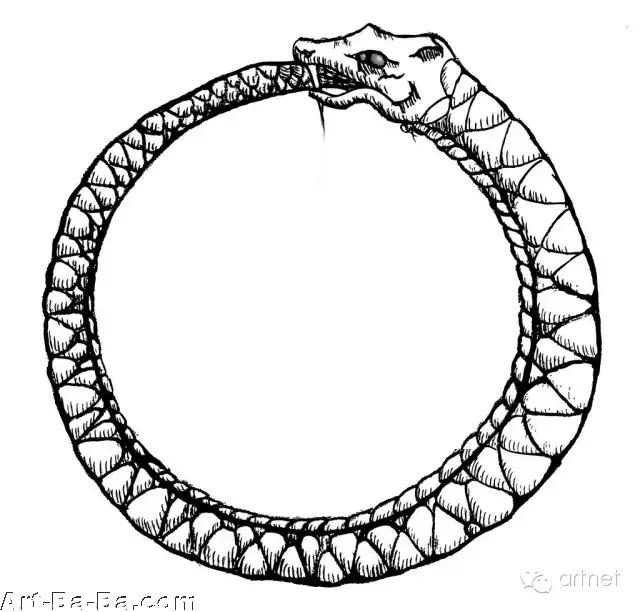
在古埃及文化中,咬着自己尾巴的衔尾蛇(ouroboros)是自我映射和循环的象征。可以说直到2016年3月7日,“大纽约"闭幕那一天,MoMA PS1这场展示从旧到新的实验性作品的展览正是这个自我吞噬的符号的完美诠释。

卢茨·巴切尔《魔术山》(Magic Mountain,2015)
图片: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oMA PS1
有着44年历史的PS1自2000年加入MoMA以来,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自立及先锋的特性。现在看来,就连来自大众汽车的赞助都像是仍然带有80年代的余绪。在一河之隔的曼哈顿,一套公寓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100万美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与商业公司扯上不光彩的关系真的很难为文化复兴带来什么正面形象。所以,展览的策展团队——策展人彼得·艾尔力(Peter Eleey)、艺术史学家道格拉斯•克莱普(Douglas Crimp)、联合策展人托马斯·J.拉克斯(Thomas J. Lax)以及策展助理米娅·洛克斯(Mia Locks)——所呈现的第四届“大纽约"打怀旧牌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展览的新闻发布资料不仅仅将1970、80年代称为“实验创作及态度"爆发的年代,还郑重其事地推出了一系列来自那个年代的并不太知名的艺术家。展览方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当下的新晋艺术家大部分是现实状况的缩影;从另一方面说,那些未被发掘的艺术家(或者可以称他们为“被淹没的艺术家”(submerging artist)),代表的就是创新抵抗力量的鲜活范例。
阿尔文·巴尔特洛普,《堤坝(以及在上面做爱的情侣)》(The Piers(With couple engaged in sex act),1975-86)
图片: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oMA PS1.
阿尔文·巴尔特洛普(Alvin Baltrop)的30多张描绘西城堤坝(West Side piers)同性恋生活的摄影能够入选,一定是这种翻案精神起了作用。巴尔特洛普记录1970、80年代男同性恋在这座城市的断壁颓垣中活动的黑白照片为一楼展厅奠定了性政治的基调(一张名为《一天的终结》(Day's End)的作品,展现的是戈登·玛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被切开的仓库,将他著名的建筑干预计划以暴力的伤口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另一个展厅,已故艺术家纳尔逊•沙利文(Nelson Sullivan)视屏影像里的变装女王和俱乐部少年,显示的是曾经辉煌一时的纽约夜生活群体。相隔几个展厅的是罗莎琳德·福克斯·所罗门(Rosalind Fox Solomon)1990年代的作品,她用照片记录下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其中的激进主义色彩与画家唐纳德·墨菲特(Donald Moffett)及女同性恋艺术家组合Fierce Pussy的作品产生共鸣。
罗莎琳德•福克斯•所罗门,《被脚手架覆盖的自由女神》(Liberty Scaffolded,1976) 图片: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oMA PS1.2015年“大纽约”给人的1970、80及90年代时期性展览的感觉在展厅的二楼有所弱化,这个美术馆中最大的展厅的主题贡献给了人类形象。极具煽动性的雕塑家托尼·麦特里(Tony Matelli)的作品是两件裸体雕塑,一男一女,他们上下颠倒的矗立在展厅当中;伊丽莎白·耶格尔(Elizabeth Jaeger)的雕塑是一对正在交媾的情侣,迷乱地显现出性感的亲密;呼玛·巴巴(Huma Bhabha)的青铜雕塑描绘了一个21世纪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与你在展览其它部分看到的一样,年轻一代艺术家探讨的主题,早已在老一代艺术家——X世代[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婴儿潮一代、甚至是大萧条一代——那里现出了端倪。在这些鲜活的后千禧年作品边上,有着更多来自元老级艺术家原始的探索——朱迪斯·谢伊(Judith Shea)、约翰·哈恩(John Ahearn)、乌戈·罗迪尼(Ugo Rondinone)、红新郎小组(Red Grooms)、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玛丽·贝丝·埃德尔森(Mary Beth Edelson)。
最终,还是两位已故艺术家为这场垂暮的老牌青年展(这个展览每五年举办一次)打了圆场。戈登·玛塔-克拉克的三张照片记录了1976年他为MoMA PS1的首个展览创作的“建筑切割”(structural cuts)(当时这所机构还只是叫PS1)。亨利·弗林特(Henry Flynt)在1970年代拍摄的57张记录传奇涂鸦组合“SAMO©”的照片,由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亲自上阵——其中的涂鸦标语不无讽刺:“SAMO© for the so-called avant-garde”( 所谓的先锋还是老样子(same old))、“SAMO© is dead”( SAMO©已死)。这些作品让人回想起1971年PS1成立之初,它是作为“艺术及城市资源研究机构”(Institute for Art and Urban Resources Inc.)而出现的——其首要使命是将纽约的废弃建筑改造成艺术家工作室。这一切都使得这些作品读起来像是那个黄金年代的挽歌——那时候,犯罪横行,地产胜景还在孕育之中,艺术家们无拘无束地进入文化产业的初级阶段。
亨利·弗林特,“SAMO© for the so-called avant-garde”( 所谓的先锋还是老样子(same old))虽然有种种遗憾,这并不是说今年的“大纽约”一无是处。其中可圈可点的是,它重新定义了新晋艺术家(emerging artist)是一个没有年龄限制的概念,同时将一系列优秀的年轻创作者带入展览,其中包括画家威廉·维拉隆戈(William Villalongo),摄影师萨拉•柯文娜(Sara Cwynar)、戴安娜·劳森(Deana Lawson),装置艺术家安吉·基弗(Angie Keefer)、卡梅隆·罗兰德(Cameron Rowland),雕塑家艾米·布莱纳(Amy Brener)和劳尔·德·尼夫斯(Raúl de Nieves)。但是,2015年的“大纽约”也标志着一系列新困惑的开端。如果像MoMA PS1这样的机构也向我们提示了纽约艺术的日渐衰落,那么是时候开始重新定义这座城市的文化与政治的异化了——从每一所博物馆开始。

“如果你一年前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这个5年一度的PS1项目的话,我会告诉你,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策展人道格拉斯•克莱普(Douglas Crimp)在纽约皇后区MoMA PS1的“大纽约"(Greater New York)项目新闻发布会上说。然而,这位知名批评家、教师以及史学家的个人印记已经深深的印在了这场2015年的展览上,其庄重的气息是以往少见的。这个以“新兴艺术家"为主体的项目以往总是带有一些派对的气息,但是今年却变成了一个涵盖更广的展览,用以反应纽约艺术的过去、当下以及未来。

道格拉斯•克莱普 图片: Courtesy Kracauer Lectures in Film and Media Theory.克莱普的策展总是与他的评论齐头并进;他1977年在艺术家空间(Artist Space)的“图片"(Pictures)展让挪用艺术(appropriation art)成为了纽约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他通过LGBT组织ACT UP参与了艾滋病激进主义活动,这与“大纽约"项目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2010年,克莱普与琳·库克(Lynne Cook)一起,以艺术家如何使用城市作为创作媒介为主题,在雷纳索菲亚国家博物馆策划了“混合使用,曼哈顿"(Mixed Use, Manhattan)展览。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PS1策展人彼得·艾尔力(Peter Eleey)透露,长岛市政府曾经试图将这个展览移到纽约,但最终未果。最终吸引了克莱普策划“大纽约" 的原因是,他可以延续之前策划的展览(艾滋病)所引发的讨论。我与克莱普聊了一下他的工作计划,以及这个针对纽约近期历史的项目对于当下的艺术家意味着什么。

吉娜·比弗斯,《本地杜泊绵羊》(Local White Dorper Lamb,2013)
图片: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oMA PS1.
本·戴维斯(BD):这个展览当中,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具有重要性?会不会有一些部分你的比重比彼得更多一些?道格拉斯•克莱普(DC): 不可避免的会有。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说:“我把这个带到了展览当中。"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和彼得说起了亨利·弗林特(Henry Flynt)的摄影。实际上,所有的影像项目几乎都是我做的。每周都会有一个电影项目,所以每周你都可以看到一两部我们推荐的电影。这个部分覆盖到了纽约历史的方方面面。所有的影片都是关于纽约的,当然了,展览当中也会有很多和纽约没有关系的作品。我与琳·库克在马德里策划的展览是关于艺术家如何使用城市的,所以我将那个展览当中的一些作品也带到了这里,比如詹姆斯·奈尔斯(James Nares)的钟摆、埃尔文·巴尔特洛普(Alvin Baltrop)的摄影——虽然不是相同的参展作品——以及罗伊·柯尔摩(Roy Colmer)的摄影,当然还有一些电影项目当中的内容,比如香特尔•阿克曼(香特尔•阿克曼)的《家园新闻》(News From Home)以及琼·乔纳斯(Joan Jonas)的《延迟歌曲》(Songdelay)。对我来说,这个时期内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艾滋病,因为我与艾滋病激进组织来往密切。格雷格·波多维茨(Gregg Bordowitz)的作品也在电影单元当中。还有唐纳德·莫菲特以及Fierce Pussy小组。Fierce Pussy的一些成员,比如乔伊·艾皮塞拉(Joy Episalla)和山冈嘉丽(Carrie Yamaoka)也参与了展览——我通过那些激进主义的创作认识了他们,而他们那些与艾滋病无关的作品也让我敬仰。乔伊今年在 Participant, Inc做了一场展览,我们都被这个展览吸引住了。我在Bridget Donahue看到了苏珊·锡安西奥罗(Susan Cianciolo)的展览,也都被迷住了。我是最后看到这个展览的人,然后我立马打电话[给彼得]:“我们必须得邀请苏珊参展。"结果我们也这样做了。
艾米·布莱纳,《化妆间》(Dressing Room,2015)
图片: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MoMA PS1.
DC: 我的朋友们给了我非常多的线索。有一位叫做史蒂芬妮·维克多(Stefanie Victor)的女孩,她做的是看起来像珠宝一样的雕塑。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去参观了她的工作室,然后就被她的作品征服了。有些年轻的艺术家并不能成为“新人",比如莎蒂·贝宁(Sadie Benning),她的作品能来参加展览,我感到非常高兴。BD: 你是如何解读这个展览的?它让人感觉是一次谢幕演出,是一次纽约的谢幕,因为在这里越来越难做出新的作品;这让人感觉是一场回顾展。DC:我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知道1976年艺术家们是如何抓紧机会使用这座城市的话——比如詹姆斯·奈尔斯的钟摆作品——你会显而易见的发现,现在在曼哈顿再也找不到可以做相同项目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想到:这是一个以特别的方式居住在这座城市当中的艺术家,他会抓紧自己看到的所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除非我们特别、特别有钱,并且想画上一亿美元去买一座高层的公寓。但是,我们总是会找到途径去实现想法。不管有钱人是如何改变了这座城市,我们还是在这里……包括艺术家。我觉得,展览当中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显现出了他们是如何来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想法的。我觉得关于纽约的问题是个开放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