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工团 文:韩见

照相机是最直接的生产影像的装置,你的手一定要碰到它,就算你拍的时候不看它,还是要拿起来,它是你的延伸,和你的关系非常直接。
文 | 韩见
当陈传兴和他的团队在民生现代美术馆为了即将到来的个展《未有烛而后至》没日没夜地工作时,日本著名摄影师和摄影理论家中平卓马因肺炎逝世了。展览开幕后,我向他提起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关注新闻的他既惊讶又叹息,出神地说:“好可惜噢,走了噢,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忙到昏天黑地、忙到天亮的时候……”
同为既拍照片,又做理论研究的摄影师,陈传兴心里无疑将中平卓马视为可与之惺惺相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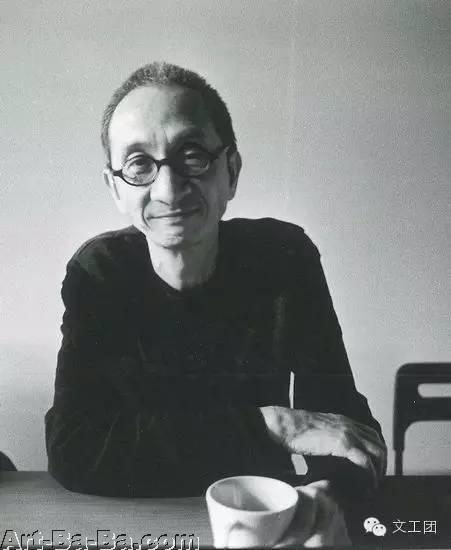
陈传兴
中平卓马在他的著名文章《为什么,是植物图鉴》里提出,摄影必须彻底排除对世界的人化和情绪化,杜绝人向世界的投影,要像图鉴一样直截了当地指示对象;陈传兴则反对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提法,在拍摄中也力图避免把对象当成“猎物”一样去捕捉的企图心。
无论在摄影观念还是影像风格上,二者都不乏相似之处,陈传兴自己也说:“我喜欢很暗的画面,拍摄的时候就会选幽暗、微明的状态,光线不足甚至是逆光,那是高挑战,中平也喜欢这样。”
他脱口而出对中平卓马的评价,也像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我认为他是日本同代摄影师里最好的一个,又有才华,又有思想,对自己的作品有清楚的认识。‘安保’那一代,他唯一的一个活得最像话的。”他说荒木经惟和森山大道如今已快变成小丑,好像在比赛谁出的书多,而中平卓马却选择把不必要留给后人的作品悉数烧毁,“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荒场:林家花园-入口与四角亭,银盐纸基,61×76cm
陈传兴自己也无法做到那样决绝。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从展览中那些同一时期拍摄但显然做了多种艺术尝试的作品,以及他对它们的阐释中隐隐透露出来。
一方面,他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不甘心让自己的影像仅仅作为历史档案存在,而希望他人能够通过“观看”这些照片看到他试图凸显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理论家,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杰作,也能够像分析他人的作品一样理性地分析自己的作品。他拍得远比许多专业摄影师好,可这话又必须由别人来说。
所以陈传兴早年留下的大量底片,尽管早已洗出来,跟着他去了欧洲,又跟着他回到台湾,可是直到40年后,他才决定并且最终决定公之于众。《未有烛而后至》里的作品是陈传兴10年影展计划的第一部分,他自比《礼记·少仪》中的执烛少年,为陌生宾客引路,同时在沉默中反身自照。
接下来,他还将分四次陆续展出其他作品。很巧的是,这一系列影展开始筹备后不久,美国业余摄影家薇薇安·迈尔生前拍摄的大量照片被曝光,立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陈传兴觉得这样是最过瘾的:“拍的时候没人知道,没有负担,哪一天突然拿出来,别人就会说,哇,你也会拍!”

淡水-淡水老街,银盐纸基,61×76cm
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所有的文艺青年总是要有一两个艺术嗜好,有人写诗,有人画画,我对社会现象比较好奇,就拍照。”选择了摄影的陈传兴在大学里完全待不住,几乎没有好好上过课,每天去晃一下,看看有没有考试,没有的话,前门进,后门就出去了。
他还有个一起逃课的伙伴,后来也当上了老师。“野孩子最后反而去教书,”他说,“教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去到外面的世界,直接接触真正的人和自然,对我比较有吸引力。特别是去像芦州这样比较偏远的地方,不能耕种的土地、荒凉的小镇、原住民,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城市年轻人,是更大的刺激。”
大学时他就有了自己的暗房,还在家尝试调感光液、做相纸,做中途曝光等各种实验。大三就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像展《芦州浮生图》。除了买书来读和自己摸索,陈传兴的摄影启蒙来自一个美国的越战“逃兵”。70年代,美国好多不愿上战场的年龄人,纷纷溜至加拿大、欧洲和亚洲各地,有一天,他的哥哥就在街上“捡到”一个美国人。

芦洲-废耕田野,银盐纸基,61×76cm
“头发很长,穿着凉鞋,皮带也没了,裤子用一根草绳拴着,脖子上的相机也撞得伤痕累累。”陈传兴回忆说,哥哥带美国人回家的目的是练习英文,而他自己则陪他去台湾东部偏僻的地方游玩拍照。美国人向他介绍了很多当代摄影家,还告诉他,如果喜欢拍照,一定要看《Aperture》这本杂志,否则不知道什么是好照片。
当时在台湾订阅国外杂志很困难,陈传兴千方百计订到了,但是真正拿到手的时候,大学已经快毕业,马上就要去法国留学了。尽管此次展览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看到《Aperture》之前拍摄的,陈传兴仍然认为那几期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那时候台湾还是相当封闭的,换美金要去银楼,外文书进来都要检查,《Aperture》是我收到的唯一的外国资讯。可那又是一个蛮好玩的年代,外部世界的知识不易获得,逼得你自己去想、去摸索,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想整理中国人的死亡观
到了法国之后,让陈传兴受益最多的仍然不是学校。他每个礼拜都有一两天去国家图书馆看原作,系统地从达盖尔开始,看到20世纪,持续了一年。后来也找机会去到MoMA、普林斯顿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看档案,“简直功力不知道增加了多少”。他现在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去亚利桑那大学看安塞尔·亚当斯捐赠的作品。
陈传兴自称是个离群又贪心的怪物,什么都学,什么都想做。“世界那么大,有很多好玩的,可以这边玩玩那边玩玩,多快活。”所以除了拍照之外,他也做老师、做导演,拍摄纪录片,担任《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总监制,创办行人出版社译介人文类书籍,甚至自己还在偷偷搞文学创作。
由于身体原因,他如今渐渐放弃了拍电影的想法,行人出版社也交棒给年轻人管了,但他有一个写作上的大计划:整理出自己的思想体系。“目前急切的事,是把手稿整理出来。关于哀悼的思想史课题,已经做了几十年。想整理中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以及它对思想史、伦理、宇宙观的影响,但又要避免掉进汉学里去。”

悼亡-送葬者 II,银盐纸基,61×76cm
陈传兴对死亡的兴趣,从他早年拍摄的以悼亡为主题的照片中就初见端倪,但因为挑战很大,他也不敢轻易出手:“老人家乱玩,会被人看破手脚。所以越来越没胆,皆剩恐惧。可是又会急,因为时间不多了。老天对我蛮眷顾的,给我很好的记忆力、很快的反应能力,我应该要还他。有时候想,再年轻十岁多好,但如果没有十年的累积,也不会有今天这些想法,也值得。”
B=《外滩画报》
C=陈传兴
B:《招魂四联作》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
C:当时家族里有一个长辈过世了,他们知道我会拍照,就问我要不要去拍,我说好啊,当然有帮他们拍纪念照,但是趁机也把整个仪式的过程拍下来了。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记录,更像像剧场和神话仪式,里面充满的绘画性和张力。那时候我就感到,人创作,拍照,能拍到好的是老天给的,不是自己的。

悼亡-招魂四联作 I,艺术微喷,铅铝复合板,200×150cm
B:把它们装裱在铅板上是出于什么考虑?
C:因为那四张的场景是在山顶做丧葬仪式,我拍摄的时候用中途曝光的方法,有意让光影有神秘的感觉。但为了表现出更庞大的神秘空间,进入神话而不是一般的人间世界,我觉得有必要让空间扩散。传统装裱方式营造不出那种感觉,反而会压缩空间。
用铅板的原因是它可以表现出厚重、庞大的感觉,而且铅的灰色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更重要的是,铅原本就是炼金术里的重要元素,有神秘的色彩。当代艺术里,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基弗(Anselm Kiefer)也有用铅。我把影像裱在铅板上面,再用低光来打,让照片接近文艺复兴后期的西班牙艺术家格列柯(El Greco)的画作。我看过他的画册,拍的时候就已经隐约想要达到他的作品的效果。

悼亡-招魂四联作 II,艺术微喷,铅铝复合板,150×200cm
B:你的很多照片里,都至少有一个人是望向镜头的,可是他们的表情又显示他们没有看到你,或者当作你不在,这是怎么做到的?
C:这是我的长处,我几乎可以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比如戏班那些,我混在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们都不觉得我存在,照样睡觉、化妆。台北车站那一张也是,一群人下楼梯,完全像舞台,我在前面看,他们就是这样安静地走下来。因为我动作蛮快的。可是现在老了,手在抖,就会被抓包。我上次来上海的时候就在路边被抓到了,他向我要肖像权。最后我买了一包烟给他。

台北车站-候车旅客,艺术微喷,61×76cm
B:你去国外之后,1978年暑假又回台湾拍了一个坤旦,为什么对戏班感兴趣?
C:其实出国前就开始拍了他们了,和野台戏班到处跑,其实流浪戏班是台湾最后的吉普赛人,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漂泊、沧桑,社会边缘的挣扎,这是很令人着迷的。那个夏天为了拍这个坤旦的纪录片,在台湾多待了一个半月,期间也拍了照片。西方绘画里其实蛮多画马戏团和戏班的,从洛可可时期的瓦托(Antoine Watteau)到现代的毕加索,都感兴趣。

戏班-等待开锣,银盐纸基,61×76cm
B:学了理论之后,创作时会受到局限吗?
C:我觉得没有,反而给了我更大的自由。没有“我像”了,还有什么可以困住你?我在教书的时候,会把整套知识还原给学生,然后提出我的想法,接着再问,你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样来来回回。也有学生问,想太多会不会受影响?你这才是真的想太多。你不去看,不去读,怎么知道那里是什么世界?你自己先划了界限,先觉得自己会不会被影响,你把自我放得好大。
B:拍了那么多年,你担心创作力衰退吗?
C:应该是不会怕吧,没什么好怕的,否则也不会有把握把拍的东西都保留下来。累积了40年,到了晚年,我开始可以诚实地思考自己和过去拍的作品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要不要展览,哪些拿出来展……其实其中也包含伦理关系。培根(Francis Bacon)经常拿刀子把自己的画毁了,O. Bach(Robert Otto Bach)画好了还要改来改去,有些都拿去展了,卖掉了,他又去拿回来毁掉,再拿一张新的给别人。不断思考自己的创作,这是很重要的伦理态度,而不是画完就算了。
B:近年来你有发现一些好的摄影师吗?
C:大陆的成都帮,骆丹、木格、塔可、黎朗,他们真的很专注珍惜他们面对的事。不炫耀、不盲目,有把握、有自信,对手、对技艺很认真,一天天在往前走,回到真正的摄影的本质。可能我上了年纪,喜欢老老的东西。

色-海岸,艺术微喷,61×76cm
B:那你用数码相机吗?
C:以前为了拍家里小孩用过,还是不习惯。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数码科技有无限可能,什么效果都可以做到,都可以美美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暗部要这么处理、要把颜色调成那样,很少人去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阻止我拿起数码相机。不过我的展览里其实用了大量数码科技,比如黑白打印我们用的是K7技术,最近两三年在美国成熟了。一般的Epson喷墨打印顶多一两种黑,K7是7种黑,层次就很丰富。我的工作室分成数码和银盐两组,我们在数码上其实走在很前端。我不是在排斥科技,我只是在问,为什么要用,采用这样的方式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根本。
B:现在大家都喜欢引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理论,但其实摄影数码化之后,我们已经离那个时代很远了,你怎么看现在的影像?
C:我们现在是影像的通货膨胀时代,急剧扩张、海量。在数码时代,整套数码程式规定你的观看方式,决定影像的生成。这种至上的、你完全看不到的规定性,好像还没有人好好思考过。其实数码时代的影像,是非常不自由的。我并不是一味鼓吹要回到银盐,而是说这背后的责任关系、从本体或伦理去思考人和影像的关系的要求反而变得更加急切。我们被内在的程式规定带着走,是不是更要思考和影像的终极关系是什么?现在不能说灵光了,灵光不在,现在只能说是“美学考古”,在影像的巨大海洋里面,如何不被利维坦这个恶灵带走。

色-哀歌,61×76cm
B:还有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问了好多摄影师,摄影真的是别的媒介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的媒介吗?
C:当然啦。摄影和最接近的电影和录像艺术,就有很大差异。电影要动用很多资源,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大时代的新的戏剧形式。电影需要叙事,即使是艺术电影,还是需要有事件的流动。摄影就只有那么小的框框,它可能会带你走出框框,但框框以外它不负责。照相机是最直接的生产影像的装置,你的手一定要碰到它,就算你拍的时候不看它,还是要拿起来,它是你的延伸,和你的关系非常直接;
而你书写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内容和手的关系,文学追求的是更形而上的、人与语言的关系,不是通过身体。最大的差异在这里。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摄影的语言是什么。我们知道写诗是最难的,因为只有短短几行字,要进入语言的极限,逼到最不可能的地步。摄影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摄影师要逼问自己的目光的极限。
B:也就是说摄影的物质性还是很重要的?
C:对,没办法脱离开,可是又想脱离,摄影就是在这种矛盾中生成的。而且和拍摄者的关系非常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