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没有敌人的当代与现代主义的理论重申
文|鲁明军
全球化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也改变了艺术生产系统乃至艺术言语的方式。当网络成为新的信息平台和话语机制的时候,艺术个体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认知的串联、形式的趋同抽掉了所谓原创的可能,并集体陷入了折中主义的危局。与此同时,全球艺术市场和博览会的兴盛,表明当代艺术与资本的关系变得愈加密切,艺术与商品的边界也越来越加模糊。而这样一种相互依赖的深入和蔓延,致使以双年展为核心的学术模式渐趋式微。就像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所说的,今天,“工具式的图像将一张一张地赶走我们最后的精神意象”,“衍生产品压倒艺术作品”,“艺术不再可视,而是让人失明”,这使得“人们不再期待天才的出现,和别具匠心的惊喜,而仅仅是事故,和终极的灾难”。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对于艺术系统(特别是资本)的整体反思和检讨,进而如何开启新的艺术方式成了双年展及各种学术话题的焦点,最典型的无疑是“参与性实践”、“事件性介入”和“人类学模式”。孰料,所有以反资本、反景观、反物质名义的参与性、事件性、非物质和人类学实践(如政治参与、素人艺术等)也很快沦为一种新的景观和资本或是其中的一部分,结果是其非但没有对艺术的资本化构成丝毫批判和反省,反而无限地扩大“当代”的疆界,没有敌人的无边的“当代”模糊了艺术家的身份,也丧失了艺术的准绳,并成为一种新的流行模式和支配体制。
正是在这一新的体制形成的过程中,现代主义及其相关问题不断地被理论界提出来。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在《后制品》(Postproduction)一书中对于现代主义的检讨,2010年前后格罗伊斯(Boris Groys)对于现代主义问题的反思,以及2013年末至2014年初德·迪弗(Thierry de Duve)关于相关问题的再思考,这三次关于现代主义的重申。尽管三次重申所针对的对象和问题不同,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也迥然有别,但是,透过对于它们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探得新世纪以来当代艺术系统的变化以及系统内部的因应之道。
一、折中的平庸与个体行动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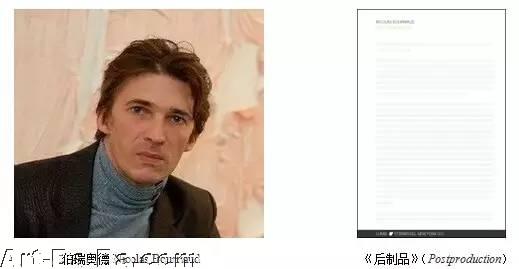
2002年,伯瑞奥德继《关系美学》(Esthétiquerelationnelle,1998)之后,出版了新著《后制品》。在这本小书的最后,他重申了现代主义及其当下意义。他认为,今天的全球文化,既是一本无限的既往史,也是一台巨大的搅拌器,很难再鉴别选择的原则。全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也随之陷入了折中主义的媚俗这一困境。历史上,折中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没有标准的品味,一种没有脊椎的思想运动,一堆不协调的选择。它将一切平庸化,并鼓吹用愤世嫉俗的冷漠来颠覆历史。而这其实就是全球化语境下“后制品”艺术模式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当代艺术所遭遇的一个难局。
面对这一问题,伯瑞奥德认为,只有重申现代主义,才有“挽救”的可能。为此他追溯到了格林伯格这里,因为在格林伯格眼中,折中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媚俗、平庸和罪恶,也是他所批判和坚决抵抗的对象。在伯瑞奥德看来,格林伯格的艺术史尽管是由线性的、目的论的形式组成,而且在其内部,每件过去作品的意义都是由它和之后作品的关系来确定的。因此,现代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对于绘画和雕塑逐渐提纯的历史。这种理论把艺术史看作科学研究的副本,它的副作用是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历史”之外。这种局限于历史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看法,造成了对新事物的强迫性观念,所以,在格林伯格这里,历史必须拥有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是由一个线性的叙事来组织的。今天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观念和实践,但换句话说,折中主义本身不也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吗?
重写现代主义是伯瑞奥德提出的方案。他说:“作为21世纪初的历史性工作,它既不是从零开始,也不被过于繁复的历史元素所困扰,而是盘点、选择和使用。进而,从一种集体的消费主义过渡到能够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个体行动主义,对一切现有的体制和形态进行一种再生产。”在他看来,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格林伯格反平庸、反折中主义的一个现代主义的遗产。此时,艺术是一种生产与世界的关系的行为,以这种或那种形态来物质化它与时间、空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他想不出其他可以概括艺术的定义。这也说明,在根本意义上,伯瑞奥德还是未能摆脱将艺术作为社会介质的“关系美学”,只是它赋予了关系一种个体的能动性,但更重要的在于,此时“关系美学”本身也已深陷折中主义的泥潭。
显然,伯瑞奥德所理解的格林伯格及其现代主义不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媒介、平面和纯粹这样一种自足的形式风格,而是内在于其中的一种现代主义动力机制和话语装置。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伯瑞奥德并不是顺势而为,而是具有极为明确的针对对象,也就是全球化带来的集体的平庸和文化折中主义。不过,伯瑞奥德并没有以一种逆向的态度和方式付诸一种批判,而恰恰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通过一种带有一定责任感的个体行动主义,诉诸持续的再生产。正如郎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艺术手段之间共同尺度的丢失,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可以自说自话,自己确定自己的尺度。这更意味着从此以后,任何共同的尺度都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而且这个生产只有通过彻底地对抗混合的无尺度才有可能。”在这里,伯瑞奥德虽然并未完全依循现代主义的线性叙事,但是他撷取了内在于其中的动力机制。对他而言,这条线性叙事,不仅意味着一种延续,同时也是一种背叛和抵抗。因为只有在线性叙事的基础上,才有明确敌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所以,所谓的风格、流派包括生产系统/机制的更替实际源自一种“斗争”实践,而此时,即便不是线性的、历史的,在横向的共时性结构中,也有一个明确的“敌人”或目标,从库尔贝、马奈、塞尚到格林伯格,他们强烈的目的论已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在今天,我们无法像库尔贝、马奈那样,有一个像古典主义这样明确的历史敌人,横向地看,艺术观众的消失意味着我们同样没有敌人,换句话说,也可能是敌人太多,或者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意识,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敌人”。因此,重申现代主义的意义就在于不仅要找到敌人,还要找到真正的、强大的敌人。难的是,这个敌人本身还一直处在变动之中,所以我们的敌人通常情况下只是一个临时的敌人。
但何以见得这种再生产或“斗争”就一定能够抵制折中的平庸呢?事实上,这背后隐含着一个潜台词,即伯瑞奥德并不认为回避或者盲目的抵制就能对抗折中,他所关心的是,在平庸的基础上如何变得不平庸,因此他无法彻底破坏或毁灭这套平庸的体制,唯一能够实现的就是让更多的个体通过行动冲决这套体制的约束。可是,当很多个体选择集体式地抵制的时候,或许又成为一个新的平庸群体和折中主义。因此,在这里诉诸现代主义的动力机制只是一种手段,它无法成为目的,而单凭手段又无法构成有效的反思和再生产。何况,手段本身也会丧失尺度。就像上个世纪初的抽象艺术一样,原本是反思和超越大众文化的一个产物,结果却很快成为大众文化或庸俗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在伯瑞奥德这里,这样一种集群式的个体行动非但不能对抗折中,反而很快又成了折中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这样一个逻辑和命运。这也是后来格罗伊斯再次重申现代主义的原因所在。那么,格罗伊斯又是如何理解和重申现代主义的呢?
二、诗学的视角与“移动的沉思”

格罗伊斯(Boris Groys)
和伯瑞奥德一样,格罗伊斯也是困扰于新的技术带来的艺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极速变革。2010年前后,在《杜尚之后的马克思:艺术家的两种身体》一文中,格罗伊斯指出影像、互联网等新技术媒介对于艺术机制的改变,认为这一改变通过消除作为著作者的工作,完成了19世纪开始的无产化进程,以及身体的现成品化和可交换机制。尽管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早已指出作者的“消失”,但在格罗伊斯这里,重申这一观点并强调无产化进程的完成,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伯瑞奥德“后制品”观点的一种回应或延续。不过,格罗伊斯所提供的方案有别于伯瑞奥德。
也是在这前后,格罗伊斯还发表了《诗学与美学》、《时代的同志》两篇短文。在这两篇短文中,他首先明确反对康德的审美自律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主张当代艺术不应以美学视角,而应以诗学的视角观之;不应以艺术消费者,而应从艺术生产者的视角审度。当然,他也强调,反对美学并不是提倡反美学,而是力图从艺术内在的生产机制中将美学彻底抽离出来。这看似是一种反现代主义的观点,但是格罗伊斯强调的同样不是现代主义的趣味和风格,他关心的是现代主义“进步”的一面。正如他所说的,“贯穿整个现代性我们可以辨认这一被动消费的大众文化和一种活跃反对之间的对立。进步的现代艺术在现代性期间已经以对被动消费(不论是政治宣传还是矫揉造作的商业品)的对立完成了自己的建构。所以,从20世纪早期先锋派到格林伯格、阿多诺以及德波(Guy Debord)他们的主张和行动都将继续回响在当下我们的文化辩论中。在这里,格罗伊斯虽然还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或者回到格林伯格的反折中、反平庸的行动,但他已经明确了这种紧张关系,以及重申现代主义的意义所在。然而,事实是,在今天,当代艺术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于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更为严峻和迫切的问题:“一位当代艺术家怎样才能幸存于一个人人都成了艺术家的世界中?”
这已经不再是艺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艺术家存在的问题。这里面的一个潜台词是,不管艺术方式如何变化,不管是大众的,还是精英的,不管是平庸的,还是前卫的,最终都无法解决艺术家得以“安身立命”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是伯瑞奥德所谓的反折中个体行动主义,依然受制于全球化资本主导的艺术体系及其“成功学”模式。因此,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艺术家身上的时候,或许可以暂时回避这样一个强大的、隐性的支配机制。
格罗伊斯认为,在这样一个没有旁观者或者说没有沉思的景观时代,或许,回到沉思是一种个体选择或自我解救。不同于从前,“这里沉思的主体无法再依赖于对无穷的时间资源和无限的时间视角的期待,依赖于对于构成柏拉图、基督教或佛教的时间传统的期待,而是一种移动的旁观或沉思”。因为,“当代的沉思生活和永久的积极流通在同时发生”,并“指向被现代生活的景观所麻痹的大众的被动性”。所以,这里所谓的移动的冷静沉思并不以产出美学判断或选择为目的,而仅仅只是一种观看姿态的永恒反复。沉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之间已无边界。几乎所有以时间为基础的艺术实践才能把时间的稀缺变成剩余,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合作者,是时间的同志,而非时间的敌人。也就是说,“即使是沉思的生活,也是一种不导致任何结果的重复姿态,它无法形成任何结论性的、有依据的美学判断”。因为,“今天,我们仍然被困在现时,并不引向一个未来”。或许,唯一能实现的就是把所有一切关于大众的、平庸的现代被动的耻辱标记从沉思中剔除出去。
和伯瑞奥德一样,格罗伊斯还是把现代主义放在抵抗大众和媚俗的框架中予以审视和反思。不过,不同于伯瑞奥德,格罗伊斯看中的不是艺术实践,而是艺术家的存在感,他将重心从艺术方式转移到了人的主体实践。如果说伯瑞奥德还局限于一个艺术系统内部的运作体制,甚至抽离了人的主体性的话,格罗伊斯考量的则是一个新的时代所带来的人的生活方式和主体位置的改变。所以,格罗伊斯并没有因此重申现代主义机制中激进行动的一面,而是选择回到一种现代主义的时间维度,即其所谓的“移动的沉思”。此时,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一种主体化的方式。
今天,时间的艺术,阅读的艺术,沉思的艺术已不鲜见,甚至成了双年展和学术讨论的主流方式,并似乎演化为一套新的体制。吊诡的是,时间的艺术和移动的沉思本身还是一种姿态,它允诺将平庸与媚俗剔除出去,但依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标准;它允诺将艺术家从既有的体制支配中解放出来,但依然无法证成作为艺术家的沉思之界限。格罗伊斯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在我看来,德·迪弗对于现代主义的考古学重申所针对的恰恰是这一新的体制。
三、现代主义的重申与艺术史自觉

德·迪弗(Thierry de Duve)
为纪念美国“军械库展”100周年,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艺术论坛》(Artforum)连载了比利时艺术史学者德·迪弗六篇长文,重新梳理了杜尚《泉》的产生,“艺术”、“非艺术”的发明,以及现代主义的诞生等一系列有关现成品与现代主义的历史问题。上个世纪80、90年代,德·迪弗已经就此已经发表过数篇论文,改变了我们对于前卫艺术、杜尚以及艺术生产的理解,而在新的解读中,杜尚不再是新动向的创造者,而变成了一名为我们送来有关早已发生的文化大变革的重要讯息的信使。不过,读过这六篇长文,我们发现,德·迪弗提出的这些问题包括其中的观点和判断基本延续了他出版于1998年的《杜尚之后的康德》一书,十五年前的这本著作可以说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也更加系统。那么,问题在于,除了纪念“军械库展”100周年以外,《艺术论坛》重新梳理和连载十五年前的这些历史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其他的现实针对性呢?恰逢今年这本书中文版刊行,似乎更有意义和必要重新思考他的这些命题对于今天艺术体制的意义所在。
确切地说,德·迪弗的《杜尚之后的康德》(Kant After Duchamp)是一部关于现代主义的考古学研究。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提出杜尚的现成品并没有终结现代主义,相反,它恰恰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延续。德·迪弗指出,现成品可以追溯到修拉这里,因为修拉的实践已经彻底从传统的手感和观看方式中摆脱出来,而在他这一科学理性的点彩技术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管装颜料的发明。在此之前,画家所使用的颜料都是自己手工磨制的,且很少使用纯色,都需要调配处理,而修拉不加调和地使用管装颜料,实际上已经将它自觉地视为一种现成品。这也意味着,现代劳动分工已经开始介入绘画领域。另外,我们一直以为杜尚的《泉》之所以成立在于它对于当时艺术体制的一种挑衅,但德·迪弗认为,这也不是杜尚的发明,早在19世纪,库尔贝、马奈其实就已经在挑衅当时的沙龙制度,只不过,杜尚是第一个将这一挑衅或对于艺术体制的自觉本身作为作品或是其中一部分的艺术家。反过来,这也表明,库尔贝、马奈在艺术机制层面上与现成品是一种同构的连续关系,而不是断裂的。

杜尚和他的作品
在这里,德·迪弗在此不仅是为“现成品”正名,也是为“现代主义”正名,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重新理解绘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他的意思是说,现成品与绘画之间实际并非如此泾渭分明甚至绝然对立,前者原本就是脱胎于后者。也正是这一说法,取消了类似绘画、现成品这样的媒介性划分,从而将它们一道纳入了一个“唯名”而非“专名”意义上的一般艺术的概念系统中。在此,他不仅回应了康德的“二律背反”,而且以康德的批判理论为视角和进路,重新检讨现代主义。一个是“纯粹现代主义的考古学”,即从艺术体制实践层面,包括生产方式、观看者、体制的挑衅等重新定义了现代主义;另一个是“实践现代主义的考古学”,从审美、道德及政治批判的角度揭示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机制。
在德·迪弗看来,杜尚唯名论意义上的“这是艺术”和康德所谓的“这是美的”实际上是同构的。这意味着,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形式或风格,自身也是一套机制,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机制性实践。而这事实上已经将现代主义绘画直接引至一个开放的当代视域中。基于此,德·迪弗重申了艺术家的身份,强调只有在成为艺术家的前提下,任何事物才有成为艺术的可能,从而修正了博伊斯所谓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误解。因此,对于今天我们所遭遇的当代窘境而言,这不再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教条式重申,而是在反思现代主义的基础上的一次价值重申。
概括而言,这一反思与重申及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德·迪弗并不认为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媒介语言,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艺术机制的运作加以对待,在他这里,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自足的形式或风格,更像是一部能动的装置。其次,现成品也不是一种逸出艺术史逻辑或断裂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实践,现成品与现代主义绘画在生产机制维度上的延续意味着它并没有终结绘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作品,它是有内在要求的,在德·迪弗看来,这个要求不是形式,而是艺术家的身份,这一身份的确定来自艺术史维度上的一种机制性认定,而不是一种形式和风格的认定。最后,虽然尚没有明确这样一种观点是否直接针对今天的参与性艺术和人类学实践,至少,对于后者所导致的当代的无边化予以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迪弗保守,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一种趣味的回归,更不是一种形式的更替,而是基于艺术史脉络的内在机制的开启和变化。所以,德·迪弗并不反对拓展艺术的边界,也不反对其他学科领域“粗暴”地介入艺术实践,他针对的是随着艺术与知识边界的消失,艺术的知识化所带来的一种主体性的让渡。因为,说到底“人类学模式”和“参与性实践”都潜在地让渡了艺术家的主体。所以,对于现代主义的考古学重申,根本意义上是一种艺术家主体性重建的努力。而这一主体既是一种艺术语言机制的探索,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的建构。
回过头看,尽管伯瑞奥德、格罗伊斯都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的艺术的无边化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而且,两位都以各自的视角和路径试图批判性地应对这一局面,伯瑞奥德通过揭示现代主义的前卫结构及其对于折中主义的反省,诉诸一种个体的行动主义及能动机制,格罗伊斯同样基于现代主义及其对于大众和媚俗的叛逆,选择回到现代主义“移动的沉思”或“旁观”这一时间性维度,重建一种新的主体的可能。然而,他们还是无力改变一个事实,当代艺术的无边化所带来的观众的消失和标准的阙如。在我看来,德·迪弗理论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从考古学的视角,为我们重探了现成品与现代主义内在机制的历史关联,借以建立一个新的艺术标准,即对艺术家身份的确认,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艺术方式和话语机制。至此,尽管三者各自针对的对象和问题不同,但是我认为他们的重叠恰恰是对今天艺术体制及其所遭遇的文化困境最有力的一种理论反思、修正和补充。
余论
诚如前面所言,伯瑞奥德、格罗伊斯及德·迪弗三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者都回避了艺术史经验中的现代主义定义——形式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而是选择从生产系统角度切入,这样一种理论实践本身也意味着,今天我们已不可能再回到一个审美、消费和风格维度上的现代主义,回到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孤绝方式,而不断趋于一种开放的、能动的机制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的重申首先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重新认识和定义。基于此,三位为我们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和方案,无论是伯瑞奥德的个体行动主义,还是格罗伊斯“移动的沉思”,抑或德·迪弗对于艺术家身份的重申,都源于对于现代主义的重新理解,他们共同为已然僵化的当代艺术体制提供了新的活力和动能。
然而,今天的问题是,在一个新的“当代”概念范畴中,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当代的一部分。因为,当代这个概念并不在现代主义的线性叙事中,它其实已经粉碎了这套叙事。譬如2007年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主题就是“现代主义对我们是否已经成为古典(过去)?”。策展人诺格尔·布格尔(Roger M.Buergel)和卢特·诺阿克(Ruth Noack)在展览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关于现代艺术的展览,而且也意识到这个做法尽管可能有点奇怪,但他们坚信这些形式和风格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将会延伸下去。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这些形式及其意义往往只有艺术家才会有所认识,而观众通常很难体会,因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去靠近这些形式的原动力,通过这一特殊的展览行动去试图影响观众。当然,也正因此,他们不仅不再凸显艺术家及其观念,也不再迎合地缘政治的身份认同。在这里,形式本身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普遍意义,而这样一种现代主义诉求及其针对性也就成了一种新的当代话语。2014年初,由深圳OCAT主办的展览“让现代继续:沉浸,等待,理想主义”中,也将形式视为现代主义的话语方式,强调这不仅是对于长期支配我们话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无声的抵抗,也是为了继续一种精神能量,提供一种不乏质疑、并真正能够建立自身思想谱系的动力。这样一种论调的确带有德·迪弗“实践现代主义”的色彩。但相比而言,2012年的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则更具颠覆性和挑战性,策展人卡洛琳(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彻底取消了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之间的时间界限,以及各个学科或领域与艺术之间的专业界限,其中不少现代主义的作品参展,展场的设计中也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申现代主义还有多大意义呢?此时我们可以说,伯瑞奥德、格罗伊斯和德·迪弗的反思实际上都已尽数被“当代”这个无底洞所吸纳,似乎只能将其视为当代内部的一种反省和检讨。所以,真实的结果是,面对活生生的艺术和展览实践,理论的反思与重申似乎只是作为一种个体姿态而不断地排演,但又似乎不断地被悬置,被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