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时代美术馆
蔡影茜:二楼的全称是“二楼出版机构”,但你们目前进行中的项目“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看起来并非一个出版项目,那么“二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葛 磊:出版更多的是一个做事情理由吧。实际上我们在出版了我们的第一本书之后,就再没有出版社敢与我们合作了,加上现在国内出版的审查尺度,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继续花精力在这个上面。出版可能还会是个结果,但不再是目的了。
蔡影茜:我看到你们的订阅号里面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定义为一个“艺术家调查项目”,这里所说的“调查”与新闻学当中的“调查性报道”有关吗?还是跟社会学里的社会调查有关呢?为什么会用“调查”这个词?
李一凡:应该和社会学和新闻学都没关系,我们强调的就是艺术家的感性的、感知式的调查,不是新闻调查也不是社会调查。我们强调的是以艺术家自己的方式、以艺术的方式,或者我们说是以感知的方式做调查,是这样的定义。
葛 磊:对,其实艺术家去村子里做什么、怎么做我们是不干涉的,有人愿意用感性的方式,有人愿意用社会学家的方式,有人愿意用另外的什么方式,都可以。其实即使艺术家使用社会学的方式,他仍然是带着艺术家的角度和意识的,他依然不会等同于社会学。但从这个项目的主体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强调不同于常规的社会学那种科学、理性的调查方式的。
蔡影茜:至今为止,“六环”已经做到第38位了,通过大量的观察与合作,如果都是以艺术家作为主体,你认为“调查”“介入”和“研究”这几个说法在概念和实践上是否有区别?
李一凡:我觉得我们还不是一个“介入”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介入”是在另外一个层面的介入,这个介入是我们对五环六环间普通人生存的评价上的介入,一种公众对五六环看法的介入,不是通常意义上具体的介入到五环六环的具体生产生活中去那种东西。我们有一个看法,艺术家虽然今天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艺术家能做什么,艺术家到底有多大本事,我们是缺乏经验知识的。所以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是调查和了解,我们首先清楚自己,或者说我们要清楚这个地方的主体性是什么,而不是像旅行者一样走马观花或者只是来自某个大师的理论的简单判断。我们觉得首先应该是艺术家进入和了解这个地方,然后再谈介入、研究。这个项目最基本的要求是呆十天,有很多人愿意参加,但这十天对于艺术圈内忙于生计的大多数人其实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一开始就有门槛的设计。人人都可以当艺术家,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实际上你能不能做,当不当得了,是值得怀疑的。
葛 磊: 我个人觉得寄希望于通过“介入”来改变什么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我说的这个改变是通过项目的影响力带来政策上或物质上的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可能更多只是一些人甚至只是我们自身对这个地区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呈现出这个地区所包含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最想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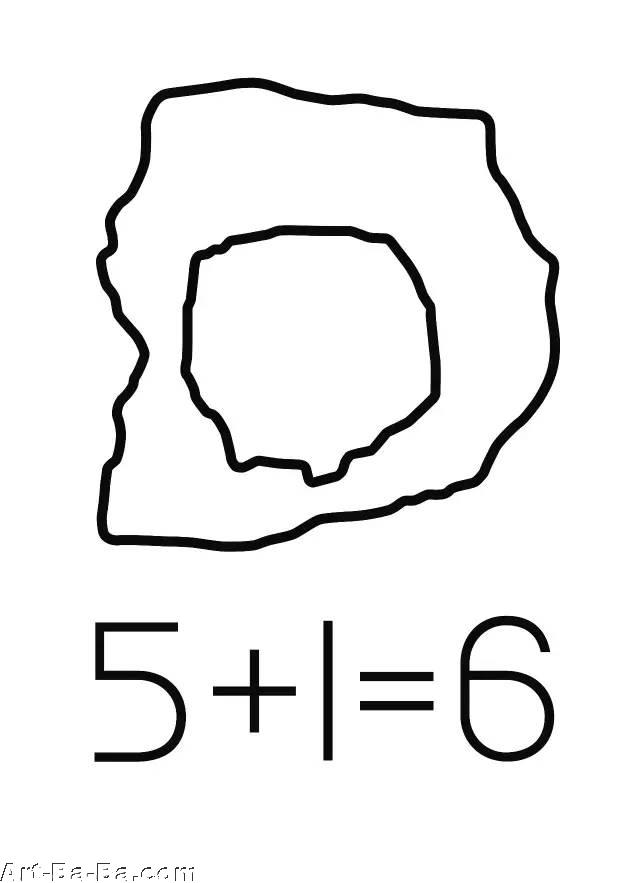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标志

标有38位艺术家调查地点的北京地图

位于草场地村的二楼出版机构
蔡影茜:那我把刚刚的问题再推进一下,更具体一点,“艺术家”作为调查主体的必要性在哪里?他们和调查所接触到的对象之间又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李一凡: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做调查,艺术家有必要去凑热闹吗?我们和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共识,认为人类学、社会学是一种知性的东西,是一种方法的启示,而艺术是一种感知,感知是最接近具体事务真实的东西。而如何让五环六环的状况被更多人知道是我们更重要的目的,事实上对于整个北京来说,特别是四环以内,属于中央直属区的那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区域的现实,我们觉得这事应该让大家知道。
葛 磊:这个地区大量外来人口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交通、饮食、卫生、居住、教育问题,五环内的人尤其是四环内的人很多是完全不知道的。
李一凡:或者说我们真正想介入的、介入的对象,其实不是当地人,我们希望介入的对象是五环里面的人,那些生活更优越的人,比如白领官员中产资产这些人。让他们感受一个他们不了解的区域的真实,改变对这个区域的看法,改变他们对北京的想象:北京不是只有四环以内的地区的。
蔡影茜:五环到六环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区域,为什么会选定北京5-6环之间的行政村作为这个调查项目的地理范围?
葛 磊:北京的城市与郊区的分界可能在所有的城市中最为明确,政府的许多政策也都依据这条线来制定,像大车在夜里11点之前不能进入五环,五环以内不能养大狗等等。而绝大多数的外来打工者都居住在这个区域与从事产业接近的村庄中,他们担负了这个城市绝大多数体力劳动和服务性的工作,自身的权利却得不到保证。据今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地区的人口就有580万,虽然我们认为远远还不止此数。
葛 非:十年前我们说的城乡交合部,是在现在的四环五环之间。到了今天四五环应该是很好的地段了,其实就是城市化的社区及配套商业已经扩张到四五环之间,居住人群也很多。那么为城市服务的务工者们又被赶到五环六环之间,可能再过十年就是六环到七环之间了。现在特别明显的是以五环为界,以外的就是城乡交合部,所以我们选择了五环到六环之间这个区域。而且从二环到五环之间每两环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但是从五环到六环,宽的距离有二十多公里,窄的也有十公里,所以这块区域是特别大的。
李一凡:这个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在中国只有北京有集中式的贫民窟,在其他城市都是弥散式的。比如在广州有很多孤立的城中村,贫民区是弥散式的。北京是环形集中式的。
蔡影茜:所以你们其实是把五到六环定义为一个贫民区的概念吗?由于城市化。
李一凡:当然这样说又有点简单化。
蔡影茜: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很少使用的,因为它形成的背景很不一样。
李一凡:我们觉得这个区域应该是一个多重描述吧,比如说城乡结合部、贫民窟,或者说是城市中最广大的区域,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域……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描述方式。但是集中式的贫民窟确实是震撼了我们。
葛 非:因为历史的原因在五六环之间也有很多别的功能区域,比如北京最好的别墅区和国际学校也在这里。不能说是贫民区,是随着北京城的扩张出现的不同的功能分区。
蔡影茜:刚才李一凡也讲了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比如说和艺术家的合作。在选定了地理范围之后,“二楼”和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葛 磊:最初的一些艺术家是我们邀请的,后来很多都是主动报名参与的,许多是学生。
葛 非:我们主要是提供服务,提供一个平台。
蔡影茜:你们的服务是什么?
葛 非:提供好多服务呢。
李一凡:比如介绍周围的、村庄的情况啊,对调查提供一些帮助啊……
葛 非:从外地来的艺术家们如果不熟悉到底选哪个村适合做调查项目,我们会把一些村子的基本资料提供给他们。而且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和艺术家们的对接工作。然后也有少量的一些住宿补助及差旅费。
蔡影茜:这是非常正规的机构的工作方式,其实已经很全面了。我好像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你们整理出来的,给艺术家提供的区域背景资料。
葛 磊:主要是村庄的资料,每个村的基本概况,不同的特点。
葛 非:中国的基本社会信息资料不太清晰准确,要我们自己各种方法的去找,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资料。而且,五六环之间村子的形态也不一样,居住的人群也是为不同的商圈及产业圈服务的,因此我们会把不同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给艺术家们介绍一下。
李一凡:北京的(艺术家)熟悉的就自己选。
蔡影茜:是不是说你们也通过艺术家的项目,加深了对每个区域的了解?在微信看到的都是单个艺术家的项目,你们会不会就整个《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以二楼作为主体做一个概括性的出版或者展示性的总结?
葛 磊:后期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版物,就是调查报告的整理、出版,另外一个是做一个文献的展览。这个展览现在也正在准备中。
蔡影茜:选择参加“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大部分艺术家似乎都不属于北京画廊和机构圈中频繁出现的面孔,另外还包括部分非艺术家身份的参与者,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葛 磊:我们是欢迎任何人参与的,我们既没有权利更没有标准说去选择哪些人、不选择哪些人,实际上所有希望参与而又时间允许的艺术家最后都参与了。至于在流水线上忙活的艺术家,没有人与我们接触过,可能参与这类项目对他们来说是在浪费时间吧。
李一凡:今天艺术在中国已经很清晰地分为了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称为表演和行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更多的人是在进行以视觉为中心的表演,只有少数建立了视觉是为行动服务的观念,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区分。在画廊——博览会体制下的这些艺术家,大多数都是表演型的艺术家,都是以图像为核心的艺术家。说句实话,今天的东西虽然和前一段的大脸和这个文革、波普、卡通表面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从来没有逃脱过图像学,所以这个是两回事。我用一块石头来举个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区分,在图象学阶段画好一块石头或做好一块石头,或者选好一块石头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它内部的问题是像不像、是不是。但行动的艺术是要把这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造成的涟漪对于行动的艺术家是更重要的。这块石头的好坏是根据对涟漪的判断而进行的。其实在审美上这个早就已经分成两部分了。
葛 非:流水线上艺术家,其实就一直在讨好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他们呈现的作品大多就是现在的一种家庭装饰陈设。如今艺术圈主流的洋行、买办加劳工的状况对于我们来说是反动的,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是那些精英阶层,我更倾向于艺术本身更需要被介入。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下,艺术能做什么?如果抛开上面说的情况,在中国,艺术的实践应该接地气,应该发生在我们现实的人生及生活语境中。因为“人生”这个概念要大过“艺术”这个职业概念,我们就活在这么一个空气有毒,食品安全都不得不到保证的现实语境下,他们这种艺术形态,我觉得挺可耻的。我们就想以不同方式去实践,而不仅仅艺术就是以工作室、画廊、博览会的形式存在,所以我更倾向于是行动这个线索。
李一凡:我前天去参加了一个人类学的会议,在民大。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会,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话语方式。比如说谈音乐,这个民间音乐对应了一个什么事,这个舞蹈对应个什么事,或者某个仪式对应什么事,非常长知识。但讲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叫刘铁什么的,是费孝通文革后的大弟子,最后做了个总结,他说我们做了那么多,但丢掉了费老的一个根本的传统,费孝通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费老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葛 非:西方当代艺术的那种精英审美趣味的展览形式及作品已经让人早就看吐了,而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多年的补课之后,方法与呈现方式上终于与西方人做的没什么两样,可以上生产线了,甚至生产效率更高。
李一凡:我觉得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到当代,其实是一个从视觉奇观的发现到观看方式的发现,最后是观看者和参与者成为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

2013年10月,李一凡在皮村与儿童聊天

2015年1月,葛磊在董村探望参与项目的漫画家子杰

2014年10月,满宇、葛非、葛磊在北四村探望参与项目的艺术家刘伟伟

2015年3月,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人庆在皮村“工友之家”举行的项目讨论会上发言
蔡影茜:观看者和参与者成为一体,那其实是不是一个观众的解放呢?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确实有五环以内的白领通过你们的订阅号了解到这样的真实了吗?他们能接触到这个渠道吗?就通过二楼的项目,是怎么接触到的呢?
李一凡:微信、自媒体还是有很多人看的。
葛 非:当然我们希望越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毕竟是有限的,只能尽我们的可能去说这个事。
李一凡:这种感知方式的东西,是微观的、渺小的、渐进的、是靠很多人做,不断的累积才有力量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种东西某些方面跟纪录片有一点像,它有两个部分的作用,一方面是史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它有艺术的价值,可以以感知的方式表达艺术家的看法。
葛 磊:这个史料的价值是我们后来才意识到的,可能这个区域五年、十年之后就会很快变成今天四、五环之间的样子。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文字、录音和影像资料,仅文字目前可能就有一两百万字,它所携带的信息量是极为丰富的。
蔡影茜:那订阅号这个媒介是怎么考虑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播有没有限制呢?
葛 磊:因为订阅号的形式所限,更多的是发布一些艺术家的工作进度和成果,其他没有太多好的形式。项目结束之后,面对大量的素材,可能我们整理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李一凡:我们的工作结束了,但艺术家的工作未必结束,他会可能继续做下去。二楼作为一个平台,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提示、服务这样的工作。二楼不是一个教育机构,也不是一个展览机构或者宣传机构。
蔡影茜:刚刚葛磊提到展览,你们认为展览这个形式仍然是必要的吗?
葛 磊:不是常规意义上视觉化的展览,是一个文献的展览。
李一凡:作为展览来说,我觉得我们在微信上每个参加的艺术家每天八次发布就是展览,就已经完成了展示他们的肉身感知,起码是某种展览已经完成了。但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区域,让大家了解这个区域比我们要去做艺术展览更重要。所以做一个当代艺术展览,还是说不做一个当代艺术展览,对我们来讲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让别人了解这个五六环间的事。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完成一个视觉上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发微信,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了解这个区域。我们的行动就是调查和发布,让人知晓这个区域,改变人们对这个区域的看法。
蔡影茜:展览是在一个特定空间和时间里,以一个三维的方式呈现的。在微信上则主要是阅读为主的……
葛 磊:空间的也是以阅读为主。
蔡影茜: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空间?为什么要有一个空间来把这一些调查、项目呈现出来?它有什么必要性?
李一凡:因为它有另外的读者群和观众群。
葛 磊:不同的方式吧,我们都愿意试试。因为微信可能在朋友圈里转转,大的人群总是固定的,无非是朋友的朋友看到了。
李一凡:包括前几天我去开人类学的会的时候,也谈到5+1=6。人类学家他们那拨人也有兴趣,但在这个之前没有我们的微信,他们不少人就表示要来看这样一个展览。
葛 磊:大多数关注艺术的人类学家,他们研究的艺术还是音乐啊、舞蹈啊这样比较传统的类型,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沟通。
蔡影茜:我采访人类学家陈晓阳的时候,她提到例如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和艺术家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这些学者几乎没有与当代艺术相关的审美经验。在他们看来艺术还是传统的绘画、雕塑等等,他们很难去想象自己的学科与艺术结合的可能性。
李一凡:我们共同面对社会和人类的某些问题,享用共同的人类知识,前几天参加人类学的一个论坛,发现我们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看的有很多书都是共同的。但是我们各自的工作是不同的,我发现今天知识界有个误会,好像我研究了社会就是社会学,我研究了人的行为就一定是人类学,那社会学研究了图像就是艺术吗?说个不好听的比喻,做了爱就是做了性学研究了吗?我们又没说我们在做社会学,我们借用了社会学的某些方法去感知社会,做的不是社会学,是艺术。
蔡影茜:但是还有一套就是语言问题……就是话语方式的问题。
李一凡: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常说人类学没有边界的,象滚雪球一样滚到哪,哪就是人类学。当代艺术何尝不是,新的语言总是产生在边缘的。
蔡影茜:学术研究一般会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问题。但是艺术家在这样的调查中,一开始往往用比较直觉的方式开展,问题的预设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所以学术研究和艺术家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李一凡:方法论肯定不同的。
葛 磊:其实人类学也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哪有绝对的客观,每个人都是带着自身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来工作的。
李一凡:它不是一回事,要是一回事的话就变成一个种类了,对吧。它毕竟不是一个种类,我觉得这种学科之间的纠结毫无意义,画地为牢是陈旧的思维。
蔡影茜:在你们这么多跟不同艺术家的合作里面,有借鉴其他的学科吗?借鉴的比较多的是哪一些?
李一凡:我们开始强调的是艺术家的方式,或者我们说以艺术家自己的方式。
葛 磊:其实对一些艺术家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的方式,像徐坦、刘伟伟和张玥,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工作的,我们的项目可以算是他们纳入自身体系一个小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来到我们的道路上走了一段自己的路。
蔡影茜:艺术家在开展研究或者调查的时候,一般都带着自己特定的概念去开展,然后会用一个相当自由的方式去诠释研究或者调查的结果,并不会去遵循一个特定学科的范式和方法。这一点在徐坦身上也是很明显的,他用一种近乎是自由联想的方式建立起研究当中语词序列。
葛 磊:这一点我们对艺术家没有任何规定,艺术家们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有的艺术家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个或几个方案,有的艺术家没有一个预设的东西,来到村子里寻找问题。这只是不同的工作方式。
李一凡:因为有的艺术家到现场之后发现他构想的方案跟这个区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会给他说这个村有这个特点,那个村有那个特点。你自己选吧,哪个适合你。
蔡影茜:你们所有的项目里,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
葛 磊:很多都有,但多数是艺术家需要自己面对的。
李一凡:也有一些做几天做不下去的,呆了几天,然后写了一个报告说我做不下去,然后就走了的。因为北方的农村挺艰苦的,也挺复杂的。
葛 非:有一个调查学校的,在这个区很多学校都是黑学校,它们生存在夹缝里,特别怕人去关注它们。当艺术家去关注它们的时候,带给它们的就是实际的压力。当艺术家面对这种现实情况,调查工作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最后放弃了。
蔡影茜:对,因为这些都是打工子弟学校。“六环”这个项目会一直进行下去吗?
葛 磊:这一阶段的工作近期应该差不多了。
蔡影茜:怎么决定该结束了?
葛 非:首先因为我们自己工作量也挺大的,第二我们希望这一阶段工作结束了会呈现出什么出来,而调查项目还能够持续发散,并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及兴趣。
李一凡:有人要继续做我们都支持,谁要把“六环五环”接过去我们欢迎。或者有人挂二楼名下让我们帮点忙也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不放在这了,我在重庆,满宇去了西安美术馆,所有事都落在葛非、葛磊身上,特别是葛磊几乎所有的具体事情都落在他身上,他们太累了。而且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开展。
蔡影茜:下一个计划会是什么?
葛 磊:有几个方案都在讨论,但还没有决定。
蔡影茜:一共开展了有多长时间?
葛 磊:去年十月开始,九个月吧。
蔡影茜:你们现在那个展览的计划会在哪做?会在什么时候?
葛 磊:会在一个书店,七月初,七月十号左右。我们没有选一个美术馆,因为书店我们觉得传播的效果会更好,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美术馆或者画廊,看到的还会是那些人,在书店,观众的群体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会做过于视觉化东西,即使图片,在这里也只是资料。你来看这个展览就是要来阅读的,当然读多读少那是你的事情。

2015年7月,单向街书店“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现场
访谈对象:二楼出版机构,李一凡
访谈人:蔡影茜
文本摘录:李承恩
校对:蔡影茜,谭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