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白壁Whitewall
Sterling Ruby——ECLPSE 蚀 /SCALES 天平
访问/Dirk Snauwaert
整理/ValerieLambert
策划及编辑/丁燕燕
摄影 / Hedi Slimane

Sterling Ruby,2010。摄影Hedi Slimane。Sterling Ruby工作室提供
2008年,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Roberta Smith(罗伯塔·史密斯)以“本世纪出现的最有意思的艺术家之一”来评价Sterling Ruby(斯特林·鲁比,1972年出生)。事实上,与同期的其他概念艺术家不太一样,Ruby每天在工作室里面挥洒劳力,将那种几近分裂的、躁动的能量尽情地发挥在他多元的创作上。他的实践往往将广泛的美学策略同时用上,让它们以爆炸性的方式相互碰撞。他的创作涵盖绘画、雕塑、装置、陶瓷、拼贴画、喷漆画和录像等,他的作品是一种平衡行为,维持着诸多元素间的恒定张力。Ruby今夏在比利时的Xavier Hufkens画廊举办了个展,带来他的全新系列《蚀》(ECLPSE)和《天平》(SCALE)。我们有幸请来比利时著名策展人及WIELS当代艺术中心总监Dirk Snauwaert与艺术家环绕着这两个主题,进行了对谈,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Ruby的作品。

《ECLPSE》展览现场,比利时Xavier Hufkens画廊,2015年。摄影Allard Bovenberg(荷兰)。Sterling Ruby工作室及Xavier Hufkens画廊提供
Dirk Snauwaert (DS):在纽约、柏林看到你的展览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也有幸每隔三年都能在比利时欣赏你的作品。《蚀》(ECLPSE)展览中透露的新方向让我颇感意外。标题本身具有一种至上主义(Suprematism)和神秘主义色彩。你是否正在经历生命的新阶段,还是其他因素激发了这种变化?
Sterling Ruby (SR):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努力精炼,让作品更容易理解,以便在更普世化的语境中呈现。我想要更直接,不需要探究作品背后历史的观念内涵。当然,现代主义还是有的,比如Bauhaus(包豪斯)、Malevich (马列维奇),但我确实希望更精炼,不仅是个人历史语境,也包括时代语境。

《DOUBLE VAMPIRE 4》,2011。布料、织维填塞物。414 x 520.7 x 17.8厘米。Sterling Ruby工作室提供
DS:你们这代人一直在与各种“后-主义”拉锯。两个系列的并置指向了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的两个重要概念——拼贴和抽象——并且现在依然在为你们提供养分,引领你们在数字化生产的陈词滥调中转向触感和手工制造。什么原因促使你这代人回归手工化艺术创作?

《ACTS/SURVIVALHORROR》,2015。氨基甲酸乙酯、染料、木头、formica 塑料面板。168.3 x 260.4 x 88.9厘米。Sterling Ruby工作室提供
SR:我今年43岁,与我同龄的也有采用现代主义手法和姿态修辞。从我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看来,大部分同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均来自一批蔑视现代主义的艺术家、理论家和哲学家;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围绕观念行为和极简主义;我们会因为试图融入真心而遭诟弊,因为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声称世上已再无真心。姿态具有欺骗性,艺术史亦不足为信,你不能创作手工性的作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时代不需要这些,它与文化和技术不符。

《Basin Theology/Red Bull》,2013,陶器。48.3 x 94 x 99.1厘米。摄影Robert Wedemeyer。Sterling Ruby工作室提供
DS:还有材质的问题。不少与你同代或更后期的艺术家选择回归二、三十年代,采用拼贴的手法,但却借助电脑完成。他们回归的是机器制造或生产,而不是手工。在你的作品中,有一种间接或直接的基础物质性和手工性,而且看不到现代主义美学的机械元素。

《Red Uniform》,2009,氨基甲酸乙酯、邦多、钢、 formica塑料面板、木头。 295 x 58.4 x 58.4 厘米。Sterling Ruby工作室及Xavier Hufkens画廊提供
SR:活动雕塑,或者说“天平”系列(我这么称呼它们)的作品都很零星、手工性很强。要做更具手工性和基础物质性的作品——我希望在工作室进行创作,从工作室中提炼瞬息,把以前创作的碎片融入新的作品中。我知道理论还在发挥作用;我也知道我们可以从历史、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角度讨论这些作品。如我所说,即使在形式和其他方面依然有叙事基础,这依然是一种精炼。
DS:我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是因为你触及了两种极端现代主义修辞:Marcel Duchamp(马塞尔·杜尚,1887–1968)的晾衣架和Man Ray(曼·雷,1890 - 1979)的熨斗所体现的运动和偶然性以及对物体的客观性的审视;新造型主义、至上主义、蒙德里安式(Mondrianesque)、包豪斯风格对物的本质的审视。活动雕塑的叙述既非后现代主义、也非自传式或英美国式的,也没有许多跳跃或断层,你可以自由联想。但在绘画中你利用了剪贴图案——这正是极端现代主义元素,纯粹的形式,如Hans Arp(汉斯·阿尔普,1886 - 1966)的作品,其形式是由自然(也是一种偶然因素)通过某种看不见的“手”塑造的,体现了纯粹的存在。在观展过程中,观众肯定会联想到Ellsworth Kelly(埃斯沃兹·凯利,1923年出生)。但你的作品还融入了其他东西。有一件让我想到Robert Motherwells(罗伯特·马瑟韦尔,1915-1991)的《西班牙共和国挽歌》(Elegy to the Spanish Republic),一种高度抽象表现主义的表达引向了极简主义。当然,最先让我想到的还是Ellsworth Kelly。但是你似乎把剪贴的正面和反面倒转了过来。
SR:很容易认出Ellsworth Kelly 作品的形状、原色和造型,但作品也借鉴了儿童书——我会给我的三个孩子念的儿童书。这让我获得了从艺术史视角转向家庭环境视角的自由。
作为美国艺术家,我觉得自传已不再是当下会话的组成部分了,但我还是希望以自传的模式工作,活动雕塑所蕴含的瞬息性不仅来自个人物品,也来自植根其中的语言——由我的空间、工作室和过往作品构成的语言。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具有隐喻意味的、悬挂式的立体雕塑。我很喜欢《蚀》这个题目,因为这是一个独立完成的过程。当然,你可以说图形也会互相重叠侵蚀,但此处的“蚀”贯穿历史和我的自传式研究,推动创作的不同部分。

《SCALES》展览现场,比利时Xavier Hufkens画廊,2015年。摄影Allard Bovenberg(荷兰)。Sterling Ruby工作室及Xavier Hufkens画廊提供
DS:没错,但在活动雕塑中,显然你用彩绘的原色和零碎的硬纸板来打破预制材料的密度。原色关乎现代主义对于透明清晰的憧憬,是最高的理性视觉原则。而你之前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不透明”也保留着,你把两种相反的概念融于一体。Alexander Calder(亚历山大·考尔德,1898 - 1976)的作品也非常超现实,具有丰富的感官联想,但在Calder或Joan Miró(胡安·米罗,1893 –1983)的作品中没有透明元素。看到你的活动雕塑我会想到Cady Nolan(卡迪·诺兰,1956年出生),感觉都非常美国。但硬纸板元素较少。
SR:从某些方面来讲,活动雕塑与我原先设想的完全相反。当我最初考虑活动雕塑时,我会听取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的想法,包括Chris Burden(克里斯·伯顿,1946 - 2015)、Mike Kelley(麦克·凯利, 1954 - 2012 )、Jason Rhoades(詹森·罗德斯,1965 - 2006)等——这批加州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点:把重量放在平衡系统中考量,特别是Chris,他在创作的时候一定要采用不同重量的物体,然后找出平衡点。但我把Chris 的作品和美国司法体系联系起来,其中有法庭的图像,而且他的作品政治性很强。Mike和Jason也是如此。但因为他们与我年代更接近,每每看到他们的作品我都会立即想到作为前辈的Calder。
DS:当然,但还有Jean Tinguely(尚·丁格利,1925 - 1991)、Alexander Rodchenko(亚历山大·罗德琴科,1891 -1956),都是反重力雕塑的先驱。反重力对于艺术家是极大的挑战,因为重力非你所能控制。而看着这些完美的造型,这又是来自于Ellsworth Kelly或Mike Kelley。这是超越画布造型之外的空间问题。
它们与周围空间形成互动,对周围空间进行定义,但并非如抽象表现主义那样只定义画布空间——如Clement Greenberg(克莱门特·格林伯格,1909 - 1994) 所言,无法超越极限。Ellsworth Kelly打破了这一谶言。所以,你的手法很有意思。你把它们放在角落,然后以原色进行标记,这样一来,它们从纸上略去,而黝暗的感觉却留在了画布里。
SR:从形式上,我考虑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在想出“ECLPSE”一词时,我想到的是监狱或黑帮用语,采用某种系统中的语言。与蛋彩颜料的哑光有着直观的联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在过去6、7年中,我一直在进行喷绘创作,其表面也是哑光的。在创作喷绘作品时,我用的是罐装喷漆,这可以说是创作风景画的“新”材料。我喜欢延续哑光表面。一旦某件事做得太得心应手了,我就会不断挑战自我。我会借鉴一下以前作品的表面或材质,但我不会照搬,不会自我复制。
对我来说,创作全新的系列、从形式上去思考问题,这些是很有趣的。在创作影像作品《自慰》(Masturbators)时,我遭遇过与现在相同的困难。我得通过色情片中介来选角、搭景并招募工作团队……现在的困难与当时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本质一样,都让人痛苦。这一系列其实非常简单,但随着我在上面投入的时间的增多,最终的结果是要么完全没有平衡,要么完全平衡。花时间在作品上于我是很愉悦的,去琢磨构图、框架、造型、形式,因为对于语境我已成竹在胸。但即便如此,其创作难度与《自慰》不相上下。
DS:我们再回到闪亮与哑光表面的问题。这些蛋彩颜料类似15、16世纪意大利绘画颜料,这很有意思。
SR : 我是Jeff Koons(杰夫·昆斯,1955年出生)的粉丝,但我觉得Koons作品的闪亮表面很现代主义,而我想通过纯手工来打破现代主义的藩篱。过程很粗暴:剪裁、布置、胶合、上色。有些我会扔掉,有些我会把碎片卷在一起放到其他作品中去;有些甚至可能会存放10年,要根据我对它们的感觉。这是我对Koons这类艺术家的回应,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价值,而我希望创作一些没有生产价值、平面、粗糙的作品。
DS:闪亮的外表也会产生排斥观众的效果,让观众有距离感。你的作品是内吸式的,那些则是爆散式的……
SR:一些采用闪亮物体进行创作的人跟我说过,这就好像一层自恋光泽,从中你可以看到自己。这种清透、镜像具有排斥性。很难清晰地指出我所探寻的历史,因为我可能会觉得闪亮的东西看起来锃亮如新,也可能觉得它们很有年代感。
DS:以Mark Rothko(马克·罗斯科,1903 - 1970)为例,其作品表面有一种浸入式的特质,其尺幅以及缺乏亮度的特点引人入胜。它们所散发的气质别具一格。
SR:Thomas Hirschhorn(托马斯·赫赛豪恩,1957年出生)等艺术家的创作,它们的政治语境我很熟悉,但这不是我喜欢那些作品的主要原因。我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直接。所以我会思考我的前辈艺术家和他们的影响。Hirschhorn这类艺术家的成名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性,而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手工性。
DS:既是物质性也是“虚假性”,因为作品本身就标榜着:我是假的!
SR:Hirschhorn的作品常常看起来像是在骚乱中构建起来的,但当然你肯定知道作品是在工作室的房间里由助手完成的。我喜欢他的这种擅于打造骚乱效果的才华。能够让作品具备鲜明的文化、社会美学意味,但同时又让人知道这是在工作室里打造的,具备这种能力的艺术家很了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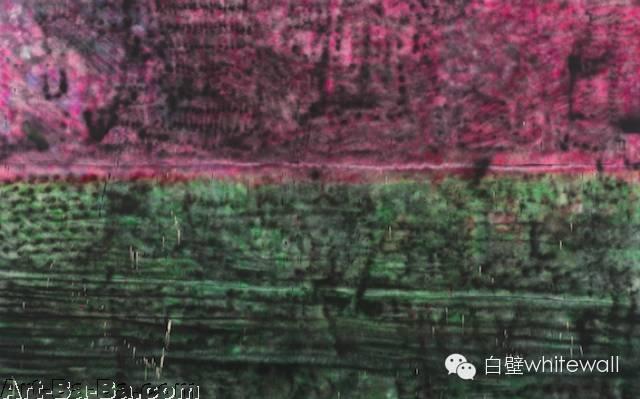
《SP108》, 2010,画布喷彩,317.5 x 469.9 x 5.1 厘米。摄影RobertWedemeyer。Sterling Ruby工作室提供
DS:你通常会使用文字标题,但这里你只用了数字。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或极端现代主义的游戏吗?
SR:我不知道。我喜欢给作品命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有时我思考的结果就是标题必须是一个图像。我会制作一个文档,然后从图像的眼光看上面的内容,大写字母通常设计呈Helvetica字体。从喷绘系列开始我便这么尝试了,这一系列的标题总是以“SP”开头加上一个数字。我喜欢这么编号,所以我连续几年都采取这一模式。当然,这也与我对城市规划、犯罪、警方代码等方面的兴趣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这种设计。我喜欢让标题看起来有图像的感觉。
DS:谢谢。
(翻译/邬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