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刘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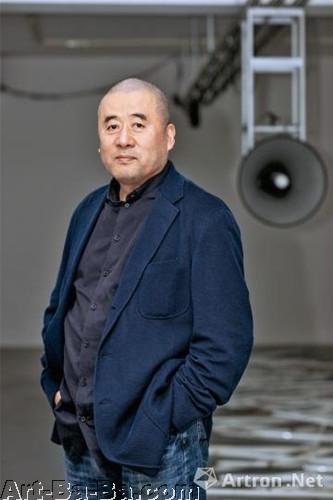
艺术家张培力
85三十年,再次回望那个没有画廊、美术馆的年代,上千名青年艺术家凭着一腔热情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谈论艺术,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关心人类命运,思考艺术本质;几年间,上百个艺术团队先后成立,无数艺术宣言发表出来,无数展览随时被关闭,却也冒着危险举办……经历了85,艺术结束了红光亮的时代,拥有了自由,走向国际和当代。
如今,85已成为被崇敬的丰碑和被纪念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来的快去的也快的时代,眼花缭乱的艺术已经把历史淹没,对于当下青年人来说,85的确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却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三十年的节点上,我们不禁发问:85精神到底是怎样的?85之于当下的意义?从85一路走来,那一代人经历了80年代的热血沸腾、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2000之后的市场洗礼之后,怎样面对时代的沉浮和身份认知?雅昌艺术网将带来这一思考:“85,现在还活着吗?”
艺术家张培力,从85至今,一直走在当代艺术的最前沿,他是杭州“85新空间”展览和“池社”的筹建者之一;1988年,他因创作了中国第一件录像作品《30×30》,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
对于85,张培力保持着艺术家应有的怀疑和反省,他始终认为:“艺术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解放,在于对权力、模式的消解。艺术一定是要呈现每个人最真实最本质最自由的那一面,艺术是多样的,所以自由是决定性的。”三十年来,张培力始终觉得艺术不应成为一种工具,85亦是如此。
85,不能被忽略的“欲望”
雅昌艺术网:在85三十年之际再回望您所经历的85美术运动,您觉得85精神是什么?
张培力:85精神是后来不断被书写、被描述、被阐释出来的,当时有一群年轻人在做了一些彼此有关系有趋同性的事情,后来被批评家和美术史家描述出来说是一种85运动和85精神,历史既然这样定义了,就是约定俗成。
85是由当时的时间来决定的,是不可复制的。85时期所有参与这些事情的人都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狂热的,把自己放很大,把这个群体也放很大,群体的力量就是彼此都是一种支撑。现在再仔细的理性梳理这段历史,我觉得即便在都很狂热的当时,不同艺术家和个人之间对于艺术、对于权力的态度差异还是挺大的。现在看来,从80年代走来的艺术家们依然各自都有对于85的不同态度,经过三十年的经历有些人的态度有所转变,有些人依然沉浸在原来85的热情中;有些人在85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如今特别愿意把85作为一种资源,似乎谈到85每个人的价值又回来了,这有点可笑。这样的意义过去就过去了,总体来说85只有在那个特殊的环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在1989年之后,艺术界迅速的从热火朝天的群体性美术运动中转换出来,有些人转变成个人化的工作,另一些人转换成商业性或艺术权力,在当代艺术中从反权威到了建立一种新的权威。
从时间角度来说,85精神是有的,是一种群体,一种对抗,但从每个艺术家对于问题的不同态度上来说,真的85精神在哪里?我不知道。
雅昌艺术网:那作为一个个体而言,在您的成长中真正受到现代艺术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培力:当我不是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了之后才去做事情的一个人,艺术家所做的事情是由早期对他产生影响的基本因素决定的,比如说我在进美院之前就已经知道塞尚、莫迪里阿尼这些艺术家,所以在进学校之前就对苏派的列宾、苏里柯夫的欣赏有了巨大转变,后来变成了一个极不规矩的人,老是要折腾,骨子里有一种不够老实的性格,老是想干坏事儿。
而85正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刚好是在文化、艺术和思想上比较开放的时期,也是第一次在原有的环境中允许你能够做跟以往不同的东西,而且自己刚刚从学校出来,跃跃欲试,对老的艺术看不惯,也觉得没有出路。艺术家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名,要获得一种关注,这是最实在的、最基本的冲动。在做了一些新作品之后被当时的《美术》《美术报》刊登,收到一些反馈。
其实现在看85时期的艺术家做艺术似乎都很单纯,但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是不能被忽略的,欲望是没有对错的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当时在媒体就是权力的背景下,媒体对于新艺术的刊登让青年艺术家们真的得到了满足,作品被《美术》刊登封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鼓舞。当然那时很多人看哲学、文学、思想史也受到影响,当我们突然有一天接触到这些跟以往学到的知识不同时,整个就乱了。
但你不能说个人的欲望在前面还是思想史在前面,两个东西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交错的,艺术家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圣人。现在很多人看老85们都像是圣人,没有人说达达艺术的艺术家们是圣人,他们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坏人”,他们也没有想过要拯救全人类,他们做的事儿好像是破坏的事儿,但客观上推动了艺术往前走。
“池社”时期
雅昌艺术网:那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整个环境开始变化了,在激情澎湃的时期找到出口了呢?
张培力:应该是第一次做了“85新空间”之后,似乎是明确了,不断的跟很多东西决裂,在艺术上决裂。我觉得艺术对文化或是思想史的贡献很多时候是偶然的、不小心的,艺术的本质可以成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部分,但艺术的思考跟哲学的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艺术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说的问题,在我看来说什么不重要;但文化史和思想史中,往往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否对人产生启发性。我觉得视觉语言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是不同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也不是为思想史和文化史服务的,但在中国我觉得一开始就被搞乱了,很多人看重的是你在说什么,视觉被变得忽略不计。
雅昌艺术网:您说的要跟很多东西决裂,是跟这样对艺术观决裂?
张培力:其实我是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当时有很多纠结,可以跟那些东西决裂,但不能跟周围的朋友决裂,不能跟支持我的批评家决裂,因为在其中我也得到了实惠和被满足的快感。实际上从86年开始,我跟杭州的朋友们组织“池社”就是表明了这样的一个态度,池社主要反对的就是“工具论”的态度,表明艺术这个东西不是用来为思想史和文化史来服务的,不是附庸的工具,艺术本身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不用去强调艺术以外的东西,因为艺术本身就是政治,就如至上主义在当时的苏联受到压制、表现主义在德国受纳粹压制、野兽派在法国受到压制,说明语言本身就是政治,这是艺术家应该去破坏的语言。艺术家要从语言上获得自由,仅此而已。艺术家不断在实践给人带来了很多启发,很多人不断在其中得到一些精髓,说明艺术不小心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内容。
雅昌艺术网:为什么取了“池社”这个名字?
张培力:是突然想到的,没有太多解释。我们有一个很短的宣言,全部都是短语组成,好像似乎对此由解释也似乎没解释。现在回想当时只是想一帮人跟猪似的整天混在一起,分不清楚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我们不是整天在讨论艺术、哲学,很多时候在一起看电影,传阅哪本书,那时候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下围棋特别疯狂,每天会画几个小时下围棋,也因为下围棋后面吃饭玩儿都在一起,然后做点儿艺术。我们不要把艺术弄的那么庄严,想调侃艺术的庄严性、庄严感和艺术家的神圣性,下棋跟做艺术有差别吗?没有差别。
那时候都是骑着自行车,大家住的也很分散,86年的时候连个BB机都没有,都用公用电话,约在一起,反正都是稀里糊涂的,现在回忆起来,池社那段时间是我整个生命当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很简单、单纯。

张培力 《仲夏的泳者》 172×170厘米 布面油画

张培力 《水中的泳者》 油画画布
性格决定的绘画
雅昌艺术网:从您85时期的线索看来,从“游泳”和“音乐”系列开始,为何会转向《X?》系列?
张培力:最初做艺术还是有一种担心的,觉得应该画一点别人能看得懂的,让人能理解的。我们做“85新空间”展览当时有一个背景,我与原来单位的领导闹翻,刚好跟美协几个人关系还不错,实际上是借调去美协,浙江美协出钱来组织这个展览,我觉得做的还应该能够平衡这种关系,当时画的是“游泳”和“音乐”两个系列。
后来觉得这两个系列有太多文学性在里面,画完“游泳”这些之后停了一段时间,想下一阶段该怎么做,虽然这两个系列已经得到很多肯定,也有一些批评家善意的提醒我说按照原来的发展下去会很好。艺术家的思考是与性格里的不安分分不开的,不愿意按照已经形成的路子继续走下去,没有欲望继续画下去,我就做不来乖孩子,别人说我的好心里会有点儿别扭。

张培力《休止音符(正面的吹奏者) 》布面油画 98.5×80cm 1986
在当时环境下大家都热衷的艺术在刺激我,包括别人对我的“游泳”“音乐”这些绘画的赞美,我突然觉得绘画从一种我们以前反对的所谓工具论又到了另外一种工具论;很多绘画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半抽象的、具象的,都跟重大命题和宏大叙事有关,似乎都在探讨哲学问题、人生问题、生命问题,这个似乎艺术承受不了,而且是不真实的,艺术就应该是探讨艺术,考虑艺术本身的问题,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态度,所以我就想画一些什么都不是的绘画。

张培力《X?》系列

张培力《X?》系列
雅昌艺术网:为何就产生了《X?》(手套)系列呢?
张培力:“手套”是86年开始画的,《X?》画出来很多人不明白,不那么容易让人理解,稍微受过一点训练的人都可以画,看上去就是物本身,就是视觉上的呈现,我不想承载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表现,就把一个莫名其妙的物甩出来。这个“手套”很简单,就是在厕所里打扫卫生的手套,从小的经验就让我会联想到一些东西,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手套不同人的生活背景、经验都可能有不同的联想。我那时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说的越少,这让人联想到的越多。就像别人说做艺术就像是一个空盒子,观众可以随意往里边扔东西。
这个系列从86年持续到87年,一年画了二十多张“手套”,很累,后来又烦了。当时意识到还是应该还原到我们讲的最基本的视觉上面来,视觉对于人的影响和心理影响是第一位的,所以实际上画手套有点儿是对于当时的一种调侃和恶作剧,你们画的里面包含着很多哲学的内容,我画一个你们看看能不能看出哲学来。
雅昌艺术网:1987年不再画《X?》系列之后呢?似乎后面的作品就很少涉及绘画了?
张培力:应该是在画完“手套”之后,87年就停了,后来我生了一场病。算起来中间停了两年,后面是90年开始画了一张作品叫作《健美》,这张画从来没有展出过,这张作品画的还是比较工整的,后来的作品就又不老实了,画开始出现很多变数、肌理和笔触的覆盖,再后面就是直接拿报纸、杂志的形象来画。1987年创作了《先奏后斩的程序——关于X?》和《艺术计划2号》两件文本作品,第二年完成了《褐皮书1号》。

《褐皮书1号》 医用乳胶手套、信件 1988
《褐皮书1号》是我从医院出来之后,需要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心里还是不安分,但又不能出门。就想通过邮局这个国家系统作为媒介来完成一件作品,我从央美的朋友处拿到一个学生的名册,通过邮局给大家寄匿名信,里面放手套和说明书。把名册里的名字以抓阄的形式一次抓十个,把匿名信寄给他们,也算是一个恶作剧。我记得一共寄了三次,方力钧、刘小东他们都在名单里面,每次去邮局都有点儿紧张,因为手套在信封里软软的有点儿厚,怕邮局的人问很多问题,反正做这个作品觉得挺刺激很兴奋,这属于蔫坏,不会抛头露面,躲在犄角旮旯里干一把坏事儿,性格使然。
雅昌艺术网:刚刚的对话中您不断强调的是性格使然,在您的艺术中性格起到的怎样的作用?
张培力:艺术家跟其他角色不太相同的地方可能是艺术家更容易受到性格的影响,性格在他的整个工作当中可能更重要,我是一个特别不安分的人,喜欢折腾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我特别怕死,其实我的性格有点儿矛盾,想做坏事儿又胆小;就像我想发坏,但是我肯定不会去干违法的事儿,因为我干不了那些我预感到可能要去蹲监狱的事儿。做艺术是安全的,可以满足一下自己比较小的使坏的欲望。

《30×30》录像截图

《30×30》录像截图:三个小时的录像,将一块玻璃摔碎然后粘贴完整
黄山会议:未得逞的“阴谋”
雅昌艺术网:接下来就是对于您来说绕不过去的作品《30×30》。
张培力:1988年的“黄山会议”我带去了《30×30》这个录像。这个作品话说白了,最基本的动机就是恶作剧,甚至原来的计划更恶毒。接到黄山会议的通知,要求艺术家带上新作品去现代艺术讨论会上交流,我就想做一个录像,完整的三个小时的录像,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我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枯燥的、乏味的、甚至让人厌烦的录像。
因为我原来想播放录像时把所有人关在房间里,找一把锁把门偷偷的反锁我就走掉了,三个小时之后把门打开。但也因为我是胆小的人,不能得罪艺术家和组织的批评家们,看了一会儿有人就说快进吧快进吧,所以我就摁快进,三个小时的录像十来分钟就全部放完了。
一方面是不能得罪大家,另一方面会议后来谈论的很多事情都是“89现代艺术大展”,那时候觉得中国美术馆就是一个宫殿,进中国美术馆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说是此生足以,所以为什么中国美术馆这样的一个展览出来那么多事,变成了一场竞赛,就是比谁做得更狠。
黄山会议那时候似乎还在组织里,但是实话那时我已经厌烦,大家在一起谈论艺术的问题,我觉得艺术不是这么谈出来的,三四天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过一天,除了在会议上放那个录像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黄山的街上转悠,我拿气枪打气球,打完转一圈回去大家还在吵架。
雅昌艺术网:那时候你已经对这种集体性的活动有排斥的心理,开始强调个体的重要性?
张培力:这样的意识不是突然出来的,其实在8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已经潜藏在性格中。当然千万别以为我是不合群的人,我是特别合群的人;也别认为我是不会跟人争论的人。

《(卫)字3号》 录像截图 内容是长时间拍摄艺术家为一只鸡洗澡,鸡从最开始不断挣扎、扑腾,到后面完全的顺从

《作业1号》 录像截图 录像内容是不断的对手指进行采血
雅昌艺术网:在这之后,能看到的是《(卫)字3号》等一系列与《30×30》的风格很相似的枯燥无聊风格时间持续很长时间的作品,大约持续了十年,为何会对这系列作品的兴趣保持这么久?
张培力:91年创作了《(卫)字3号》《辞海》《作业1号》,这样的作品持续到2000年左右。这可能跟我92年到96年期间频繁去美国看到很多录像作品有关系,有一些作品会让我特别兴奋,就像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在录像语言上的感受是相通的,那时我突然发现我特别想要有一种可以跟他们对话的语言,不需要看任何文字和解释,也不需要关心作品的背景,可以直接从录像中找到大家都可以解读出的东西,录像艺术是可以做到的,看到很多国外的录像之后感觉像是我很熟的朋友,突然间就心有灵犀的碰到了,在语言表达上大家心照不宣,所以回来之后把精力全部放在录像上。恰好那时候朋友有一台公司的摄像机在我家一直放着,我觉得最方便、最有可能来做的就是录像,所以那个时期我就猛做录像。
雅昌艺术网:那在这十年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变化的吗?
张培力:艺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关心的问题是自己常用的手法和语言上的新变化,比如我会把之前的方式推翻掉,像《30×30》这样长时间行为的录像就不想再做下去了,接着就继续寻找,因为录像语言在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发的,是一种自我完善和寻找的过程。有时候看到国外的艺术会有启发,比如从单视频到多视频录像的改变,我意识到录像可以成为装置当中的一个元素或录像艺术本身也可以成为装置,录像从视觉上对观众心理、感官上的影响是绘画做不到的;录像在屏幕中所出现的影像本身,其可能性是无限的。
1998年纽约MOMA的电影和录像部主任来中国跟我说,可以让我有机会去纽约学习一些纯粹的技术,我没有去,我觉得自己琢磨比正儿八经学一个东西要自由开心得多,对于技术我总是一知半解,不够用再去学,用完了就扔掉了,所以都是完全从作品角度来考虑录像。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肃,我也做不了特别严肃的事情,想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这对我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也是最开心的。
千禧年开启的“现成品”阶段
雅昌艺术网:可能外界对您录像作品的了解,除了这类早期的作品之外就用老电影片段剪辑而成的作品,这系列的产生基于怎样的契机?
张培力:我一直在讲,有新鲜感的工作会让人兴奋,对前些年的作品也会有厌倦,所以那个阶段之后,开始发现拍摄和剪辑无论怎样都避免不了主观性。现在想来觉得我的工作其实都是与客观条件是相关的,正好二十世纪过去,到了千禧年,网络兴起,我也有了自己的电脑。我想着要针对千禧年做点儿事情,我就写了一封信放在国外一个朋友的网站上,要征集世界各地在12月31号这一天晚上当地时间七点钟最重要的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关于千禧年的报道,我想看看不同国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何不同,结果就真的收到了二十多个录像带。
正好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就是影像。我就把每个国家的录像带进行简单处理,把广告剪掉,把新闻原原本本展出,每个国家的新闻用一台电视机,围成一个圆,声音也外放出来,现场声音非常吵,这个可以说是我第一个视频的现成品。
雅昌艺术网:从此之后,就产生了用老电影片段,也就是影像现成品所做的《台词》、《遗言》、《向前、向前》、《喜悦》等作品?
张培力:接着就是2001年的一个偶然事件,许江做了中国美院的院长之后希望建立新媒体系,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美院建这个系,我觉得对于教育这个事情我是愿意和感兴趣的。那时候美院先建了一个新媒体艺术中心,前期学校花了大约50万元买了一套大洋的设备,这可能是我做录像艺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操作这么严肃的设备。刚好那时候社会上盗版盛行,而且包括我小时候经常反反复复看的老电影,其中的很多台词、音乐、情节我已经再熟悉不过,当它们消失了很多年之后在盗版片里再看到,就特别兴奋,我就把老电影的光盘全买了。

《喜悦》 录像内容是对老电影的不同镜头进行拼接
在学校的时候就琢磨着去熟悉那套设备怎么玩儿,有一次就把老电影的光盘转换成数字版本,就在操作鼠标的过程中拉动影响的时候,我看到影像在屏幕当中的变化,那个刺激对我特别大,我突然发现影响力存在了一种书写的可能性,书写是不可重复的,一遍完成,而每次引动这个影像也是不一样的,我就特别想把此纪录下来,让它成为一个作品,纪录这个过程,但发现当时的设备是无法把视频实时发生的进程都纪录下来的,所以就把我想要的内容进行拼接,把原来电影的故事结构完全抛开,留下来全部都是片段,这个片段跟电影的本质是有关系的,对这样的语言和故事结构进行结构,让它还原到一种最基本的元素中去。
开启这一系列作品之后,我做的挺开心的,我觉得很轻松,这样的方式对我形不成任何约束,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由的、完全开放的剪辑,所以是一种自由的完全开放的一种剪辑,特别开心。观众也有不同的观感经验,像我这样对老电影有记忆的人来说再重新看这些东西,这种经验会产生一种对比的关系在其中。
雅昌艺术网:这系列作品的展出率很高,是各大重要联展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发展到后来是否也出现变化?
张培力:后来做过老电影元素的作品,跟后来的作品有很多关系,就是我在电影视频中加入了感应的效果,最早的一件是2006年的《短语》,我截了一段老电影中的一个解放军说的一句话。电影的背景是上海刚刚解放时在街上庆祝游行,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美国外交官说:“我要向联合国抗议。”一个中国的解放军说了一句话:“联合国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呢!”

2006年的《短语》展览现场
这是很经典的一句话,那时候中国也不是联合国的,我就用这句话的影像片段用两个液晶显示器面对面的播放,显示器下面各自有一个红外感应器,中间的距离是6米左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有一个门是从中间3米的位置进去,红外感应器设定的距离也是3米。这样,观众站在两个作品中间的时候视频是正常的,只要靠近一个,两边的视频的图像和声音都会发生变化,一个是加快,一个是放慢,声音也会跟随速度变细和变粗,两边的变化正好是相反的,所以只有观众站在中间的时候,两个视频才能正常播放。
这是第一件我把老电影作为素材跟红外感应结合,让作品跟观众的身体发生关系的作品,大约在2006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作品。
2007:虚拟与真实的电影式拍摄
雅昌艺术网:这个期间还开启了另外一种作品的模式,那就是“场景性”作品的产生,在此前的作品中很少会涉及这样“现场性”的作品,是如何产生的?
张培力:最早的尝试是07年的《窗外的风景》,那是我第一次用电影的方式来拍摄录像,把虚拟的场景跟真实的场景混淆起来。我当时在杭州位于灵隐的一个空间,从房间里的窗户看外面的院子是一种古典园林的感觉,窗户是很高很细的简单的窗户。

《窗外的风景》
我就用这个窗户拍了院子里气候的变化,从早上开始很安静的院子,然后开始起雾,雾消失之后开始起风,接着是狂风大作、垃圾满天飞,然后是风把垃圾吹赶紧了,天暗下来,开始闪电、下雨再到暴雨,下完之后阳光出来,院子回归安静,整个过程是虚拟的,但很诗意,是用电影的拍摄方法来制作了一个循环。我把这个影像打在了那扇真实的窗户的对面墙上,观众一进去可以体验真实的窗户和影像的窗户之间的关系。
雅昌艺术网:《阵风》《静音》就是从这件作品发展而来?
张培力:《窗外的风景》就影响到了我2008年做的《阵风》,其中的刮风就是这两件作品中的关系,《阵风》规模更大,虚拟的成分更多。过程是本来是一个安静的客厅随着起风而出现杂乱,随着风越来越大,客厅里的窗帘、鱼缸、壶、落地灯都被摧毁,整个客厅残破不堪,最后残破的客厅再次归于平静,这个作品是先搭出了专业的内景,又把它摧毁,我想告诉观众的是影像的虚拟与真实的关系,把虚拟和真实交织在一起。

张培力《阵风》 影像装置 2008年

张培力《静音》影像装置
拍摄《静音》时,是我正在准备做深圳的个展,作品是我在杭州的一间服装厂里拍摄的,那时的社会背景时中国的服装鞋帽在欧洲遭到抵制,我也了解服装这个行业的暴利和现状,我特别想做一个跟服装相关的作品,花20万元买下了一间即将要拆迁的服装车间。
在车间拍摄了两组录像,几十台老旧的缝纫机摆放在展厅中,没有人,只有机器、厚厚的灰尘和凌乱的现场,是双视频的投影。另外一组镜头我用了40个监控摄像头,按在还在工作的工人头顶上,记录他从早上工作开始到下班的全过程,用一组电视墙拼起来。展出时还展出了一台缝纫机,在缝纫机面前是两个巨大的屏幕和四十面小屏幕,大屏幕上放映了老缝纫机曾经所在的制衣厂大场面,小屏幕则放映着当时工作每个工人的近镜头。

张培力在"意派"中展出的作品《现场报道》
2009以来:机械、声音与技术
雅昌艺术网:关于这类“场景性”实验的作品之后呢?又对什么样的艺术感兴趣?
张培力:2009年开始的应该是机械和影像的结合。高名潞在今日美术馆策划了“意派”,我当时烧了一辆车,在车上装了60个针孔摄像头,又安装了一个60路视频的视频切换器,每一路信号都是一秒钟,视频不断的切换,通过大投影打在车背后的墙上,所以观众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被拍到,在这个作品中观众发现其实自己在观看的同时已经是被看了,他已经形成影像的一部分,这个作品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完全的机械,应该说是一件复杂的录像装置。
纯粹的机械作品应该是在上海徐震做的展览中的一件作品,我用两个骨头做了件机械装置,一个是真的牛的腿骨,一个是按照这个骨头翻制的玻璃钢的骨头,两个骨头在不断的碰撞,下面的骨头用用弹簧固定的,撞了之后总是不断的晃动,两侧都有针孔摄像头,拍摄到骨头相撞的影像通过投影投射出来,这算是最早的机械作品。
雅昌艺术网: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从影像到机械,是有原因的吗?
张培力:我对于机械也一直感兴趣,虽然之前没有做过这类作品,但是在2003年中国美院新媒体系有涉及到机械这方面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到机械也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途径,也是一种可能性,也收集了很多资料,学生们也做了很多机械的作品。后来我也就想着做一些机械和声音相关的作品。

《碰撞的和声》 机械声音装置 2014年
雅昌艺术网:所以就有了《碰撞的和声》?
张培力:这件机械和声音结合的作品在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最后的效果会怎样,在工作室里花了一段时间实验,把作品安装起来不断调整,即使在展出时安装起来依然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写程序和机械特别专业的结合。
声音跟视觉是一样的,我们讲人的生理和心理都会有一种固定的认为什么是好听的,也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接收的,跟生理的承受是相互抵触的。比如我身边有个艺术家是从台湾来的做声音艺术,主要做噪音,说实话一开始我接受不了噪音,它对我的生理承受是一个挑战;但时间长了之后,我似乎能从噪音中听出一些东西来,所以我是想利用这种关系,通过人固定的承受和不能承受的声音的矛盾性来进行一种呈现,这其实是人承受的一个限度空间。我主要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矛盾对于这件作品很多人会联想到人际关系、交流等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
雅昌艺术网:那最近的关注点又在哪里呢?
张培力:技术的可能性会影响到我,但我不承认我是技术发烧友。对于艺术我现在的态度有所改变,我以前反对艺术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审美,但是现在觉得艺术能够给很多人来愉悦也不是一件特坏的事情,只要你的作品不是有意识的去讨好市场就可以了。在艺术中,我一直反对的是模式化或是被模式化,艺术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语言而不是其他,更多的是要获得一种自由和对语言本身的思考。
再来谈85要反省的问题可能就在这里,85不是把艺术从一种工具变成另外一种工具,也不是从反对一种权力到建立另外一种权力,如果所谓的85精神实际上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反对的。艺术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解放,在于对权力、模式的消解。艺术一定是要呈现每个人最真实最本质最自由的那一面,艺术是多样的,所以自由是决定性的。
雅昌艺术网:那作为一位85时期的代表艺术家,经历了80年代的狂热、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2000年之后的市场洗礼之后,您觉得您这代人对于艺术的思考会有怎样的变化?
张培力:会不一样,不会像那个时候一样把那件事儿看的那么严重,这也是由个人的生活决定的。所以说“性格即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只能认命。如果一件事情你想做,最后结果怎样其实是不重要的。就像做艺术不是为了拿奖,拿了奖可能说明你做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共鸣,得到鼓舞。现在我总觉得好的艺术家越来越多,跟好的艺术家在一起对话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艺术家在没有交流之前,总会强调自己的特色、身份,会有非常多不满,会埋怨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你的艺术,但随着交流和对话你会发现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些问题看得淡一点吧。
雅昌艺术网:感谢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