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鲁明军

颜磊,《我能看看您的作品吗?》,1997年,印刷品
北京的艺术界似乎特别喜欢自说自话,以至于“北京”这个词被用于修饰“研讨会”的时候,往往不是在限定地理范围,而是在暗示话题的宏大、开会的密度、产生话语的频率。今天无论是机构举办的对话还是艺术家们随时打开的话匣子,其实都是批评家权力旁落的产物,也许,正是通过互相影响、碾碎、重造和传播,新的批评方式正在形成。
图像与语词、视觉与叙述之间的分歧和争执贯穿着艺术史。上世纪初,随着艺术的系统化、体制化和观念化,艺术和知识的关系变得愈加暧昧。格林伯格的声名鹊起,特别是“艺术界”的形成,一度赋予了艺术批评空前的话语权力,而展览策划、媒介传播以及艺术史叙事等也都随之成了这个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者说是艺术本身的一部分。
独立批评的消失或批评家权力的旁落无疑源自艺术体制的变化、建设性的参与,或者是对话自然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式。“胡志明小道”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2010年由长征空间策划组织的一次结合田野调查和学术对话的项目,参与的艺术家、学者包括卢杰、高士明、陆兴华、王家浩、汪建伟、徐震、刘韡、张慧及黎光定、阮如辉等越南艺术家和策展人。时隔五年多,在汪建伟看来,“胡志明小道”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所有当时参与对话的艺术家后来的变化,2011年他在UCCA举办的个展“黄灯”就是直接源于当时关于“黄灯共同体”的讨论,可以说就是在一种“强迫性”的对话中挤压出来的。包括后来的一系列思考和实践方式,或明或暗都与当时的讨论有关。所以,他一直期待重新找到一种类似“胡志明小道”这样的对话方式和机会。在这之后,徐震也曾坦言,当时参加“胡志明小道”原本不抱对话的期望,但后来发现,像陆兴华这样的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和方式原来和艺术家没有什么区别,是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于是,活动结束一回到上海,便在他的“怂恿”和没顶公司的支持下,金锋(小)策划组织了“未来的节日”项目,几乎每周一次对话和讨论,持续了将近四年多,内容涉及艺术、哲学、政治、历史等各个领域,参与的艺术家还包括杨振中、周啸虎、石青、张鼎等。其间,还邀请格罗伊斯、郎西埃做了专题演讲和对话。去年,石青创办了“激烈空间”,将不定期的小型论坛和对话作为空间的一个长期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延续这一方式和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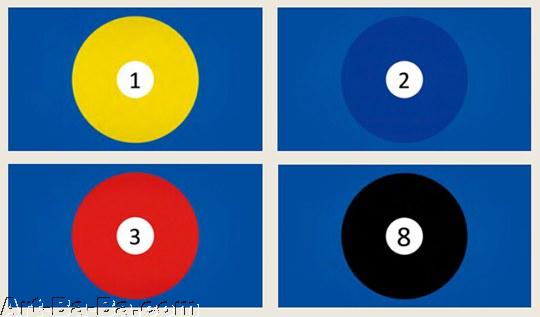
刘韡,《谈话》(视频截图),2008年,27频影像装置
本质上,诸如“胡志明小道”(包括坚持了数年的巴厘岛对话,以及2012年时代美术馆主办、沈瑞筠策划的“脉冲反应”,等)这种对话还是在一个“自足”的艺术系统内部进行对话。但实际上,哲学、政治等本身就包括了艺术的维度,而像医学、伦理学、法学等其他一些学科和领域与艺术还是缺乏直接的关联,所以,当艺术实践将视角伸向这些学科的时候,动机并不在于从中获得直接的参照和启发,而是同其一道,意在探触一种观看和审视世界的方式。因此,对话的前提不是实用和依附,而是一种并行的关系。就像前面所说的,能否构成有效的对话不再重要,知识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去年年底,由汪民安策划的“福柯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红砖美术馆举行。讨论主题涉及福柯与哲学、政治、伦理、艺术四个方面。会议吸引了不少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参与,并在艺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会议是在美术馆举行,而是由于福柯的思想乃至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当代话语的行动。所以,福柯理论尽管零星涉及艺术和艺术史,但在根本意义上,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实践。
迄今,国内艺术界的学术论坛基本都是临时的、松散的,尚未形成一种长效机制,用以确保某一个话题的深入思考和对话。相比而言,近年来由陈光兴、张颂仁、高士明策划的“从西天到中土”项目一直在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样一种延续自然取决于一套制度的保证。问题在于,随着社会、政治及思想潮流的变动,相对固定的论题或许会逐渐失去其现实感和建设性,也会疏离于当下艺术体系。除此之外,2005至2012年期间,黄专在OCAT根据其研究计划和展览实践而组织的一系列相应的讨论,都是围绕艺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展开的。他一直试图在艺术界与思想界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但他深感实际并不理想,有效的跨学科、跨领域对话很难展开。也或许因此,在确立OCAT文献馆学术定位的时候,他又将视角拉回艺术史。当然,这并不是重建一个封闭的艺术史知识系统,而是以此为基点,通过与宗教、哲学、考古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对话,建立一种阿比·瓦尔堡所谓的作为“文明的整体性”的艺术史知识范式。所以,自去年开始,他们将整理、译介西方艺术史学的演变作为现阶段工作的重心。这一知识方式显然不再直接针对当代艺术实践和体系,而是诉诸文明的解释这一历史叙述。
尽管这种“传统”的方式还是在延续,但实际上除非仪式性的讨论本身就是作品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公共教育、商业传播等),否则今天普遍还是更愿意选择类似微信这样的社交软件随时展开对话,所以讨论本身并没有因为“仪式”的缺席而中断,只是一个新的临时的、变动的“共同体”渐渐取代了旧有的知识方式或艺术方式。此时,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当作为知识生产的艺术方式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则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让渡。于是,如何重建艺术家身份成了一种新的焦虑和发声的起点。
前文附录
艺术家刘韡在2008年的作品《谈话》中采访了生活在北京不同文化领域的朋友,在这场不多见的艺术家主导的讨论中,涉及多位艺术家对讨论的看法,以及艺术家交流的某些特征,也包括对艺术与公共话题的、艺术体制的关系的简要讨论。
刘韡:很高兴这次给你做访谈,我想问一下你对访谈这个事情怎么看?
储云:如果说这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话,应该是像一种格斗吧。
刘韡:如果做访谈的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真实的一面表达给别人,另外一方面则不是一个很真实的表达,是做给别人去看的,你怎么看?
储云:我觉得真实的表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应该就是一种表演。
刘韡: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表演,怎么去进行呢?还有作用吗?
储云:大家假装就可以真实地自我表达,然后进行一种交流,好像可以发现事实的真相。我对访谈是有看法的,起码对我自己来说。它比较接近我们虚构的一种比较真实的事实的真相,但真实性其实在于它是一个事件而已,仅此而已。
***
刘韡:你上学的时候很认真吗?会很认真想问题吗?
杨勉:我觉得以前比现在认真多了。四川美院是一个小的圈子,你只有选择每天跟谁玩,在重庆那种环境里面其实没多少人可以交流。如果对艺术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可以经常一起谈话的人,就从理想中的朋友变成学术中的朋友,最后变成酒肉朋友。
刘韡:绝对会是这样,一开始大家都在谈学术,谈到最后可能无聊了,但大家又见面,就会变成不谈学术,变成酒肉朋友。
杨勉: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基本上你的思想我完全知道,干吗还要谈?
刘韡:学术上其实也没那么多问题。
杨勉:而且很多问题是不能拿出来交流的,是要藏在心里默默去为这个东西而努力的。其实艺术是一个人去为这个努力,如果有人愿意加入那就加入。艺术家其实不是说自己总结……如果有一个健全的体制,艺术家都不需要总结,自然有人给你总结。你只需要把你系统里,那些不对的东西,还不是正确的东西,挑出来,放大。如果是正确的东西,还要把它放大,我觉得这个艺术家挺傻的。
***
刘韡:我还是比较喜欢跟策展人有一种交流的互动,可能从我的作品本身也是这样一种状态。
王卫:你认为互动的必要性在哪儿?
刘韡:有时候可能会扩展我没想到的一些区域,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展览现场实施的,这种交流的过程让我可能更清晰自己的一些想法。
王卫:以前做作品我会去问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但现在我觉得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东西,跟别人一点关系没有。聊出来的东西其实挺表面的。不是一个深层思考产生的东西,我有时候不太相信大家能聊出来,当然思想的交流肯定是需要的,但具体到作品来说,这个东西是完全不能,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做艺术家有很孤独的感觉?因为它太独立了,不像做电影,它的展示是有社会性的,它是可以交流的,艺术家恰恰相反,完全是做给自己的一个东西,即使现在它已经非常社会化了,但是它的个性化还是很强。
***
刘韡:诘苍,你在欧洲待了很多年,聊聊你的身份以及各个方面的改变?
杨诘苍:欧洲的二十年对我来说很重要,见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经历的也都是惊心动魄的东西,但是更具体的话就是我的家庭都是欧洲人,从里面所体会到的那种所谓的欧洲或者所谓的中国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我喜欢从这里面具体的小细节去插入所谓对欧洲和中国的一些看法及对世界的看法。
刘韡:你做的东西,比如说欧亚细亚的旗或者珠江三角洲,更底层的想法是什么?
杨诘苍:最近看一个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的对话,说我们人类的思想现在还处于欧洲部落的那种状态,我马上就觉得很配我的思路。不管广州也好或者北京也好,欧洲、美国也好,从天文学家的眼中来看就像一个沙子那么小,如果我们的立足点就像一个天文学家的话,这个思路就会开一些或者开很大。看远一些的话,谈话的可能性就多得多。
***
杨勉:其实在中国物质文化生活是特别好,但是文化生活的品质我觉得是很贫乏,甚至我经常觉得我跟那些没文化的人比,比他们高不了多少,因为我们最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一起享受的比较统一的文化资源。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对文化的消费永远是滞后的,我们今天捡起来的东西是别人以前的东西,以前的东西是有一个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的制定已经完成,不需要我们去制定,不管是电影、电视、文学,全部都是。中国成了一个最大的文化翻译厂,谁翻译出来的接受面越大,它在中国的生态里边越受到重视,越得意,如果哪一天这个阶段过了,我们可以同时生产一些东西出来,完全不能代表大众,只代表个人,它就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
刘韡:你觉得时尚和艺术圈或者和其他的行业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张丹:我觉得它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吧,我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它有一部分跟审美有关,它的实用性可能更强一些。它是一种能消费的创造力。根植于两点:一,它必须是能消费的;二,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它这种美必须得是有创造力的审美,一种对美的创造力,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分解出去—可能是通过大众来消费这个东西。
刘韡:那么艺术呢?
张丹:我觉得审美只是艺术的一部分吧,我觉得艺术跟人有关系,比如说有喜怒哀乐、恐惧、愤怒什么的,它可能跟美完全没有关系。
刘韡:当然艺术圈它也有一个审美问题,但不同于比如说更大众传媒的,比如说影视这一类的。
张丹:大众审美可能要更窄一些,但它可能跟人生理上的东西更直接一些。
刘韡:动物性吗?
张丹:当然也有教育的因素在里面。
刘韡:但是我觉得恰恰不是动物性的,恰恰它只是一个引导,完全不是出于生理的需要或者什么样的需要。
***
刘韡:你怎么去想,关于现在的体制,世界的或者中国的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储云:我觉得如果说“体制”或者“系统”,就太学术了,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全球艺术公司。当然这个现在也在变,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出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可以承认公司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结构,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可以创造很多价值,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还是可以去探讨另外的一种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