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rie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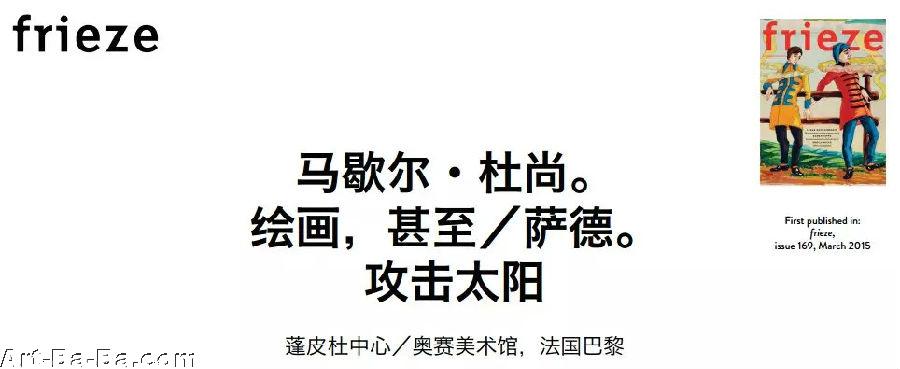

左:马歇尔·杜尚,《新娘》,1912;右: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维纳斯》,
1532;“绘画,甚至”展览现场,蓬皮杜中心/奥赛美术馆
2015年1月5日,周一,我到了巴黎,任务是证明一个假设,该假设由两个看似相互巧合的大展所引起:我想找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地狱之犬”萨德侯爵与20世纪观念艺术先驱杜尚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决定性的关联,不仅仅是“萨德展”中包含的几件杜尚作品,我怀疑这其中有着更深的渊源。6日下午我返回柏林,然后我们都知道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自那以后,仿佛在我的记忆中,两个展览总是被对那群漫画家和作者的集体谋杀事件所玷污。我必须“忘记”杀戮,才能重新看清展览;同时我又必须记住那件事,这样才能理解我如今为何,如何对意识形态、讽刺和暴力冲突产生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看法。
“杜尚展”策展人Cécile Debray抛出了一个有力观点,那就是绘画作为某种目镜使得杜尚看似支离破碎的作品全体得以完整呈现。这也是展览标题所暗示的:法语的“LaPeinture, Même”直译过来是“绘画,甚至”——意思是“是的,即使通过绘画,杜尚也可以而且必须被认知。”而标题的读音又很像“la peinture, m’aime”——“绘画爱我”,好像在说:杜尚也许在1918年放弃了绘画,但绘画可从来没放弃他,影响力与艺术家同在。考虑到杜尚实际的画作总数不多,展览借来很多其它作品,从他早期的漫画到晚期的手稿,还有其它艺术家包括马蒂斯、席里柯等人的作品,但这并不是一个障碍,相反,使得整个时代都鲜活起来。我们能看到杜尚在1912年之前的艺术形成期内是如何受到报纸上的讽刺漫画及早期默片的杂耍色情元素所影响的,比如投影在墙上的默片片段:一连串并非全裸的新娘表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一位姑娘脱了一半,一名躁动的追求者躲在折叠屏风后面。“要知道我不是和画家生活在一起,而是和卡通画家混在蒙马特……”这是墙上引用杜尚的一句话。他刊登在幽默类期刊中的漫画线条精确、节制。一幅《无题》刊登在1910年的“笑”杂志上,画的是一位姑娘戴着帽子穿着长袍躺在沙发上等待她的伴侣更衣;她问他干嘛要那么久,他回答到:“La critique est aisée, mais la raie difficile”——“批评是容易的,但是把头发分开则很难”。这句诗是杜尚从他非常崇拜的诗人Raymond Roussel那里借来的:“la raie’”的发音跟“l’art est”很相似,后者表示“艺术是”,这是一句双关语,指向一句法语俗语“批评很容易,艺术很难。”

保罗·塞尚,《被勒的女人》,c.1875–76,布面油画,31×25 cm
尽管文字游戏一直占据杜尚创作的重要位置,但他并不满足于当一名温和的讽刺漫画家而是走向了绘画探索。考虑到其最终完成作品的数量之少,其绘画的成功率是惊人的。他的《艺术家父亲的肖像》(1910)有一点点塞尚的风格但总体写实,画的是尤金·杜尚斜靠在椅子上,手臂顶着秃头挤出前额皱纹——这是对沉思人格的研究。同一年的《杜慕夏医生肖像》则大不相同,有着马蒂斯般浓烈的色彩,然而同时还有某种原始的超现实特质。杜慕夏医生是杜尚的老同学,是最早提倡在医疗中使用X-光的人,但是环绕他手边的奇怪光圈暗示着第四维度。此外还有《幻觉》(1879,“在梦里”系列之
8)中悬浮的,有光圈的眼睛中蕴含的魅像摄影以及Odilon Redon对于不可见物的暗黑视觉化。
讽刺的是这如此清晰地显示出杜尚这位一再强调“大脑”先于“视觉”的艺术家实际上竟然花费了生命中这么长时间持续观看:从早期具有野兽派风格的亲密沐浴场景如《坐浴缸中的女裸体》(1910)到后来复杂难解的《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的新娘,甚至》(1915-23)乃至他最后的杰作《鉴于……》(1946-66),在现场由Ulf Linde(1993–94)的小模型代替。
你所见的与作品所指之间的滑动在《下楼梯的裸女 No.2》(1912)中显现。如今关于1912年沙龙的立体主义委员会为何让杜尚把画布上的标题涂掉(从而导致画家的退出)一事还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与标题过于直白有关。鉴于杜尚的机智,委员会肯定还担心在本来已不寻常的主题背后还隐藏着某种一语双关——女裸体竟不是在闺阁或者大自然中,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半公共环境中。“裸女下楼”中的分解模式,把身体扇形地打开成断裂的机械,在同样创作于1912年的《新娘》中达到第二次巅峰。杜尚在一次慕尼黑的短暂停留中创作了该件作品,这一次他毅然与立体派和野兽派风格决裂,以微妙的色调,几乎是模仿古典大师的风格创作,仿佛他要回到历史中才能继续往前走。充满肉色的调色盘将复杂嵌套的齿轮装置转化为姿态万千的反常。1949年,杜尚提到他在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所看到的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作品是他的主要灵感,蓬皮杜这次在杜尚作品旁边展出了克拉纳赫1532年的作品《维纳斯》,合理地交代了这一事实。
杜尚令人不安的,对于女人体的冷漠的、解剖般的对象化矛盾地扭转为一种对于女性性欲的赞颂——这一主题在奥赛美术馆中展开,尽管调子要更黑暗一些。萨德侯爵,正如已故的Angela Carter在她的划时代著作《萨德式女人》(1979)中所指出的,以他“对性行为的恶魔般的抒情”,将“女性性欲的事实看作并非是道德困境而是政治现实”。在萨德笔下残酷的女主角朱丽叶那里,性行为的放荡无可避免与自由的观念相连:只要政治平等一天还未确立,性将被设想为一种暴力的,具有亵渎性的,对政治平等缺席的界定。“萨德。攻击太阳”的策展人Annie Le Brun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研究萨德问题的专家。像Carter一样,她把侯爵从男性主导的哲学化阅读中复苏成为一股自足的哲学力量。作为《萨德:一个突然的深渊》(1990)一书的作者,Le Brun在现场放映的一系列二十世纪电影片段奠定了展览的基调,从Luis Bunuel的《黄金时代》(1930),到Michael Powell的《偷窥的汤姆》(1960),再到帕索里尼的 《索多玛120天》(1975),后者正面挑战了我们所能忍受的残暴折磨图像的极限,也由此直面了法西斯的变态行径。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提醒我们,艺术家在离开这种对抗之后很少有毫发无损的,至少在道德制高点上,而我们这些被吸引的偷窥者也难逃一劫。Le Brun让这一潜台词贯穿了整个惊人的展览。 展览中历史意义最突出的媒介是印刷品,从18世纪JeanJacques Lequeu优雅的性学解剖图,到19世纪末Alfred Kubin对欲念与恐惧的想像,预示着卡夫卡和恩斯特的到来。

查尔斯-弗朗索瓦·让德尔,《两名被缚的裸女,各自侧躺》,
c.1890–1900,晒蓝照相,17×12 cm
复制品至少会让我们与艺术家之手产生一定距离;但当我们观看塞尚描绘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勒死的生动笔触(《被勒的女人》,1875-76)或者戈雅的小幅画作《食人族准备他们的牺牲品》(1800-08)时,我们不禁好奇艺术家在努力“移情”于对象的过程中究竟包含着多少黑暗。同样,对我们来说也不存在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疏离”——这些图像似乎直接诉诸我们最深的恐惧及最恶劣的欲望,假装后现代的麻木被证明只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被有关震惊价值的问题带偏,而应该像萨德本人一样思考战争与欲望之间的关联。毕竟战争——夺权与创伤的滴血盛宴是萨德所受的主要教育:他在有过百万人身亡的七年战争(1756-63)期间曾是一名青年陆军上校。“为了偷盗而杀人,”他在1799年前后写道,“小偷与将军相比作恶少得多,后者仅仅为了一己之虚荣而毁灭各国。”(他是想着拿破仑么?)整个展览不断引用的那些色情化的战争罪行画面,包括德加的《中世纪战争场景》(1863-65),上面被焚烧的村庄和被杀或被俘的裸体妇人都揭示了萨德对于接受暴君统治的万般不愿——他曾经帮助一名逃兵使他免受处死,并且是死刑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主张假如公民无权杀人,那么国家也无权杀人。
不管萨德个人从描写惨绝人寰的折磨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快感,可以明确的是,他本人从未犯过什么超越当今某个换妻俱乐部所能容忍的法律界限的恶行(至少根据他两次牵涉的法庭诉讼来判断):然而,他是第一个坚决将暴力色情化视为某种权利欲的特定形式的作家。他甚至可能是第一个毫无保留、事无巨细地描写暴力的性幻想的进行仪式,将其作为从压抑的性身份中解放的解药的作家。“攻击太阳”展览通过囊括萨德的怪异追随者而强调了这一点,从比亚兹莱到捷克艺术家托忍(Toyen),后者对于自己模糊的性别和性向供认不讳,在她的超现实同时代人中也算大胆超前——她还为萨德的《正义》(1791)一书配插图。杜尚的《飞镖物》(1951)是一件奇怪的、模棱两可的作品——一具用女性肋骨制成的软弱的青铜男根,后来将成为杰作《鉴于……》的一部分,另一个说明杜尚作品中性别倒置线索的例子。杜尚扭曲的平静也许可以视为萨德冷笑的好战的一种别样的继承——就像今天的教养和自由表达观念可以被视作与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性暴力相连一样。此刻,或者任何时候,都是重新审视这些联系的好时机。
Jörg Heiser
PUBLISHED IN : FRIEZE NO.169 MAR.2015 WWW.FRIEZ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