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网“翕如的日记”
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
1. 质疑碧山计划,乃是因为创始人说要建立“碧山共同体”,谈“村民自主自治”,但介绍理念PPT是全英文的,满是civil society、social engineering、party politics等等大词,不断提的是诸如瓦尔登湖、Skinner、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西文典故;特别强调记设想的本子是Moleskine。一切细节与Status Symbol都不断生成着文化的区隔,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甚至,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是村民,还有城市中不具有经济文化资本的普通市民。那么,当我们说"共同体",这是谁的“共同体”?
“碧山计划”的审美是极精英主义的;试图取悦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趣味、是从喧嚣都市短暂离开后能看到"盛开的油菜花"。碧山村没有路灯,村民十分想要——但是从外面来碧山的游客却认为,没有路灯,可以看星星。村民想要开小店、修马路、搞文化旅游卖门票创收,这一切,精英知识分子是不认可,甚至可以说是不屑的(当然和南京先锋书店一样,碧山书局里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售价108元)。精英知识分子来到田园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个体的人生路径不加以评判,然而当形成"计划"后,这过程中对田园乡村的想象,就成为了一种Othering,甚至能类比西方对“东方”的凝视。最后,“乡建”实验背后都有伦理议题——农村,是谁的农村?谁该决定村庄的发展走向?然而对乡建伦理的思考警惕,在一切讨论中都彻底缺位。
2. 和村委会座谈,说起碧山计划,村委会使用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不断强调的是“发展碧山村文化产业”,是请城里的“老师”来“打造我们包装我们”,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打造文化村、休闲度假村的建设”。而在村中和村民聊天,普通村民的说法是另外一套:“就是一群城里人来我们这买房子建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精英知识分子标榜的是“远离资本”建立“落地的乌托邦”,乡村治理者强调的是“发展文化产业”“青山绿水,吸引游客”,普通村民则似乎是游离于这一切之外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权力、社会结构与各种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故事。
3. 在碧山村,参观了农家书屋,也看到村里大会堂晚上妇女跳广场舞---不用花钱,人人能参与,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然而,碧山村仍然没有路灯,夜里出门,固然可以看到萤火虫,十分美丽,然而饭后一群人去买水果,雨后,没有路灯寸步难行。村民好心,打着手电送了一程。不到九点,四下俱寂。
4. 在此澄清一点,我从不质疑创始人本人的人生选择,更不诛心:认为他人品格和用心恶毒。我也不质疑创始人本人和那个小群体标榜的所谓"初心",所有质疑,针对的只是精英阶级充满优越感的自我满足与自我崇高化话语,以及这套话语中对精英文化、边界(symbolic boundary)与不平等的消费与再生成。创始人所标榜的"精神""悲悯""善良的心",这本身并没有问题,甚至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精神才是值得坚守的灵魂与精神,这虽然值得商榷,但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观,也可以。然而必须警惕的恰恰就是,这一套话语本身,就是精英主义与阶级性的,是将自己与作为他者的村民对立起来,隔绝开来。而这种警惕,就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视角。
5. 说起和正式话语里不是碧山计划一部分,但关系密切的某酒吧,村口大爷如此说:“他们和我们没有关系,关起门来搞……”
酒吧的经营模式,纯粹是经营者的个人选择,在此不做评价。但从这其中,或可窥见,这从始至终,并不是一个关于“共同体”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区隔”的故事。
6. 再放一则报道,似乎是媒体采访创始人本人的:http://www.yicai.com/news/2014/02/351488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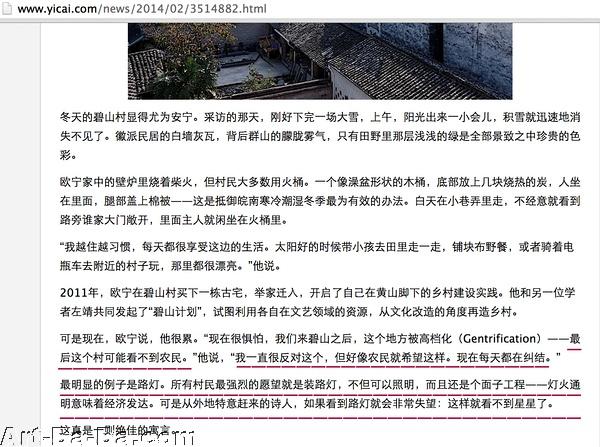
一些声音认为我提“路灯”vs“看星星”是断章取义(甚至用心恶毒),可以看一下这篇报道里的话语:
“最明显的例子是路灯。所有村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装路灯,不但可以照明,而且还是个面子工程——灯火通明意味着经济发达。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前文提到,在碧山的夜里,没有路灯寸步难行。其实不仅困难,而且相当危险——我和同行者在返程途中,就差点把住处前一片满是浮萍的水塘,当成了可以抄近路的水泥平地。然而,在这里,村民对路灯的渴望,被说成是对“面子工程”的追求——面子工程,在我国当下有什么样的语义和隐意?那么,是谁在诛心呢?
在这篇报道里,同样也有对“高档化”(Gentrification)的反对。且不说“高档化”(Gentrification)本身,就是对不同利益群体利弊极其复杂的,就说这里,碧山计划中反对高档化的立足点,并不是村民本身的意愿和生计(农民自己想要高档化,因为形成旅游产业后可以搞创收),但知识分子城市精英认为“高档化”后“村里就看不到农民了”,农村就没有农村"该有的"样子了------那请问在这场乡建运动里,农民是乡村的主体,还是为了满足精英对田园想象的、知识分子下乡后的“审美物”?
与此相似,在整篇报道里,碧山计划呈现一种强烈的对“农村该是什么样”的想象,甚至还有一种针对村民的“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为你们)好”的俯视心态。而这种想象和俯视心态,恰恰是充满已成为城市精英的局外人视角的——这种心态背后不自知的精英主义优越感,也是这篇文章批评的焦点。然而,农村真的有“该有”的样子么?农民真的有“该有”的样子么?就算有,一个村庄的样子,该由谁决定?农民是什么样,做什么事,如何生活才是“对”的,该由谁做主?
碧山计划的创始人,对西递宏村充满反感,认为村民“在村口抢生意、卖假古董”——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一面反感不屑“村民在村口抢生意”,然而碧山书局同样也卖价格昂贵的纪念品,此外还有城市精英知识分子来到碧山经营价格昂贵的乡村客栈。都是生意,都是经营,都是生活,却生生为它们赋予了价值秩序、情怀和品味的区别和差序,这其中的逻辑,如何自洽?
西递、宏村的发展固然不完美,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和空有其名的“碧山共同体”相比,在西递、宏村的发展中,村民至少是参与度更高、也有所获益的,而西递、宏村,对于城镇收入与教育程度在精英知识分子以下的“普通人”,也是更加可以接近(accessible)的。而当批判西递、宏村是在“表演”生活的时候,“碧山丰年庆”,就真的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表演吗?
最后,引用师兄的一段话,作为总结:“无论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都试图尽可能地融入到村民日常生活中去——以村民为中心,而不是以知识分子或者基层政权为中心。来自知识分子的新奇指导和鲜丽包装也许可以带来很多有趣的猎奇经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乡村建设运动,很难达成“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 的愿望。”
---
这篇文章,不针对个人行为。说的直白些,针对的是某种不自知的俯视与不自觉的、更毫无反思与自省的精英主义优越感。中国农村发展,到了如今,的确不该再存在"农村该是什么样"的想象,甚至这想象本身,就是局外人的视角。我不反对开一夜千余元的乡村客栈卖108元的笔记本本身,也同样不反对村民自己开店创收想要路灯和修马路。我反对的,或者认为应当警惕的是,将这两种行为,赋予价值秩序与情怀上的差序。我不反对各地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但我反对的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复制一套阶级性的不平等话语。碧山计划,从资本商人到乡村管理者,无论是说情怀精神乌托邦,还是文化产业旅游村,每人都有一套话语,在我们听到的讨论中,唯独缺失的声音,是居住于此的村民的声音。
从碧山书局回来路上,被一位老大爷拉进院子里聊天,我问他:"碧山计划和你们有关系吗?"
"没关系。我不晓得。"
又说起老大爷家四百多年的老房子,我问他:"这房子有人想买,你会要卖吗?"
老大爷回答:"有,我不卖,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我为什么要卖。"
这样的村民,也是这个村庄的居住者,却在很多时候,是被资本、权力、文化挤压到了失语的,沉默的居住者。
---
关于精英主义,多说两句:
和安徽农村出生的朋友聊天,说起油菜花,他提到一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他说,在观赏者眼中看到的是灿烂的油菜花,但是在农民眼中,看到的是从选种-播种-收获-卖钱(如果年时不好,就卖不到钱)的一套程序——一个是审美逻辑,一个是生存逻辑。这里并不是要说,审美逻辑是错的——这篇文章想说的恰恰是,同一件事物,因为观看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的区别,所看到的、关注的侧重点,就是迥异的。就好像村民想要路灯,但是外来的游人知识分子会认为,没有路灯,可以看到星星。这篇文章的核心,便是要说,所谓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对自己的结构位置具有自省。
我其实不太喜欢在评论文章中注入过多私人情感和情绪——那样很容易演变成:“我和你说道理,你和我讲情绪;你和我说逻辑,我和你谈感情”之类的沟通模式。但是行文至此,说几句私人的话:
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从小接受的始终是极其精英主义的教育。精英主义教育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断告诉你,"你和别人是不同的”——本科新生入学典礼有一个程序,是大家一起在校歌声中佩戴上P大校徽。这个程序非常具有仪式感,因为佩戴上校徽后,老师会深情地说,“从此之后,你就成为了‘P大人’”;哈佛博士新生入学典礼,校长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祝贺你终于made it,是the best of the best。精英教育,也讲情怀、将理想、讲服务,但是,它讲情怀、理想、服务时,始终是以“你们与他们不一样”为前提的(比如说“为民众如何如何”,这种话的隐意,其实就是把自己和“民众”分离开的)。那么,这其中,倘若稍不谨慎,一旦走偏,情怀、理想、服务,就成了具有俯视意味和优越感,甚至是“拯救心态”的情怀、理想、服务——于是生成与复制的,仍然是原有的不平等与分隔。
我对精英主义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当然,精英(虽然谁是“精英”本质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义,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谈“共同体”谈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时,用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生成着新的不平等、区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谈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时,带有的是一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农村该有的样子”的想象与俯视心态——那这其中的自我矛盾与不自洽,就成了观者批评和质疑的空间。
顺着上面的话说开去,看到一些批评,提到为什么我总要说我的“社会学视角”:同一件事情,因为学科背景、成长经历、思维模式等等,自然看的是不同结果。说我的“社会学视角”,恰恰是为了在一切讨论之前,为自己的理论设定范围(所谓scope)。当然,社会学者内部也不是同质的整体、不同社会学者的“社会学视角”同样千差万别——这和P大与H大的学生构成一样:倘若有同行,看不惯我的理论、行文,这和任何异见的存在一样,都很正常,我也十分乐意交流。
最后,这篇随笔不是论文——它是基于有限观察、具有一定学术意味的随笔。这篇文章,从数据的深度与广度、到行文的理论和分析、到评论里一位朋友提出的我“爱用大词”,自然,也有这文章自己的局限。但是,有时想想,学术训练目前而言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或许,就是在一篇篇论文被导师、同行、Reviewer从各个角度批评、修改、“虐成渣”后,面对这社会这世界的局限时,同样能够尽量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与不全能。
----
最后的最后,我必须澄清一点:这篇文章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和N大暑期班无关。感谢N大暑期班提供的机会,与N大社会学院诸位老师的费心安排。
我来把事情经过说说。
哈佛女博士“一音顷夏”在7月2日作为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来到碧山,领队陆远跟我说,这个班有40多人,“来自全世界三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人”,“七八个老外,其他是中国海外留学生和青年学者”,希望我和他们分享一下碧山计划。陆远原想在碧山书局二楼咖啡安排这个分享,我觉得那里地方容不下,于是联络猪栏酒吧的寒玉,她同意提供猪栏三吧的场地和投影仪并提供简单茶水。我问陆远用什么语言讲,他说用中文讲,暑期班成员大都能说中文。我选用了上个月为纽约大学一个研讨会准备的英文PPT,因我关于碧山计划的中文PPT久未更新,而我也没时间在一天内准备中文PPT。
我在前半部分分享了碧山计划所借用的各种思想资源和我研究参考的世界不同地区的乌托邦实践和农村社区建设经验,这一部分很多是我的个人兴趣,是我希望有可能放入碧山计划这个实验里的一些想法,后半部分的分享才是我们已经在碧山做过并做成的事情。我说到碧山计划想做的事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乡村建设,文化生产和社会工程,前者是希望接续民国以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实践,第二是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比较擅长的,第三是探讨艺术与社会互动的可能性。然后我说到实践乌托邦,先分享了我对不同政治模型的理解(从政党政治到公民社会到公共场域的危机失败到依靠民智和民力的“非正常生活政治”的可能性),然后介绍了我注意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者,特别是我在新西兰走访的一些嬉皮公社和生态村。这些嬉皮公社和生态村都是避世式的另类社区,但他们对于永续农业、合作居住和公识决策的探索却是对今日中国农村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也介绍了法国字母主义者们出版的杂志《冬宴》的概念,北美部落里的礼物经济与中国农村的交工互助传统的一个共同点是没有使用货币,这个跟后面我说想要在碧山发行时分券是有关系的。
随后“一音顷夏”就在微博和豆瓣上发起了她“对碧山计划的质疑”。如果是在尊重事实和深入调查基础上的批评,我真的非常愿意和她探讨。但她却刻意把我的原话歪曲成相反的意思,用有色眼镜抓取一些表面的现象,好嵌入她的社会学理论,以达到她一鸣惊人(或像她的化名那样,“一音顷厦”)的个人目的。谁不痛恨那些为了自己能看星星而不愿村民修路灯的人?!谁不讨厌显摆奢侈笔记本的人?!在农村用什么英文PPT啊,耍精英范装逼找死啊?!猪栏酒吧死贵,碧山书局卖咖啡,这不是大学课堂上社会学老师讲的“区隔”理论活生生的例子吗?!这些最能挑动仇恨G点的“证据”再裹上Othering, Symbolic Boundary之类理论词儿,像臭大粪一样泼洒到我们头上。可能担心“被批评对象”看不懂什么是Othering,她最近又转发了一张图以明示。
关于“路灯vs看星星”,暑期班成员李思磐已经证实我原话的意思:
“作为在场参访者的一员,我确定欧宁说到'看星星'时,恰恰是强调了村民需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的是:文人可能觉得没有路灯正好可以看星星,但村民们没有路灯十分不便,并且很没有面子。欧很抱歉自己只有能力在有文化节庆时解决了短期照明,而没有资金解决路灯问题。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误会。” (7月4日 00:44)
现在那天的录音也已经找到并发布网上了(http://pan.baidu.com/s/1bndAENd ),人人可以去听证。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我只说到Moleskine这个词一次,我是否在用显摆的语调提到这个牌子大家也可以去听。这个笔记本起因是2010年Moleskine邀请我参加他们在上海的一个展览,他们给我一本Moleskine,我可以在上面随便写画然后和其他人的笔记本一起展出,当时我正在思考如何开展碧山计划,于是便把那时的一些读书研究笔记和天马行空的想法写画在上面。和人分享碧山计划时,我都会说这个笔记本,目的是为了对比当初的想法,而不是显摆这笔记本有多贵。
至于在碧山用英文PPT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怕是我触动了哈佛女博士的特权了。难道在农村就不可以用英文PPT吗?你要碧山村是原始社会才符合你的想象?或要我请教你Othering是什么意思你才感满足?猪栏酒吧贵让你很不爽,那你知道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财力来修这些老房子?他们为本地解决了多少个工作岗位,他们缴了多少税你知道?碧山书局卖文创产品有罪吗?一百多万码洋的书放在这里只是为了显示品味?是为了制造区隔?你引用的那位姓方的村民说,这比开赌场和麻将馆好多了。你空降碧山只一天,你看不到村民来书局看书,小孩来上网,也看不到村民到我家串门,一是因为你时间太短,二是因为你心中“区隔”太大。都什么时候了,还用阶级斗争那套来动员仇恨。
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看得见农村的主体,只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才会警惕区隔,而我们是只知显摆“中产阶级品味”和沽名钓誉的傻冒。你的很多观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并说得厌烦了,所以才想起要做事。去做事并不意味着可以等着收获赞美,在农村住着做碧山计划并不能让我天然具有道德优越感,我努力做好,也许想头太大,也许个人能力或现实条件有限,但我试着尽力。失败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知识分子不是什么伟大力量,人民群众也没你想象那么苦大仇深,人各有缺陷,能住在同一个地方已属不易。这个说法我也说得太多了,在这里迫不得已再啰嗦一遍。总而言之,如果你想要解决自己深陷精英教育的人生困境,除了深情自省之外,拜托你不要刻意曲解别人用作靶子,以满足自己的私心。
听说未来几年,要推行村村亮的计划,让每个村子装上LED路灯。
到时候碧山的精英们就看不见星星了,他们应该会很生气的。
回应欧宁
---
回应欧宁
既然是回应与对话,那么对于欧先生,我就用第二人称写。
整场讨论,我始终明确了一点,这次批评,对事,不对人。但看到您的回应,认为我一条和朋友互动的无关微博是为了给碧山“泼粪”,认为我批评英文PPT“怕是触动了哈佛女博士的特权了”,乃至您认为我“心里区隔过大”——类似的诛心之论,不仅莫须有,并且仍然是对人,不对事的。
“星星” vs. “路灯”,是在说审美区隔。并且,从微博到豆瓣,从始至终,我一直说得很清楚,要看星星的是"外来知识分子",并没有特指你们。不过,我也给出了媒体对您的采访,认为村民想要路灯,是“面子工程”,这话,却的确是您说出来的——“面子工程”,在我国当下语境里,有什么样的隐含语义?将村民对路灯的整场渴求,说成是对面子工程的追求,是否是想当然的?
Moleskine说的是身份标识(status symbol),status symbol和通俗语义里的“炫富,完全是两个概念。对身份标识的拥有与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边界的方式。当然,这或许是一种学术话语与理解,造成误解,十分正常。
碧山书局和南京的先锋书店十分相似——碧山书局里,有一整面书柜的钱穆先生全集、有108元的牛皮笔记本、雨棚上写的是法文的“先锋书店”(librairie avant-garde)等等,说它的审美趣味是精英的,不知您异见在哪?实话说,我在碧山两天,没有看到一个村里人来祠堂改建的书局---但我在豆瓣和友邻交流时,也说得很清楚,两天的观察,样本量太小,所以我也从来没拿那说事儿。
说您用英文PPT(并且PPT里全是大词,那些词,翻译成中文也是“大词”)、说您提到各种西文典故,是在说整套话语知识、品味和趣味的区隔——针对的仍然是碧山计划的话语,而非您个人。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和心路历程,外人无权评判。不过,既然是讨论碧山计划,那我就多说一句建议:您在演讲和回应文章中,不断提新西兰、美国、日本等地的经验,这固然是您的观察和体验,但是,听者读者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是,这些经验能否被用于中国的乡村建设?您在演讲中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为了理解中国的乡村与乡村建设,我去了美国伊萨卡……”,这是否是理解中国乡村的好办法?就好像有人说我,爱用西方理论套用中国——这是我学术训练带来的局限,对方说的很对,我也虚心接受,那么,同样的,既然是建设中国乡村,这些海外经验,多大程度上适用,应该被怎么拿来用,如何避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你们作为实践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
说星星vs.路灯、说Moleskine、说碧山书局的审美趣味、说英文PPT与西文典故,这些,都是在说碧山计划的话语里(而不是您个人)存在的“区隔”。我的文章,本就是一篇讲文化再生产的文章,虽然不是一篇论文,但的确是立足于学术话语的。豆瓣上有评论说我爱用大词,我认为说得十分有理,虚心接受——我的文章,的确是在借用布迪厄谈区隔与文化。如果您要是非认为,谈点布迪厄的区隔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煽动仇恨戳人G点——不说这其中诛心得可怕,这也逼得我只能非常无礼地回应一句:多读点书好嘛……
下面再来说一些我认为您并未回应的问题:
你们看不惯西递宏村的发展模式、反对碧山村民自己想要的“高档化”(Gentrification),认为如果这样搞,就没有农村该有的样子——那请问,农村该有什么样子?凭什么是你们决定农村该有什么样子?你们看不惯西递宏村村民“在村口拉生意”,可是猪栏酒吧也是搞盈利性经营——都是生意,都是生活,为什么要被赋予情怀与价值秩序上的差异,这其中,你们的逻辑如何自洽?
甚至,说开去,您说我是空降碧山——其实追根溯源,你们和我一样,不也是空降碧山吗? 你们真的和民国几位先生一样,尝试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吗(不是有人来做个客就叫“融入”),真的搞的是以村民、而非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乡建吗? 既然是要搞乡村“共同体”,那么如何平衡计划话语中的精英主义倾向与文化区隔?共同体,究竟是谁的“共同体”?
说开去,和村委会座谈,村委会对于碧山发展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是一个“休闲文化旅游度假村”——村委会对于您、对于左靖先生的态度也很明确,是“城里来的老师,帮助打造我们的文化产业”。村委会也坦言,村民有的意见很大,也有不少来反映过问题。您的碧山计划,和村委会的发展目标不同,和村民的诉求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听到了您说要“远离资本远离基层政府远离NGO”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情怀,然而我却并不知道,靠着这种“远离”与情怀,在中国当下的模式下、在碧山的具体情境中,共同体如何能平衡好乡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关系,成为真正包容(inclusive)的“乡村共同体”,而不是外来知识分子小团体?
您说有和村民的沟通座谈,这我不否认——然而那天的座谈中,也有人提问了,参加座谈的“村民代表”,就是不多的一些老年男性。在后续的Q&A中也说到,“老年男性”常被看成是村民中的“智者”。那么不说别的、不说“智者”和“非智者”的划分,就说在这里,女性村民,也是在你们的沟通座谈中缺位和失语的——那么,还是回到我的那个问题,当我们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个乡村共同体,又是谁的共同体?
对于您对我个人的质疑和攻击,回应如下:
您看不惯我"深情"回忆与反思自己的精英教育经历,这没问题,就和我看不惯碧山计划话语里的精英主义一样。可您一面单向地,甚至是恶意地曲解我的用心,一面大呼“我恶毒揣测您”作委屈状,那么,我还是那句话,您如何自洽?还是,这仍然是和看不惯村民拉生意但又赞美知识精英下乡经营一样,搞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招数?
你说我一条转发朋友的微博,转发是为了给你们“泼粪”——对此,我真的不知该说什么,或许只能大笑三声——我这边已经准备从网络辩论中翻篇儿了,和自己生活中的好友微博正常互动,压根就没提到你们,你们也要上赶子来自己对号入座——且不说这行为本身就是您自己批判跳脚的"刻意曲解别人用作靶子以满足自己的私心。",就说你们,真的,能不能,别这么玻璃心且擅长脑补啊。要知道,这个世界、别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时时刻刻都围着你们转的好嘛……您(至少对我)还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事实上,我文章里批评的知识精英的自我满足、自我膨胀、自我拔高的优越感,很多就来自一种觉得别人啥事儿都是针对揣测你欺负你误解你的"莫名自矜"(self-important)。
现在,再来说两点澄清:
一、您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和一位方姓村民交流——我不知您从哪里得到了这个信息。我从未在任何文章里公开被访谈者的可识别信息。和我交流的村民不姓方(或者说,我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他真名儿到底姓不姓方)——所以,对您还是那句话,既然说到别人“曲解自己”时情绪激动,那自己也就少脑补一些。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这种对个人访谈对象的私人可识别信息,想想也知道,我怎么可能随便公开。
二、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和南大暑期班无关。对于南大暑期班,写文章前,并未料到文章会发酵至此(毕竟我的微博与豆瓣,都是和朋友交流的地方,关注量有限),但这的确也是我顾虑不周。如果对暑期班造成了任何影响,我都表示十分抱歉。对于陆远老师,十分感谢这两周您的费心安排,也感谢去碧山一路帮助照顾。
最后想说,我从来不想以对抗的心态来讨论问题:中国环境的复杂性,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加上不同人不同的视角,得到的观感,看到的东西,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一个计划,甲认为好,乙认为不好,这很正常;您认为碧山计划十分有利,我认为其中有值得商榷之处——我把我认为不好、值得商榷的方面和原因讲出来,这也很自然。
不能因为提出批评,就认为别人是居心不良——这是良性沟通的重点。
也有支持您的评论,认为您“做”,就是比“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里我不想趁机标榜自己其实也“做”过什么,我倒是想说,不是所有“做”,都是天然正当绝对正确的。倘若归个谬,难道做得全错,也是正当的“做”吗?“说”和“做”并不天然矛盾,提出批评意见的旁观者,也不是抱着看实践者笑话、说风凉话的心态去的。就好像批评质疑碧山计划,又并非是希望您计划破产、又并非是希望碧山村“倒掉”,对于猪栏酒吧——我也没有断人财路的爱好。您那天也提到了“自我审查”,既然都觉得“自我审查”是问题,那么当别人实践自己的“言论自由”时,不是应该抱着更加理解的态度吗?
还是我前面那句话,既然自己觉得被曲解的委屈,那就也不要去脑补他人的出发点、心态和用意。
在网上写文章,的确发现,我经常被人拿“哈佛女博士”说事儿——我自己写文章批评精英主义时,的确也会说自己在北大和哈佛的教育经历,这倒不是像一些人揣测的那样“为了变相秀优越感”或者“压人”——我想说的恰恰是: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人(甚至如今仍有痕迹),也一直身在精英教育的体系里。不仅北大哈佛,我的小学与中学,都是入学要各种选拔、在某种意义上十分讲精英教育的地方——我不避讳自己的成长经历、不避讳曾也是个精英主义者,所以当我批评精英主义、谈文化与区隔时,我其实也是在回溯与反省自己与自己身处的环境世界,也正恰恰是因为这样,反而不是把“我”和“你”对立居高临下的。
我对精英主义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当然,精英(虽然谁是“精英”本质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义,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谈“共同体”谈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时,用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生成着新的不平等、区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谈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时,带有的是一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农村该有的样子”的想象与俯视心态——那这其中的自我矛盾与不自洽,就成了观者批评和质疑的空间。
就说这些,最后祝您在碧山生活开心。
周韵
精英能否建设新农村?——碧山的争议
廖伟棠
出身於广东农村的著名文化人欧宁,今年经历了一些风波:先是他创办的新锐文学杂志《天南》停刊然後又易帅复刊,近日又有哈佛社会学博士强烈质疑他投放了全部精力的新农村运动「碧山计划」,且应和者不少。
《天南》是近年大陆最好最有国际视野的文学杂志,停刊可惜,但我很理解欧宁的放弃,不只是因为文学曲高和寡的销量问题,更是因为欧宁越来越倾向於实际行动,作为一个积极无政府主义者对改造世界的热情,急需付诸行动而不是文艺的纸上谈兵,所以「碧山计划」应运而生。
「碧山计划」,根据执行者自述:「是一个关於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金(Peter Klopotkin)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激活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它主要是针对目前亚洲地区迫人的城市化现实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试图摸索出一条农村复兴之路」。
而在旁观者看来,简单地说,这是以欧宁为首的一批文化人在安徽黟县碧山村进行的一场新文化实验,是一个主动丶前卫的知识份子上山下乡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基於无政府主义者互助精神的「碧山共同体」,在开发碧山村的农村活力的同时保留农耕文化传统,具体操作包括兴建碧山书局丶「猪栏」酒吧,举办文化节「丰年祭」丶本土手工艺「百工展」等。
老实说,这的确非常困难——正因此那位化名「一音倾夏」的博士的质疑来得非常轻易。中国的农村保守文化根深柢固丶村干部对开发资源的想像急功近利丶地方部门对知识份子的警惕等,这些都是必然影响理想主义蓝图的阻力,我可以想像欧宁的团队遇到不少丶也不得不妥协不少。但正因此,他们的努力才显得可贵。
哈佛博士明显是更典型的西方左翼「政治正确」者的样本,她抓住欧宁团队存在的精英主义和艺术家气质,大力质疑後者的理想主义与农村实际存在的「区隔」,在到碧山参观一天後,便在微博上连续发文发图「揭露」她所认为的阶级分野和话语权不公。然而透过她剑拔弩张的文字,我想起了毛时代对知识份子的批判,不外乎「脱离群众」丶「小资中产趣味」等等老帽子,再加上「後殖民」丶「审美他者化」等新帽子,但对於怎样更好地建设碧山丶处理好知识份子与本地农人关系等她毫无建言。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本身带有的精英想像:比如她觉得碧山书局出售的现代艺术书籍丶高端学术书籍是和农民格格不入的,这不正正显示了她早已先入地划分了阶级分野?她把身上西方左翼的知识份子原罪感和平等焦虑轻易地在碧山计划上面找到了投影。
作为实验者,碧山计划团队当然存在种种力未能及之处,欧宁作为诗人和艺术家也的确存在乌托邦情结和某些精英的或者「小资」的姿态,更大的危险还存在於比如对美术馆体系的依赖丶对既有前卫社区概念的依赖等。但若是从碧山本身的发展出发,只要没有伤害农民的利益和文化,这一切实验都应该鼓励的,批评者也应该基於帮助的态度去指正和讨论改进的办法。啓蒙必然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如果一律简单定义为阶级分野的居高临下,则所有啓蒙均不可为,包括梁漱溟和晏阳初都能成为批判对象,更何况欧宁乎?
(原刊于香港东网.游目族专栏)
来自豆瓣上的评论摘选:
2014-07-03 11:51:49 圆月超人 (看前面黑洞洞)
看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另一个话题,城市是谁的城市?
我觉得在一个社会剧烈转型期,出现这些情况都是很有趣而且必然的,因为从事公益事业,倡导公平和平等,但是最后仍然要反思,平等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此看来,精英主义和普通民众是必然对立的,因为如果你要想真正平等,那些精英就首先要放下自己能获取的利益,转而服务于普通民众。
碧山村最后的发展,最后会变成精英单纯的掠夺本地村民,还是本地人坑害这些外来人口,在我看来,本质上都是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但是历史的潮流是这些农民要变成市民,传统的农耕社会回不去了,精英主义的PPT不仅仅是给中产看得,也是给这些农民看的,只有他们见过,才会在自己的圈子和阶层里重新洗牌产生本地精英,带动这个社群向前发展。
2014-07-03 12:57:04 本当无人 (urbanect)
我最近在看另一个样本。建筑师王灏(就是那个做了一个像HERZOG一样的农民房的建筑师,但这个不是他最喜欢的作品)的乡村实践,这两者可以放在同一个社会学背景下去谈。
另外,共同体这种大词,本来是左派和底层人民抗争专用词,现在变成大右派们嘴上的时髦词汇,那我以后避免使用就好了。
2014-07-03 13:05:03 蝴蝶舞沧海
今年4月份去了碧山,访茶时无意中去的,因为有朋友是碧山人,可以住在他家,因此在碧山中居住逗留了半个月。那时,碧山书局尚未开张。我们返京后一周,碧山书局开业。
当地人对于碧山书局,所谓碧山计划,不说一无所知,其实也是一知半解。
同时,另有当地人也在做一个计划,什么陶行知乡村教育啊,什么国学讲座啊,什么书画院啊……他们谈起碧山书局,是谓不屑一顾,认为外地人搞不起来,且不理解碧山。
然而,自己也要修建祠堂,进去后发现祠堂有个匾额非常漂亮,且历史悠久,就随意的挡在大门边。因说起,要将它重新修缮,然后启用,才是真正的传承。对方说,哦,不用那个,这个当时被XX(申请项目时)要走了,送给他了。
某天我在闲逛,一位大爷热情的迎我进门,带我看房子,四处介绍。然后说这房子是卖的。我问多少钱?大爷说,我这大,三四十万,有小的,也就十几二十万。此时是四月上旬。
返回后,在京跟朋友说起有古老房子出售,朋友询价之后立刻起了兴致,随后即抵达碧山买房,被告知最少也要一百万。此时六月中旬。
2014-07-03 17:32:55 Ou Ning
这位哈佛女博士空降碧山一天,抓住本人片言只语进行歪曲,把与一两个村民的对话当实证,抢占“平民”、“平等”之类道德制高点,以“质疑”吸引点击率,使用的话语比她要批判的“精英话语”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有无人拍摄昨天我说话的视频,如果可以拿出来对证,就知道你的曲解恶毒到什么程度。你要显示你的平民关怀,先像我一样来农村待上一阵再说吧小姐。
2014-07-03 17:50:32 本当无人 (urbanect)
人家跟你也无怨无仇,何必端起阴谋论大旗呢?本来就是一个学术问题,何必要搞成‘出来跟我对峙“云云。这太像天蝎座的反击方式了。
2014-07-03 18:22:50 本当无人 (urbanect)
你经常跟别人论坛对话什么的,我想应该清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惯习,来自不同的场域,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本来就是反的,或者根本对不上的。各种论坛现场对话都不能说清楚,何况别人的一篇文章。正确对待学术的方式,就是试图去理解对方说的到底什么意思。仅此而已。本来,现在任何所谓实践都是对自己产生意义(不一定只是利益),打着为别人的旗号多少是让人不服的。
2014-07-04 17:19:43 蕾丝鞭。 (抚鞭长叹莫及辟入里。)
做为一个小书店,我们也在探索中做了一些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譬如发起向碧山农家书屋捐书的活动,戳这里,http://t.cn/Rv1Q0du 第一次捐书的书目戳这里:http://t.cn/Rv1Q8Lb 当然农家书屋是村民自己的图书馆,主要供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阅读。碧山书局会定期赠送农家书屋新的图书,并联合开展读书文化活动,后期还会有暑期志愿者活动,致力于村民文化生活的改善。
当老一辈村民逐渐老去,年轻人出外求学工作逐渐离开村子。
可能并不是年轻人不想回来,而是可能已经不会种地,或者传统的手工业。
即使回来也没有可以施展自己才能或力量的地方。
也就是说,当一个村子的人口在逐渐减少的时候,我们如何让一个村子不衰落呢。
西南或西北的农村衰败现象,您一定看过或者至少应该看过文献。虽然我不是社会学专业,但也看过几本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呼吸》、《十四家》、《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受苦人的讲述》、《高家村》。您虽然是研究社会学的,可能并不知道没有人住的房子会倒塌的特别快吧。所以,我觉得不管如何建设农村,首先需要有人,有年轻人。
可能您会觉得碧山书局出售的物品比较贵,不是村民能够承担的。可是我们为两个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而且薪资是跟南京的员工一样的。而且因为碧山书局的原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碧山,他们会在那里消费。譬如住在了碧山村民自己的泰来农庄里。泰来农庄里的员工都是本地的居民呢。他们的收入会增加。
外来的人们会从这里买特产,笋,茶叶,草鸡蛋等等。至少我们上次去的近百人,几乎都买了,草鸡蛋和笋呢。又便宜又好吃,是小时候记忆中鸡蛋和笋的味道。这些都在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呢。我们还打算发起网购。村民有了收入,村里有了资金,路灯就不远了。欢迎社会学博士能够给乡村建设提供更多的建议。
若有冒犯,请多见谅。不管如何,感谢您关注碧山,关注农村。
2014-07-04 22:56:39 本当无人 (urbanect)
我来梳理一下城市知识精英的逻辑。
”城市生活太无聊了,农村太困苦了,农村需要现代化,城里人也需要回归传统。现有的现代化方式太不给力了,弄的一团糟,只知道经济发展,不注重环境的乡土,弄的乌烟瘴气,农民也没有足够的自己故乡和土地的认识,只知道乱盖房子乱卖旧东西。这不是我们想象的乡土,这不美好。农民不该离开自己的土地,不能等我们到了乡下一个农民也没了,那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来告诉农民怎么做才配的上乡土,农民也应配合我们建设真正的乡土,我们来告诉你们乡土有多美好,农民都留守了,有田有地有老宅,这样的乡土才美好,到时候我们在乡下买个宅子,想去休闲就休闲一下,想城市了开车回去分分钟,农民也会因此富起来,来城市里买个楼,想当城里人就当城里人,想回故乡就回故乡。这才是城乡和谐的未来的共同体。“
呵呵呵呵呵呵。
2014-07-04 23:46:12 蕾丝鞭。 (抚鞭长叹莫及辟入里。)
乡村除了成为城市的开发区、工业园、卫星城、八环九环或者旅游景区(同里、周庄、西递、宏村)之外有没有更好的路?
如何让乡村在老一辈不断老去,年轻人外出求学打工后,依然保此活力而不衰败?
另外以上回答的里面有农民么?
我是农民,反正我们那儿的大部分人都想富裕起来,他们都是这样说的,“想过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除了等待征地拆迁后被搬到开发区的高层拆迁安置房里,如何才能成为城里人呢?
种地?一亩地投入500多元,收入1000多元,种两季,落下一千多?
读书?你们城里的小学都在集团化,我们乡下的小学都在拆并,村子里都没有小学,没有完小,镇子上都没有中学,上一个学要走多远的山路?学费就靠种地?还是种地之后出来打工?
碧山计划引哈佛博士周韵与策展人欧宁笔战
7月流火,在微博与豆瓣上,一位哈佛女博士与文化策展人欧宁吵了起来,引来彭晓芸、廖伟棠等一系列大V关注。争吵中不乏“精英”“高档”“知识分子”等词汇。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碧山计划”。
2011年6月5日,艺术下乡项目“碧山计划”在广州时代美术馆正式启动,该计划将举办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寻求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第一财经日报》将其概括为当代知识分子移居乡野的社会实践。
安徽黟县碧山村是个典型的徽州村落,白墙黑瓦,背后群山常笼罩在雾气中。发起人欧宁和左靖选定这里想动员一些知识分子共同在这里进行生活实验,创造一个乌托邦,建立独立的视觉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甚至还准备设计护照、社旗、衣服。
有这样的初衷,是因为这位来自广东遂溪县农村的艺术家现在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欧宁小时候非常讨厌农村,拼了命读书,就是为了逃出来,但等到作品获得国际认可、自己在城市里找到位置,年纪渐长,反而觉得曾经的贫困农村生活是宝贵的财富。于是,他想关心乡村建设,为农村做些什么。
三年来,在欧宁等人的推动下,碧山村有了碧山书局和猪栏酒吧,举办了碧山丰年祭和黔县百工等活动,也受到了媒体和民间机构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的人连续两年来拍纪录片,以民国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先生》当中晏阳初一集把欧宁作为延续民国乡建的现实案例,《南方人物周刊》也在今年年初以碧山为重头推出“抢救故乡”专题。但他还是悲观地告诉媒体“碧山计划最终是会失败的”,欧宁认识到村民的观念很难转变,乡村建设人才、资金短缺,碧山村甚至连路灯都没有。



“碧山计划”实行第三年,45岁的欧宁遇到了另一个“挑战”,“挑战者”是比自己年轻20岁的周韵。这位南京姑娘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乌尔都语专业,2011年周韵被美国哈佛大学全奖录取,现攻读社会学博士。7月2日,她作为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来到碧山,和40余名小伙伴一道探讨“碧山计划”。
期间,周韵连发十余条微博质疑“碧山计划”,并发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欧宁发文回应,双方有来有往,好不精彩。甚至引来欧宁同道中人,香港诗人廖伟棠助阵。也有青年学者“mujun_soc”“长亭”思维发散,撰文讨论起周韵在文中多次强调自己北大、哈佛的学习经历是否恰当。
一位匿名读者的评论将人们的视线从学历、话语又拉回到“碧山计划”上,从他的言语中可知,他似乎去过碧山村。这位读者向人们推荐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综合农协实践,“他们从教农村妇女跳舞,组织村民进行麻将比赛开始把村民联合动员起来,然后组织集体化生产,建立青年农场,集体购买化肥种子,解决小孩入学,解决农产品销路,组织农副产品加工,这是以农民和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乡建。”说到“碧山计划”,他认为这只是“对文物建筑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恋物”。“如果碧山计划真有意乡建,教农民开淘宝店,以碧山计划的知名度卖点火腿,竹笋,茶叶,土鸡蛋也算是好的,说不定路灯的钱早赚到了。”这位读者在最后谈到。
反思的出发点
mujun_soc(豆瓣ID:Lebenswelt)
前两天看翕如就碧山计划发表了一篇见解。碧山计划我知道得也不多。究竟是成是败,大家可以讨论、批判。今天下午翻到翕如又修改了自己的文章,还加了一些内容。倒数第二段是新加的:
======
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从小接受的始终是极其精英主义的教育。精英主义教育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断告诉你,"你和别人是不同的”——本科新生入学典礼有一个程序,是大家一起在校歌声中佩戴上P大校徽。这个程序非常具有仪式感,因为佩戴上校徽后,老师会深情地说,“从此之后,你就成为了‘P大人’”;哈佛博士新生入学典礼,校长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祝贺你终于made it,是the best of the best。精英教育,也讲情怀、将理想、讲服务,但是,它讲情怀、理想、服务时,始终是以“你们与他们不一样”为前提的(比如说“为民众如何如何”,这种话的隐意,其实就是把自己和“民众”分离开的)。那么,这其中,倘若稍不谨慎,一旦走偏,情怀、理想、服务,就成了具有俯视意味和优越感,甚至是“拯救心态”的情怀、理想、服务——于是生成与复制的,仍然是原有的不平等与分隔。
======
觉得特别不舒服。忍不住想多说几句。
看起来都是不错的,要有反思精神,不能俯视,有优越感,拯救心态。但我很怀疑这个反思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学家在做调查、收集数据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求学经历而产生什么需要反思的优越感。从我个人来说,倒是经常感到自己很卑微。没错,我有时候确实会出于“炫耀”的目的告诉别人我在田调过程中能接触到很多人,套出很多话。但实际的情况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尴尬如影随形。你是女的,年纪小,从来没有出过校园。留美博士,饭桌上的奉承,最一般的社交礼仪,没有比这再浅的东西了。很多人心里会把你当小女孩,过于深的东西不能跟你讲。因为他们觉得很多社会上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
也确实懂得不多。我不知道怎样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不知道怎样游说两会代表,不知道怎样帮基金会评估草根组织的项目绩效。我现在做完田调了,在我学术圈的朋友里敢聊聊这些话题。但还是不敢到我的研究对象面前去“班门弄斧”。学历在这里不是很有意义。除非你觉得蜻蜓点水一下就好了,除非你觉得社会学的分析就是看一眼事情再贴上几个学术的标签,话语的霸权,他者的凝视,除非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进入别人的生活,同时也让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你不会成天惦记着自己胸前别过哪一校的校徽。
我写过自己跟何晓波做工伤探访的经历。我说,何晓波在病房里跟刚刚死了儿子的大妈聊天。大妈的老公又查出来尘肺三期。她活灵活现地跟我们讲自己怎么把垂死的儿子从医院抢回来,好让他逃过被火烧的厄运。何晓波就在边上跟她一起乐。有些人看了这一段就写信问我,你当时是不是特别痛苦,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社会阴暗面导致垂头丧气了。不是。当时我一个人杵在边上,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安慰人我又不会,想跟老实的老头说可以依法维权,又怕她老婆一冲动做出点什么来遭了更大的罪。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还是何晓波们对社会更有价值一些,而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学家简直就是累赘。虽然何晓波们经常很客气地跟我说,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势啊,你要把你的书写出来啊,肯定会对我们很有启发的啊。
别误会我。我不是在宣扬一种民粹主义的精神:北大和哈佛教的东西都没有用,真理和智慧都在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事实上,坐回写字台前,我也会批判。那个人口是心非,那个人说的话与另一些事实不相符,或者讨论,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已经发生了,那些人却没有意识到。
但你得明白,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无法相互通约的。我们理解别人的第一步是先要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还根本就不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的想法,做的事,即使我们竭尽全力也只能了解一二。而不是先假定自己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受过精英主义教育的人有能力站在高位俯瞰,然后出于谨慎的心理往后退了一步,说,嗯,我不能太有优越感呢。
抱歉。可能我不该说这些不客气的话。也不该讲这么多自己的经历。好像我自己已经是好学者了,有资格告诉别人要怎样做研究。
只是,看到翕如反复强调自己是社会学家的视角,忍不住要觉得荒唐。算上本科,我入社会学这个门也有十年了。我们这个学科是要教人干啥?教人喊一些反思和批判的口号吗?
翕如、Mujun、欧宁让我想起的一则小故事
长亭
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知识分子比武。一个叫西门吹雪,一个叫叶孤城。
动手的地点约在碧山之巅。
他们是两个社会学家。
寒风,杀气凛冽,剑已出鞘。
出招前的一刹那,西门吹雪突然转身,背向对手。面向劳苦大众,他跪了下来,磕了三个头,一行泪水滴落。不知怎地,尽管他空门大露,但叶孤城掌中的剑,竟再也刺不下去。
叶孤城不得不抛了剑,也转身对着劳苦大众磕三个头。
他磕头的声音还要大些,咚咚作响。然而,他跪得,毕竟比西门吹雪稍晚了一些。
两个剑手彼此念了谜一样的四句话:
“我即是他们”,
“你不是他们”,
“我代表他们”,
“你永远不能成为他们”。
叶孤城突然吐血而死。
围观的百姓都惊呆了——“你们倒是快动手,快说说俺们村的问题呀!”
西门吹雪慢慢道:“不必动手,心已经诛了”。
——“高手过招,只在出手前那一刻的姿态。”
话音未落,他已消失在残阳外、西风里。
空留一城的百姓,“我们村到底咋回事儿?他俩个打了没得哦?”
叶孤城呢? 你又卿本佳人,奈何为寇。
============================================================================
1、这件事的态度上,我是挺翕如的。欧宁的回应写得很漂亮,但我在她的文章下边回应了这么一段话:
“不管质疑合理与否,拿“哈佛女博士”这五个字开篇可真够没劲的。明明可以在理地拿出事实说“你看错了”,非要加上“你看错了是因为你只想看这个”。正当防卫之外顺带诛心,把质疑者推入精英主义的境地,结尾又做祥和气象。文笔好确实能掩盖住气量小。什么时候开始政治正确行在项目问题实质之前了?”
质疑可能有对有错,但行文里刻意加上质疑者的“名校背景”,反过来质疑“质疑者的动机”,我很难接受。 攻击别人的“动机”是辩论里非常低劣的一种做法。翕如第一次的批评出来之后,是对事不对人的,欧宁的回应直接对人。我觉得回应之后翕如处于弱势。
2、人的性格有许多种,有的人自负一些,有的人谦和一些。毫无疑问谦和更让人喜欢。但让自负的人自负地讲道理,谦和的人谦和地讲道理,高傲的人高傲地讲道理,自卑的人自卑地讲道理。然后我们去看道理本身,看批评本身。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的态度。
3、我是在形成这样的观点后才看到Mujun的文章的,Mujun写过很多很好的文章,我也很佩服。但这次我想说的是——
任何一个人都有缺陷,任何一件事、一个批评的眼光都有改进的空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完美的事,但正确且重要的事并不太多。所谓“大是大非”,除了批评之外,更要看什么问题更值得批评。不是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拣出来的。
一个北大哈佛毕业的人,哪怕真的是如Mujun在文中所说:“假定自己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受过精英主义教育的人有能力站在高位俯瞰,然后出于谨慎的心理往后退了一步,说,嗯,我不能太有优越感呢”,我也没觉得有多大问题。人无完人,性格各异,翕如又确实是受过精英教育的人,有谨慎自省的意识,已属难得。在别人的论战中,指着弱势的一方,说“你的谦和并不完美”——这个批评正确吗?很正确。正当吗?未必正当。
4、这个段子只是耍小聪明。翕如、Mujun都写过让我非常欣赏的文章。只是希望讨论多集中在碧山计划本身,而不是转向质疑者的动机、学历、头衔和教育背景上。仅此而已。村民的声音,我已经听不到了。
一位匿名读者的评论
对乡建感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永济蒲韩社区综合农协的实践。他们从教农村妇女跳舞,组织村民进行麻将比赛开始把村民联合动员起来,然后组织集体化生产,建立青年农场,集体购买化肥种子,解决小孩入学,解决农产品销路,组织农副产品加工,这是以农民和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乡建。
反之,被女博士质疑的碧山计划则是创始人受到诗人小光寒玉夫妇经营的猪栏酒吧旅馆启发,想复制放大推广猪栏酒吧旅馆的经验(低价买入作为农民祖屋的文物建筑,按照自己作为文化人艺术家的品位进行修复和改造,然后用来自己居住以及作为经营),以对抗西递和宏村的“低端旅游”(门票和喧哗)。
碧山计划一开始是以自身先享受有品位有文化的田园生活为前提的,以拯救文物建筑为目的,以艺术展和各种文艺活动拓展资源的文艺旅游活动,谈不上是乡建。碧山计划的源头来自对文物建筑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恋物”。农民和农业生产都仅仅是一种生活样板和文物建筑的附属品,而且一开始就是作为他者存在于创始人的视野之中的。
哈佛博士很敏锐,空降两天就发现“区隔”的存在,但她没有论述清楚的是,碧山计划的出发点就是来自“区隔”,而不是在实践中,创始人的精英气质和中产阶级身份导致了“区隔”。碧山共同体指的是外来的精英艺术家,知识分子和高端经营者,这个共同体是不包括村民的。
如果碧山计划真有意乡建,教农民开淘宝店,以碧山计划的知名度卖点火腿,竹笋,茶叶,土鸡蛋也算是好的,说不定路灯的钱早赚到了,而不是在回应女博士质疑时一再强调,来参观书店和艺术展的人买了多少竹笋和土鸡蛋,高级咖啡馆,旅社雇佣了几个村民。
.
像“路灯和星星”这样的疑点,周韵还在碧山的时候就应该当面和男策展人欧宁沟通的,回头再小文章也不迟,以避急于抓住别人小漏洞之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