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光·梦之解析
项丽萍 对话 余旭鸿
2013年8月26日
项:访谈正式开始前,我先插播一些有趣的情况。你的系列新作我一直听人提及,但不曾谋面。不知道是你的作品太神奇,还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自夸一下),8月15日第一次看过你新作的照片之后,我当晚居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你的工作室(场景像个教室)里,我看到两面墙上都挂有你的大幅风景画,用透明塑料布盖着,一幅是棉麻质地的壁挂,一幅是丝质的,丝质的这幅还在轻柔飘荡。
我揭起塑料布细看其中一件,画作一下子就变活了,画面闪闪发光,画的空间深邃奇妙,中间位置竟有一入定老僧,面壁而坐。然后你陪我出去看风景,指给我看你笔下风景的出处,其实现实的风景是极普通的,看来画中的风景是被你化腐朽为神奇了。
而且整个梦是彩色的。其实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梦本身就是一支生花妙笔,往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是人自己常常不能理解其中奥妙。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做这个梦的原因,也许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话和梦的解析可以找到答案。
余:还是你的梦神奇,居然把我不同系列的画给串联起来了。我画中选取的一部分景物的确是画室门口常见的场景,比如竹林、篱笆、雪堆等,我曾经画过一批在丝绸上半透明的小画,画面具有丝质的轻柔;也曾经画过一些和精神性有关的题材,画面比较凝重。这其实是我好多年来一直在发展中的“光影”母题的不同系列的作品。
项:我想先从形而下的问题开始,先说色彩,这个系列作品的色彩鲜亮闪耀,尤其是那蓝色和黄色,感觉是雪地里或是暗夜里的宝石光芒。你是怎么做到的?
余:就色彩而言,关键是利用色彩的对比,建立画面的色彩关系。我在画面上一开始使用比较单纯的颜色,并非把颜色都调熟,而是让它带有一点“生”的感觉,通过颜色的反复覆盖与透底,调和成色彩的对比。至于画面中光的闪烁主要是通过颜料的挤压,透出略突出画面的底色,从而达到林影中的波光效果。而这种波光,又让人感觉像是物体自身发出的光,那是因为这似要融化但又结冰的雪,在月与光的折射下闪耀着犹如发光体一般晶莹剔透的光芒。
项:你的作品标题是“夜光”,夜一般而言总归是暗的,但画面实际上看着很透亮,你为何选择这个题材,为何如此处理?这些问题对应着你的作品在我的梦中“画面闪闪发光”的原因。
余:“夜光”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 在一般意义上说,夜是黑暗的,其实,夜并不黑暗。在月下的寒林雪景中,夜是透亮的。对于事物本身而言,无论见与不见,它都在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描绘的月影夜光,我们感受不到黑暗。现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乔仲常的《后赤壁赋》,描绘的月下行吟场景就是透亮的。
“夜光”的另一组作品是一个关于现实与文化生态记忆的幻境,人物的形象来源于外在的光源,在晦暗的竹林中浮现历史的“现场”,从李鸿章到新文化运动,从可见之景到“可触之光”,是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昨日重现”,是历史与现实的频道切换;在林间阴影深处,在历史之光与自然之影的触及中,把握“刀锋上的临界点”,通过超越性的光,穿越现实的困境。
其二,从视觉原理而言,“夜光”是通过瞳孔进入眼睛的“暗箱”之中的光,它让我们看见事物。在古希腊,明眼的艺术女神雅典娜拥有猫头鹰一样的眼睛,它穿透黑夜,使通常不可见成为可见,艺术家则是“明眼高手”(tech nites),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的眼光应当是“夜光”。
项:嗯,你对于“夜光”的解释让我想起了阿甘本在其《何为当代人》中的描述:“当代人是一个坚守他对自身时代之凝视的人,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对那些经历当代性的人而言,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当代人就是一个知道如何目睹这种晦暗,并能够把笔端放在现时的晦暗中进行书写的人。……那些可以自称为当代者的人,只是那些不允许自己被世纪的光明所蒙蔽并因而能够一睹那些光明的阴影,一睹与光明密切相关的晦暗的人。”看来,对历史和现实之黑暗与光明的“凝视”使你成为了阿甘本所说的“当代人”。
从笔法来看,这批画乱而不乱不乱而乱的点和线既有米氏云山的笔意,又有点彩派的趣味,和你此前一个系列的风景有延续但变得更加潇洒、精到,逸笔草草,酣畅淋漓,也让我想到了沈括对黄子久画作的评价:“其用笔甚草草,近观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你的画作也是,需要退到一定的距离去欣赏,那些原本放纵不羁的笔触一下子变得极其服帖并合理。
余:笔法是物的显“象”之法。在色层的层层覆盖中,在形与色的交汇中,在光影的虚实衍变中,在每一笔的起承转合中遭遇了“物”的生长,经历了绘画的时间性,在“物”的形象“显影”的过程中开启了画家的内心体验,恰是此种绘画中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聚集切近物性的“象”。“夜光”是对弥散的光之捕捉、影之描绘,亦是探索“象”的触及。“让不可见成为可见”,在心与物的交融,意和形的交替中,得其意象。
笔法是画面空间生长之法。绘画的过程是寻找一种可能性 - 建立画面的矛盾性与开放性的过程,这种“变化”的过程其实是很丰富的。在湿底上用笔时会产生一种惯性,会长出一种东西,画面完成的过程是一个空间生长的过程,也是形成笔乱与不乱的矛盾过程。我的画面看似近乎平面,但又有丰富的空间感,这种空间又不同于散点透视或写实绘画的空间,而是物本身的空间感觉。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小笔,中国的毛笔或硬的笔,游刃于软与硬、侧锋与主锋之间。那种感觉和平常的油画笔是不一样的,在颜料的粘连之间会产生特殊的肌理,比较放松,画画会产生“近观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之感,近看与远看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视觉生成的过程。
项:你能否再透露一下你的具体画法?
余:我是在较厚的湿画底上作画,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巧妙地演绎了每笔下去后的状态,有时会控制不住,但这又是接近对象的特点,接近原物自我的张力。就像丢勒的绘画有很多细微的特征,比较切近原物。但由于他画的薄,画在板上或纸上,用很湿淡的颜料、很小的笔,易于表现对象的形态。但如果是在光板或非常湿的底上作画,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你想控制它但又无法完全控制,这是矛盾与破解的过程。
每个物都有自己的物性,非常微妙而有趣。一是我所描绘的物,比如山水、风景。二是在颜料、笔与画布接触的瞬间,颜料、笔与画布三者也有各自的特性。画面的形成会自然而然,有自己的味道。材料本身也是一种事物,有自己的法则,它会尽量去寻找自我的内在架构,这种架构不一定那么好控制,所以画面中会出现“乱与不乱”的感觉。但是当我整理完一遍的时候,整体上会有微调,让画面生长的过程更加合理。这种画的过程比较有趣,而且具有挑战性。
项:听起来很有趣。托尔斯泰说过:“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作者只能根据人物的性格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卡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季斯娅娜只能根据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意愿行事的原因。”你的创作情况很接近这种状态,仿佛画面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有了自我生长的能力,它没有根据你预定的框架发展,而是你在顺画面之势而为,画作最后的结果似乎也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
余:对的,我比较注重画面的生长性。在湿底上作画,还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这刚好和湿壁画有某些相似的特性。这种底子就像西方中世纪的壁画,琴尼尼在一本手抄本《绘画之书》中曾提到,这其实是一种工序,颜料的特殊效果,在于掌握好干湿的火候。正如我们在看西方湿壁画和布面油画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看壁画时感觉会更加自然朴实,气更畅,因为画家没法去层层加工,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画完。布面油画因为可以反复调整,所以画面会更加精致,但生动性会丧失很多。就像到安格尔时,虽然画面上细微之处很多,但生动性少了很多。
给我感触比较多的是伦勃朗的油画,他的《夜巡》是加工的比较完整的杰作。但他很多自画像却比较放松,是和自我的看法结合在一块的。这样的画面有生长性,反而会更加有活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有些画照片的画,虽然画面效果很接近对象,但画面的活力却反而减弱了很多。
项:这大概是你的画作让人感觉生动的原因,因为是一气呵成,也没时间让你去磨,很多新鲜而直观的东西被保留下来了。我在想,你这种笔法和我梦中的塑料布是否有关联,有着从朦胧到清晰的变化?
余:我的笔法与你提到梦中的塑料布之间的关联,是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如照片底片显影的过程一般。其实我们的视觉经验,很多是在看到事物后,从大脑的库存中寻找相接近的东西,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所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世界时已经加上了很多界定和判断。
我在画画时则会尽量少一点这种判断,让画的对象本身慢慢浮现出一些东西。这在我的色粉画和人物历史系列中会更加明显,里面映了两种景,一种是最破烂不堪的现实场景,一种是历史的现场。这两种现场互相重叠又相互抽离,形成朦胧和清晰的对应,似有似无。有可能是把所描绘的对象虚掉了,有可能是把历史的现场画实了。有时历史的现场模糊了,景物实了……,两者搅合的过程是画面用笔碰撞的过程。色粉画面比较麻烦的是,要一笔笔画,颜色本身很强烈,我的色粉画中会带有用刀的痕迹,因为全是侧锋用笔,如刀锋一般切入。
项:那么从取材来看,你画的大多是生活中常见的甚至容易被忽略的景物,你选这些题材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正如我的梦所示,你是怎么把这些平凡的景物变得如此“神奇”的?
余:神奇倒是谈不上。谢赫“六法”中曾提到“经营位置”,其实是画面营造的结果,需要用巧心、匠心反复琢磨。我恰是在无心有心之间,在画面的生长中顺其所为,“情性所至,妙不自寻”。
我希望在平凡的东西中“忽逢幽人”,司空图的《诗品》十八品“实境 ”说:“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前两句可理解为直面事物本身,不必巧用心机刻意搜寻,直接感受自然事物。“忽逢幽人,如见道心”,保持在幽暗中的隐蔽者不期而至忽然显现,如画面上黑之中透出光来,画面上点亮的那一瞬间是不可事先设定的。
项:有道理,通过画面的精心经营来使现实中的普通物象变得耐人寻味。同时,在精心的经营中又不丧失直觉的生动性,保持了“忽逢幽人”的新鲜感。
从风格上看,我觉得你的新作有着“池塘生青草,园柳变鸣禽”的平淡清新,如清风拂面,可以对应我梦中丝质的那幅在轻柔飘荡的意向。我很喜欢法国著名哲学家于连的专著《淡之颂》,他分析了中国文化艺术之所以如此重视“平淡”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人“平淡”的理想人格和“平淡”的艺术理想之间的关联,我在想,你是否在有意追求这种风格?还是自然而然,天性使然?
余:在我个人的绘画过程中,有些画面比较沉重,比如在生活中寻找可超越之物,这并非是我个人的生活而是群体的生活。随着当下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精神层面反而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隐藏了很多问题,会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反思:比如对自然的返观、生存环境、PM2.5等。
司空图《诗品》中的“自然”和绘画的思想意境非常相似:“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这是中国人对时空、对自然的观念,可以超越出来看问题。
我所去游的现场,月夜雪后的林中,人迹罕至,所畅达的心境和自然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是可通古的状态,可以远离尘嚣,我在寻找和体察清新的气息。正如清人笪重光《画荃》中说:“林间阴影,无处营心;山外清光,何从著笔。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
今年七月,我陪同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罗森教授参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在看到王澍教授获普利兹克奖后最新的作品——水岸山居时,罗森教授讲,她见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作品,但没有一件如眼前这般可以给她带来如此深刻的感觉,她明显感觉到王澍教授的意图 - 复活中国古人对山水的体验,曲径通幽之处,凉风吹来,转弯遇险,高山流水。这两位汉学家参观完之后非常兴奋,他们觉得非常神奇,原来对中国古代的山水观念,除了用符号表现外,还可以直接和自身体验发生关系。
项:好一个可通古的状态!平平淡淡才是真,中国艺术一向追求平淡恬静之美,也许我们应该往回看,在传统艺术中寻找指引我们继续前行的灵光。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西方的先锋派艺术曾被列奥塔归入崇高的范畴,因其常以出人意表的观念和做法制胜,往往会忽略形式和技法本身的和谐,这里的崇高也包含了先锋艺术所具有批判性的意味。但是,当吃死婴、自残等等做法已经在当代艺术领域中被一一挖掘实践,当惊吓已经让人麻木,我们如何重新回归平常和平淡?
朗西埃指出,列奥塔的崇高说在今天已经不再适用,那么如何重新回归平常心和平淡美是一个新的课题。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平淡的美学理念可能也应当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一如我们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
余:霍米·巴巴曾说:“朝后看,往前走。”至少我不是特别崇敬喧嚣的作品,或观念大逆反的作品。当代艺术需要和时空发生关联、和历史的根源深处发生关联、和当下体验和超越当下困境相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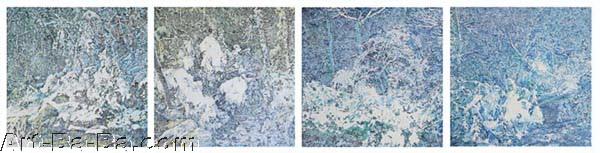
项:我同意,当代并不排斥历史和传统,反而是对历史和传统的重新理解和体验。所以阿甘本还指出:当代性通过首先使当下变得古老而把自己铭写在当下之中;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一种秘密的姻亲关系,因为古老的形式是进入现代的关键;当代人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
从境界上看,你的新作让我想到了一花一世界的禅境,有很通透的感觉,也有着浓厚的宇宙感,正好对应了我梦中的老僧入定。人在面对大自然时,往往油然心生感慨,历史感宇宙感一起被激发,比如陈子昂登幽州台而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听说你带学生去敦煌写生时,看日出日落颇多感悟和感慨,能否详细介绍?
余:2011年秋冬时节,我曾带美院油画系学生去敦煌考察,我们凌晨3点披星戴月去雅丹地貌看日出。在茫茫戈壁之中,天地竟是如此之近,人显得极其渺小,一道亮光钻出地平线驱走了闪耀的启明星,一切皆空,刹那间天地交融。
落日时分,在中国和蒙古边境的额济纳旗,汽车以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沙尘暴中艰难穿行,茫茫中什么也看不见,极其惆怅。在翻过一个小山包时,若隐若现某种迹象,于是下车跑到弱水河畔另一个稍高的山坡,这时彻底惊呆:夕阳下沙尘中弱水河胡杨林群山坡,看到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时空穿越。遭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能感慨德国画家基弗所说:“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项:陈子昂是因为怀才不遇,才会登临有感,从而创作了千古传颂的力作,其实登过幽州台的人何止千万,未见他人有何大感慨。同样,当时和你一起去敦煌的人很多,怎么就你感触最深,仿佛一下子参透了人生的感觉。八卦一下,这和你的年龄有关吗?还是和你的经历有关?
余:的确,视觉经验和人生体验,与绘画创作有极大的联系。对绘画而言,在传统与当下、对象与自我的坐标中,确立自己的方位异常重要。对我来说,油画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富矿中可开发的资源远未穷尽。
“诗为无形画,画为有形诗” ,在中国文化中,光影与人生感慨交相与共。
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月,幻出月、影、人三者。欢、忧、聚、散乃人之常情,醉游太空,携月影同游,何等飘逸。
诗的意境和中国传统的山水意境有很大的关联性,可以让我们触摸绘画的内核。我尝试写了《夜光》诗一首:
“雪景寒林,夜光初现,清影方见。古贤秉烛夜游,观览山水,遗形得色。
波光林影,灯火阑珊,人迹罕至。今人踏雪寻踪,畅饮林泉,寻诗绘意。”
项:不曾想你还有此雅兴。非常感谢,今天的对话也算是给我的梦做了一次深入的解析,我也找到了答案。可见,古人的卧游山水乃至神游、梦游都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