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天中土 文/陈家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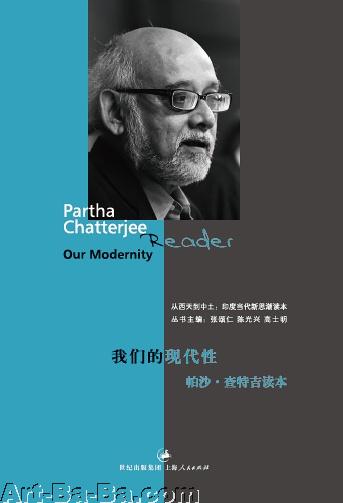
这是一位学者,兼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用孟加拉语创作了六部戏剧作品并最后公演。
这位查特拉先生显然更关心的是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所提出的问题,比如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与自己的当下时代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是否定性的,即“逃离”。查特拉先生说,如果说康德所理解的“当下”,指的是对“过去”的场域的“逃离”的话,我们所要“逃离”,恰恰是自己“当下”所处的场域。那么也就是说,在康德那个时代,西方的现代性是逃离过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现代性则是逃离当下。
“逃离当下”是什么意思?查特拉先生其实指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途径、方式或既定目标的逃离,而不是现代性本身。他举了这样一个极有意味的例子:1894年4月8日,孟加拉邦最伟大的文学家般吉姆·钱德拉·恰托怕德亚(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去世,去世后三周,当时最著名的两个图书馆准备在一个剧场举行一场追悼会(发言人就包括当时崭露头角的诗人泰戈尔),邀请孟加拉邦另一位最受尊敬的文学家纳宾钱德拉·森(Nabinchandra Sen)担任主持;但纳宾钱德拉·森婉拒了这一邀请。为什么?众人有着多种猜测。最后,纳宾钱德拉·森自己说明了其中的缘由:追悼会是一种世俗化了的西方基督教仪式,我们为什么要模仿英国人也召开这样的追悼会?什么是孟加拉邦自己原有的悼念仪式?纳宾钱德拉·森说,“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可以组织一场公众集会来表达哀思。一场表达哀思的集会,想想都觉得可笑!”他说,哀思是神圣的,它要我们远离人群,我们也不会通过佩戴黑纱来悼念逝者;在礼堂的集会只会营造一种欢乐气氛,我们悼念死者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追悼会上作了一场精彩发言的泰戈尔反驳了纳宾钱德拉·森,他的主要观点是:不错,追悼会是对欧洲习俗的模仿,但印度与欧洲的接触已经使我们接受了这种习俗,“满足需要的新方式也应运而生”,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是欧洲的习俗就拒绝接受。
下来的问题涉及到什么是“人造的社会形式”,比如追悼会的形式就是人造的,人造的即为器物,就是虚构的、非自然的,因而也就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但纳宾钱德拉·森不这样看。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追悼或悼念是否属于一种强烈而私密的个人情绪,所以它就不适合通过公众集会来表达。
于是再下来的问题就更进了一步: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为什么要把本属个人私密的悼念活动变成公共活动?因为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了一种叫做“共同体”的东西席卷了整个社会领域,于是就有必要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规定和管理;大型的集会,包括追悼会其实是社会这一“共同体”的需要。与此相关,也就有了完全不同于“私人”(private)的“公共”(public);而我们之所以要以公众集会的形式追悼公众人物,就是因为他不再属于他的家庭,而是属于社会,属于公共福祉。
一旦涉及到“公共”与“私人”,对我们这些熟知康德关于启蒙定义的人来说,马上就想到了这正涉及到了一个关于启蒙的核心问题: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泰戈尔的反驳之所以有力,就在于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共同体还不完善,还需要教育,还亟待完善各种公共生活的规定与管理,而追悼会不过是其中的一项活动而已。他说,欧洲的伟人总是面对全体大众,他们不仅仅限于家人与朋友,而是公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所以他们一旦去世,悲伤就会笼罩整个社会,而印度的伟人们在公共领域却远没有这么显眼,所以我们必须以公共集会的形式来悼念般吉姆。泰戈尔一生致力于对公共生活中的美德与伦理规范的信仰,这使得他既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康德式的理性主义者。
纳宾钱德拉·森并不那么容易被说服。他说,追悼会上有的人并不悲伤,有人在嚼着烟草,有的人哼着小曲,我们与其组织这种浪费时间的聚会和讲话,还不如把精力用于保护诗人的诞生地,让人们如过去那样定期去“圣地”祭奠。
真正具有某种“后现代”反讽意味的是:纳宾钱德拉·森反对以追悼会的形式祭奠伟人,泰戈尔则竭力想通过公共祭奠的形式使公民走向成熟的公共生活。历史证明了泰戈尔的想法是对的,现在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公共祭奠的方式;但泰戈尔1941年逝世后,他却成了印度民众心目中的神,他的出生地也成了朝圣地,而这一切,却正是纳宾钱德拉·森当年所想恢复的本地传统。
大凡实现了现代性目标的国度或民族,其自身的传统反而会得到更好的彰显,这也是我的日本时所看到和想到的一个问题。
查特吉的精彩之处在于他通过纳宾钱德拉·森与泰戈尔的辩论,想到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人们的“伦理生活”的划分,这就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阶段。他首先告诉我们“现代”这一概念包括七个方面:健康、教育、民生、社会生活、道德、政治制度和宗教。这七个方面首先通过“市民社会”(其实也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可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来体现人们的共同体生活,它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独立、出入自由、契约、共同商议的决策程序、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等等方面。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市民社会要以这些原则抵御国家的干预,竭力“去政治化”,但事实上,上述七个方面的“现代生活”或市民社会的若干原则又无一不具有政治性,于是也就可能模糊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别。
查特吉的理论贡献在如下两点上:第一,他认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观念中,我们应该把社会的单位从“家庭”转变为“人口”(population),这样,人口就构成了社会中的“异质材料”,它和同质化的家庭不同,人口从来就不是规范性的,而是描述性和实证性、统计性的,它包含了大量“更自然”、“更原始”的元素,“某个特定人口群体的内部组织原则是无法从理性角度加以解释的,因为它不是理性契约联盟的产物,而可以说是前理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印度的早期殖民现代性时期(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是早期现代性时期)那些杰出的思想领袖为什么要竭力建立起一种“现代结社的公共生活形态”。要建立这种形态,首先要破除家庭(伦理),其次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伦理生活(在西方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模式)。查特吉说,这一新的伦理生活在一开始还只能对精英开放,因为“公众”作为“人口”还无法适应它。教育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教育什么呢?查特吉的第二个理论贡献就体现为对公众政治生活的强调。他说,在黑格尔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并没有格外强调政治生活的重要;而思考人口与国家之间起调节作用并与市民社会平行的制度领域极其重要,这就是他所强调的政治生活。说是政治生活,其实主要是政府如何通过社会福利这一政府功能来与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发生关联。市民社会是为了满足新的伦理生活的要求(这让我们想起了麦金泰尔等人的社群主义学说),政治生活则是为了要政府满足人口新的福利生活(这又让我们想起了罗尔斯的政治学说)的要求;前者是取代了“家庭”后的现代结社的公共生活形态;后者则是为了以政治生活的方式处理人口与国家的关系(也只有国家才能通过疏导和规制来满足那些非精英人口的社会诉求)。
查特吉为什么要用“人口”取代“家庭”,为什么要在“市民社会”之外再加上一个“政治生活的领域”?因为他发现在西方社会,家庭已然契约化了(黑格尔当然是强烈反对的),契约成为婚姻法、财产法、遗产法以及个人税收法的依据(中国也正在慢慢成为这个样子)。西方世界的“共同体”依旧以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为核心。但印度是决不会走到这一步的,不能让家庭关系(甚至包括亲情)契约化,但又必须建构非家庭的共同体,确立非家庭亲情关系的伦理规范,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国家的政策法规来实现西方社会通过个人契约所要实现的东西。所以他既强调人口,在人口之上发展出具有契约能力的市民社会;又同时引申出不具有这种能力的政治社会,让国家来满足人口的福利诉求。而在这一满足中,最重要的教育与训练当然就只能是民主,也只有民主才能概括政治社会(政党、运动、非党派的社会福利诉求)的社会动员形式。
取代黑格尔那里的家庭伦理生活的是市民社会这一共同体的伦理规范与国家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很有创建的政治设想,事关未来,是想象力的产物,但又完全立足于印度的社会现实。
所以,查特吉最后的结论就是:第一,殖民时期最重要的变革场所是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后殖民时期的变革场所是政治社会(国家民主);第二,殖民时期统领社会变革相关讨论的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在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社会里,统领全局的问题是民主问题;第三,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完全有可能正在见证现代性与民主(即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逐渐形成的对立。
我们真是这一巨大变革的见证者吗?查特吉是相信的,他与我年龄一样大,但比我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