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ficial Hells: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人造的地狱:参与性艺术和观看者政治” (Verso 2012)
作者/claire bishop
译/杜可柯
--------------
相关链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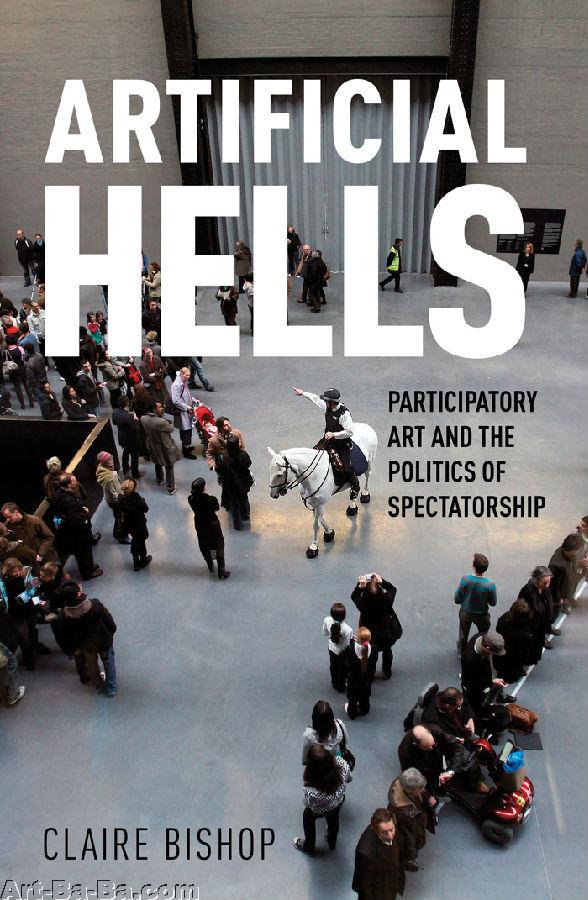
第一章
The Social Turn: Collabo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社会转向:合作及其不满
目前有关参与合作式艺术的文献里,反复出现的几个理论参照点包括:瓦尔特•本雅明、米歇尔•德•塞尔托、情境主义国际、保罗•弗雷勒、德勒兹和加塔利、哈基姆•贝(Hakim Bey)等。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法国电影人/作家居伊•德波。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抨击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异化和分裂,同时对集体生产的“情境”进行了理论阐述。对许多左派艺术家和策展人来说,德波的批判让人深切感受到参与作为一项事业为什么很重要:它能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工具性的压制下日益麻木和碎片化的社会回归人性。按上述说法,由于市场已经几乎完全浸透了我们的图像库,艺术实践就不可以再专注于制造供被动旁观者消费的物品。相反,我们需要一种行动的艺术,进入现实,一步一步(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地修复社会联系。例如,艺术史学家Grant Kester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被缩减为由原子化消费者组成的伪社群”的世界里,“景观和重复麻痹了我们的感知力”,而艺术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反抗这个世界。荷兰艺术家Jeanne van Heeswijk写道:“艺术家对展示者-观看者这种被动过程不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交流实际上已经彻底被商业世界窃取⋯⋯说到底,如今你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获得审美体验。”最近,艺术家/活动家Gregory Sholette和艺术史学家Blake Stimson提出“在一个完全臣服于商品形式和景观的世界里,唯一的行动剧场是直接介入生产力。”就连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在描述九十年代关系艺术时也把景观作为他的核心参照点:“今天,我们已进入景观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个体从被动和纯粹重复状态转向市场力量分配给他的最小限度的活动⋯⋯此处,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变成景观的剩余。”正如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指出的,“对景观的批判”常常成为“艺术的政治”最初也是最后的依托。
除了关于景观的话语以外,过去十年的先锋艺术开始了新一轮对集体的肯定以及对个体的贬抑,后者已然成为冷战后自由主义与其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同义词,即: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经济实践。很多这类讨论都受到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的影响和推动。在此框架之下,拥有一技之长的当代艺术家就变成灵活、激动、非专业化劳动力的典型代表,能够创造性地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竖立他/她自己的品牌。该模式的对立面则是集体:协同合作实践被自动看成社会团结的另一种模式,无论其实际政治如何。正如Paolo Virno所说,如果鼓舞并连接历史前卫艺术运动的是核心政党,那么“今天的集体实践则连接于构成后福特主义社会合作的去中心、异质性的网络”。大量展览和活动对这种新生“诸众”的社会网络进行了价值肯定,比如“集体创造力”(Collective Creativity, WHW, 2005)、“还政于民”(Taking the Matter into Common Hands,Maria Lind et al., 2005)、“民主在美国”(Nato Thompson, 2008)。除了“乌托邦”和“革命”以外,集体与合作是过去十年先锋艺术和展览策划最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无数作品从各个身份角度处理了集体欲求的问题,例如Johanna Billing略带哀伤的录像,他用音乐将年轻人召集到一起(《革命项目》,2000,“魔法世界”,2005);Kateřina Šedá预先安排好一天的活动,然后邀请一个捷克小村庄里的所有人参加(《那里什么也没有》,2003);Sharon Hayes为同志社群组织参与式活动(《革命之爱》,2008);Tania Bruguera让盲人穿上军装,站到街头拉客(《圆房革命》,2008)。即便在并不直接是参与式的艺术作品里,对社群、集体性(无论是已经失落的,还是实际存在的)和革命的指涉也足以暗示一种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批判距离,尤其因为目前的商业艺术系统和美术馆工作仍然围绕利润丰厚的单个艺术家运转。
因此,社会领域的参与项目在运作过程中似乎带有一种反抗和改善的双重姿态。它们通过将个体创作身份消解在集体合作活动中反抗了主流市场秩序,同时(用Kester的话说)超越了“否定和利己的陷阱”。参与式艺术不为市场提供商品,而是试图将艺术的象征资本导向建设性的社会变革。鉴于这些明确公布的政治以及此类作品背后的坚持,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今天的前卫艺术形式:艺术家利用非物质、反市场、充满政治诉求的项目创造出各种社会情境,继承了前卫运动让艺术在生活中发挥更关键作用的遗产。然而,这一社会任务的紧迫性造成的结果是:所有社会合作实践都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抵抗姿态,不存在失败的、无疾而终的或无聊的参与式艺术作品,因为对于修复社会联系的任务而言,它们都同样重要。我能理解后者的雄心,但还是认为将此类作品当作艺术来讨论、分析和比较也非常必要,因为赞助和传播它们的机构领域毕竟还是艺术界,尽管艺术范畴始终被排除在有关此类作品的讨论之外。
I. 创造力和文化政策
对欧洲来说,这一任务尤为紧迫。英国新工党(1997-2010)为了说明艺术公共支出的必要性,使用了一套跟社会动员艺术的实践者们几乎一模一样的说法。急于问责的新工党在1997年上台之初提出的问题是:艺术能为社会做什么?答案包括提高人们获得雇佣机会的能力,减少犯罪,鼓舞士气等等,独独没有把艺术实验和研究本身当成有价值的东西。艺术的生产和接受因此被改装放进政治逻辑,观众人数和营销数据成为确保公共资金的核心要素。新工党御用关键词是“社会排斥”:在学校教育上掉链子,后来又无法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最有可能对整个社会福利系统造成问题。因此,新工党鼓励艺术增加社会包容性。尽管听上去很美,但该议程受到来自左派的批判,主要因为它试图掩盖社会不平等,将其变成表面问题,而不是结构问题。这个概念代表了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分割:一边是被包含在内的多数群体,一边是被排斥在外的少数群体(过去它的名字叫“工人阶级”)。社会排斥相关话语暗示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跨越上述分割线,从被排斥的少数变成被包含在内的多数,尽可能让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给自足式消费主义的圣杯,而不需要依赖社会福利。此外,社会排斥很少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而更多被定性为边缘(和个体)问题,比如吸毒、犯罪、家庭破裂、青少年怀孕等。参与成为社会包容性话语里的热门词汇,但与其在当代艺术中的功能(自我实现和集体行动)不同,对新工党来说,社会包容性实际上指的是消除那些惹麻烦的个体。进入并参与社会意味着有全职工作,有可支配的个人收入,能够自给自足。
被吸收进入新工党文化政策的社会包容性话语严重依赖于François Matarasso的一份报告。Matarasso在这份报告中证明了艺术里社会参与的积极作用,他一共列举了五十项“好处”,指出社会参与实践能够减少社会隔绝,帮助人们交到更多朋友,发展社区网络和社交能力,促使犯罪者和受害者共同解决犯罪问题,提高人们的就业能力,鼓励人们以更积极的态度接受风险,同时改善公共机构的形象。最后几点也许潜在的问题最大:社会参与之所以被冠以正面评价,是因为它创造了顺从的公民,这些公民尊重权威,面对日益缩减的公共服务,愿意接受自生自灭的“风险”和责任。正如文化理论家Paola Merli所说,上述结果中没有一样能改变,甚至能使人更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里的结构性条件,它只能让人更好地接受现状而已。
因此,社会包容性议程的重点并不在于修复社会联系,而在于促进所有社会成员成为自我管理、运转良好的消费者,使他们能够在不依赖福利国家的前提下独立生活,能很好地适应一个去监管、私有化的世界。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社群概念就不是要建立社会联系,而是要侵蚀这种联系;借用社会学家Ulrich Beck的话说,社会问题变成个人问题而非集体问题,我们感到不得不“为系统矛盾寻求个体解决方案”。按照这种逻辑,参与社会只不过意味着个人把过去国家应该解决的问题抗到自己肩上而已。2010年5月,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上台以后,这一责任下放过程就进一步加速:大卫•卡梅隆的“大社会”看上去是要把权力交还人民,使公众能对图书馆、学校、警察和交通等公共部门的运作状况提出质疑和挑战,但实际上却只是给自由放任的政府模式披上了一件培养“志愿者、慈善和社会行动新文化”的漂亮外衣罢了。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机会主义的面具:要求志愿者用无偿劳动填补政府削减开支形成的漏洞,同时把那些用来保证社会成员能平等获取教育、福利和文化服务的公共部门私有化。
⋯⋯
(待续)
这样做并没有像我们可能在某些跨学科的艺术实践里看到的那样,催生出富有生产力的跨界和综合,反而把一切都化简为经济问题:“从经济实用的角度看,某些人对某些领域在艺术上的贡献更大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一年后,也就是2006年,荷兰政府启动了投入1500万欧元的“文化与经济”项目,旨在把创意打造成荷兰特产的出口商品,这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把De Stijl的逻辑扩大成创业机会。同时,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开始了一系列积极行动,要把荷兰首都改造成一座“创意城市”:“创意将成为核心议题”,因为“创意是赋予这座城市魅力和活力的发动机。”
荷兰项目学的是新工党,后者就总是强调创意和文化在商业与“知识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这其中包括把美术馆作为城市再生的动力源,同时投资“创意产业”,将其作为传统制造业的替代选项。新工党继续发展了保守党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公开的工具论处理方式:2001年的一份《绿皮书》开篇就说“人人都是创意者”,把政府的任务设定为“解放每个人的创造潜能”。然而,这一解放创造力的目标并不是扩大社会福祉,实现人的真正潜能,也不是对乌托邦式替代选择的想象,而是为了生产出“一个由社会背景多种多样的创意产业工人组成的未来世代,他们的想法和技术不仅需要被灌注到艺术文化领域,同时也能做成好生意。”(社会学家Angela McRobbie语)
简而言之,一个流动的创意阶层的出现服务于两项目标:一方面把人们对福利国家的依赖程度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免除企业对员工永久雇佣的责任。所以,新工党认为在学校开发创造力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艺术家(就像波伊斯说的那样),而是因为与创意相关联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成为必要:人们必须有创业精神,愿意接受风险,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打造自己的品牌,甘心自我剥削。再引用McRobbie的说法:“如何解决不同人群中间存在的大量不同问题——比如不愿回到全职工作上去的家庭主妇——新工党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雇佣’(self employment),做自己的生意,做你想做的事情。像一个艺术家一样生活和工作。”社会学家Andrew Ross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家已经成为被他称作“没领”(No Collar)劳动群体的模范:艺术家为不稳定劳动阶层(precarious labour)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仿范式,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的心理状态建立在灵活性基础之上(不是朝九晚五地上班,而是一个一个地接项目),同时经过了牺牲式劳动(sacrificial labour)概念的打磨(即:愿意接受更少的报酬,以此换取相对的自由)。
我们在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有关参与型艺术的文章里都可以发现这种艺术与创意话语的混淆,两者对作品的评判标准都基本上是社会学性质的,注重可展示的实际效果。比如,策展人Charles Esche在写丹麦艺术小组Superflex的 Tenantspin项目(该项目针对利物浦一座破败塔楼里居住的老人制作了一个网络电视台)时,就在文章中穿插了大量有关英国廉租房的政府报告,暗示了社会学背景知识在理解艺术家这个项目上的重要性。但他对Tenantspin的核心评判建立在该项目作为一种“工具”是否“有效改变了塔楼及其中居民的形象”基础上;他认为,Tenantspin项目最大的成绩是“增强了这座塔楼里的社群感”。Esche是政治化的艺术实践在欧洲最坚定明确的支持者,也是最大胆激进的美术馆馆长之一,但他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我想拿出来供大家思考的一种批评倾向。他没有讨论Superflex把这个项目当成艺术来做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使得他的价值判断最终变得跟强调实效的政府艺术文化政策毫无区别。
就这样,我们滑进一种社会学话语当中——可美学上哪儿去了?“美学”在过去几十年已成为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词,至少在英语文化圈内,学术界对社会历史和身份政治的关注导致美学变成一个碰不得的概念,因为它掩盖了(种族、性别、阶级等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压迫和排除。这一倾向往往把美学等同于形式主义、去语境化、去政治化三大敌人;结果,美学慢慢变成市场和保守文化阶级的同义语。虽然这些论述在70年代对于打破白人男性精英的权威地位非常有必要,但如今它们俨然已僵化成批评教条。
很有意思,喜欢看Bishop





反思我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