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恩斯特-贡布里希
发起人:shirley_88 回复数:0
浏览数:1981
最后更新:2011/12/20 12:13:35 by shirley_88
来源:搜狐艺术
作者:理查德·贡布里希[Richard Combrich]
翻译:许玮 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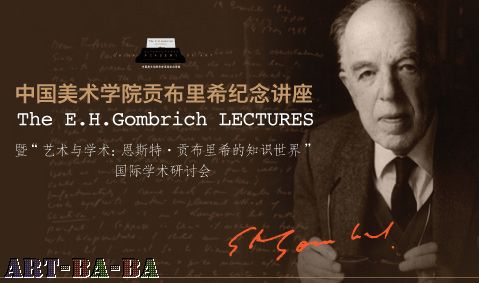
我的父亲恩斯特·贡布里希,于1909年3月30日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父亲名叫卡尔·贡布里希[Karl Gombrich],从事于律师工作,母亲名叫利昂妮·霍克[Leonie, née Hock],是一位著名的钢琴老师。用社会经济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我的父亲有两个姐姐,但没有兄弟。
我的父亲诞生在奥匈帝国,儿时的他曾经目睹过弗朗兹·约瑟夫皇帝[Emperor Franz Josef]于1916年所举行的葬礼。对于当时的景象,他仍记忆犹新。1919至19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维也纳的很多儿童遭受到营养不良的摧残,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1920年,蒙恩于一家延续至今的慈善团体的救助,父亲和年长他两岁的姐姐丽思伯兹[Lisbeth]被送往瑞典,他们被乡间的一个木匠家庭所收养,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光。当时,他们姐弟俩对瑞典语一窍不通,而收养他们的家庭也不会说德语,这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多的不便。那时,我的父亲虽还只是个孩子,却已饱尝了饥饿的滋味,而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这些经历,都使得我的父亲具有宽广的胸襟和悲悯的情怀。
在当时,人们彼此之间不分“种族”。我的父亲曾回忆道:“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纳粹主义运动尚未大行其道,没人会在意他的朋友是不是犹太人。异族之间经常结为连理,反犹太主义为人所不齿。(Eribon, pp.27-8)我的祖父母都出生于所谓的犹太家庭,但他们并没有信奉犹太教。结婚之后,他们都皈依了新教。因此,我的父亲来自一个新教家庭,尽管他们并没有严格地遵守新教教义。
然而,当纳粹执掌大权之后,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我父亲一家都被划分为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也都遭到迫害,而被迫逃亡;而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人们,都亡於非命。父亲对这一事态的转变早已未雨绸缪。1936年1月,他首次来到英国,并在瓦尔堡研究院谋得一职。而此时的瓦尔堡研究院,也刚刚因为纳粹而从汉堡迁至英国。最初,他的研究员工作为期两年,薪酬微薄,其工作是整理学院创始人阿比·瓦尔堡的论文。此时,瓦尔堡本人已于汉堡去世。1970年,父亲出版了他的煌煌巨著《阿比·瓦尔堡——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这部书的问世便得益于他早年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尽管他曾在私下承认,这份差事有些令人乏味。
我的父亲回家与我的母亲完婚,旋即和她一起返回伦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俩于1936年相识于维也纳,当时,我的母亲曾跟着我的祖母学习钢琴。1937年,我在伦敦出生了。战后,父母便获得了英国国籍。他们是坚定的亲英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美国曾数度向我的父亲递来橄榄枝,当哈佛大学邀请他担任教授时,父亲颇为动心。但我的母亲却对英国依依不舍,即便在美国父亲的收入要多得多,母亲也不为所动。父亲告诉母亲,美国最吸引他的一点,便是在早餐中能喝到橙汁。于是母亲答应父亲,在今后的每一顿早餐中,他都能喝上这样的一杯橙汁。母亲坚守了她的诺言,而这也是父亲向母亲所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橙汁从此与父亲的早餐相伴,直至他去世。
尽管我的父亲无疑是一名维也纳人,但他从不以此为荣。他甚至总是认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出身或长相为荣是愚蠢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这一点在他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二战结束若干年后,他甚至都不愿意踏上维也纳的土地,理由是他的亲友与旧识大多都已逃走或遇难。正因于此,他对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颇有微词,尽管他从未将这样的想法公之于众。对于自己被说成是一名犹太难民,他也总是表面上默不作声,但心里却耿耿于怀。他并非难民,因为在事态迫切前夕,他便已筹划好前往英国;同时,只有在纳粹主义的“人种”划分下,他才算是一名犹太人,而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种划分无比丑恶和愚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嗤之以鼻。他会在私下里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是多么的可怕。
我的父母初次见面便以德语进行交谈,之后也一直如此。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决定跟我说英语。这一做法当是审慎之举,因为当我正在咿呀学语的时候,英国正与德国兵刃相向。但我以为,即便时局并非如此,他们仍然会教我说英语。我的父母认为民族之间不应存在隔阂,他们相信,在一个新的国度里生活,就应该去适应那里的环境。在他们看来,我是一名“理所当然”的英国人。为了学好英语,他们可谓煞费苦心。在这一点上,我的父亲成绩斐然,他的英文写作常常得到赞誉,而我相信这也让他颇感欣慰。即便如此,他有时还是会把我看做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向我提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标点的细节上征求我的意见。
二战开始之后,我的父亲为BBC工作,监听敌人的广播。对于这份工作来说,我的父亲可谓最佳人选,不仅因为他对德语和德国文化谙熟于胸,还因为他有着异常敏锐的听力。直至终老,他几乎都还保持着这一天赋。最初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监听员,但很快便被提拔为监听指导员。六年间,他都是在夜间工作,因为最重要的广播往往都是在夜里发布。监听站设在乡间,我的父亲便总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往往是在夜色中往返。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生活,但我并不觉得我的父亲对此心生抱怨。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仅因为他在战火中能够偏安于一隅,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这场战争尽自己的一份力。战事结束之后,有人邀请他留在那里从事类似工作(或许是一份情报工作),为英国政府效力。出于责任感,父亲沉吟片刻,随即便决定重新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他坚信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一名艺术史家。他在护照里也是这么填写的。
在这里,我应该回溯一下父亲在维也纳的经历。当他选择在大学期间研习艺术史时,他就已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会让他将来在奥地利无法谋职。然而,命运弄人,他的一位出版商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份差事,让他为儿童写一部世界史,要在一个月之内交稿。他接受了这一挑战,《写给儿童的世界史》一书因此得以问世。在战争爆发之前,这本书就已被翻译为数种东欧文字。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此书杳然无闻。当父亲变得远近闻名之后,一些颇具商业头脑的出版商注意到了这本早期著作,并将其翻译为其它语言付梓。多年来,我的父亲一直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他认为在英语版本中,这本书需要一些修改,因为原书是以欧洲大陆为视角而写就的。他同时还意识到,这本书的整体内容或许已显得有些陈旧。然而最终,他同意该书大部分内容仍然按原样出版,而他只进行了少许改动。在他去世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利昂妮就将该书完成并出版了。对我父亲来说,为儿童写作是一次颇有价值的经历,因为文字必须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这帮助他在日后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艺术的故事》。
战火停息之后,我的父母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伦敦,父亲重拾起他在瓦尔堡研究院的工作。此时的瓦尔堡研究院已经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在此数年之后,他被授予了终身教席,而不再需要每年都被重新聘用。在其它方面,我想我的父亲在那里的工作是愉快的,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成了我们家的密友。
他的薪酬依然微薄,实际上还达不到战前的水平。我并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当时他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今天英国的大学讲师一个星期的工资。一想到这一点,就令人不禁莞尔。尽管我的母亲必须勤俭持家,但我并不觉得微薄的收入困扰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我记得家里只捡便宜的猪肉买,上面尽是肥肉和软骨。父母的生活习惯也很节俭,他们从不吸烟,也不饮酒。我的父亲对珍馐美馔毫无兴趣,我想他最喜爱的食物就是面包了。而他们也从未想过拥有一台彩电或一辆汽车(我的父亲一直没有学开车,而且本来就无意于此)。我从未感到过生活的匮乏,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要么在免费的公立学校读书,要么拿到了名校的奖学金而去那里上学。我们一家享受英国的国家医疗保健服务,受益颇多。在战争开始后的好几年里,我们家一年只能享受一次为期两周的假期,对此都已习以为常。直到1948年,我才来到瑞士,开始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
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的父亲与卡尔·波普尔曾有过数面之缘。烽火硝烟中,波普尔和他的妻子亨妮在新西兰躲避战乱,并完成了其著作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本该在英国出版,但当时的通讯十分不便。为了帮助波普尔,父亲用微缩胶片编辑此书。当波普尔于1946年开始供职于伦敦经济学院时,他们便开始频繁往来,并成为挚友。
《艺术的故事》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也让我的父亲名声大噪。在已出版的他与迪迪耶·艾里彭[Didier Eribon]的“对话录”中,详细记录了此书的诞生经过(pp.62-6)。因此关于这本书,我已无需太多赘言。他能够完成此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一位好友的坚持,此人名叫贝拉·霍洛维兹[Bela Horowiz],是费顿出版社的创始人。二战前夕,父亲已用德语写出了部分章节,但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无暇遣笔,并对此书心灰意冷。霍洛维茨将已写好的那几章的英文版拿给他的小女儿汉娜看。汉娜时年16岁,她建议他的父亲将此书出版。为此,霍洛维茨给了我的父亲50英镑的预付款,并一再敦促他写完这本书。父亲以无法完成为由推脱此事,但霍洛维茨却不肯拿回那50英镑。父亲为此事反复踌躇。因为当他回到瓦尔堡研究院时,时任院长德国人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 Saxl]告诫他,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儿童读物上,而是应该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扎克斯尔的突然辞世让父亲感到十分难过,但对他而言,这未尝不是一次命运的转机。父亲总是对霍洛维茨,尤其是汉娜心怀谢意,尽管不得不承认,霍洛维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用50英镑从我父亲手里买走了版权,幸好经波普尔的劝说,父亲转而要求抽取版税提成。可想而知,霍洛维茨在这本书上赚的比我父亲要多得多。不过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非常感谢霍洛维茨,没有他的投资,这本书就不会问世。父亲常说“我用黄油做饭”[“Ich koch mit Butter”],在战后的艰辛岁月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他对霍洛维茨手下的图书设计师路德维希·戈德沙依德[Ludwig Goldscheider]博士也是敬重有加,与他的合作令父亲感到十分愉快。
正像父亲所回忆的那样,《艺术的故事》令他声名鹊起,并让他很快就成为牛津大学的斯莱德艺术教授。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为期三年的讲座。从此之后,他平步青云,并于1959年开始担任瓦尔堡研究院的院长,直至退休方才卸任,但仍担任着其它的一些职位。与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所不同的是,父亲对于教学工作乐在其中,从未离开过讲台;也没有荒废过管理工作,对此他尤为重视。1976年,父亲在退休之际提到,他从未休过学术假期,也没有申请过研究补助金。他为瓦尔堡研究院鞠躬尽瘁,尽忠职守。
在这里,我并非要对父亲的工作或学术生涯进行简要的介绍。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的所有成就与活动几乎就是他参与公共活动的记录。《艺术的故事》一书现今已被翻译为近40种文字,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那之前,我只是一名清贫的学者,和外界没有联系,在工作中也默默无闻。”而在此之后,他说:“人们都认识我,知道我是《艺术的故事》的作者,但他们都不知道我还是一名学者。另一方面,我的许多同事都没读过这本书。他们或许看过我关于普桑或莱昂纳多的论文,却对那本书视而不见。这可真是一种奇妙的双面人生。”尽管父亲还出版过很多其它著作,并发表过很多论文,但真正让他从经济上获益的,还是这本《艺术的故事》,以及在他去世之后所出版的英文版《写给儿童的世界史》,尽管后者的知名度要小得多。他的后半生也因此而过得富足惬意,但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行文至此,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他的性格和业余爱好。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据我所知,他与他的父亲非常亲近,而他的母亲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且魅力过人,性格开朗。她主持家事,必定对我父亲的早年生活影响至深。父亲曾向我提及,他非常喜欢有年龄较大的妇女陪伴于左右。我可以证实这一点,而这与他的母亲必定有很大的关系。在其一生当中,父亲有少数几位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他与她们经常联系,即便她们身在异国也是如此。我想,公允而论,在他所亲近和乐于相处的人当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而且通常比他年长。父亲的性格较为腼腆,喜欢和温文尔雅的人相处。然而,他之所以更喜欢女性,尤其是年长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厌恶那些醉心于权力之辈,以及喜欢摆布他人的家伙。对此,我还要再多费笔墨,略述一二。
父亲的姐姐蒂雅[Dea]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当时父亲对她非常爱戴和钦慕,而她的脾气却喜怒无常,对于她的怒火,父亲感到害怕和不安,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他小心翼翼地与蒂雅相处,却与另一位姐姐丽思伯兹非常要好,也更为亲近。丽思伯兹终生未婚,这或许让她与父亲的关系显得更为敏感。不仅于此,他们在瑞典的时光也是一起度过的,蒂雅也在瑞典呆了一小段时间,但没和他们住在一起。
丽思伯兹为人非常谦逊。她在语言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我的父亲对此激赏不已。而丽思伯兹对我的父亲也是敬慕有加。她将父亲的一些著作翻译成德语,或是从德语翻译为其它语言。在父亲看来,她的这些翻译无人能及。丽思伯兹一生坎坷多舛,我想我的父亲对于她的不幸也略感歉疚。在三个兄弟姐妹中,丽思伯兹排行第二,她和她年迈的父母同住,如同他们的保姆。尽管她在音乐方面并非没有造诣,但在某种程度上,她被视为天资最差的家庭成员。客观的来说,这一看法十分可笑。
在我父亲的一生当中,音乐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与视觉艺术相比,他认为自己可能对音乐的反应更为本能。我的祖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其乐感罕有人匹,弹琴能够带给她无比的欢愉。她是莱谢蒂茨基[Leschetitzky]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助手;而莱谢蒂茨基又师从于车尔尼;车尔尼的老师是贝多芬,后者又是莫扎特的门生。与此同时,我父亲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是我祖母的学生。如果没有二战的爆发,那么我母亲很有可能成为一名职业钢琴演奏家。我们家的客厅里放着我母亲的三角钢琴,她时常弹奏,有时能弹上好几个小时,几乎终生不辍。
父亲与母亲的邂逅是一段值得重提的佳话。起初,母亲跟随我的祖母学习钢琴。祖母生性善良慈爱。不久,她就关心起这名年轻的学生,询问她是谁陪着她来到维也纳。当她获知我母亲是孤身一人之后,她又问她生活状况如何,是否游览了这里的名胜。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她便叫来自己的儿子,并让他陪着这位年轻的女士在城市里四处看看。当我父亲来到母亲的房间时,按照当时的习惯,他像军人那样,先用脚后跟轻叩地板,然后向母亲鞠躬致意。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母亲,但我母亲惊讶地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并不陌生。就在几天之前的晚上,母亲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二楼的座位上听音乐,这些座位是专门为前来享受音乐的人而留下的。音乐研习者可以带着乐谱,在这里跟唱。不一会儿,她注意到,在她的身边坐着一名年轻人,在她唱谱的时候,仔细端详着她的乐谱。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终其一生,我的父亲有时会想不起早年旧识的名字和面容,但从未忘记过那个人写了什么书。
我祖母的好友几乎都是音乐家。我想其中和祖母最要好的一位,要数小提琴家大师阿道夫·布施[Adolf Busch]。据我料想,正是我的祖母向布施介绍认识了同样伟大的钢琴家鲁迪·塞尔金[Rudi Serkin]。后来塞尔金成了布施的乘龙快婿,并一直在舞台上保持合作。他们一家与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并不太熟悉,但他们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这位伟大的指挥家,这成了让他们引以为豪的一件往事。
当我长大之后我认识到,在父母眼中,音乐就如同宗教一般神圣和重要,而且对于我的祖父母来说,很可能同样如此。当然,他们自己并不会这么说,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音乐要比宗教重要得多。布施、塞尔金、托斯卡尼尼、卡萨尔斯[Casals]——他们将这些音乐家奉若神明,这些人的唱片被单独摆放在一起。父母经常播放他们的音乐,满怀敬意地一再聆听。补充一句,这份名单并未结束,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也加入其中。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某一天里他听了一会儿音乐,那么他就会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对他来说,“音乐”意味着西方的古典传统。他常常提到,西方文明所发现的和声学系统,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实际上,他的欣赏范围较为狭窄。他的姐姐蒂雅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师从于阿道夫·布施,并曾在托斯卡尼尼手下演奏。她在维也纳的先锋派音乐家圈子里颇有人缘,还首次公开演奏了阿尔班·伯格[Alban Berg]的小提琴协奏曲。我母亲的欣赏口味则宽泛得多。父亲在晚年只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感兴趣。他也欣赏巴赫,但在当时,海顿之前的音乐在维也纳并不怎么受欢迎,或许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我想在今天,我的父母所说的“聆听音乐”这回事,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甚至能够理解了。音乐可以是轻松愉快的,甚至诙谐幽默也无伤大雅,但聆听音乐却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参加一场音乐会必须郑重其事,依礼行事。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人们要排队进入艺术家的休息室,向其道贺。人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簇拥在艺术家周围。他们将艺术家视为挚友,甚至奉为偶像。我的父母会常常打开收音机或留声机,倾听从那里面流淌出的旋律。音乐一旦开始,就不可被打断。电话听筒被搁在一边,任何人进入房间后,要么安静地坐下欣赏音乐,要么离开此地。在他们看来,把音乐当成烘托气氛的道具,不仅是焚琴煮鹤之举,甚至是对神明的亵渎,是对作曲家和演奏者失礼的野蛮行径。因此,我的父母会拒绝在播放背景音乐的餐厅里用餐。要是某人声称雅好音乐,却在音乐演奏时心有旁骛,那么此人就会被视为粗鄙之徒。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父亲自己几乎不怎么演奏音乐。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大提琴,他的大提琴箱就放在我们家的三角钢琴下面。但他拉得并不在行。首先,他显得有些笨手笨脚,除了能用双手变出肥皂泡逗孩子们开心之外,他就再也玩不出别的什么把戏了。其次,对于一般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来说,他的家庭以及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音乐标准显得高不可攀。要是他真把拉大提琴当回事儿,那么每天必须要练习至少一个小时,而对他来说,这是做不到的。在伦敦的时候,蒂雅经常来我们家,与我的母亲演奏室内乐,有时她让我的父亲也加入其中,来一段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三重奏,但他并未乐在其中。我想,他是觉得这有些丢脸,对此我深表同情。
从父亲给我的职业建议中,我觉得可以窥见他对音乐的一些看法。他经常说,有两个职业他不建议我去从事。首先,他不想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乐评家。在他看来,乐评家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人,只会信口开河。然而,另一个他不让我从事的职业,却是音乐家。对此,他的理由截然相反:他认为职业音乐家的生活太过艰苦和紧张,这会使人耗尽精力,无暇去做别的事情。当然,如果我的确具有音乐天赋,他也不会拦着我,不过幸好,这个问题从未出现过。
我的父亲为人温文尔雅,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非会偶尔动怒之外,平常他并不表露自己的情感,真不知道那些和他并不熟悉的人该如何去评判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会经常开一些玩笑。但他的幽默里总是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没有开过那种直白粗俗的玩笑。他笑得并不多,也不会放声大笑。
父亲对人文价值倍加关切,我想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憎恶惨无人道的暴行,即便是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内容,他也难以容忍。不仅于此,他还笃信于人类的平等,尽管他没有就这一点而高谈阔论。我的言下之意是,他只关注于人们的内在品质,对他来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毫无价值。父亲最在意的是人的心智。我记得,在他谒见了女王陛下之后,他谈论起女王,其措辞如同在描述任何一个寻常之人。尽管他丝毫不在乎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过我想,有人会指责他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慢。但在他看来,这种清高和傲慢正是对某种事物的尊重,这种事物要比其它事物更有价值,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比滚石乐队的歌曲更胜一筹一样。
我的父亲不愿看到人们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常说,在他年轻的时候,贫穷是一种真切的感受。一个不再有穷人的社会,当然是美好的。对于财富,他同样不以为然。他并不宣扬革命,但我相信,在他眼里,坐拥大量的财富是愚蠢的。令一些来访者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位艺术“专家”的家里,墙上竟然没有一幅值钱的画。他认为,如果一件艺术品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那么就应该将它公之于众,最好是放在公共博物馆里。他会欣然前往,一次又一次地到博物馆去观赏它,而不是整天和它生活在一起。在我眼里,他对金钱和财富的看法与一名得道高僧或基督教修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诚然,父亲对金钱的看法的确与众不同。他认为金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话题,对于那么多人喜欢谈论它,父亲感到不可思议。他绝不会在钱财方面浪费时间。他从不买股票,也不做其它的投资,只会把他的所有收入都存入银行。对于那些千方百计想要逃税的做法,他嗤之以鼻。他认为,税收终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诸如在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他对金钱的态度在一桩小事中表露无遗。有一次,他和出版商订立了一份新的合约。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去看望他,并提及此事,询问他商谈结果如何。当父亲告诉她结果之后,我的女儿大吃一惊。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和别人讨价还价,而是任由出版商宰割。当女儿劝慰他时,他说:“那人可真是个财迷,就随他去吧!”
要是有人因窘困而有求于我父亲,那么他会给人留下很慷慨的印象。但我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很乐善好施。我们之间从不谈钱的事儿,因为 我知道,但凡我需要什么,他都会解囊相助,并且相信我确有所需。我想,他对我的母亲也一定是照此行事。
除了钱财之外,我的父亲对其它某些事情也漠不关心。例如,他对运动就毫无兴趣。他会偶尔和孩子们一起游戏,但我想,在他看来,运动一定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在上学的时候,我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母亲很支持我这样做,而父亲则默不作声。我想他很难体会到那些喜欢观看比赛,或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感受。一般而论,父亲对体育竞技没什么兴趣。他总是喜欢念叨一件旧事,但我怀疑这件事是否属实。有一次,沙特国王前去拜访维多利亚女王,女王便邀请他一同去看赛马。父亲说,他弄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看点,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匹马会第一个冲过终点。
关于宗教,他认为在艺术、建筑和音乐方面,它向世人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但在其它方面,他赞同伏尔泰的观点,认为宗教有害无益。对于自己的葬礼,他的唯一要求是千万别请神职人员参加。
他对政治也不太关注,尽管是出于别的原因。我已经提到过,他憎恶暴力,对于那些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者,他避之犹恐不及。因此,他对政治家颇不以为然,尽管他也承认,政客当中亦有良莠之别。
他对政治的反感有两个层面。首先,他对法西斯主义者深恶痛绝。在这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几乎绝口不提,如果有人对他们稍加袒护,那么父亲便会勃然大怒。要是有人来我们家做客,滔滔不绝的谈论他们所犯下的暴行,那么父亲就会如坐针毡。因此,他从不会直接提及那些杀害了我们家亲戚的纳粹分子。他也拒绝踏上任何一片被独裁者所统治的土地。
相对而言,英国的政治生活较为平和。在这个层面上,父亲还是留心于国内政治的,但仍然宁愿置身于事外。显然,至少在他的晚年,他就再也不想去投票了。我相信,他对穷人的同情促使他从不把票投给保守党。他很少提到他支持哪个党派,但我母亲总是支持自由党,我想父亲应该也是如此。
他认为,英国社会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便是很少有人热心于政治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或是被它们所左右。这些事物只会干扰平静的生活,而人们本该将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去,比如艺术和音乐,当然并不仅止于此。他喜爱大自然,喜欢到乡间或是伦敦的公园里漫步,总是乘兴而去,尽兴而归。他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予以肯定。他认为,科学为人类所带来的福祉,远大于它所造成的危害,在科学领域里,人类得以尽其所能,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展现他们的才华。对于文学,父亲或许倒不那么热衷,当然也不会去翻览现代小说。但他在阅读欧洲古典文学方面非常在行,并喜欢将它们默志于心。他热爱意大利。
在个人生活习惯上,父亲是一个保守的人,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三件套,或是披上睡衣。在这方面,他完全是个老古董。但在精神层面上,他是一位真正的自由的思想者。他打趣的说,他这个院长当的就像一位“万事管”。为了确保在一天当中,至少有一段时间能让自己专心致志地思考,他在每天早餐之后都会花上很长时间洗个澡,而我的母亲则会把他的衣服准备好了放在外面。这样,他就可以不用为穿什么衣服而费心了。总的来说,父亲的性格有一点悲观,但绝不愤世嫉俗。医学的进步缓解了人类的病痛,延长了生命的期限,但并没能让人类变得更加睿智。当我们急于摒除我们的传统中那些愚昧的因素时,也匆忙地抛弃了种种传统的价值。因此,这个世界究竟是在变得更加美好,还是正在滑向堕落,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但至少,我们仍旧可以去聆听海顿与莫扎特的美妙音乐。
注释请参考E.H.贡布里希《一生的兴趣——与迪迪耶·艾里彭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对话》(泰晤士与哈德森出版社,伦敦,1993),1991年首版于法国。
作者:理查德·贡布里希[Richard Combrich]
翻译:许玮 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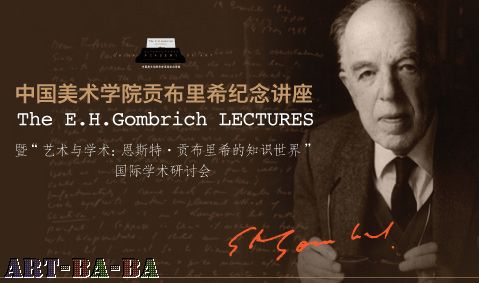
我的父亲恩斯特·贡布里希,于1909年3月30日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父亲名叫卡尔·贡布里希[Karl Gombrich],从事于律师工作,母亲名叫利昂妮·霍克[Leonie, née Hock],是一位著名的钢琴老师。用社会经济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我的父亲有两个姐姐,但没有兄弟。
我的父亲诞生在奥匈帝国,儿时的他曾经目睹过弗朗兹·约瑟夫皇帝[Emperor Franz Josef]于1916年所举行的葬礼。对于当时的景象,他仍记忆犹新。1919至19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维也纳的很多儿童遭受到营养不良的摧残,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1920年,蒙恩于一家延续至今的慈善团体的救助,父亲和年长他两岁的姐姐丽思伯兹[Lisbeth]被送往瑞典,他们被乡间的一个木匠家庭所收养,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光。当时,他们姐弟俩对瑞典语一窍不通,而收养他们的家庭也不会说德语,这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多的不便。那时,我的父亲虽还只是个孩子,却已饱尝了饥饿的滋味,而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这些经历,都使得我的父亲具有宽广的胸襟和悲悯的情怀。
在当时,人们彼此之间不分“种族”。我的父亲曾回忆道:“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纳粹主义运动尚未大行其道,没人会在意他的朋友是不是犹太人。异族之间经常结为连理,反犹太主义为人所不齿。(Eribon, pp.27-8)我的祖父母都出生于所谓的犹太家庭,但他们并没有信奉犹太教。结婚之后,他们都皈依了新教。因此,我的父亲来自一个新教家庭,尽管他们并没有严格地遵守新教教义。
然而,当纳粹执掌大权之后,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我父亲一家都被划分为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也都遭到迫害,而被迫逃亡;而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人们,都亡於非命。父亲对这一事态的转变早已未雨绸缪。1936年1月,他首次来到英国,并在瓦尔堡研究院谋得一职。而此时的瓦尔堡研究院,也刚刚因为纳粹而从汉堡迁至英国。最初,他的研究员工作为期两年,薪酬微薄,其工作是整理学院创始人阿比·瓦尔堡的论文。此时,瓦尔堡本人已于汉堡去世。1970年,父亲出版了他的煌煌巨著《阿比·瓦尔堡——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这部书的问世便得益于他早年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尽管他曾在私下承认,这份差事有些令人乏味。
我的父亲回家与我的母亲完婚,旋即和她一起返回伦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俩于1936年相识于维也纳,当时,我的母亲曾跟着我的祖母学习钢琴。1937年,我在伦敦出生了。战后,父母便获得了英国国籍。他们是坚定的亲英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美国曾数度向我的父亲递来橄榄枝,当哈佛大学邀请他担任教授时,父亲颇为动心。但我的母亲却对英国依依不舍,即便在美国父亲的收入要多得多,母亲也不为所动。父亲告诉母亲,美国最吸引他的一点,便是在早餐中能喝到橙汁。于是母亲答应父亲,在今后的每一顿早餐中,他都能喝上这样的一杯橙汁。母亲坚守了她的诺言,而这也是父亲向母亲所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橙汁从此与父亲的早餐相伴,直至他去世。
尽管我的父亲无疑是一名维也纳人,但他从不以此为荣。他甚至总是认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出身或长相为荣是愚蠢的,因为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这一点在他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二战结束若干年后,他甚至都不愿意踏上维也纳的土地,理由是他的亲友与旧识大多都已逃走或遇难。正因于此,他对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颇有微词,尽管他从未将这样的想法公之于众。对于自己被说成是一名犹太难民,他也总是表面上默不作声,但心里却耿耿于怀。他并非难民,因为在事态迫切前夕,他便已筹划好前往英国;同时,只有在纳粹主义的“人种”划分下,他才算是一名犹太人,而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种划分无比丑恶和愚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嗤之以鼻。他会在私下里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是多么的可怕。
我的父母初次见面便以德语进行交谈,之后也一直如此。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决定跟我说英语。这一做法当是审慎之举,因为当我正在咿呀学语的时候,英国正与德国兵刃相向。但我以为,即便时局并非如此,他们仍然会教我说英语。我的父母认为民族之间不应存在隔阂,他们相信,在一个新的国度里生活,就应该去适应那里的环境。在他们看来,我是一名“理所当然”的英国人。为了学好英语,他们可谓煞费苦心。在这一点上,我的父亲成绩斐然,他的英文写作常常得到赞誉,而我相信这也让他颇感欣慰。即便如此,他有时还是会把我看做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向我提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标点的细节上征求我的意见。
二战开始之后,我的父亲为BBC工作,监听敌人的广播。对于这份工作来说,我的父亲可谓最佳人选,不仅因为他对德语和德国文化谙熟于胸,还因为他有着异常敏锐的听力。直至终老,他几乎都还保持着这一天赋。最初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监听员,但很快便被提拔为监听指导员。六年间,他都是在夜间工作,因为最重要的广播往往都是在夜里发布。监听站设在乡间,我的父亲便总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往往是在夜色中往返。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生活,但我并不觉得我的父亲对此心生抱怨。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仅因为他在战火中能够偏安于一隅,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这场战争尽自己的一份力。战事结束之后,有人邀请他留在那里从事类似工作(或许是一份情报工作),为英国政府效力。出于责任感,父亲沉吟片刻,随即便决定重新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他坚信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一名艺术史家。他在护照里也是这么填写的。
在这里,我应该回溯一下父亲在维也纳的经历。当他选择在大学期间研习艺术史时,他就已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会让他将来在奥地利无法谋职。然而,命运弄人,他的一位出版商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份差事,让他为儿童写一部世界史,要在一个月之内交稿。他接受了这一挑战,《写给儿童的世界史》一书因此得以问世。在战争爆发之前,这本书就已被翻译为数种东欧文字。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此书杳然无闻。当父亲变得远近闻名之后,一些颇具商业头脑的出版商注意到了这本早期著作,并将其翻译为其它语言付梓。多年来,我的父亲一直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他认为在英语版本中,这本书需要一些修改,因为原书是以欧洲大陆为视角而写就的。他同时还意识到,这本书的整体内容或许已显得有些陈旧。然而最终,他同意该书大部分内容仍然按原样出版,而他只进行了少许改动。在他去世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利昂妮就将该书完成并出版了。对我父亲来说,为儿童写作是一次颇有价值的经历,因为文字必须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这帮助他在日后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艺术的故事》。
战火停息之后,我的父母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伦敦,父亲重拾起他在瓦尔堡研究院的工作。此时的瓦尔堡研究院已经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在此数年之后,他被授予了终身教席,而不再需要每年都被重新聘用。在其它方面,我想我的父亲在那里的工作是愉快的,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成了我们家的密友。
他的薪酬依然微薄,实际上还达不到战前的水平。我并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当时他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今天英国的大学讲师一个星期的工资。一想到这一点,就令人不禁莞尔。尽管我的母亲必须勤俭持家,但我并不觉得微薄的收入困扰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我记得家里只捡便宜的猪肉买,上面尽是肥肉和软骨。父母的生活习惯也很节俭,他们从不吸烟,也不饮酒。我的父亲对珍馐美馔毫无兴趣,我想他最喜爱的食物就是面包了。而他们也从未想过拥有一台彩电或一辆汽车(我的父亲一直没有学开车,而且本来就无意于此)。我从未感到过生活的匮乏,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要么在免费的公立学校读书,要么拿到了名校的奖学金而去那里上学。我们一家享受英国的国家医疗保健服务,受益颇多。在战争开始后的好几年里,我们家一年只能享受一次为期两周的假期,对此都已习以为常。直到1948年,我才来到瑞士,开始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
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的父亲与卡尔·波普尔曾有过数面之缘。烽火硝烟中,波普尔和他的妻子亨妮在新西兰躲避战乱,并完成了其著作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本该在英国出版,但当时的通讯十分不便。为了帮助波普尔,父亲用微缩胶片编辑此书。当波普尔于1946年开始供职于伦敦经济学院时,他们便开始频繁往来,并成为挚友。
《艺术的故事》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也让我的父亲名声大噪。在已出版的他与迪迪耶·艾里彭[Didier Eribon]的“对话录”中,详细记录了此书的诞生经过(pp.62-6)。因此关于这本书,我已无需太多赘言。他能够完成此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一位好友的坚持,此人名叫贝拉·霍洛维兹[Bela Horowiz],是费顿出版社的创始人。二战前夕,父亲已用德语写出了部分章节,但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无暇遣笔,并对此书心灰意冷。霍洛维茨将已写好的那几章的英文版拿给他的小女儿汉娜看。汉娜时年16岁,她建议他的父亲将此书出版。为此,霍洛维茨给了我的父亲50英镑的预付款,并一再敦促他写完这本书。父亲以无法完成为由推脱此事,但霍洛维茨却不肯拿回那50英镑。父亲为此事反复踌躇。因为当他回到瓦尔堡研究院时,时任院长德国人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 Saxl]告诫他,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儿童读物上,而是应该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扎克斯尔的突然辞世让父亲感到十分难过,但对他而言,这未尝不是一次命运的转机。父亲总是对霍洛维茨,尤其是汉娜心怀谢意,尽管不得不承认,霍洛维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用50英镑从我父亲手里买走了版权,幸好经波普尔的劝说,父亲转而要求抽取版税提成。可想而知,霍洛维茨在这本书上赚的比我父亲要多得多。不过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非常感谢霍洛维茨,没有他的投资,这本书就不会问世。父亲常说“我用黄油做饭”[“Ich koch mit Butter”],在战后的艰辛岁月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他对霍洛维茨手下的图书设计师路德维希·戈德沙依德[Ludwig Goldscheider]博士也是敬重有加,与他的合作令父亲感到十分愉快。
正像父亲所回忆的那样,《艺术的故事》令他声名鹊起,并让他很快就成为牛津大学的斯莱德艺术教授。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为期三年的讲座。从此之后,他平步青云,并于1959年开始担任瓦尔堡研究院的院长,直至退休方才卸任,但仍担任着其它的一些职位。与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所不同的是,父亲对于教学工作乐在其中,从未离开过讲台;也没有荒废过管理工作,对此他尤为重视。1976年,父亲在退休之际提到,他从未休过学术假期,也没有申请过研究补助金。他为瓦尔堡研究院鞠躬尽瘁,尽忠职守。
在这里,我并非要对父亲的工作或学术生涯进行简要的介绍。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的所有成就与活动几乎就是他参与公共活动的记录。《艺术的故事》一书现今已被翻译为近40种文字,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那之前,我只是一名清贫的学者,和外界没有联系,在工作中也默默无闻。”而在此之后,他说:“人们都认识我,知道我是《艺术的故事》的作者,但他们都不知道我还是一名学者。另一方面,我的许多同事都没读过这本书。他们或许看过我关于普桑或莱昂纳多的论文,却对那本书视而不见。这可真是一种奇妙的双面人生。”尽管父亲还出版过很多其它著作,并发表过很多论文,但真正让他从经济上获益的,还是这本《艺术的故事》,以及在他去世之后所出版的英文版《写给儿童的世界史》,尽管后者的知名度要小得多。他的后半生也因此而过得富足惬意,但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行文至此,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他的性格和业余爱好。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据我所知,他与他的父亲非常亲近,而他的母亲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且魅力过人,性格开朗。她主持家事,必定对我父亲的早年生活影响至深。父亲曾向我提及,他非常喜欢有年龄较大的妇女陪伴于左右。我可以证实这一点,而这与他的母亲必定有很大的关系。在其一生当中,父亲有少数几位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他与她们经常联系,即便她们身在异国也是如此。我想,公允而论,在他所亲近和乐于相处的人当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而且通常比他年长。父亲的性格较为腼腆,喜欢和温文尔雅的人相处。然而,他之所以更喜欢女性,尤其是年长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厌恶那些醉心于权力之辈,以及喜欢摆布他人的家伙。对此,我还要再多费笔墨,略述一二。
父亲的姐姐蒂雅[Dea]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当时父亲对她非常爱戴和钦慕,而她的脾气却喜怒无常,对于她的怒火,父亲感到害怕和不安,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他小心翼翼地与蒂雅相处,却与另一位姐姐丽思伯兹非常要好,也更为亲近。丽思伯兹终生未婚,这或许让她与父亲的关系显得更为敏感。不仅于此,他们在瑞典的时光也是一起度过的,蒂雅也在瑞典呆了一小段时间,但没和他们住在一起。
丽思伯兹为人非常谦逊。她在语言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我的父亲对此激赏不已。而丽思伯兹对我的父亲也是敬慕有加。她将父亲的一些著作翻译成德语,或是从德语翻译为其它语言。在父亲看来,她的这些翻译无人能及。丽思伯兹一生坎坷多舛,我想我的父亲对于她的不幸也略感歉疚。在三个兄弟姐妹中,丽思伯兹排行第二,她和她年迈的父母同住,如同他们的保姆。尽管她在音乐方面并非没有造诣,但在某种程度上,她被视为天资最差的家庭成员。客观的来说,这一看法十分可笑。
在我父亲的一生当中,音乐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与视觉艺术相比,他认为自己可能对音乐的反应更为本能。我的祖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其乐感罕有人匹,弹琴能够带给她无比的欢愉。她是莱谢蒂茨基[Leschetitzky]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助手;而莱谢蒂茨基又师从于车尔尼;车尔尼的老师是贝多芬,后者又是莫扎特的门生。与此同时,我父亲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是我祖母的学生。如果没有二战的爆发,那么我母亲很有可能成为一名职业钢琴演奏家。我们家的客厅里放着我母亲的三角钢琴,她时常弹奏,有时能弹上好几个小时,几乎终生不辍。
父亲与母亲的邂逅是一段值得重提的佳话。起初,母亲跟随我的祖母学习钢琴。祖母生性善良慈爱。不久,她就关心起这名年轻的学生,询问她是谁陪着她来到维也纳。当她获知我母亲是孤身一人之后,她又问她生活状况如何,是否游览了这里的名胜。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她便叫来自己的儿子,并让他陪着这位年轻的女士在城市里四处看看。当我父亲来到母亲的房间时,按照当时的习惯,他像军人那样,先用脚后跟轻叩地板,然后向母亲鞠躬致意。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母亲,但我母亲惊讶地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并不陌生。就在几天之前的晚上,母亲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二楼的座位上听音乐,这些座位是专门为前来享受音乐的人而留下的。音乐研习者可以带着乐谱,在这里跟唱。不一会儿,她注意到,在她的身边坐着一名年轻人,在她唱谱的时候,仔细端详着她的乐谱。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终其一生,我的父亲有时会想不起早年旧识的名字和面容,但从未忘记过那个人写了什么书。
我祖母的好友几乎都是音乐家。我想其中和祖母最要好的一位,要数小提琴家大师阿道夫·布施[Adolf Busch]。据我料想,正是我的祖母向布施介绍认识了同样伟大的钢琴家鲁迪·塞尔金[Rudi Serkin]。后来塞尔金成了布施的乘龙快婿,并一直在舞台上保持合作。他们一家与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并不太熟悉,但他们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这位伟大的指挥家,这成了让他们引以为豪的一件往事。
当我长大之后我认识到,在父母眼中,音乐就如同宗教一般神圣和重要,而且对于我的祖父母来说,很可能同样如此。当然,他们自己并不会这么说,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音乐要比宗教重要得多。布施、塞尔金、托斯卡尼尼、卡萨尔斯[Casals]——他们将这些音乐家奉若神明,这些人的唱片被单独摆放在一起。父母经常播放他们的音乐,满怀敬意地一再聆听。补充一句,这份名单并未结束,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也加入其中。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某一天里他听了一会儿音乐,那么他就会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对他来说,“音乐”意味着西方的古典传统。他常常提到,西方文明所发现的和声学系统,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实际上,他的欣赏范围较为狭窄。他的姐姐蒂雅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师从于阿道夫·布施,并曾在托斯卡尼尼手下演奏。她在维也纳的先锋派音乐家圈子里颇有人缘,还首次公开演奏了阿尔班·伯格[Alban Berg]的小提琴协奏曲。我母亲的欣赏口味则宽泛得多。父亲在晚年只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感兴趣。他也欣赏巴赫,但在当时,海顿之前的音乐在维也纳并不怎么受欢迎,或许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我想在今天,我的父母所说的“聆听音乐”这回事,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甚至能够理解了。音乐可以是轻松愉快的,甚至诙谐幽默也无伤大雅,但聆听音乐却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参加一场音乐会必须郑重其事,依礼行事。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人们要排队进入艺术家的休息室,向其道贺。人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簇拥在艺术家周围。他们将艺术家视为挚友,甚至奉为偶像。我的父母会常常打开收音机或留声机,倾听从那里面流淌出的旋律。音乐一旦开始,就不可被打断。电话听筒被搁在一边,任何人进入房间后,要么安静地坐下欣赏音乐,要么离开此地。在他们看来,把音乐当成烘托气氛的道具,不仅是焚琴煮鹤之举,甚至是对神明的亵渎,是对作曲家和演奏者失礼的野蛮行径。因此,我的父母会拒绝在播放背景音乐的餐厅里用餐。要是某人声称雅好音乐,却在音乐演奏时心有旁骛,那么此人就会被视为粗鄙之徒。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父亲自己几乎不怎么演奏音乐。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大提琴,他的大提琴箱就放在我们家的三角钢琴下面。但他拉得并不在行。首先,他显得有些笨手笨脚,除了能用双手变出肥皂泡逗孩子们开心之外,他就再也玩不出别的什么把戏了。其次,对于一般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来说,他的家庭以及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音乐标准显得高不可攀。要是他真把拉大提琴当回事儿,那么每天必须要练习至少一个小时,而对他来说,这是做不到的。在伦敦的时候,蒂雅经常来我们家,与我的母亲演奏室内乐,有时她让我的父亲也加入其中,来一段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三重奏,但他并未乐在其中。我想,他是觉得这有些丢脸,对此我深表同情。
从父亲给我的职业建议中,我觉得可以窥见他对音乐的一些看法。他经常说,有两个职业他不建议我去从事。首先,他不想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乐评家。在他看来,乐评家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人,只会信口开河。然而,另一个他不让我从事的职业,却是音乐家。对此,他的理由截然相反:他认为职业音乐家的生活太过艰苦和紧张,这会使人耗尽精力,无暇去做别的事情。当然,如果我的确具有音乐天赋,他也不会拦着我,不过幸好,这个问题从未出现过。
我的父亲为人温文尔雅,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非会偶尔动怒之外,平常他并不表露自己的情感,真不知道那些和他并不熟悉的人该如何去评判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会经常开一些玩笑。但他的幽默里总是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没有开过那种直白粗俗的玩笑。他笑得并不多,也不会放声大笑。
父亲对人文价值倍加关切,我想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憎恶惨无人道的暴行,即便是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内容,他也难以容忍。不仅于此,他还笃信于人类的平等,尽管他没有就这一点而高谈阔论。我的言下之意是,他只关注于人们的内在品质,对他来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毫无价值。父亲最在意的是人的心智。我记得,在他谒见了女王陛下之后,他谈论起女王,其措辞如同在描述任何一个寻常之人。尽管他丝毫不在乎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过我想,有人会指责他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慢。但在他看来,这种清高和傲慢正是对某种事物的尊重,这种事物要比其它事物更有价值,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比滚石乐队的歌曲更胜一筹一样。
我的父亲不愿看到人们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常说,在他年轻的时候,贫穷是一种真切的感受。一个不再有穷人的社会,当然是美好的。对于财富,他同样不以为然。他并不宣扬革命,但我相信,在他眼里,坐拥大量的财富是愚蠢的。令一些来访者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位艺术“专家”的家里,墙上竟然没有一幅值钱的画。他认为,如果一件艺术品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那么就应该将它公之于众,最好是放在公共博物馆里。他会欣然前往,一次又一次地到博物馆去观赏它,而不是整天和它生活在一起。在我眼里,他对金钱和财富的看法与一名得道高僧或基督教修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诚然,父亲对金钱的看法的确与众不同。他认为金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话题,对于那么多人喜欢谈论它,父亲感到不可思议。他绝不会在钱财方面浪费时间。他从不买股票,也不做其它的投资,只会把他的所有收入都存入银行。对于那些千方百计想要逃税的做法,他嗤之以鼻。他认为,税收终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诸如在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他对金钱的态度在一桩小事中表露无遗。有一次,他和出版商订立了一份新的合约。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去看望他,并提及此事,询问他商谈结果如何。当父亲告诉她结果之后,我的女儿大吃一惊。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和别人讨价还价,而是任由出版商宰割。当女儿劝慰他时,他说:“那人可真是个财迷,就随他去吧!”
要是有人因窘困而有求于我父亲,那么他会给人留下很慷慨的印象。但我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很乐善好施。我们之间从不谈钱的事儿,因为 我知道,但凡我需要什么,他都会解囊相助,并且相信我确有所需。我想,他对我的母亲也一定是照此行事。
除了钱财之外,我的父亲对其它某些事情也漠不关心。例如,他对运动就毫无兴趣。他会偶尔和孩子们一起游戏,但我想,在他看来,运动一定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在上学的时候,我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母亲很支持我这样做,而父亲则默不作声。我想他很难体会到那些喜欢观看比赛,或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感受。一般而论,父亲对体育竞技没什么兴趣。他总是喜欢念叨一件旧事,但我怀疑这件事是否属实。有一次,沙特国王前去拜访维多利亚女王,女王便邀请他一同去看赛马。父亲说,他弄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看点,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匹马会第一个冲过终点。
关于宗教,他认为在艺术、建筑和音乐方面,它向世人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但在其它方面,他赞同伏尔泰的观点,认为宗教有害无益。对于自己的葬礼,他的唯一要求是千万别请神职人员参加。
他对政治也不太关注,尽管是出于别的原因。我已经提到过,他憎恶暴力,对于那些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者,他避之犹恐不及。因此,他对政治家颇不以为然,尽管他也承认,政客当中亦有良莠之别。
他对政治的反感有两个层面。首先,他对法西斯主义者深恶痛绝。在这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几乎绝口不提,如果有人对他们稍加袒护,那么父亲便会勃然大怒。要是有人来我们家做客,滔滔不绝的谈论他们所犯下的暴行,那么父亲就会如坐针毡。因此,他从不会直接提及那些杀害了我们家亲戚的纳粹分子。他也拒绝踏上任何一片被独裁者所统治的土地。
相对而言,英国的政治生活较为平和。在这个层面上,父亲还是留心于国内政治的,但仍然宁愿置身于事外。显然,至少在他的晚年,他就再也不想去投票了。我相信,他对穷人的同情促使他从不把票投给保守党。他很少提到他支持哪个党派,但我母亲总是支持自由党,我想父亲应该也是如此。
他认为,英国社会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便是很少有人热心于政治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或是被它们所左右。这些事物只会干扰平静的生活,而人们本该将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去,比如艺术和音乐,当然并不仅止于此。他喜爱大自然,喜欢到乡间或是伦敦的公园里漫步,总是乘兴而去,尽兴而归。他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予以肯定。他认为,科学为人类所带来的福祉,远大于它所造成的危害,在科学领域里,人类得以尽其所能,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展现他们的才华。对于文学,父亲或许倒不那么热衷,当然也不会去翻览现代小说。但他在阅读欧洲古典文学方面非常在行,并喜欢将它们默志于心。他热爱意大利。
在个人生活习惯上,父亲是一个保守的人,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三件套,或是披上睡衣。在这方面,他完全是个老古董。但在精神层面上,他是一位真正的自由的思想者。他打趣的说,他这个院长当的就像一位“万事管”。为了确保在一天当中,至少有一段时间能让自己专心致志地思考,他在每天早餐之后都会花上很长时间洗个澡,而我的母亲则会把他的衣服准备好了放在外面。这样,他就可以不用为穿什么衣服而费心了。总的来说,父亲的性格有一点悲观,但绝不愤世嫉俗。医学的进步缓解了人类的病痛,延长了生命的期限,但并没能让人类变得更加睿智。当我们急于摒除我们的传统中那些愚昧的因素时,也匆忙地抛弃了种种传统的价值。因此,这个世界究竟是在变得更加美好,还是正在滑向堕落,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但至少,我们仍旧可以去聆听海顿与莫扎特的美妙音乐。
注释请参考E.H.贡布里希《一生的兴趣——与迪迪耶·艾里彭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对话》(泰晤士与哈德森出版社,伦敦,1993),1991年首版于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