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实验——评罗发辉的作品
发起人:shirley_88 回复数:0
浏览数:1125
最后更新:2010/12/27 10:48:15 by shirley_88
转自 查常平的艺术空间

本文发表于2010年12期《上层》
深度的欲望、深度的伤害、深度推进的极限实验。
通过这样的文字,我们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实验场为罗发辉可以找到准确的定位。对于他而言,人的深度欲望,同都市文明的生存状态相关;人的深度伤害,同人际关系的欲望追逐相关;艺术的深度推进,同当代艺术的典范图式的寻求相关。但是,艺术家围绕某种主题或选择一种媒材的极限实验,依然应当是当代艺术中出现经典图式的深层原因与法则之一。罗发辉的油画创作,为此给出了个案。
1.写意性玫瑰的原初图式
仅以花系列为例,罗发辉总是在不断往返中推进自己的艺术图式。花与女人体两种元素,最初出现在他的油画《姑娘们》(1998)、《女孩·花》系列(1999)中。他从前者脸上的玫瑰花芯、后者身体的变异造型中反复提炼推演,形成后来的花系列与人体系列。《玫瑰1999》、《玫瑰2000》、《玫瑰2001》,明显带着写实性的痕迹,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艺术。其花芯开始的枯萎凋烂意象,作为对某种长期受到欲望侵害的女人阴部的象征,揭示出我们这个肉欲时代的深度。之后的系列《玫瑰2002》、《玫瑰2003》、《玫瑰2004》、《玫瑰2005》、《大花2003》、《大花2004》、《大花2005》、《大花2006》,写意性日益强化。


《玫瑰2002》,标志着罗发辉在艺术上从写实性转向写意性的一个图式转折时期。他在其中对大红、紫红、绿色、浅灰色所能够表现的玫瑰图式展开实验,但在总体上,它们都不属于现实中的玫瑰而是一种从没落到腐朽的充满欲望的主观图式。艺术家着力于花芯、花瓣、花所置放的背景的色彩关系,以此传达出现代人丰富的否定性的人性欲望。它们如同一张张要把人吞没的欲望之口,似乎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满足,既期待着人的强烈进入,又没有能力把他彻底征服。这些写意性玫瑰欲望图式,作为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种原初图式,标示着罗发辉作为艺术家的成熟。此时,不少评论家也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他的作品,用意象、欲望、变异、畸形这些术语来形容它们的特征。正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原初图式,他随后至今便进入了一个系统性的创作状态。在此意义上,他1996年以《荒原上的树》参加上海双年展,只不过赋予一个艺术家确立其外在身份以可能性。即便后来也举办了几次个展,罗发辉作为艺术家内在身份的确定,以其原初图式的最后出现为开端,却经历了六年漫长岁月的探索。今天,在展场和市场上成功太早的人,如果没有对个体性原初图式的执着追求,最后很可能和21世纪初的中国艺术史毫无关系,他最多称得上是一个艺术上的财主而不是艺术家。
2.否定性欲望的极限描绘
和个体性原初图式一起,人类性的艺术观念的表达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内在特征。在罗发辉的艺术书写中,除了写意性的玫瑰溃烂图式外,便是他对当代人的否定性欲望这一观念的极限描绘,其结果形成了系列的《玫瑰2003》、《玫瑰2004》、《玫瑰2005》。评论家仅仅把罗发辉的这个系列总结为深度欲望的表达,还是没有刻画其艺术观念上的独特性,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深度欲望。因为,我们从周春芽2005年创作的《桃花风景》系列里面,也能够见到这种对欲望深度的表现。不过,罗发辉的玫瑰系列,经历了从写实性的玫瑰自然图式到写意性的玫瑰溃烂图式再到意象性的玫瑰纵欲图式。,而且,这种纵欲图式,似乎要把人带向毁灭的地步。我们从中再也看不到自然玫瑰的凋谢痕迹,我们只能见到一朵朵纵欲过度的玫瑰开放再开放,一种毫无羞耻感的玫瑰意象,一种以展示放纵的欲望为美学的意象玫瑰。它们只有欲感而无爱感、只有死亡而无生机、只有虚假而无真诚、只有接受而无施与、只有绝望而无希望、只有颓废而无复兴、只有发泄而无收敛、只有消耗而无生产、只有无奈而无反抗、只有消沉而无崛起、只有溃烂的花芯而无完整的花瓣,只有殷殷的红色、鬼怪的绿色、浅浅的灰色彼此渗染的混沌效果而无层次分明的相互分裂的解构。凡是能够唤起艺术爱者否定性心理意象的词语,我们都能够用来描述它们。所有这些以否定性欲望为特征的艺术观念,愈到后来愈得到肆无忌惮的强化,到《玫瑰2005》系列演变为如同末日来临前的片断云彩,玫瑰的造型完全屈从于艺术家的主观需要图式,除了花芯周围的殷红能够帮助艺术爱者辨别其为何种花的图式外,其本身仿佛正在隐约塌陷的黑洞。我们甚至可以质问:如果罗发辉继续这样画下去,它们会不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心理伤害?难怪早在2003年,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个系列的艺术实验。这或许是为了求得艺术创作的心理平衡。
系列《大花2003》、《大花2004》是玫瑰系列的放大版。《大花2004 N.3》,为其作为否定性欲望图式的玫瑰系列在主题关怀方面做了总结。一朵只有一片红色的花瓣欣然开放的花,一根红色的如勃起的男性生殖器的花芯,从花瓣上方插入、静静地躺在花瓣上,背景为黑灰色。它不可能唤起艺术爱者美好的对性爱的回忆感觉,相反,它使人产生一种猥亵的、令人厌恶的激情体验,恰当地隐喻着当代社会广泛盛行的淫乱风习。罗发辉的全部玫瑰系列,始终都属于某种匿名的受伤害的欲望图式。或者说,它们不只是一种欲望的溃烂图式,而且是一种欲望的伤害图式。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从他的艺术作品的图式走向看,我们可以说与纯粹俗世化的中国当代都市文明相关。
俗世化的中国当代都市文明,区别于当代欧洲-北美世俗化的基督教都市文明以及日本神道教的都市文明。世俗化相对于神圣化而言,是神圣世界的回光反照。在其中生存的人,无论怎样不道德,都存在着一个道德的、精神的底线。俗世化的中国当代都市文明,纯粹以物质主义和肉身主义为意识形态,其中没有任何神圣化的东西。关于这点,只要把马克思所批判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虚伪和我们今天满街盛行的造假等现象相比较便可以明白。

《大花2005》、《大花2006》出现在城市上空。花与城市的构图关系,总是前者压抑着后者的上下关系,大花构成了城市的苍穹、边界,但并不是都市人仰望的星空世界,而是某种灾难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预表。另一方面,大花的如此欲望溃烂的构形,它为什么像乌云一样悬浮在城市空中,这一切都应当和城市所居住的人相关。任何观众初见这样的大花作品,都会自然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广岛、长崎上空原子弹爆炸后升腾形成的蘑菇云景观。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多了一份欲望的色彩。艺术家在这里挪用城市建筑物,只是想对他的花系列作品中内含的否定性欲望图式的根源做出回答。这是他在大花系列中依然仅仅把城市建筑当作低处的背景或前景构图来处理的原因,更是他在画面中依然选择意象性的大花为主体图式的理由。罗发辉今后和城市相关大花系列的发展,如果要在否定性的欲望图式之外开出新的图式,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对艺术和都市文明、尤其是其中的人的生命情感关系的感受思考。一种肯定性的、健康的欲望图式,应当说预示着他开新的可能性。因为,《大花2005》、《大花2006》中的不少作品,已经显现出这样的因素。就我们所见的上述作品而言,他开始在作品画面上注重利用光的效果,即使在那些以城市之夜为背景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一个艺术家用六年的时间来画一朵受伤的玫瑰,可见其中内含着怎样恒忍的信心与执着。他的《云雨2005》系列、《云雨》(2006),其意象元素最早出现在《移动的云》(1993)、《绵延的山》(1995)、《大地上的两个人》(1996),更是花系列的一个平行推进,只是借助云来烘托受伤的花的造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看到随着自然规律而开放凋零的玫瑰。至于受到伤害的花朵,本是艺术家个人对社会伤害的投射。因此,对伤害之物的关注,离不开对受伤害者的关注。这或许是罗发辉从其早期作品中演绎出受伤的人体系列的原因之一:《溃·艳》系列(2005)、《无题》系列(2005)、《两个人》系列(2005/06)。
3.深度伤害的死亡安息
罗氏的花系列,其主题关怀可以用“欲望的深度”来描述。他以《溃·艳》、《无题》、《两个人》命名的人体系列沿用了玫瑰溃烂图式的构成笔法,而《尤物之迷》系列(2005)却是借用花系列的背景造型手法,但它们都和“欲望的深度”无关,属于一种受伤与安息的否定性情感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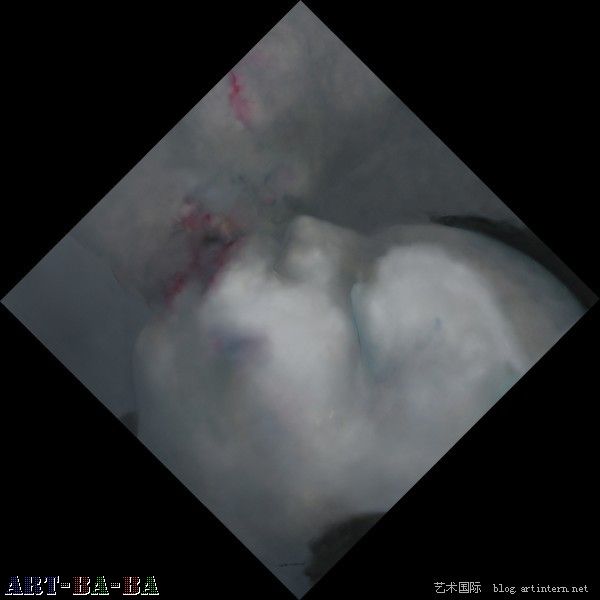
在和花系列类比的意义上,《溃·艳》、《无题》、《两个人》所呈现的主题,乃是人受伤害的深度,或者说是深度的伤害。《溃·艳》择取刚刚离开世界的死者的头部,或为秃顶,或前半部分头发脱落,从前的玫瑰溃烂图在这里转换为嘴角或脸部的受伤溃烂图,即人体局部溃烂图。他们大多无可奈何地躺在灰濛濛的云层中,一束柔和的白色光照射在脸上。《无题》应当说是《溃·艳》的缩小版。《两个人》系列,似乎是要对这种伤害根源提出反省:有的在静默的守候中受伤(《两个人 2005 No.3》),有的在抱怨的梦境中受伤(《两个人 2005 No.6》),有的在冷漠的同床中受伤(No.2),有的在肉欲的满足中受伤(No.3),有的在情爱的戏虐中受伤(No.5),有的在相爱的接吻中受伤(No.6)。人人关系,不再是互相造就、彼此建立而是共同损伤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主题关怀上,《两个人》中的No.4( 2006)应当纳入《尤物之迷》系列。艺术家将它归入其中,或许是为了说明人人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伤害与受伤的关系,至少在人离开世界后的瞬间还有相互共在安息的关系。人死后的安息共在,正好构成《尤物之迷》探索的主题。

120x120cm.尤物2006No2-Oil-Picting.
不过,任何伟大的艺术家,都不会甘心于单一主题的极限实验。《尤物之迷》、《母子》系列(2006),是罗发辉游览了梵蒂冈的圣像雕塑后受到启发完成的作品。其中的人体形态,平躺在白云似的裹尸布上,头部或侧或立或隐,身体肥满具有弹性,四肢轻松自然。它们不再给人受伤害的感觉,而是充满死亡般的肃穆。它们作为没有灵魂的身体,只具有生命的外形与轨迹。换言之,即使在这些刚刚死亡的身体上,依然内含着不可替代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乃至文化生命。它们是其主体的生命活动在历史时段上的见证。女人体以上下关系置放在画面中心,除了在象征生命欲望的性器官、嘴唇上略带一点红色,其余都是灰色。另一方面,光的明暗效果的处理,早已隐含在罗发辉城市大花系列对光的使用中,其所指为人类肯定性的生命情感。这些尤物,一类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异样美女,一类只有肉身的肥美而无智慧、无精神的美女。艺术家着力于描绘她们沉浸在欲念中并无邪荡的身体,或者说是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身体,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她们同自己的男人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在人间可以用初生的婴儿与母亲之间恬然无惧来形容(《母子2006 No.2》),即使是在脸部受伤的母亲那里也能够见到母爱的慈祥(《母子2006 No.1》)。在形式构成上,后者显然借鉴了花系列、《溃·艳》系列中的溃烂图式。不过,这种图式,已经开始从母亲转移到婴儿身上。血渗透在婴儿的全身肌肤,成为一种血液过剩图式。
4.推进模式的跌宕起伏
罗发辉在创作的时候,总是会同时在几个系列上展开。并且,对于相同的主题,他在完成了其他主题系列后又会返回来重新开始。虽然主题重复,但其艺术书写图式因为时间的沉淀往往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前,为了避免和太多画人的艺术家重复,他选择了能够自由表现人的心理需要的玫瑰意象,在变化中实现自我否定。他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性理解中,以简练的色彩呈现人心中否定性的纵欲或伤害的生命情感(《图像的伤害》系列,2008-9)。近两年的作品如《仙境》系列(2007-08)、《我的花园》系列(2009),他开始逐渐摆脱了这种溃烂图式,在呈现对象上从人的否定性的病态生命情感转向肯定性的康健生命情感。如何将此推向极限表达,艺术爱者只能在艺术家将来的实验书写中寻求答案,其关键的难题在于怎样从玫瑰溃烂图中蜕变出一种全新的原初图式。我们不知道这种转向是否和艺术家本人的生命处境相关,但是,毕竟人的生命情感具有丰富的多重向度。艺术家可以在其中的任何向度上开掘,不过,他更需要执着地在一个向度上跟进到底,直到无可表达乃至不能表达的深度。

本文发表于2010年12期《上层》
深度的欲望、深度的伤害、深度推进的极限实验。
通过这样的文字,我们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实验场为罗发辉可以找到准确的定位。对于他而言,人的深度欲望,同都市文明的生存状态相关;人的深度伤害,同人际关系的欲望追逐相关;艺术的深度推进,同当代艺术的典范图式的寻求相关。但是,艺术家围绕某种主题或选择一种媒材的极限实验,依然应当是当代艺术中出现经典图式的深层原因与法则之一。罗发辉的油画创作,为此给出了个案。
1.写意性玫瑰的原初图式
仅以花系列为例,罗发辉总是在不断往返中推进自己的艺术图式。花与女人体两种元素,最初出现在他的油画《姑娘们》(1998)、《女孩·花》系列(1999)中。他从前者脸上的玫瑰花芯、后者身体的变异造型中反复提炼推演,形成后来的花系列与人体系列。《玫瑰1999》、《玫瑰2000》、《玫瑰2001》,明显带着写实性的痕迹,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艺术。其花芯开始的枯萎凋烂意象,作为对某种长期受到欲望侵害的女人阴部的象征,揭示出我们这个肉欲时代的深度。之后的系列《玫瑰2002》、《玫瑰2003》、《玫瑰2004》、《玫瑰2005》、《大花2003》、《大花2004》、《大花2005》、《大花2006》,写意性日益强化。


《玫瑰2002》,标志着罗发辉在艺术上从写实性转向写意性的一个图式转折时期。他在其中对大红、紫红、绿色、浅灰色所能够表现的玫瑰图式展开实验,但在总体上,它们都不属于现实中的玫瑰而是一种从没落到腐朽的充满欲望的主观图式。艺术家着力于花芯、花瓣、花所置放的背景的色彩关系,以此传达出现代人丰富的否定性的人性欲望。它们如同一张张要把人吞没的欲望之口,似乎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满足,既期待着人的强烈进入,又没有能力把他彻底征服。这些写意性玫瑰欲望图式,作为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种原初图式,标示着罗发辉作为艺术家的成熟。此时,不少评论家也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他的作品,用意象、欲望、变异、畸形这些术语来形容它们的特征。正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原初图式,他随后至今便进入了一个系统性的创作状态。在此意义上,他1996年以《荒原上的树》参加上海双年展,只不过赋予一个艺术家确立其外在身份以可能性。即便后来也举办了几次个展,罗发辉作为艺术家内在身份的确定,以其原初图式的最后出现为开端,却经历了六年漫长岁月的探索。今天,在展场和市场上成功太早的人,如果没有对个体性原初图式的执着追求,最后很可能和21世纪初的中国艺术史毫无关系,他最多称得上是一个艺术上的财主而不是艺术家。
2.否定性欲望的极限描绘
和个体性原初图式一起,人类性的艺术观念的表达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内在特征。在罗发辉的艺术书写中,除了写意性的玫瑰溃烂图式外,便是他对当代人的否定性欲望这一观念的极限描绘,其结果形成了系列的《玫瑰2003》、《玫瑰2004》、《玫瑰2005》。评论家仅仅把罗发辉的这个系列总结为深度欲望的表达,还是没有刻画其艺术观念上的独特性,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深度欲望。因为,我们从周春芽2005年创作的《桃花风景》系列里面,也能够见到这种对欲望深度的表现。不过,罗发辉的玫瑰系列,经历了从写实性的玫瑰自然图式到写意性的玫瑰溃烂图式再到意象性的玫瑰纵欲图式。,而且,这种纵欲图式,似乎要把人带向毁灭的地步。我们从中再也看不到自然玫瑰的凋谢痕迹,我们只能见到一朵朵纵欲过度的玫瑰开放再开放,一种毫无羞耻感的玫瑰意象,一种以展示放纵的欲望为美学的意象玫瑰。它们只有欲感而无爱感、只有死亡而无生机、只有虚假而无真诚、只有接受而无施与、只有绝望而无希望、只有颓废而无复兴、只有发泄而无收敛、只有消耗而无生产、只有无奈而无反抗、只有消沉而无崛起、只有溃烂的花芯而无完整的花瓣,只有殷殷的红色、鬼怪的绿色、浅浅的灰色彼此渗染的混沌效果而无层次分明的相互分裂的解构。凡是能够唤起艺术爱者否定性心理意象的词语,我们都能够用来描述它们。所有这些以否定性欲望为特征的艺术观念,愈到后来愈得到肆无忌惮的强化,到《玫瑰2005》系列演变为如同末日来临前的片断云彩,玫瑰的造型完全屈从于艺术家的主观需要图式,除了花芯周围的殷红能够帮助艺术爱者辨别其为何种花的图式外,其本身仿佛正在隐约塌陷的黑洞。我们甚至可以质问:如果罗发辉继续这样画下去,它们会不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心理伤害?难怪早在2003年,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个系列的艺术实验。这或许是为了求得艺术创作的心理平衡。
系列《大花2003》、《大花2004》是玫瑰系列的放大版。《大花2004 N.3》,为其作为否定性欲望图式的玫瑰系列在主题关怀方面做了总结。一朵只有一片红色的花瓣欣然开放的花,一根红色的如勃起的男性生殖器的花芯,从花瓣上方插入、静静地躺在花瓣上,背景为黑灰色。它不可能唤起艺术爱者美好的对性爱的回忆感觉,相反,它使人产生一种猥亵的、令人厌恶的激情体验,恰当地隐喻着当代社会广泛盛行的淫乱风习。罗发辉的全部玫瑰系列,始终都属于某种匿名的受伤害的欲望图式。或者说,它们不只是一种欲望的溃烂图式,而且是一种欲望的伤害图式。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从他的艺术作品的图式走向看,我们可以说与纯粹俗世化的中国当代都市文明相关。
俗世化的中国当代都市文明,区别于当代欧洲-北美世俗化的基督教都市文明以及日本神道教的都市文明。世俗化相对于神圣化而言,是神圣世界的回光反照。在其中生存的人,无论怎样不道德,都存在着一个道德的、精神的底线。俗世化的中国当代都市文明,纯粹以物质主义和肉身主义为意识形态,其中没有任何神圣化的东西。关于这点,只要把马克思所批判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虚伪和我们今天满街盛行的造假等现象相比较便可以明白。

《大花2005》、《大花2006》出现在城市上空。花与城市的构图关系,总是前者压抑着后者的上下关系,大花构成了城市的苍穹、边界,但并不是都市人仰望的星空世界,而是某种灾难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预表。另一方面,大花的如此欲望溃烂的构形,它为什么像乌云一样悬浮在城市空中,这一切都应当和城市所居住的人相关。任何观众初见这样的大花作品,都会自然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广岛、长崎上空原子弹爆炸后升腾形成的蘑菇云景观。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多了一份欲望的色彩。艺术家在这里挪用城市建筑物,只是想对他的花系列作品中内含的否定性欲望图式的根源做出回答。这是他在大花系列中依然仅仅把城市建筑当作低处的背景或前景构图来处理的原因,更是他在画面中依然选择意象性的大花为主体图式的理由。罗发辉今后和城市相关大花系列的发展,如果要在否定性的欲望图式之外开出新的图式,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对艺术和都市文明、尤其是其中的人的生命情感关系的感受思考。一种肯定性的、健康的欲望图式,应当说预示着他开新的可能性。因为,《大花2005》、《大花2006》中的不少作品,已经显现出这样的因素。就我们所见的上述作品而言,他开始在作品画面上注重利用光的效果,即使在那些以城市之夜为背景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一个艺术家用六年的时间来画一朵受伤的玫瑰,可见其中内含着怎样恒忍的信心与执着。他的《云雨2005》系列、《云雨》(2006),其意象元素最早出现在《移动的云》(1993)、《绵延的山》(1995)、《大地上的两个人》(1996),更是花系列的一个平行推进,只是借助云来烘托受伤的花的造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看到随着自然规律而开放凋零的玫瑰。至于受到伤害的花朵,本是艺术家个人对社会伤害的投射。因此,对伤害之物的关注,离不开对受伤害者的关注。这或许是罗发辉从其早期作品中演绎出受伤的人体系列的原因之一:《溃·艳》系列(2005)、《无题》系列(2005)、《两个人》系列(2005/06)。
3.深度伤害的死亡安息
罗氏的花系列,其主题关怀可以用“欲望的深度”来描述。他以《溃·艳》、《无题》、《两个人》命名的人体系列沿用了玫瑰溃烂图式的构成笔法,而《尤物之迷》系列(2005)却是借用花系列的背景造型手法,但它们都和“欲望的深度”无关,属于一种受伤与安息的否定性情感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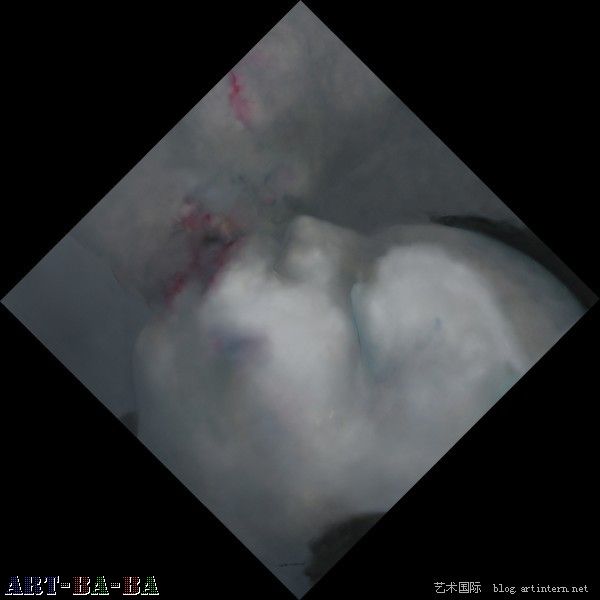
在和花系列类比的意义上,《溃·艳》、《无题》、《两个人》所呈现的主题,乃是人受伤害的深度,或者说是深度的伤害。《溃·艳》择取刚刚离开世界的死者的头部,或为秃顶,或前半部分头发脱落,从前的玫瑰溃烂图在这里转换为嘴角或脸部的受伤溃烂图,即人体局部溃烂图。他们大多无可奈何地躺在灰濛濛的云层中,一束柔和的白色光照射在脸上。《无题》应当说是《溃·艳》的缩小版。《两个人》系列,似乎是要对这种伤害根源提出反省:有的在静默的守候中受伤(《两个人 2005 No.3》),有的在抱怨的梦境中受伤(《两个人 2005 No.6》),有的在冷漠的同床中受伤(No.2),有的在肉欲的满足中受伤(No.3),有的在情爱的戏虐中受伤(No.5),有的在相爱的接吻中受伤(No.6)。人人关系,不再是互相造就、彼此建立而是共同损伤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主题关怀上,《两个人》中的No.4( 2006)应当纳入《尤物之迷》系列。艺术家将它归入其中,或许是为了说明人人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伤害与受伤的关系,至少在人离开世界后的瞬间还有相互共在安息的关系。人死后的安息共在,正好构成《尤物之迷》探索的主题。

120x120cm.尤物2006No2-Oil-Picting.
不过,任何伟大的艺术家,都不会甘心于单一主题的极限实验。《尤物之迷》、《母子》系列(2006),是罗发辉游览了梵蒂冈的圣像雕塑后受到启发完成的作品。其中的人体形态,平躺在白云似的裹尸布上,头部或侧或立或隐,身体肥满具有弹性,四肢轻松自然。它们不再给人受伤害的感觉,而是充满死亡般的肃穆。它们作为没有灵魂的身体,只具有生命的外形与轨迹。换言之,即使在这些刚刚死亡的身体上,依然内含着不可替代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乃至文化生命。它们是其主体的生命活动在历史时段上的见证。女人体以上下关系置放在画面中心,除了在象征生命欲望的性器官、嘴唇上略带一点红色,其余都是灰色。另一方面,光的明暗效果的处理,早已隐含在罗发辉城市大花系列对光的使用中,其所指为人类肯定性的生命情感。这些尤物,一类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异样美女,一类只有肉身的肥美而无智慧、无精神的美女。艺术家着力于描绘她们沉浸在欲念中并无邪荡的身体,或者说是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身体,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她们同自己的男人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在人间可以用初生的婴儿与母亲之间恬然无惧来形容(《母子2006 No.2》),即使是在脸部受伤的母亲那里也能够见到母爱的慈祥(《母子2006 No.1》)。在形式构成上,后者显然借鉴了花系列、《溃·艳》系列中的溃烂图式。不过,这种图式,已经开始从母亲转移到婴儿身上。血渗透在婴儿的全身肌肤,成为一种血液过剩图式。
4.推进模式的跌宕起伏
罗发辉在创作的时候,总是会同时在几个系列上展开。并且,对于相同的主题,他在完成了其他主题系列后又会返回来重新开始。虽然主题重复,但其艺术书写图式因为时间的沉淀往往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前,为了避免和太多画人的艺术家重复,他选择了能够自由表现人的心理需要的玫瑰意象,在变化中实现自我否定。他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性理解中,以简练的色彩呈现人心中否定性的纵欲或伤害的生命情感(《图像的伤害》系列,2008-9)。近两年的作品如《仙境》系列(2007-08)、《我的花园》系列(2009),他开始逐渐摆脱了这种溃烂图式,在呈现对象上从人的否定性的病态生命情感转向肯定性的康健生命情感。如何将此推向极限表达,艺术爱者只能在艺术家将来的实验书写中寻求答案,其关键的难题在于怎样从玫瑰溃烂图中蜕变出一种全新的原初图式。我们不知道这种转向是否和艺术家本人的生命处境相关,但是,毕竟人的生命情感具有丰富的多重向度。艺术家可以在其中的任何向度上开掘,不过,他更需要执着地在一个向度上跟进到底,直到无可表达乃至不能表达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