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界面 林子人
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一书的末尾,编著者留下了一个邮箱地址,邀请读者针对书中谈及之处提出问题或异议。该书从人类学家项飙的个人经验切入,探讨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诸多重要议题。
自2020年7月出版以来,《把自己作为方法》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读者来信也纷至杳来——它们来自年轻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插画师、财务工作者、管理咨询师、法官、地质工作者或城管保安等基层工作者,提出了诸多与人在当下社会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问题,包括知识人的自觉、亲密关系、城乡差异、互联网和大环境变迁带来的焦虑感等等。
日前,在“对话在继续——《把自己作为方法》一年后”的直播连线中,作者项飙、吴琦和该书的责任编辑罗丹妮选择了读者来信中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加以回应。在与读者的隔空对话中,项飙将《把自己作为方法》中的很多概念进行了再解读和再反思。
“把自己作为方法”不是关于自己,而是怎样通过自己去应对
将“把自己作为方法”作为标题和全书出发点,其实不是编著者的第一选择。罗丹妮说,最初项飙不是很愿意做个人化的经验分享,他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经验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中介。“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一说法可能会自然地引起一种担心——它是否会让我们盲目地放大自我,而止步于自我?
项飙认为,“自己”不是目的,而是通向另外一个目的的方法和途径,那个目的就是世界。这里所说的世界不是空泛的世界,而是“你能够看见,能够去分析、理解和思考,同时对你的行为和情绪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世界”。因此,“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不是关于自己,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自己去应对世界。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 吴琦 著
单向空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7
项飙注意到,当下年轻人对世界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的,这背后固然有生活阅历不够的原因,但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教育系统非常强调灌输“大的范畴/概念”,导致年轻人失去对自身经验的审视、描述和诉说的能力。他提醒我们,当概念被抽象化,非常容易导致观点的极端化,让我们对概念背后的历史来源、复杂关系失去兴趣,进而“几乎成了一种范畴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地缘政治等宏大叙事总是格外有兴趣,“为什么我们觉得宏大叙事比较有趣?正是因为它把过程简单化了,简单化之后好像变成了一个戏剧,有了一些角色在舞台上对抗……把戏剧化作为看待真实世界的方式后,你就好像觉得细节本身没有意思了。”项飚说。
关于如何将个人经验问题化、如何找到问题切入口的问题,项飙认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切入口就是“纠结”:“纠结是有矛盾,背后就有文章。”在他看来,难点不在于找到切入口,而在于如何把自我的纠结转化为一个问题,这是需要分析能力和一定的努力的——因为当我们遇到纠结时,逃避往往是下意识的反应。“不要去否认问题。我们的生存环境永远是不让人满意的,永远需要去反思、去推进、去调整。”
“‘自己’很不重要,但是‘自己’有一点价值,它能够作为方法——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这个是实实在在能够把握住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为什么比较重要呢?因为自己的经历总是在变化的,如果你把那个东西作为方法,我们的探索求知就会是一个很具体开放、同时又非常持续的过程。因为总会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新的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身边冒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项飙在直播中说。
农民工的艰辛是一回事,互联网大厂打工人的艰辛是另一回事
一位读者对《把自己作为方法》提出尖锐批评。TA认为,在一个自我不存在的时代以自己作为方法几乎是一种巨大的奢侈——对于00后或者更年轻的人来说,现实生活的处境非常艰辛,他们面临的巨大竞争导致他们能够享受的教育资源或许不如更年长的一辈,这让“谈自我”变成了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对话在继续——《把自己作为方法》一年后”的直播连线截图
项飙表示,我们需要更严谨地审视“艰辛”。从1990年代初开始,他的研究对象包括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东北的出国者,以及住在印度三线城市、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去学计算机的年轻人。他注意到“躺平”、“内卷”在过去一年里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词,但在他研究并因此熟悉起来的那些人群中,很少有人会用这样的语言。那些在工厂中打工的农民工不会用“内卷”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回应方式是写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比如在深圳打工的流水线工人许立志在诗集《铁月亮》里大量使用“铁”之意象,以此展现自身生命在巨大的铁机器下被打磨的切身痛楚。
我们因此需要意识到,艰辛对不同人群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这个艰难是指留守儿童的艰难,或者说是真正的打工人的艰难,可能是一回事;如果说是二线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前往一线城市,在互联网大厂里觉得有工作压力,可能是另一回事。”
项飙认为,我们需要对社交媒体上的某种主流话语保持警惕:“能上社交媒体说话的人,会觉得自己的感受是全世界的感受,或者是全中国的感受,听不到其他群体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会把一些问题放大,就会失真。”
关于“躺平”,项飙在后面的讨论中又提出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躺平”倡导的是退出无意义的竞争,回归最放松、最简单的自我。它是否能从一种话语转变为一种推动变革的实质性力量,或许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改变自己身边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和周围不同的群体产生联结,一起探索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乡绅的研究风格是做细致观察而非宏大判断
在直播连线中,项飙还回应了读者对“乡绅作为方法”的疑问。他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指出了乡绅在当下的存在可能性,“把自己的小世界弄清楚,对大的体制、权力也理解得很透。”
项飙以食物为例解释了乡绅的思考方式:从“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一个小切入口开始,探究食物在供应链中如何流转(是从小区便利店买的还是在城中心的超市买的)、在家庭中如何被消费(是全家人一起吃还是各吃各的)。如此这般,从对周边附近的观察开始一层层深入思考,将身边一件寻常事物与世界格局建立联系,这就是所谓乡绅的思考方式。
“‘乡绅’这个词描述的是我自己比较向往的研究风格,它所指的不是这个群体,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成为‘乡绅’这样的人。”在项飙看来,乡绅的研究风格要对事物做非常细致的观察,但不贸然做宏大的判断;要看具体的实践,不讲空道理,通过日常生活的道理来打动听者,启发新的思考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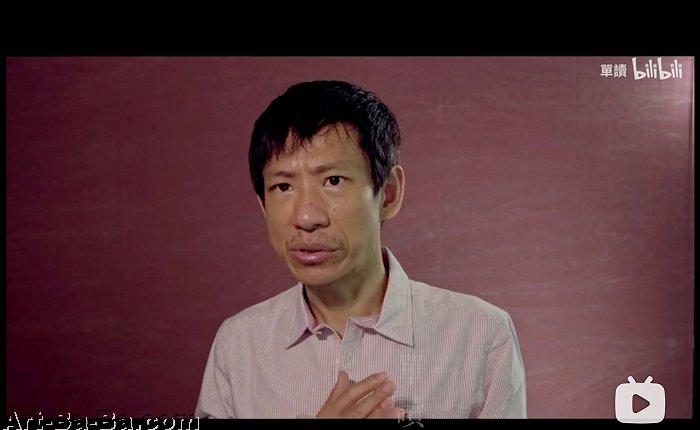
项飚,“对话在继续——《把自己作为方法》一年后”的直播连线截图
如果确实要将“乡绅”理解为某一种群体,项飙认为中小学老师在历史上就是一种“准乡绅”——他们在社区事务里扮演重要角色,对事物有更系统的观察,接受的资讯较多,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对下一代的成长肩负责任,他们的观察就带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探索。但遗憾的是,如今教师这个职业已经被扭曲,他们的主要目标和对地方社会的唯一考量是如何“往外送人”,有多少学生能上重点大学,“这是因为培养人这个事情本身变得非常功利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化。”
不平等能激发人的狼性,最终结果是没有真正的创新
针对许多读者来信中流露出的“教育焦虑”,项飙又回顾了书中提出的“人的再生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活在世上主要从事两件事,一是从事物质生产,二是从事人的再生产,即结婚生子,抚养下一代。长久以来,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在物质生产,人的再生产的存在意义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物质生产的附庸。
但当下在全球范围内,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关注被放在了人的再生产本身。“人的再生产不是为了经济服务,而是成为终极目的,人的再生产的具体过程不再是一个附属性的系统,而是越来越变成一个大家每天都要考虑的中心环节,而且它内部所涉及的利益极大,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项飙批评认为,现在教育的主要动力是出人头地,是“把你的同班同学刷下来,证明你比你的同龄人更好,今后就业时有更多机会,晋升时比别人强”。这种目的又和教育的等级化和商品逻辑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大学排名。然而,在大学排名的主要依据是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时,大学的“在地性”或者说它对所在城市的真实贡献是有些可疑的。
在项飙看来,大学的主要功能是给“寻找例外”的学生创造一个充分安全的、鼓励的环境。循规蹈矩地走主流路线固然安全且容易获得个人利益,但社会要如何对待那些其实为他人做出很多贡献的“失败者”,如何给他们回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至少在大学里是容易做到的——在精神上和环境上保护他们,鼓励他们。
与此同时,他认为人的再生产问题也与再分配问题息息相关。他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误区是认为再分配会磨损人们的奋斗和创新动力,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再分配问题处理不好,贫富差距过大,人们就会倾向于用机会主义的方式赚钱,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实在的利益。不平等的确能激发人的狼性,但最后的结果是自杀性的,没有真正的创新。“说不平等才能刺激人,它是刺激某一种欲望,但是它会消灭很多人更加丰富、更有意思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