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新闻中文版 欧宁
在1958年,当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刚刚走出他严重自我怀疑的抑郁期,又在奥斯威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纪念碑的国际竞标中无功而返时,中国正在各地农村和城市建立“人民公社”,发起“大跃进”运动。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方的户县,涌现出大量反映农村新风貌的“农民画”。它们虽然是政治动员的结果,却也热烈生动,富有美感。这种由当地传统的剪纸、壁画、年画、刺绣等孕育出来的视觉表达,很快被定义为“人民公社”运动独有的美学风格,在官方宣传推广下扬名全国。如果博伊斯有机会看到这些农民的画作,他一定会把他们称作“艺术家”,因为这符合他那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著名观点。

一般而言,“农民”与“艺术家”之间难以划等号。但在1973年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户县农民画展”之后,那些洗去泥腥、拿起画笔的农民也就成了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国内外收藏,还在官方支持下出国访问。“艺术家”这一称号一直代表着一种权威认证,过去来自皇家宫廷,现代则来自国家政权,或批评家、艺术媒体、收藏家、画廊、艺博会、美术馆、双年展等,它们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力量,决定着艺术家的身份,同时也就影响着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成为成功的艺术家意味着可以享有专权:收获声名,环球旅行,因作品可以进入市场流通而得以积聚财富。

户县农民画

博伊斯主张“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德国浪漫派先哲诺瓦利斯(Novalis)和席勒(Schiller)的影响,相信人类普遍具有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因为相信艺术具有促成社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潜力,而制度性的力量则是对艺术的约束。在“户县农民画”的例子里,也许唯一不符合博伊斯原则的是,把农民变为“艺术家”的是国家政权;而他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主张却要挣脱所有制度性力量的约束,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在香港,人们对去世的“九龙皇帝”曾灶财的街头涂鸦是否应被美术馆收藏曾有热烈的争议,在我看来,曾灶财无疑是个素人(shirouto)艺术家,但他并不需要美术馆制度的追认,因为把他的涂鸦移入白立方空间无疑掐灭了它们在街头的能量,这将是个巨大的讽刺 。

“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意味着把制度的“垂直权力”变为“水平权力”,它不是权力的夺取和垄断,而是激活和分享,从而走向一种平等政治。它要求每个人的参与,并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与之紧密相连的还有博伊斯的“社会雕塑”(SozialePlastik)观念,即社会是一个由其全体成员不断塑造和完善的“雕塑作品”。由这两个观念构成的“扩展的艺术观”(Erweiterter Kunstbegriff) 实际上溢出了艺术的传统范畴,变成了博伊斯的政治哲学。正如他喜欢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运动的创始人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在研究蜜蜂时所说,“人们必须记住蜜蜂——人们不是在与单个的蜜蜂打交道,而是必须把它们视作整体,互相归属的一个整体。”单个蜜蜂并不特别,但蜂群却凝聚起令人惊讶的集体智能,因此蜂巢可以说是“社会雕塑”的完美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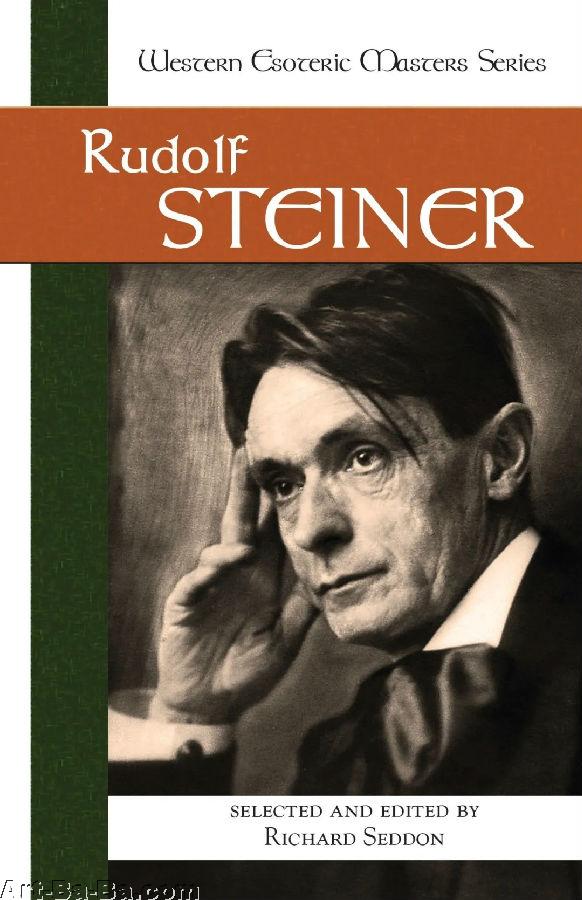
蜜蜂靠生物动力建立起自我组织、分工协作的群集模型。这种能力被互联网研究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概括为“蜂巢思维”(hive mind):蜂巢是去中心化、分布式的结构,具有自治能力,每只蜜蜂都贡献自己的工作,并彼此紧密合作,构成互相联系的网络,从而产生非线性的因果关系。蜂群的工作原理不仅影响了博伊斯的艺术和政治观念,还被用来指导今日的互联网、区块链、云技术、人工智能、人脑接入技术的开发。这些新技术是否能和博伊斯所期望的那样,把人类社会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理想国,仍有待观察;但凯利和博伊斯一样都可被视为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向往一个更好的社会,怀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努力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寻找“治愈”(healing)的可能或“替代”(alternative)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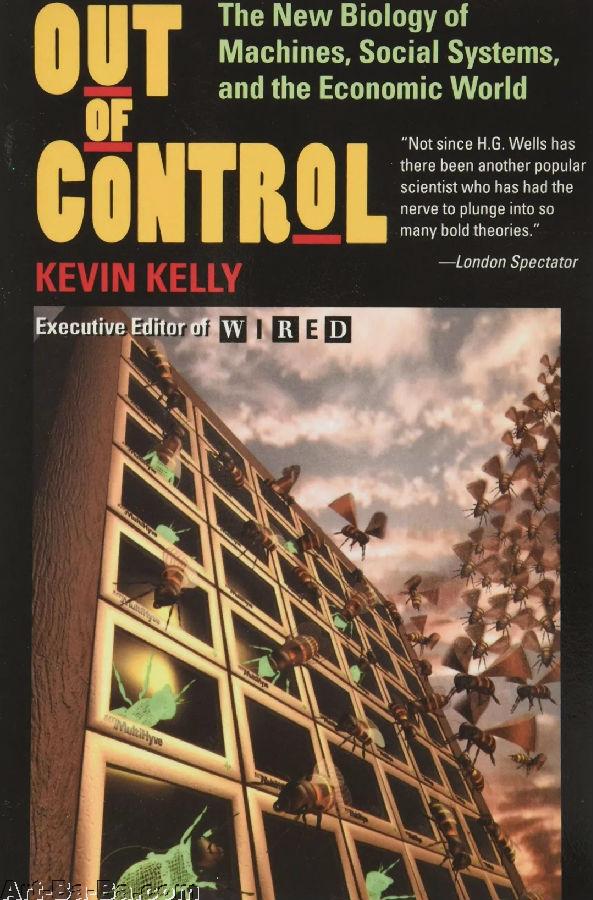
所谓集体意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社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认同感,而是对人类全体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全体”(the whole earth)包括自然环境和所有物种的认知和呵护。凯利曾经担任编辑的《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传播的正是这种观念。博伊斯的“七千棵橡树”项目以及他在德国绿党中的政治活动也显示了他对地球环境议题的强烈关注。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他对艺术作品的“寒”和“暖”的表达的话,它绝对不止于生命个体对温度的感受,而与人类和地球全体的“寒”、“暖”有关。中国科学家竺可桢曾以物候学(Peonology)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发现在平均气温从高于现代水平的极暖点跌入低于现代水平的极寒点的年份,往往会发生社会动荡和朝代更替。极端气候会导致农业歉收,饥馑流行,于是农民起义,皇朝颠覆。地球的寒暖会影响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全球变暖”并非一句与你无关的“恫吓”。

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类要绵续传承就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存环境。世上本无桃花源,但不甘心的人总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建造理想家园。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主义者都会把教育作为实现梦想的首要路径,博伊斯也不例外。他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要求取消对学生入学资格的甄别制度,在教学中打破艺术与社会的分界,导入民主化的“环形讨论”(ring discussions),这些都是对他的“人人都是艺术家”和“社会雕塑”观念的实践,其中隐含了平等政治和集体乌托邦的雏形。这和中国知识分子陶行知1927-1930年在南京晓庄所进行的乡村教育实验颇有共同之处:在这三年里,他们和村民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人人都是老师,人人又都是学生,通过在底层的乡村社会的教学实践,进而推而广之,试图达到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宏大目标。和博伊斯同年(1921年)出生的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巴西发展出“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的理论,两人不一定知道彼此,但在教育思想上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环形讨论”形式出现的工作坊现场实景,图片来源:寒山美术馆
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教育即政治,教育即解放”,主张用提问式教育和对话行动来打破“被压迫者”的沉默文化,激发他们的革命潜能。他同样强调“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授予“被压迫者”的“武器”包括“合作”(cooperation)、“为解放而团结”(unity for liberation)、“组织”(organization)和“文化合成”(cultural synthesis)。他对格瓦拉的领袖人格和毛的阶级斗争理论非常着迷,后者在掌控了中国政权后实施了规模宏大的乌托邦计划——人民公社运动。可以说,作为乌托邦主义者的博伊斯和上述各人一样,都怀有集体梦想,致力于“人的解放”,但以艺术家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实现这一宏愿,于是主张反制度的博伊斯也不得不参与组织绿党,在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展开“斗争”。但令人感慨的是,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变成美术馆制度和艺术市场的“宠儿”,绝大多数都成了公共机构的“文化财”(ぶんかざい)或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品。正如我最近在一次网络会议上听到意大利艺术家Luigi Coppola所说,“人们播下乌托邦的种子,收获的却是现实。”
作者欧宁,2009年担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2011年创办《天南》文学双月刊并任主编。2016-2017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学院。2019年至今担任CAD+SR(艺术、设计与社会研究中心,波士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