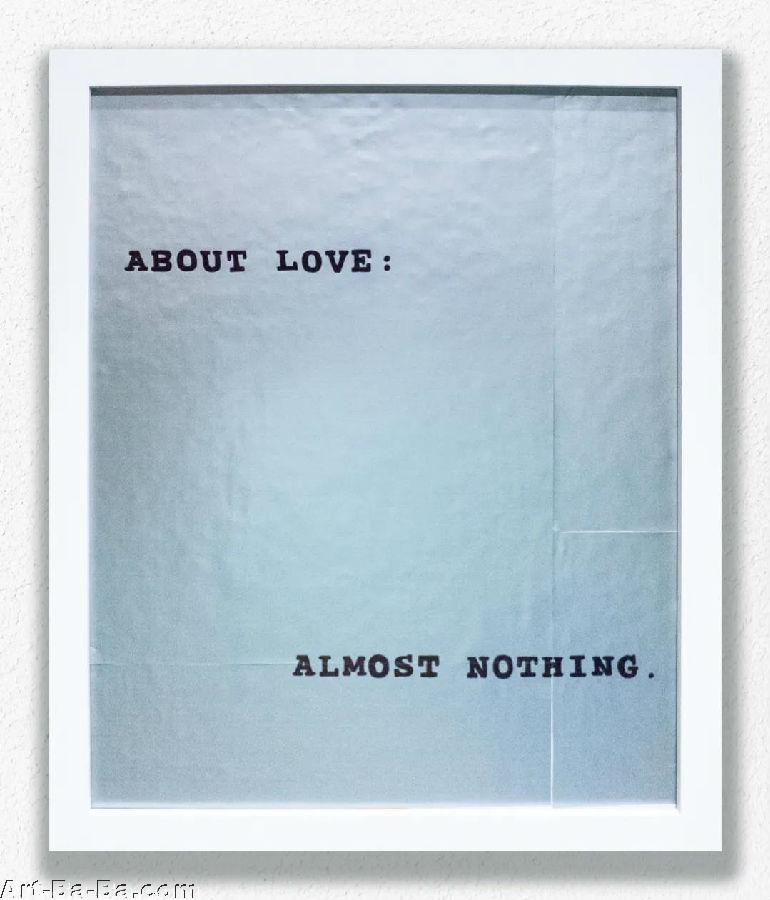来源:打边炉ARTDBL

《Chess》,杨乐宜,行为,45分钟,2019
4月15日,杨乐宜个展“自恋深渊(Narcissist Echo)”在美国洛杉矶一尾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杨乐宜近一年来创作的装置及油画作品,展览将持续到5月8日。展览期间,《打边炉》和她进行了交谈。杨乐宜是一位在深圳长大,从芝加哥艺术学院和旧金山艺术学院毕业后,留居旧金山做创作的青年艺术家,我们希望通过对话,了解她如何在流动和成长中探寻出适合的表达方式,反复调试自己艺术语言的同时又如何认知自己的创作。杨乐宜的视觉作品总微妙地与文字融合,只言片语里拆解了日常的逻辑,腾挪出极大的想象空间。正如她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入口,进去之后,方向全由观众把握。她不相信任何的定义,创作中,她以不断发问或大量留白的方式,勾起一场没有答案的讨论,看似无意义,实则另辟蹊径,不经意地接近真实。
“自恋深渊”展览现场
ARTDBL:相较于过往的油画、影像或行为,个展作品的材料性强了很多,你对材料的选择有着怎样的考量?像石头、镜子这些材料偏日常,你如何将日常的材料转化为带有叙事性的创作材料?
杨乐宜:我原来基本都在工作室里创作,去年三月,受疫情影响工作室关闭了,忽然不知道该用什么继续做作品,觉得自己很没用,太依赖工作室。于是我开始走进厨房,用咖啡画画,开始捡石头、木头回来刻,都是很日常的材料。材料在作品中可以带有隐喻性,但我的选择主要从物理性质出发,材质要能配合作品叙事带动情绪。镜面系列用了带反光性的材料,镜子为主,也包括有机玻璃。我做作品的时候是个“处女座”,这个系列花了大半年试验不同材料的反光性。选择反光材料跟我想表达的主题有关,个展讨论浪漫关系,灵感最初源自纳西索斯(Narcissus,自恋“narcissism”的词源)的故事,纳西索斯是希腊神话里最俊美的男子,但他自负貌美,拒绝了一众女神,其中包括山林女神伊可(Echo,意为回声),最终被施诅咒,因爱上了自己水里的倒影,落入湖中而亡。我在想,我们自以为的罗曼蒂克真的浪漫吗,还是说只是一种自我感动罢了?反光性的材料能让观众看到自己,镜子的易碎性让人像湖边的纳西索斯一样,处在多踏出一步就会失去平衡的边缘。我还利用了材料的物理性质和刻在上面的文字形成一种反差,比如在石头上刻“soft-centered”,然后把石块一个个垒起来,让它们处在一种极易受环境影响而倒下的临界状态里,我很喜欢这种微妙的平衡。创作打破了我对这些日常材料的原有感知,又不断触动我去尝试新的材料。
《Under the bridge》,杨乐宜,装置,镜子、喷漆,12x12 Inch,2021
ARTDBL:文字经常出现在你不同类型的作品里,作为一位以视觉艺术创作为主的艺术家,你如何理解文字创作?
杨乐宜:文字一直是我作品里常见的元素,最初是因为受到赛·托姆布雷(Cy Twomly)的影响,他的画里会有些零碎的文字,线条也带有书法性,你读不出什么具体的含义,但很多人都从他的作品中体会到了诗意。我也很喜欢读诗,像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诗,每个词都很好懂,连起来虽然好像读不懂,却极具感染力。我所理解的文字创作,就是去探索文字除了我们赋予它的本意之外,还能如何创造出别的意思。所以我作品中的文字故意表达得比较模糊,具有一定指向性的同时又有开放性。油画、镜子、石头,都是表达的途径,本质是将情绪转化成文字再结合不同的材料去写诗,尝试一下不同的方法能带出怎样的文字以外的体验。过去的文字创作因为深受托姆布雷的影响,比较在意涂鸦式的表现性,现在更偏向于文字含义间的不同组合,不太在意形态表现了。个展作品中的文字特别规整,用了印刷字体,我希望它们看起来能有一点冷漠、不近人情的感觉,就像一个没有表情的局外人在客观地言说,当你读进去这些文字,才发现她内心其实风起云涌。
《If I Could Crawl》,杨乐宜,布面油画,48x48 Inch,2019
准确地表达模棱两可
ARTDBL:作品中的文字量不多,有点碎片化,这些文字的来源是什么?你提到模糊,如何把握这个模糊的度?
杨乐宜:我是一个必须去生活才能做作品的人,去到不同的城市和角落,遇到各种陌生人,很多油画上的文字来自于日常当中非常随机的对话,偶尔别人说出的一两个单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把这些经验带回工作室反复想很久。工作室的地板上有一块大画布,一有什么灵感就在上面随意涂写,到现在也快积累了一年多了。镜子上的文字尝试了不一样的制造方法,我追求语义的模糊,自己和他人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似乎能更接近模糊。于是找了做行为艺术的朋友大雷和创意写作的朋友melody Niu合作,一对一聊天,聊着聊着达成某些共识,决定一起编造一出极端情况下的爱情故事。编好故事后由对方书写,我对故事的书写要求用偏诗意的语言,不要过多的限制性。而最终呈现在镜子上的文字是我从故事书写中摘取的,我认为最能代表故事氛围的词句。其中一面有机玻璃上写了一句中文“可怜之人必有可爱之处”,是那位编剧朋友写的,当时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个电影故事,故事的女主不停地给男主投毒,男主在知道的情况下又不断地喝下解药,从中我们延伸出另一个关于蝴蝶的故事。这句中文很微妙地传达了故事的荒诞感,我们想引出一个思考,当知道结局的情况下,好比蝴蝶的寿命只有21天,是否还要去体验过程。
《Surrender to me》,杨乐宜,装置,有机玻璃双面镜、乙烯基贴纸,12x12 Inch,2021
文字的来源不一样,但作品想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用模糊的语言给观众留下空间。要准确地表达出模棱两可的模糊感挺难的,写太多了过于清晰,写太少了又完全不成立,反反复复推敲了好久。
文字原本是相对明确的,诗句的文字给人创造氛围,让你联想到很多东西,而联想的东西全都超越我们赋予这些字的本意。文字还经常导致误会,语言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我们的一切认知都基于语言之上,当我们想要触及一些真实感受的时候,通过言语一说,就像是翻译,怎么样也无法靠近内心。何况每个人的理解系统不一样,我时常怀疑当我们看到同一个东西时,我们是否真的在看同一个东西。
《A Loud Silence》,杨乐宜,模型膏、丙烯、油画颜料,30x40 Inch,2020
ARTDBL:文字和视觉画面的阅读方式不太一样,对于观众而言,文字可能比没有明确指向的视觉更好进入,在你看来文字和文字的载体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创作过程中,文字又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杨乐宜:文字固然是极具表现力的,可一旦过量,作品有可能无法承载,这是我不希望的。因此文字量需要小心翼翼地控制,文字的载体要能跟着文字一起去营造主题,而不是相互抵消。油画新作是先有文字,再根据文字的感觉来创作视觉画面,文字和视觉部分的结合主要依靠直觉,也需要一定的逻辑支撑,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来回的转换,最终达到一种统一性。为了像文字一样具有模糊感,我抹去了过往画面中太直接的形象,特地调了轻薄的颜料,一层层地叠加出朦胧的质感,仔细看的话又能透出暗含的线条和形状。我从未把作品中文字和文字的载体分开看待,文字和油画颜料一样都是材料,它们是一体的,没有高低之分。你说文字不是视觉,它也有视觉上的呈现,同时它还包括听觉,你把文字读出来又是另一种感受。媒介归根结底都是有联系的,或是形式上的关联,或是感觉上的,在于当下想要追求的氛围用哪种媒介表达最舒服。尽管我时不时地会在创作中理性地控制一下,多数时候还是随着感觉发生,文字看起来偏理性,但文字部分其实是我最不会去控制的,大部分文字都非常原生态,随性写下来后不会再反复推敲。梁铨老师曾跟我说,无意的流露才深刻,所以理智的时候就是要去看看那些无意的流露。除非表达得过于直接,感觉不对了,就得控制自己找个新的角度继续。
《Not a Good Lover》,杨乐宜,木板油画,12x8 Inch,2020
ARTDBL:文字的收集或生产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呈现出来的“信息量”不一定很大,你如何搭建创作过程和观众观看过程间的桥梁?
杨乐宜:创作过程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过程不饱满,那最后的作品我自己也不会喜欢,所谓饱满,就是接受过程里的每一个失败。我的创作过程总是断断续续,期间的尝试不都顺利,做着做着会突然间感到虚无,不知道怎么继续。因此我更看重的不是最后的作品,而是自己有没有用尽全部心思去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代艺术甚至当代社会都缺乏只看过程不看结果的勇气,画廊看的也是结果,我也很矛盾,想埋头苦干只管过程,但是不行。所以作品里能带出一点过程性的东西很重要。就像我说的,镜子作品背后其实写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还有一段很长的对话,整个过程我没有拍下来,因为作品已经把最能传递核心感觉的文字摘取了,比起完整的揭露,留白更加有力。
《Blue 1》,杨乐宜,装置,有机玻璃、乙烯基贴纸,12x12 Inch,2021所谓的浪漫关系很复杂,大家探索了这么久其实没有人有答案,我也还在理解当中。我的作品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而是希望不断挖掘这个领域更多的问题,提问的根本目的也不只为了一个答案,而是引发出更好的问题。个展提出的还是一个认知问题,我认为的浪漫,在他人眼里可能不是浪漫,不过这不是我的立场,个展是一场公开讨论,我的作品只是入口,大家进入作品后,由于个体经历不尽相同,于是开始往不同的方向走。创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既是私人经历的记录,也是私人情绪的释放,当我把作品放到你面前,可以勾起你的私人情感,我觉得就够了。
《I Perish》,杨乐宜,木板油画,10x10 Inch,2020
ARTDBL:你强调作品在想象空间上的留白,那么观众和作品间发生的关系显得很重要,你如何考量作品感知传递的有效性?
杨乐宜:我喜欢观察观众在我作品前的反应,作品能完成,需要在一个空间里和观众发生对话或互动。悄悄说一句,我是那种会在博物馆里偷偷摸画的人,我很好奇观众在展厅里会不会主动摸我的画。个展上我特别创作了一件带涂层的作品,有点像刮刮乐,很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观众真的触碰了这件作品,又真的刮开了底下的文字,之后慢慢地有更多观众也开始大胆地刮。可能得益于这次个展的空间比较小,缓和了艺术带来的心理距离,观众才会不自觉地伸手触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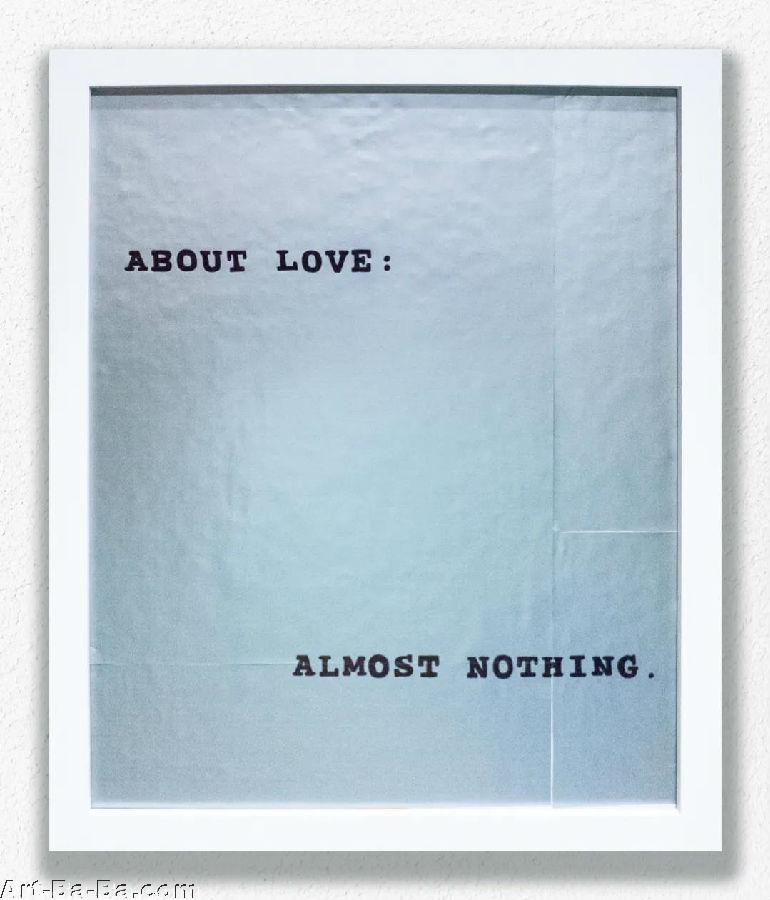
《About Love:almost nothing》,杨乐宜,裱框装置,可刮涂层、油墨转印、复合纸板、油漆笔、油画颜料,无框尺寸11x14 Inch,2020
我真的不太避讳别人摸我的作品,留下任何痕迹都OK。我有很多用色粉画的画,色粉容易掉,但我不太会喷定画液,任它随着时间产生变化。触摸也是一种感官体验,和视觉一样,那为什么对于艺术品的阅读不能包括触摸?我一直想问,我的作品什么时候变成了艺术品?艺术品又什么时候变成了不能触碰的艺术品?很多距离和边界都是我们自己设立的,我还想尝试一下,我的石头砖头搬进画廊是艺术品,如果我把它们放在画廊之外的公共空间,还会被当作艺术品吗?
作品《About Love:almost nothing》在展览期间被观众刮开了底层的文字,一位小孩在他妈妈为他解释了展览寓意后,在作品中写下了一句话。
ARTDBL:很多时候当代艺术在通过作品去探讨问题,你的个展也在提出问题,背后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思辨。在做艺术之前,你曾在哲学系研修,哲学如何影响你的艺术创作?
杨乐宜:读艺术之前,我读了两年哲学,当时读到尼采、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我其实非常感兴趣,可学着学着就意识到他们讨论的大部分问题尽管深入,但都没有结果,只是自圆其说,别的哲学派系还会来指出很多漏洞。于是我想换一种方式参与或推进这些领域的探讨,正好当时辅修了美学哲学,加上机缘巧合,就转行去做艺术。创作中,我延续了对虚无主义的兴趣,表面上我关注的都是一些无意义的事物,实际上我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定义一个对象有意义或无意义呢?人类赋予一个对象有意义或无意义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一切都是人为的,风有意义吗?我不知道,但我在风中做一场行为,每天有风的时候就在风里画画,记录下当时的日期、地点、天气、时长、观看人数和画的名字,为期一个月,然后诚实地和观众分享,我觉得能有一些人,让我在他们生命里的某一时刻,跟他分享我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呀。我也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有没有意义,我在意的是创作过程是否保持真诚和热情,比起意义,我觉得当下社会更缺乏真诚。我也有很观念性的一面,特别是做行为艺术的时候,但可能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或许是哲学带给我的习惯,总是爱自我反驳。当代艺术很强调观念,有的作品看起来跟哲学理论一样难懂,我觉得还不如把观念直接贴墙上更当代。观念的探讨也没有结果,循环在解构和重构之间,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定义,所以你的意图很重要,有一个带意图的出发点让你这么做,否则在作品完成后套一个概念就会很牵强。即便是行为艺术中的随机性,那也是艺术家非常有意识地制造或拥抱那种随机性。我作品中语义模糊的文字,也是我故意去传达一种模糊的氛围,并且我相信这足够挑起观众的想象力和感受力。
《A Perfect Situation》,杨乐宜,行为,一个月,2020
ARTDBL:在海外发展艺术,身份总是一个无法回避或被迫面对的问题,亚裔艺术家的身份对你的艺术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乐宜:身份不是一个问题,“亚裔艺术家”是一个标签,和生活中的很多标签一样,而到头来我们都是一个需要面对生活琐碎的普通人。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艺术是很私人的事情。所有的客观性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我确实是亚裔是中国人,但我的作品暂时没有涉及到种族问题,也没有站在这个角度发声。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艺术应该是毫无束缚的,而我的创作就是这样诚实,再私人不过了。其实一切都是流动的,语言是流动的,文化是流动的,身份也是流动的。我不抗拒任何定义,但也不会让任何“定义”定义我。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创作的侧重点,只是我暂时没能力去讨论太宏大的话题。自己的野心并不大,蛮知足的,遇到的困难基本都是创作上的,成名对我来说意味着有资源做“无厘头”的作品,可艺术家出名就跟警察立功一样,很快,但需要运气。我一直很想做具有社会性的行为艺术,但需要名气的支撑,不然根本组织不到人。曾经针对全球变暖的话题,设想过召集十万人憋气一分钟,看起来挺可笑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是传达一种观念,但我还没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组织不到这么多人。目前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经验,很多东西先想着,有机会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