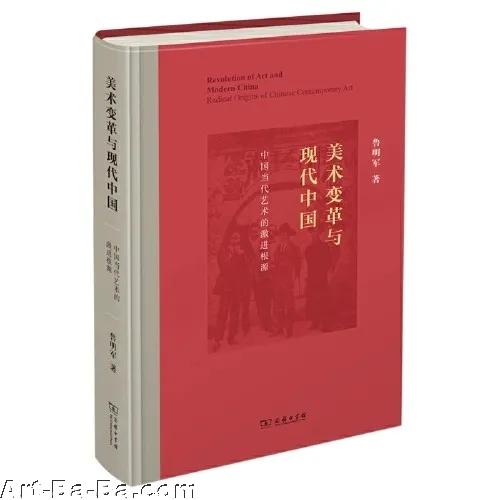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鲁明军新作《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连同他为复旦大学艺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艺术展览与艺术理论专题”课程,都可谓是中文艺术史论界极为稀有的尝试。以一百年前的“美术革命”这一事件为起点,鲁明军在书中展开寻找中国当代艺术激进根源的五个新角度,重审中国当代艺术、“美术革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借以激发当下艺术生态中隐伏的动能和力量”。鲁明军并非在为中国当代艺术重新寻找一个历史起点,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在现实与历史之间重探另外的关联,进而调动起更多隐伏在历史烟云中的感知与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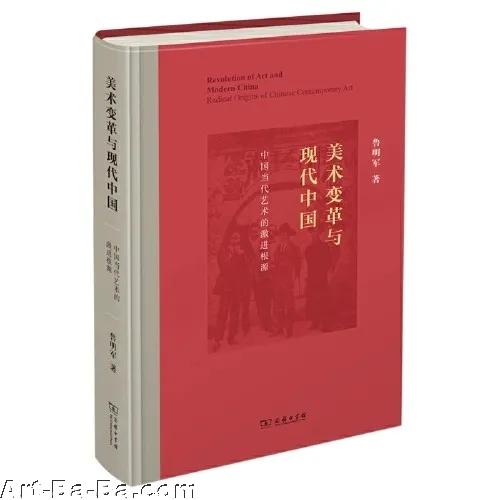
作者:鲁明军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月:2020年10月第1版
在旁观者看来,鲁明军过去一年极为忙碌:他先后策划了蜂巢(北京)当代艺术中心展览“恶是”、深圳坪山美术馆展览“缪斯、愚公与指南针”、上海chi K11美术馆“绝地天通”和武汉剩余空间五周年展览“形式的‘密谋’”,还担任了华宇青年艺术奖的终评委、实验影像中心(CEF)的学术主持,组织了一系列线上学术讲座和讨论。不过,处于看似艺术繁荣以及个人成果丰收的时刻的鲁明军,似乎也有着极大的困扰和焦虑。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他不止一次地追问——策展在今天到底能做什么,写作和批评在今天能做什么,甚至,艺术创作在今天能做什么。在2021年的开端,我们对这些追问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


鲁明军,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A:作为策展人,今年越发感到展览的无效性和无力感,简单说,就是你突然找不到着力点。有些问题和角度看似很好,但是依然切不进今天的现实,触及不到这个时代真正的痛处。也许是因为现实太强大了,它自身就有着很强大的弹性,任何的击打都会被轻轻弹回来,突然找不到一把足以切开一个口子的刀。展览也好、写作也好,你总是希望能够切开这个东西,但你发现,其实还不是刀的问题,而是对象太硬了,你切不进去,即使切进去一点,它也会很快愈合。以前也有类似的感觉,但今年尤其明显。这可能也不是个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大环境或整个时代的问题。Q:似乎重要问题都被回避掉了,似乎大家都不做有挑战性的事了。您觉得,这种思想上的萧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A:很难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但这种体会这两年越来越明显。▶ 一是依赖于既有的惯例,比如这几年普遍消费各种社会、政治和历史议题,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套路;
▶ 二是依赖于西方流行的趣味,其实这个也体现在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探讨的话题都是别人给定的,我们对艺术的判断取决于在西方流行什么,以至于欧美美术馆馆长到了上海看不到他们想看的中国当代艺术;▶ 三是艺术家和策展人不再是艺术系统的主导者,反而完全受制于艺术系统,我们不再是玩艺术,而是被艺术玩得灰头土脸,导致感知力和想象力的枯竭;▶ 四是艺术与现实的脱节,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关注现实不够,或对现实不够敏感,而是找不到一个新的连接方式,丧失了针对艺术提出问题的能力和犯错的勇气。Q:是不是因为艺术行业生产性越来越强,慢慢就变成做数据——展览数量有多少,参观人数有多少,交易有多少,数据变成了重要的?A:是的,以前我们策划展览不考虑观众人数的,但今天这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甚至在线做个讲座,都要考虑观众流量。所以,今天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不管不顾,况且那种不管不顾也无法应对今天的现实,我们要考虑的是在今天这个历史条件下,如何从这种体制化的约束中找到突破口。以前艺术家可以有洁癖,玩高冷,今天没人觉得这是一种高级(贵)品质,因为这个不再是提升自己的“价码”和扩充自己流量的条件。另外,以前是一个垂直性的结构,“敌人”很明确,不说欧美,就说我们自己,比如“美术革命”要革传统文人画的命,“星星”“无名”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感性”直接针对的是观(概)念艺术,非常明确。但今天是平滑的,一盘散沙,找不到敌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法真的联合起来,而且,反抗者之间是更加残酷的竞争。
A:也许是吧。前几年看了太多展览,每年出去看很多展览,即使只待半个月或一个月,还是能看到刺激你的东西。在国内,很少碰到这样的展览,也许是太熟悉了,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们太单一。也不只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而且,现实比艺术还要魔幻,民间比艺术界还有想象力,这些都给今天的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还能做什么?作为策展人,你还能做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A:我觉得是能动机制不同,动力源不一样。临时的也好,恒久的也罢,他们普遍都有明确的目标和针对性。特别是这些年,政治环境的动荡和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也给当代艺术提供了很多动力源。比如这些年出现很多潮流,无论是朝向未来,还是回溯历史,还是产生了很多艺术浪潮和运动。国内也意识到了这些变化,甚至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麻烦在于,一旦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依赖程度过高,就逐渐丧失了我们对自我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找不到着力点,展览最后可能就变成了知识竞赛,可是这些在知识系统内大多又经不起检验。策展是一种“现场写作”,策展人是一个“行动的写作者”。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随着策展的机构化,固然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标准,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展览的活力在萎缩。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非机构化的策展尝试,比如重建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看似带来了一种活力,但这个时候我们恰恰需要考虑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边界在哪里,因为有了边界才会相互激荡。这两种情况,都带来一个结果,作为作者的策展人在消失,展览的个性越来越弱,前者被规范耗光了,后者则被大众文化吞掉了。
不是说策展人都应该成为时代的英雄,但至少不能沦为行业链上的螺丝钉。和艺术家一样,策展人还是要有一定的主体性和辨识度。Q: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头看看历史,从其中寻找着力点?A:是的,比如这学期在复旦大学开设的“艺术展览与艺术理论专题课”,我还是放在展览史的框架下去讨论。如果只是讲怎么做展览,其实没有用。所以,一方面想让大家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这三个重要的时期,为什么会冒出一大批激进的实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类似的方式为什么不能适应今天,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哪些历史资源是可以调用的。这些问题可能还是需要长时段去看,不能只归咎于当下的文化和政治生态。但是这个在今天越来越难,你可以想象为什么那些独立空间和临时空间坚持不下去,这还不光是运营的问题,最主要是发不出强有力的声音。然后又要投入很多成本进去,做到最后艺术家自己都没了激情。另一方面,我觉得今天可能还是需要形成有效的跨学科协作。目前的所谓跨学科还比较初级,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深度对话和合作还没有出现。这个其实对每个人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以前是艺术家之间的理想主义合作,比如“池社”“后感性”这样的,今天这种方式一是无效,二是也合作不起来,国内几乎所有的艺术小组都解散了,但跨学科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比如有一些年轻策展人已经在尝试,我们复旦艺术哲学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A:剩余空间做了五年了。今年因为疫情只做了一个展。这五年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尝试,要求只有一条,就是在不同的时刻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是最低要求,也是很高的一个标准。2019年,我们举办了“街角、广场与蒙太奇”,2020年是“形式的‘密谋’”,两个展览是息息相关的,都是因应当下敏感事件的回应,前者针对的是香港乱局,后者主要考虑到疫情下集体的非理性,但展览不是新闻,恰恰是要借此打开一个可以纵深思考和讨论的空间。比如现代主义,其实是困扰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通过写作、策展各种途径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2020年,剩余空间五周年特展“形式的‘密谋’”展出作品:周啸虎,《峰会-NYSE》,2003年,陶土动画情景雕塑,尺寸(L)130 × (W)112 × (H)74cm,逐帧动画静帧,片长3分25秒Q:现代主义不仅是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如《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里说的,它也很积极、很正向,譬如美国进步时代,相信物质的富足和生产力提高,本身也是现代主义,这才造成它20世纪初的艺术形态。A:这种很“正向”的力量,它需要形式来召唤,未来主义、至上主义都是如此,即使像瓦尔堡的图像学,也有一个形式基底的,更别说蒙太奇、包豪斯了。艺术走到今天,水泥、塑料、木头、各种现成品,包括身体、数字……物质、媒介的可能性不能说已经被穷尽了,但至少都开始感到厌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想,重申形式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出口,会不会提供一个新的动力空间。很多人寄望于技术会带来艺术的变革,但艺术其实应该先于技术。艺术不是对技术的反映,也不单是非以技术的方式呈现,但艺术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技术尚未触及或抵达的问题。科学家当然很伟大,但艺术家不能跪在科学家面前。这是对艺术家很高的要求。但同时我们不妨退一步讲,即便是延迟的反应,是否反应到位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艺术都是预言性的,延迟的反应也可以增殖,可以将事件转换成一个结构化的创制,进而让它变得更有持久性的力量。我在《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一书的结尾也提到这一点——尽管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同意这一点。今天批评为什么没有了?因为简单的好坏判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更致命的是,这个时代的包容性大到足以消化一切矛盾和冲突,“敌人”的免疫系统太强大了。Q:对于目前艺术界的发展,您觉得哪些问题和动向特别值得关注?A:病毒已经发生变异,疫情还在大规模地传播和扩散,欧美的社会政治动荡也看不到短期内停息和恢复常态的征兆,国内疫情虽然基本得到控制,但我们无法自外或独立于周边以及整个世界。至于全世界的洗牌会不会引发艺术上的变革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会成为艺术家实践和行动重要的驱力。不过,国内情况和西方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未来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和动向值得关注:▶ 一是以往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那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会变得彻底无力,或会转向新的对峙;▶ 二是随着制度自信,当代艺术受到的限制也许会越来越严;▶ 三是逆全球化趋势和所谓的“内卷”会导致行业内部长期找不到目标,加上技术的疾速发展和大众消费文化的扩张,相对滞后的当代艺术会陷入一种无处着力的疲软和茫然。A:有一两个展览已经在准备了,今年我会把视角转向一些更加基础或根本的问题上,比如以展览的方式尝试探讨一些类似“艺术地活着?”“艺术家及其性格”以及“展示如何思想,思想如何展示”这样的话题。
1999年,北京在芍药居公寓地下室“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展览中呈现的作品:王卫, 《水下1/30 秒》, 1999年, 灯箱声音装置另外有两本书争取顺利出版,一本是《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2020)的附篇《裂变的交响: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三个当代时刻》,从“1919”“1979”和“1999”三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的艺术发生出发,通过对“美术革命”“星星美展”和“后感性”“超市”三次相应的艺术运动和展览实验的全新解读,不仅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做一次切片式的价值重估,也试图赋予“当代”一个新的内涵和定义。另一本《艺术力:论图像的潜能与形式的意志》签了出版合同,但书稿还没有全部完成。其实这几本书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基本涵盖了前几年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采访/撰文 姜伊威 编辑/童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