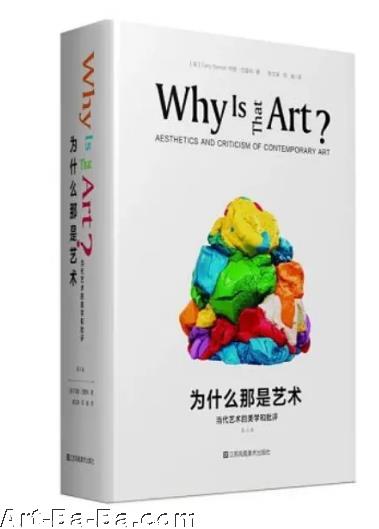来源:空白艺论KONGBAI 文:Terry Barrett
本文节选自巴雷特《为什么那是艺术?——当代艺术的审美与批判》(文末有购买链接)一书的第一章,相对于公号此前翻译的《十月》圆桌会议“艺术批评的现状”上的讨论以及埃尔金斯等人的文章,巴雷特对于艺术批评的观察,在表述上更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也少了些许“批判”的意味,但对于我们理解艺术批评的复杂性以及反观当下国内的艺术批评,仍然有所帮助。
“艺术批评”一词相当复杂。美学家莫里斯·韦茨将“批评”定义为“有关艺术作品的一种经过一番研究的论述的方式,这种方式系使用语言来试图促进和丰富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美学家马西娅·伊顿(Marcia Eaton)指出:批评“促使人们去关注一些特别的事情”。她进一步提到:批评家“‘指出’那些能够被我们认知的事情,同时也引导了我们的认知”。好的批评会让“我们自己去领会,并继续依靠自己前行”。
批评是在有根据的情况下针对艺术作出的论述,这样的论述能提高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欣赏水平。这个定义适用于针对所有艺术形式进行的批评活动,包括针对舞蹈、戏剧、音乐、诗歌、绘画和摄影的批评。“论述”(discourse)一词包括谈话和写作。后面几个章节将引述许多艺术家的访谈内容。“有根据”一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设定,由此将批评与涉及艺术的简单谈论和不明所以的见解区别开来。当然,并非所有关于艺术的文字都算是批评。某些涉及艺术的文字是新闻性的,它们不能算是批评,而是关于艺术家和艺术界某些事件的新闻报导。
在对艺术和艺术批评津津乐道的美学家语言中,以及在艺术批评家的语言中,“批评”一词通常指代一系列活动,包括描述、解读、评判理论总结,而不仅仅是评判这一个行为。韦茨是一名美学家,他一手建立起有关艺术的开放式概念,对艺术批评也深怀兴趣,并且针对艺术批评家在批判艺术时进行的活动进行了调研。他收集了史上所有关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批评文章,以此作为他的研究案例。在通读了几个世纪以来针对《哈姆雷特》写成的所有批评文本之后,韦茨得出如下结论。批评家进行批判时,会作出下列四类行为中至少一类以上的行为:对该艺术作品进行描述;对其进行解读;对其进行评判;总结出关于该艺术作品的相关理论。一些批评家基本只进行描述性批评;另一些批评家也描述作品,但主要是宣扬他们对于作品的解读;还有一些批评家则既有描述,也有解读、评判和理论总结。韦茨有关批评的研究有多个结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四类行为中的任何一类行为都构成批评;并且,评判并非是批评必不可少的成分。
描述既是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它试图识别出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全部元素,这件作品是由谁,用什么材料,在哪里,针对什么样的观众群创作的;同时描述也是一种言语提示:“请留意这里,注意那里”。
解读艺术作品是要弄清作品的意思。解读是寻求阐明一件作品涉及的会是什么内容,对它所可能表现的含义作出解释。解读艺术作品是让我们观察到某些对象是“再现某些事情,表现某些事情,关于某些事情,回应某些事情,归属于特定传统,展示特定形式特征,等等”这意味着我们要探究和回答如下问题:我们看到、听到或是以其他方式感觉到的这件对象或事件究竟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它要再现或表现什么?它对于创作者自身有何意义?它属于什么的一部分?它是否代表什么?它的参照是什么?它要回应什么议题?它为何会成为现在这样?它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它属于哪个传统?一件作品可能为创作者或收藏者达到怎样的目的?它为与作品相关的人带来了怎样的愉悦和满足?它解决或缓和了什么问题?它解决了什么样的需求?它是否起到任何负面作用?它对我有何意义?它有否影响我的生活?它是否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评判艺术作品是评估艺术作品的好坏。完整的评判应包含三个方面:(1)对于艺术价值的评估;(2)有关评估的理据;(3)明确的(或暗示的)评判标准。
韦茨主张描述是事实性的,因此可以有正确和错误、准确或不准确之分。解读、评判和理论总结都是基于对于作品以及与之有因果关系的生成环境的描述,它们属于主张,而非事实,在可信度或说服力上有高下之分。艺术史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埃德蒙·费尔德曼(Edmund Feldman)基于韦茨识别出的解读过程,开发出一套由四个步骤组成的艺术批评方法,用于其艺术教学:在艺术教学范围内,费尔德曼批评法首先是描述且仅限于描述,然后开展正式的分析,此后且仅限于此后再进行解读,此后且仅限于此后再进行评判。公开发表批评的艺术批评家却很少采用这种套路,他们根据自己针对艺术作品想要阐明的内容,自由运用不同的套路来进行艺术批评。
描述、解读和评判三者相互关联,也相互依存。我们如何去评估件作品,也会影响我们对作品的描述;我们对一件作品的理解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评判。例如,我会说这件或那件艺术作品从审美角度非常吸引人,但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应予谴责;又或者,另一件作品很丑,但具有其社会意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评判本身即可称为批评,并且这种意见还很普遍,尤其在日常谈及艺术批评的时候。某哲学百科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对一件艺术作品作出艺术批评,是对该作品的整体性价值或缺陷作出判断,而且还要参考作品拥有的特征,为此判断提供依据。”
对于所谓评判在艺术批评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说辞,一些艺术批评家总比另一些艺术批评家更为坚定。格林伯格是现代艺术最重要的批评家,他主张:“一名艺术批评家的首要责任是给出价值判断。”他对这一点还十分坚持,“你不可能避开价值判断。不作价值判断的人都是些笨蛋!除非你还是一个孩子,否则,拥有自己的观点与否决定了你有料与否。”《纽约时报》的艺术批评家罗伯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说:“你必须写出你的想法,亮出你的观点比描述更重要,退一步说,至少也是与描述同等重要。“她还补充说:“你也可以用你不喜欢的东西,来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批评家。”《时代周刊》的艺评家罗伯特·休斯以“批评决定一切”为名写了一本书,在他看来,“批评”就是“评判”。
撰写和发表美学和艺术史文章和著作的人,其中大部分之所以能得到大家认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但也并非总是如此)都拥有哲学或艺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或美术硕士学位。部分作者既是批评家,也是美学家,有些时候会在同一篇文章中扮演这样的双重身份。部分艺术家也撰写艺术批评,如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这位《新闻周刊》的前艺术评论员,也是一位时常参展的艺术家。艺术家有时通过写作,直接为美学、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出力。所有艺术家都对美学和艺术批评起作用,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如果艺术家不曾进行艺术创作,那么有关美学也就没什么可写的,更不用说艺术批评了。新艺术形态能推动美学,而美学上的新观念也可以影响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家们对新艺术形态和新艺术观念作出回应,反过来又影响后两者的发展。
在那些积极参与美学、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活动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仅靠写文章或艺术创作而在经济上生存。大多数美学家、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靠教书或其他一些基本工作来维持生计。
艺术批评家的称号或多或少都是他们自封的。艺术批评家通过写作发表艺术批评文章而成为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的是博物馆策展人——这些策展人撰写有关艺术馆展册的文章或对艺术家进行访谈供艺术媒体发表。最重要的是,艺术批评家是专长研究新近艺术的写作者。他们的信誉建立在他们文章的读者——尤其是艺术界内的同行——给予他们的尊重之上。艺术批评家兼诗人巴里·施瓦布斯基(Barry Schwabsky)在《国家》杂志上,就他的批评观写道:
批评家都是自封的观察者,意思是说他对于审美体验作出了清楚描述。例如,1846年,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当时还很年轻的波德莱尔有这么一句“画中映照着一颗聪慧敏感的心灵”,对于艺术批评家而言,博学与否并不要紧,想象力和热情才是更为基本的东西。针对观念和解读的发挥能力,比考察、核验能力更有价值。
《纽约客》批评家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有过一个提问:“作为一名批评家,我能在画廊里做什么?他接着自答道:“我揣摩作品,靠近作品,围着作品走动;如果我胆子够大,我还可以触摸作品;同时,我在心中提出问题,思来想去为它们找答案——直到我的思想和感觉能初步统一,直到我感觉疲累。”这意味着,他把判断滞后了,努力抗拒脱口而出“我喜欢这个作品”或者“我不喜欢这个作品”。当施杰尔达碰到他不喜欢的作品时,他不会不屑一顾地轻轻走过,而是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假设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话,我为何会如此创作?”这是我接触一件艺术作品时要解决的工作问题之一、(而不是“我也会如此创作”。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对一件令我讨厌的作品,我有一套公平对待的方法,我会问“假设我喜欢这件作品,那它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喜欢?”当我无法想象自己是一件作品的目标观众或潜在观众时,我问自己这件作品的观众究竟是哪一类人?
戴夫·希基在谈及他撰写的艺术批评文章时说:“我用心领会作品,把这种领会转化成视觉想象,再把这种视觉想象转化成语言,再附带上我认为与场景相适的我对作品的预期和特殊诉求。”他一丝不苟地对作品保持开放态度,以一种浓厚的好奇心看待作品,在对作品的理解上,他反求诸己,而非推谈作品或作品的创作者。罗伯塔·史密斯提及她的批评有时“不过是提出了某些观点……批评中最美好的部分是:你时不时——也许更为经常地——写出的东西是那些从未曾被写过的,涉及的是你知道的新艺术家的新绘画作品,或者涉及不知名艺术家的新作品”。
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唐纳德·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问道:“为何我们会对这名艺术家创作的圣母与圣子的图像有反应,而对那名艺术家创作的图像没有反应?为何我们喜欢某种特定的质感,而不喜欢另一种质感?”他接着说:“艺术批评家任务的一部分,同时也许是其中最难的部分,就是把艺术作品在我们内心中引发的感受清晰地说出来,而这些感受恰恰是非常复杂的主观的。”
乔安娜·弗鲁伊(Joanna Fruch)针对撰写艺术批评时需要依靠情感和直觉的问题,有如下论断:
艺术批评,如同其他使知识分子受人尊敬的学科一样,在其中,直觉自然产生的知觉——即从感观得到的知识,还有经验和心灵基本都是缺位的。但神经连贯整个身体,将感觉、一点一滴的知识传导到大脑;从心脏泵进泵出的血液在我们身体各个角落流滴。知觉是完整鲜活的存在,而不只是在智力意义上的存在,它是对于人的一种认可,是整个身体的智力。知识分子也许会感到被其考虑的问题所控制,但愿他能逃离他的身躯;只是我们唯有接受身体是前住自由的道道,灵魂才会飞翔。
大部分艺术批评家都认为他们的著述不是终结性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是阶段性的。换言之,他们所写的内容并非结语,特别是当这些内容涉及的是新作品时更是如此。当代现存的、最具知名度、最受世人仰慕的艺术家之一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讲过一个关于约翰·卡纳迪(John Canaday)的故事,卡纳迪当时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艺术批评家,他“讨厌我的作品。在他去世前我刚好见过他,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个人。在一个开幕典礼上,这个矮小,老态龙钟的人走到我面前,说:‘克洛斯先生,我想告诉你,对于你的作品,我犯了大错!我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不明所以,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犯了大错,我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十分抱歉。’这件事简直太神奇了!”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Katz)对克洛斯的讲述回应道:“每个人都有权改变想法。艺术家如此,艺术批评家也如此。”施杰尔达最初也不欣赏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的新具象作品。十年后,他在发表的文献上承认他终于认识到这些作品非常出色。
对艺术批评的批评
库斯比特在为艺术批评家文章选集写的总序中,基于这些艺术批评家对复杂艺术问题作出的精到解析,称赞他们为“大师级艺术批评家”。他赞扬这些批评家观点独立,赞扬他们拥有关于艺术批评的自我意识。他仰慕他们的热诚,他们的理性,他们对于教条主义的免疫力。“他们刺激我们觉醒。”
《伦敦星期日时报》的艺术批评家玛丽娜·韦西(Marin***aizey)在评论阿瑟·丹托的著作时,赞扬丹托的著作能让读者“去感觉,去感受,还有更重要的,去思想”,并且他的著作能把“一件特定作品所蕴含的纯粹的迷人魅力”给描述出来。”她对什么是好的批评,有一套判断标准,包括批评文字的文学水平、评判的格局要超越地域性,以及关于艺术的洞见具有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力能超越当代评论期刊那些文章所涉及的短暂时间跨度。
马西娅·伊顿赞赏H.C.戈达德(H.C.Goddard)的文学批评,认为他是一个“超级指针”,一名导师,启示我们要如何去思考和观察艺术,才可以让艺术给我们带来快乐。他不用去扭曲原文来让我们看到当中隐藏的含义,也不试图把他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并且,他在观点交流方面,抱持谦逊和乐意的态度。他是一名出色的引路人。
库斯比特、韦西和伊顿提供了一套标准来评判何谓好的批评,具体包括:对艺术的精到解析、批判性的独立精神、在批判过程中的自我意识、满怀热诚的思辨、对于教条主义的免疫、在不扭曲艺术作品原意的前提下对作品内涵令人豁然开朗的深刻理解,还有谦卑的态度《纽约杂志》的批评家凯·拉森(Kay Larson)还将“公平对待艺术家”补充为另一条标准。马克·史蒂文斯(Mark
批评和美学
艺术批评和美学活动时常重叠进行,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明显——特别是在当下,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被刻意消除。批评家通常针对个体艺术作品和这些作品提出的议题来进行评说,但他们的批评文章触及的范围,没有美学家文章关注的范围那么广。美学家倾向于提出有关“艺术”的主张和思辨,而他们所谓的“艺术”经常是指涉“全部”艺术。许多美学家撰写艺术专著时,整本书都不曾出现一件艺术品。如果一名作者试图建立有关艺术的哲学思想,那么,像这样大的课题,总有着宏大的目标,针对其中的部分目标,美学家罗伯特·斯特克有这样的说明:
同一套艺术理论可能会触及多重这样的议题,展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有时,也仅限于有时,艺术理论也会根据上述部分艺术特征,试图对艺术、艺术价值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进行定义,或对两者都进行定义。
关于艺术、美学和批评的怀疑
部分观众基本上认为当今艺术界,特别是在推销“现代”艺术时,是在“玩弄他们”。电视新闻周刊《60分钟》的节目主持人莫利·塞弗(Moley Safer)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一段节目应和上述观点,他在节目中对近期艺术及其推手大加鞭笞。如此看来,这些观众和塞弗先生对于本书复制和讨论的大部分艺术极有可能也采取同样立场。
也有些艺术家对于艺术批评的价值和必要性感到怀疑,他们对批评家侵入他们的艺术创作领域心怀不满,特别在他们认为批评家“根本不懂”自己的创作时,尤为如此。一些艺术家也对美学、批评或普遍意义上的“理论”都不感兴趣。他们常说“我只是想做我的艺术”,抑或如画家巴尼特·纽曼所说的,“美学之于艺术家,如同鸟类学之于鸟”。
美学、艺术批评和视觉文化
认同自己美学家身份的学者们在他们关于艺术的考虑中往往会忽略日常流行文化物品,但认同“艺术理论”这个词的学者通常都把流行艺术当成他们论述中的核心关注点。
舒斯特曼观察到:“流行艺术在美学家群体中根本就不流行……就算他们不是完全把流行艺术视为粪土,他们基本上也是将流行艺术视为没有灵魂、毫无品味的垃圾。”不过,舒斯特曼建议美学家不要轻易地忽视流行领域,不要以为流行领域没有意义、不重要、缺乏让我们洞见世界的内容。他提到:“对于高雅趣味和低俗趣味,对于美学价值和功能价值,我都坚持给予承认。艺术(无论高雅还是低俗)本身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即艺术能够以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层次上,得到人类的欣赏。”
视觉文化学者寻求把学术研究从所谓的“高雅艺术”扩展至所有人类创造的视觉物品,并考虑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含义。“视觉文化”这个词所涵盖的实物和影像,范围广大,对于这类学者而言,所谓“高雅艺术”(fine art)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杰茜卡·埃文思(Jessica Evans)是一本书的合著者,他们在把某些物品当作视觉文化物品来考虑时,甄别出他们最感兴趣的几样主题:“再现的政治;男性凝视以及关于女性凝视的可能性;‘镜像阶段’;恋物癖和偷宠癖;图像的复制;种族化论述所投射的“他者”。
倡导将视觉文化置于艺术教育中心位置的学者凯文·塔文(Kevin T**in),针对所有视觉影像——而非只是限定在“高雅艺术”范畴里的那些实物和影像,向我们提出如下问题:
在视觉文化中,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影像是些什么呢?在特定影像中我们有怎样的投入?这些投入是什么?我们能从这些影像中学习到什么?什么是我们从这些影像中无法学到的?这些影像是否能向我们表现或显示某种生活方式或感觉?这些影像是否能帮助我们宣泄我们内心的欲望,愤怒或快乐?我们是否相信这些影像带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残疾歧视或等级差别的意涵?这些影像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整理和被规管的?权力是如何在这些影像中或张扬或含蓄地得到表现的?
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都可以用来审视和评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所有人工制品。从这些理论中引申出的评判标准并不限于适用艺术馆内的那些艺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赏电影电视节目,都可以用到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