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空白艺论 李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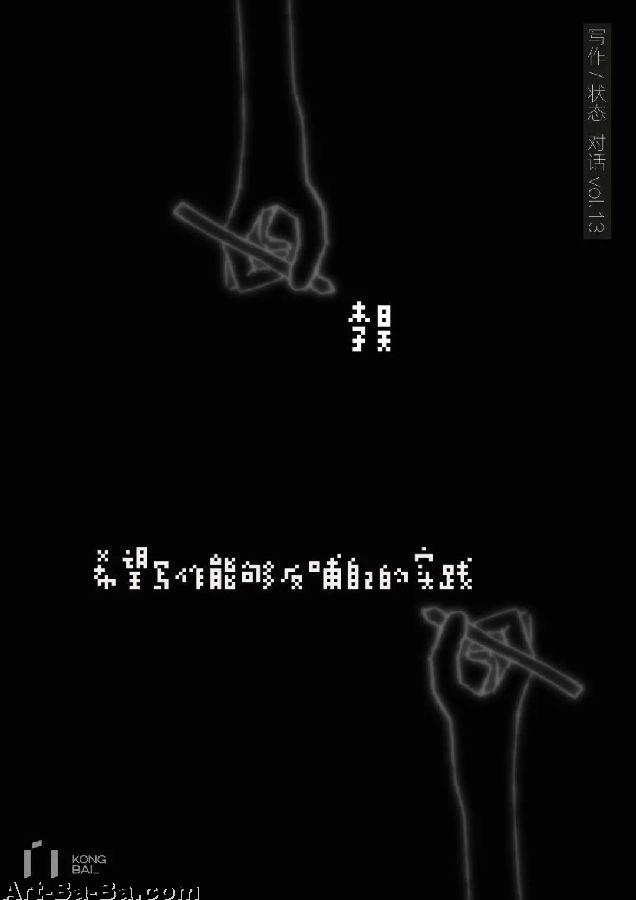
最近李昊兄将他的批评长文《绘画书写:锥股之刺》打散之后陆续发在了个人公号“下山工作室”上,这些文案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回应和讨论。艺术家从事批评/写作这件事并不新鲜,但是在当下,这种行为本身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回应,恰恰说明,艺术家们轻蔑的并不是批评/写作本身,而是如今已经泛滥的行活儿,而那些真正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文字,也即李昊兄所谓的“真批评”,即便不够成熟,不够学术,但依然有效而可贵。
旷:聊一聊最近的写作状态吧~
李:这篇长文写了一年,成稿之后断断续续改了一个月吧。应该说,最近这一个月挺有浓度的,有点像我印手制书或者剪辑第一部试验电影的那两次持续一个月的体验,只是这一次只能在带孩子的间歇中写作,时间没那么完整。修改增补、做减法的状态相比刚刚有个想法迸发出来去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有几次要崩溃了。尤其是当发出几期后,读者朋友们的反馈给了我挺大压力,因为我起了一个很大的头,总担心自己后面写得不够好。而且,有时候真的脑汁不够用,明显感觉到读书太少不能左右逢源或者不能自洽的痛苦,就像牙膏挤完了一样。当然也会有惊喜,马上要发新一期推送时甚至会在朋友圈捡到意外收获,比如在关于语义的那一章的开头我跟朋友李振洲的对话。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没有触及特别深的哲学或者美学问题,即使触及了我也假装不知道,因为目的也不是多么学术。
旷:为什么想到去写批评?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实践和写作的关系?
李:除了一些不成模样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什么写作经历,这是第一次这么正式地进行批评写作,虽然在真正写作的人看来它可能会很幼稚。写作的动因当然是我自己在艺术实践过程中的思考,文本框架的设定或者对其他艺术家的批评也好夸评也罢其实都是在拷问自己的实践。而最终我当然希望写作能够反哺自己的实践,就像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将们曾经的经历吧。
旷:我理解你的这种批评一方面是基于你对当下绘画现状的观察和反思,另一方面你的问题意识则直接源于个人的绘画实践以及实践中的困惑或疑问,你希望通过理性的分析去厘清自己的一些认知,最终还是要回到实践本身。你觉得写作是否给你的实践带来一些变化?未来是否会继续写下去?
李:最初的动机就是希望能够用自己对绘画长久以来的观察和思考,给绘画同仁们关于当代绘画要做什么、能做什么的一些启示。另外就是文章开篇前言里写的,觉得绘画应该战斗,应该结束自甘堕落的安全状态。
我是边写边廓清了一些自己的认知,尤其在阅读艺术家们的作品时,往往有意外的收获,让我对我应该写的内容有所深化。因为写作和平时思考触及的地方不会完全重合,写作有点被迫的意思,就会刺激自己的想象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在一种压力或者限制下人会比平时更加敏感。实践的话暂时还没有影响,但是我会更加理性地反省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会更严苛、更具体。
写作对于我还是适可而止吧,毕竟我还有太多想做没做的事情了,似乎除了画画,我很难持续去做已经做过的工作。当然,一些轻松一点的写作是肯定会继续的,毕竟我的公号得经常更新。
旷:写作是迫使自己深入思考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也是表达观点的利器,我觉得写作也不一定局限于长篇大论,精短的评论,朋友圈的留言,都可以被视为艺术写作,只要能够构成有效的交流和讨论。我在你的文章里看到一些朋友圈的留言截图,比如讨论“铁公鸡”那段,以及“真批评”系列发出来之后别人对你的回应,这些讨论很有趣,让我看到艺术实践者之间的“真交流”。这在当下似乎并不容易,至少在我来看,微信时代的公共领域并没被拓宽,公共舆论空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压制甚至消解了,一个事件产生后,只有站队和表态,而难以形成深入的对话,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想这其实也涉及到你为什么做公号这件事。
李:微信确实有它的问题,容易陷入“朋友圈”内部的自嗨或者自掐,很难达到公共性,但是我倒觉得可能更容易展开真交流,因为毕竟都有所认识,不会像素不相识的人扔过来一块砖一样充满敌意,但是毕竟网络本身或者说距离本身在塑造暴力的气氛,所以还是挺难有真交流的。
确实,我做公众号是想有交流的,不管是同行之间还是跟学生之间,但只是线上交流很耗时间精力,面对面还是难以替代。所以我也会弄“塔楼聊天”活动,会跑到荆州去跟朋友们聊天。前两天在荆州新风村双年展上,王鹏杰讲座提到了建立“共识系统”的努力。微信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它有面对面交流不可能有的广度。
旷:比如我们这种某种程度上,微信重新塑造了交流,让趣味相投的人更容易发现对方,但深入的交流依然需要线下,或者诉诸文字的方式。
李:对,立体的交流。
旷:回到你的批评,在推送前言里你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真批评”?如何判断批评的“真”与“假”?
李:“真批评”看来被大家当成主要的话题了。其实说实话,这一次的所谓负面的批评并不像我几个月前在“绘画艺术坏蛋店”发的对童昆鸟作品的批评那样是动机单纯的批评。我只是当时文章写出来很发愁,因为字太多怕没人看,所以想出来两种将文案打散重组的方式。抛出“真批评”也是一个噱头吧,所以自然也招致很多批评意见。
对于我而言,“真批评”首先有一个独立的前提,当然这种独立只可能是相对的。比如我批评认识的朋友必然没有我不认识的艺术家用词锐利,并且评述更具体而深入,这我必须检讨。语言学地来看,“真批评”由三个部分组成:真,是真实的感受,不弄虚作假,以“批评真理”为追求目标,是一种批评道德;批,是态度,是撸起袖子来放手诊断、勘谬;评,是切入腠理以内的具体评述,以理服人。
至于真与假的问题确实没有能够参数化的一个标准,但是你只要看这个批评用什么样的话语大概就能明白,比如如果通篇只是在艺术周边绕圈圈,不能痛入骨、肉,或者喜欢用一些时髦而无当的术语(褶子、根茎...),扯虎皮用一些跟艺术作品没什么关系的他学科术语吓人,或者即使是“表扬”也只会用很抽象的词汇等等。
旷:你提到在艺术周边绕圈圈,这个问题很普遍,你如何看待当下的艺术批评现状?是否觉得存在“危机”?
李:大多数批评的东西我是不看的,浪费生命。危机在这个圈子里基本早就有共识了吧。我在想,除了特殊交情或者为了人前献媚,批评家或者策展人有几个会去看同行的东西?遑论其他人了。
旷:批评/写作不能痛入骨、肉,只是在艺术周边绕圈圈,这样的文字自然没有人会去看,也就无法构成有效的交流和讨论,批评也就变得越来越无效,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李: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吧。首先是艺术市场起来以后,部分老的批评家从批评、策展中获得了话语权与经济实惠,因此开始形成圈子,批评成为利益交换的中介,于是开始做高空自由落体运动。其次,大量现在的中年批评家当时根本不是学艺术的,也不是出于兴趣,只是因为英语好而考了史论研究生或者读了学习班从此发迹。他们的特点是看了不少外文文献资料,能丢出两个冷僻词汇,但是基本不懂艺术。这两股批评家占据了现在各个话语山头。第三,资本主导艺术圈之后,批评话语的力量被削弱并且与资本形成雇佣关系,策展文案逐渐取代批评出现在艺术圈,大量披着学术外衣实则空洞、抽象的艺术甜话成了展览的装饰,自然不会再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第四,在当代艺术起来的最初阶段,艺术杂志扮演了重要的阵地角色,我就是在高中学画时在老师的杂志上看到了栗宪廷批石冲的文章。但是随着网络兴起,实体杂志受到冲击,并且体制内的职称跟发表开始挂钩,所以现在这些杂志成了假学术的集中营。微信推送的出现加剧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订阅艺术杂志?第五,一批海龟年轻的艺术批评家学来了非常技术化的西方批评话术,但是并非都对中国艺术生态有深切认识,她/他们的文案往往陷入学术控的怪腔调中,看那些拗口晦涩的文案还不如刷一部烧脑神剧。
旷:哈哈哈哈你对中年批评家的评价太精准了,很多人根本就是不懂艺术,即便不是英语出身的很多史论系学生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肯定不这么觉得,比如一定会有人举德勒兹的例子,其实培根并不认同他对于自己作品的解读,但这并不妨碍德勒兹的写作成为经典。
李:哇,你拿德勒兹的例子太太太高看他们了,那更早还有贾科梅蒂说萨特不懂他的作品。不是一回事,哲学家的观看和艺术家的观看不是一个维度,里面重要的不是作品解读,而是提供观看的通道,给别人启发,所以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是观看维度的错层问题。那一部分中年批评家们的不懂是没有艺术内部的判断能力,他们只会用一些理论去套,比如说社会学。
旷:我可没高看他们hhh,只是这帮人总会拿德勒兹们做挡箭牌,就像你说的,爱拽时髦而无当的术语(褶子、根茎...),不过,艺术内部的判断能力,究竟是什么呢?好像很难言说,所谓艺术内部,又是指什么?我想肯定不仅仅是艺术语言,也不是用趣味、灵性这种概念去含糊言之。
李:其实也很简单,这件作品好,好在哪里?他要能说具体就算对艺术内部的形式感知、语义系统等等有非常细化到的认知,然后就是说得准不准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敏感性问题,这个更难。不管是格林伯格还是奥利瓦,他们都有这种能力,所以他们推向国际的这些艺术家经得起时间考验。
旷: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我们的知识经验本身就来自格林伯格这些人的理论和话语,我们觉得他们推出来的艺术家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是在他们搭建的框架下思考,而无法脱离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经典叙事。同样,我们对于古代中国文人画的观看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我很认同你说的一点,就是写作者能不能进行非常细化的分析,可能再加上深入性,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至少能够构成一篇有效的论述。至于准不准,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界定,或者说,在不同的视角下,敏感的点往往有差异。我发现从事实践的人,更看重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有时候多少会带有一点排他性的感觉。
李:对,实践的人出发点不一样,肯定是一种局限,比如我看书,如果这个理论家写的不能跟我的实践印证我就会怀疑,就不想看了。但是我一本格林伯格的书都没有读过,不妨碍我进入罗斯科他们的作品。当然,当代艺术作品不一样,不能纯用视觉经验了,需要有知识框架的指导。
旷:现在是一个“作者之死”的时代,你怎么看待艺术写作脱离创作者意图这件事?
李:不管认不认同“作者已死”这一著名论断,它对于我们都意义重大。但即使我们面前的大多数艺术作品的作者都没有留下过自己的意图宣示,我还是不能断言艺术写作能够冷漠对待创作者意图,但至少我这一次的写作在努力抛开创作者意图而进行一场阅读的较量。
因为语言学家告诉我们的如下事实在我们自身创作以及阅读体验中屡验不爽:作者意图传递具有不确定性;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并非全知,有时甚至完全无知或者在极端的案例里曲解自己的作品(比如巴尔蒂斯不认为自己后来的作品有色情意味);作品携带了足够的讯息并且会在创作者缺席的情况下展开自己的独立言说;观者对作品有误读的权力,等等等等。因此,艺术批评大可不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但是,对作品无根据的浮夸式发挥也是我深恶痛绝的。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我的这一次写作意不在主观误读,而是希求以不同的评述角度给对于作品阅读仍然不得其门而入的朋友们提供可能的启示。等我稍微得空一点,会请朋友来对我写的这篇东西进行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真批评”。因为确实,我看的书太少,有些东西各方面都不是特别严谨难以自洽,甚至是很多是错误的幼稚的观点。我会做这么一个事儿来收尾。
旷:最后,推荐一两个你最喜欢的写作者吧,或者你喜欢的艺术批评文章/著作
李:我很惭愧,读书太少,大家普遍推荐的艺术写作基本没有看过,比如贡布里希、格林伯格、罗杰弗莱,就算了解也大多是二手渠道来的。想了半天可能还是读书时候看过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我影响比较大,那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艺术史写作,完全不同于一般编年史的那种冷漠。另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大二用一个暑假抄过一遍但是基本只看懂了一点点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从艺术史中提取概念这一方法给了我极深刻的影响,我昨天才反应过来,我写的最后一章《建构与漫游》其实就是“日神、酒神”精神的衍射。另外,我一位老师Marc DECIMO关于杜尚的书写得非常好,很广博很深入,国内只会复述艺术发生史的杜尚学者根本不在一个学术层面上,但是某出版社的译者翻了一半放弃了,现在很遗憾我也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去为他联系新的出版社。
李昊(下山工作室),1982年生于湖南。本科毕业于川美油画第一工作室,研究生毕业于央美油画第一工作室。毕业后游学法国五年,在奥尔良大学当代文学专业和巴黎索邦第三大学电影理论专业注册并听了少数课程,认识了两位对我的写作有启发意义的老师,其中一位是罗兰·巴特的学生,另一位老师的博士学位是关于语义学的,读书时尚且处于懵懂状态,所以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进行了语言学启蒙。同时,在奥尔良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巴黎吉美亚洲艺术中心的工作给予了我一种艺术史的视野。回国至今在湖北美院基础部工作了七年。
旷之,“空白艺论”主编,一个被迫以文字为生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