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空白艺论 王志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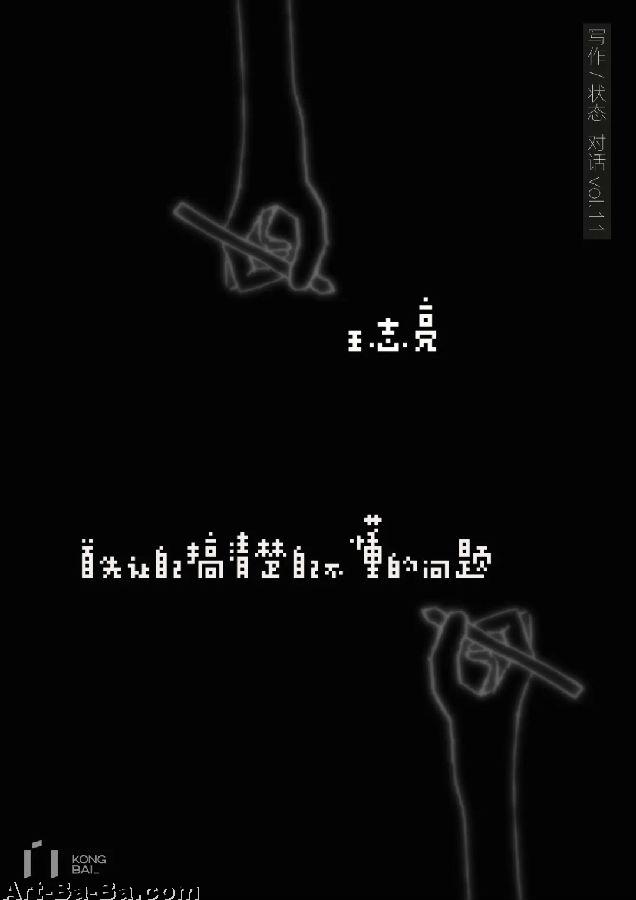
针对当代艺术批评的现状,志亮兄在17年撰写的《后批评状况,抑或批评的政治哲学转向》一文中,曾非常系统地论述过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构想。因此,在这篇访谈里,除了几个常规问题外,我主要针对《后批评状况》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些问题。作为一名从事艺术理论和批评史的专业研究者,志亮兄的回答态度鲜明,富有启发。或许,在讨论批评的问题之前,我们更需要清除关于艺术批评史本身的幻觉。
旷:聊一聊最近的写作状态吧~
王:时间方面,我一直很规律。一般早晨送孩子上学后,8点左右能开始阅读和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继续,然后接孩子放学。晚上孩子睡觉后,再工作一会。一年下来,一般上半年写新东西,下半年,尤其是10月份之后,大概就是开会和改文章时间。有人说开会就是浪费时间,但我觉得,开会至少会督促自己写作,你总不能每次开会都拿同样的内容蹭会吧,这样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内容方面,上半年刚完成一本书的书稿——《大众、体制和参与——前卫艺术理论的范式转向》,这部书稿有望明年和大家见面。内容主要是我2010年读博时开启的前卫艺术理论研究。上半年写完最后一部分,共30余万字,算是对自己前卫理论研究的一个工作总结。我的写作一直关联着三个领域,一是西方当代艺术理论和批评史;二是当代艺术批评的实践;三是中国80年代的美术史。第一项内容是我现在手头正在写的东西,第二项内容最近一年因为疫情,没怎么出去看展览,今年一篇也未成稿,第三项内容基本都已展现在我2019年1月出版的那本书中了——《话语与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的两个关键词》(上海书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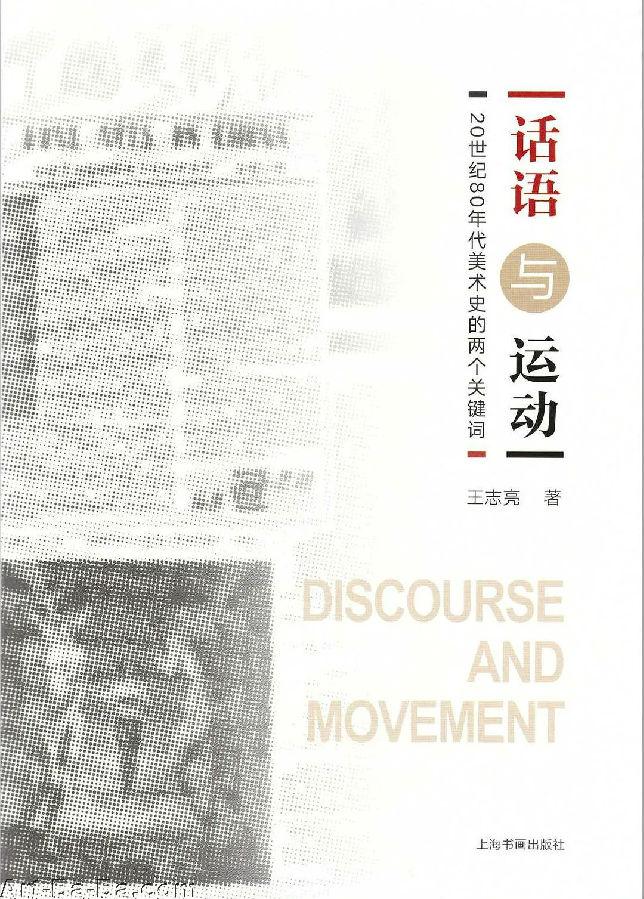
旷:对于你而言,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王:我在学校主要教授西方艺术批评,所以,批评方面的写作动力一部分归于自己的教学任务。面对学生,你总不能只说应该怎们写批评,别人怎们写批评,而自己却干着与批评不相关的事吧。另外,其他的写作动力主要就是一种工作状态,自明性——首先让自己搞清楚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当然,最主要的动力还是自己的兴趣,这与我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我在四川美术学院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经历,已经决定我不会去搞古代艺术史论研究,受高名潞、王南溟、沈语冰、岛子和王林等老师的影响,我在人民大学哲学院读博士时,也选择了牛宏宝老师的现当代美学方向。10年的学习经历和8年的工作经历,已经让我把研究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当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这些,还能做什么呢?读硕士时,在北京跟随高名潞老师策划展览,我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策展,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我还是喜欢书斋一点的工作状态。偶尔根据自己理论研究的趣味,去看看相关展览,写写评论,岂不快哉!
旷:推荐一两个你最喜欢的写作者吧,或者你喜欢的艺术批评
王:我博士的研究内容涉及《十月》杂志的批评家本雅明·布赫洛,我想,还是推荐他们这个团体的写作者吧,尤其是其中的豪尔·福斯特。现在看来,他们的写作有些过时,尤其是在西方,而且也很难读懂,但读进去之后,依然会受益良多。虽然国外现在基本不再关注《十月》,但这群写作者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批评史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我们国内的批评,依然极其缺乏类似《十月》编辑团体那样的理论敏锐度和高度的方法论意识,而且他们爱憎分明,喜欢什么艺术,不喜欢什么艺术,用的是哪些理论,推导出哪些结论,这些都有清晰的学术谱系。即便其他学者批评他们西方中心主义,搞小团伙,艺术倾向狭隘等,我觉得这都不构成问题。批评就需要一定的小团伙主义,如果当代艺术界出现多个小团伙,并且都清晰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有方法论意识,那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旷:在《后批评状况》中你指出中国批评家所谓的“失语”,是权力与能力的双重丧失。你觉得批评家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理论素养?批判性?还是对艺术的直觉?抑或其他
王:2017年那篇《后批评状况,抑或批评的政治哲学转向》一文,主要是受到豪尔·福斯特的启发而写。当代批评的门槛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如同策展的门槛一样,但要是做好,并不容易。我认为具有系统的知识结构是批评的基础,然后就是保持自己观点的尖锐性。因为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对当代艺术的判断有何价值取向,系统知识结构是基础。有人可能觉得直觉最重要,但我不这么认为。另外,就是观点要尖锐,喜欢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和稀泥”,没有棱角。批评应该是当代艺术领域最锋利的尖刀。只有不同批评家之间的喜好有别,我们才能进入到对话和碰撞的多元话语空间,批评的生态才能健康。当下,中国正是缺少多把尖刀对抗的情况。“和稀泥”式的多元化只能把批评拖入泥坑。
旷:文中提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批评家纷纷转行为策展人,关键原因是出于一种失落感,对于60后那批人确实有这方面因素,但对于80后这些新一代的写作者而言,他们一开始就选择了策展人这个身份,并从事写作,其实已经不存在批评职业化的问题,你觉得现在这种写作者、艺术家、策展人、学者等身份的重合给批评带来了哪些变化?批评的失语状态是否得到改变?
王:我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批评不应该职业化,而且批评自从产生开始,从来没有职业化过,例如从早期狄德罗和波德莱尔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批评从一开始就是处于“第三空间”。国内美术界讨论的“批评失语”,也是基于批评曾经有过话语权的幻觉。在1980年代,批评家们看似具有话语权,其实那是批评的幻觉,真正具有话语权的是作为编辑的批评家、他们同时还身兼美协职务。
现在写作者、艺术家、策展人、学者等身份在批评写作中的重合,我认为这是批评的正常形态。不同的批评写作者,会带来不同形态的批评。比如策展人和媒体工作者的批评写作,可能更简洁,对作品的感知更敏锐,涉及的面更宽。学者的批评写作涉及的艺术作品相对少,但喜欢写逻辑性的长篇,文字比较晦涩。
中国当代批评的问题是,现在处于一线的策展人少有深入的、理论化的写作,而呆在学院的学者则困于职称和考核的发表压力,无太多精力针对艺术现场发表意见。现实总是存在某种撕裂,能够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的批评家,我熟悉的不过几位而已。
旷:之前和子云聊他也提到,现在国内很缺乏学院批评。以各美院系统为例,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人普遍看不上批评,这点和西方差别还挺大的,像《十月》编辑团体中的不少人后来虽然进入高校,但还是对当代艺术抱有极高的热情。
王:这个问题得分几个方面看。从学院角度讲,自古学院就是一种保守机构,它所承载的都是一些即成事实,已成定论的知识。那些当代未成定论的知识,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常常以异端的形式存在,这是学院的属性使然。学院的这一属性决定了教师的研究方向、课程的设置等细节。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搞艺术史的,尤其是古代艺术史的学者,往往会轻视批评,但我坚信,优秀、明智的学者,一定不会简单地否认艺术批评的重要性。就批评的写作者来说,很少有学者依靠批评写作来某得一个教职,他们往往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比如现当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这又回到批评的业余性。学院批评的生产,很大程度上靠兴趣。不过,我们依然要看到这些年学院体制的积极转变。首先,学院开始设置专门的批评课程,这要得益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建立,艺术批评成为与艺术史、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三大基础课程之一。其次,学院中的当代艺术史、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教职也在逐渐增多。例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锋、董丽慧和李洋,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李笑男,央美也有王春辰、刘礼宾和赵炎等,鲁明军在复旦大学,何桂彦在四川美院,胡斌在广州美院,等等。总之,现阶段而言,依靠批评在学院立足,确实很难,这个需要我们积极争取。
旷:这点我相信未来会更好,像志亮兄和彦华姐是我接触的年轻一代里做的很出色的,子云毕业之后大概率也会进入学院系统,未来可期,另外王鹏杰虽然接触不多,但也是很活跃的一位,当然还有其他的青年学者,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王:彦华是女超人。我们现在写批评最大问题是无法评职称啊,很少有核心期刊发批评文章。
旷:所以回到“第三空间”的构想,是否有些理想?业余化即意味着要依靠其他身份谋生,这种平衡其实挺难把握的。
王:批评的“第三空间”也可以说是批评的业余化,这首先是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一般性描述,也是某种既存的事实。因此,我曾说过,“批评家之死”的观点,其实就是罗兰·巴特和福柯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者之死”的命题。今天我们如果依然固执于批评家的身份、话语权力,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主体中心化的幻觉。在中国这样的语境中,我们由于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批评家应该能够依靠批评写作自食其力,从而让这个“第三空间”很难纯粹起来,显得有些理想化了。所以,“批评家”这个主体,一经产生就具有了后现代的特征——分裂和去中心化。
旷:在《后批评状况》中你提到政治哲学被引入当代艺术批评领域,这是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转向的表现之一,而这种转向离不开参与式艺术实践在国内的流行,但参与式艺术并不是当代艺术的全部,面对其他形式的艺术,政治学或者说朗西埃的那套理论是否有效?
王:我当时谈到的政治哲学介入艺术批评,也只是说出了当代艺术批评的一种理论倾向。当然还有其他各种理论,例如针对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人类世等理论等。参与式艺术这几年在国内只能说是逐渐多起来,还远未到流行的程度,真正的参与式艺术可能永远不会流行起来。朗西埃的引入,确实特别贴合参与式艺术,但其他政治哲学理论依然适合,只不过国内批评界并未在这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如果按照朗西埃的意图,他的理论显然不是专门针对参与式艺术开发的,基本可以适用于分析任何艺术形式。
旷:距离《后批评状况》已经3年了,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或对之前观点的修正?
王:我现在基本还是维持《后批评状况,抑或艺术批评的政治哲学介入》的观点。批评应该业余化,而非职业化,政治哲学依然是当代介入艺术批评的有效理论,只不过,我们需要开发更多的政治哲学理论资源。后批评状况之后(其实就是当下的批评状况)的批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有这样一些可以不断完善的条目:1、政治哲学已是批评的有利武器;2、批评正在加速学院化,同时也在大众化;3、新一代策展人的批评写作呈现弱化趋势;4、受惠于当代传播媒介的发展,批评的传播渠道无限增多,同样受众也不断增多,在这个层面上,我不太认同詹姆斯·埃尔金斯的判断——他认为批评文本被大量生产着,也被极大地忽略着;5、批评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权力”幻象已经消失,批评正在回归它的原始位置——即业余性,永远不要心存职业批评家的幻想。
旷:志亮兄所说的批评的“大众化”是指什么?如果从微信端看,艺术批评依然局限在特定的群体内,阅读量通常很惨淡,即便作为展览的“标配”,都很少有人会点开认真地看完,这是否是一种“忽略”?
王:我说的批评大众化主要是指写作者增多了。所以,”大众化”在这里或许应该详细解释一下:首先是写作者增多,其次是传播渠道增多,最后读者增多。你所说的阅读量有限,这个要看和什么比。如果和我们80年和90年代的批评比,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批评阅读量应该是比以前多了。无论是一条的视频,还是《艺术论坛》的500字。所以我所指的批评、是广义的批评三大类:媒体批评、美文批评、学院派/学术批评。我们没办法说哪些是真正的批评,哪些不是真正的批评。所以,我对批评持包容性的态度,而我自己的写作算是学院派批评。
旷:我理解的“大众化”可能更倾向于去专业化,或者说依托于大众传媒的传播,而非艺术类媒体,比如《三联》、《新周刊》、《澎湃》上的艺术批评,他们的受众就更加趋向于普通读者,包括现在的一条内容,算不算广义的批评呢?这个可能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而大众传媒上的批评写作,由于面对更广泛的读者,在内容和行文上也会更加贴近大众。
王:同意你对大众化的解释。十几年前,《新周刊》上会有当代艺术批评专文,人事变动后,现在好像没有了。另外,搜狐艺术频道的批评算不算,凤凰网艺术频道算不算批评?😂
旷:孙琳琳是当时《新周刊》艺术批评的主笔,后来还出了书,包括张宇凌刚出的那本《竹不如肉》也是三联文章的合集,可能在我看来,新周刊和三联还是有一定口碑和用户基数的大众媒体,至于搜狐这些反正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看hhh
王:我对批评本身的现状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和80、90年代相比。往前看,我甚至想过怎么用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去做批评😂
旷:也有朋友建议我注册个抖音号,我还真注册了一个,但说实话,从传播上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成爆款,可如果不考虑流量,新的大众传媒对我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所以我选择还是在高校,做不了大V,先影响自己的学生吧😄那些想用批评影响更多人的批评家,很多就成了策展人。这就是批评的宿命吧。
旷:影响力是一种诱惑,批评史也助长了这种幻觉,比如波德莱尔、弗莱和格林伯格,在后世的书写中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似乎正是他们推动了当时艺术的发展,如果这是事实,是否意味着批评家曾经一度比较重要过?或者说这只是一种非常态?
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考虑:如果没有波德莱尔,德拉克洛瓦是否依然重要?如果没有格林伯格,抽象表现主义是否依然重要?如果没有罗杰·弗莱,后印象派是否依然重要?然后才是,他们是通过何种形式介入了这些艺术实践。波德莱尔是用写作的形式,据我读的文献所知,波德莱尔本身文学造诣要大于批评造诣;弗莱是策展和写作并重,格林伯格主要是写作。如果没有他们三人,在艺术史书写中,我觉得相关流派和艺术家还是会存在,只不过会是以另一种解释方式存在。其中,格林伯格我认为是美国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格林伯格之后,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其实,我们前面讨论的内容,并不是在否定批评的重要性,我只是一再强调不要过于沉迷于批评的某些特殊的时刻——那时批评家看起来可以呼风唤雨。批评依然重要,不在于有多人写,有多人读,而是在于我们在若干年回顾和书写艺术史时,批评文本是越不过去的一手材料,是解释艺术作品,讨论艺术作品历史价值的基础,所以我很同意把批评看作“艺术史的前史”的观点。
旷:我理解可能把批评视为一种介入当下的方式,而不要幻想通过批评获得话语权,认清这一点其实对批评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少一些功利性,这样筛选出来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对艺术对写作抱有热情和负责的人。
王:是这样的。批评不是争夺话语权,而是介入当下的方式,批评应该面向未来,而非过去。
王志亮,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教于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主要教授艺术批评、西方美术史、艺术史方法论等课程,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现当代艺术史论,先后在《文艺研究》《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优秀),教育部项目各一项,出版专著《话语与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的两个关键词》(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
旷之,“空白艺论”主编,一个被迫以文字为生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