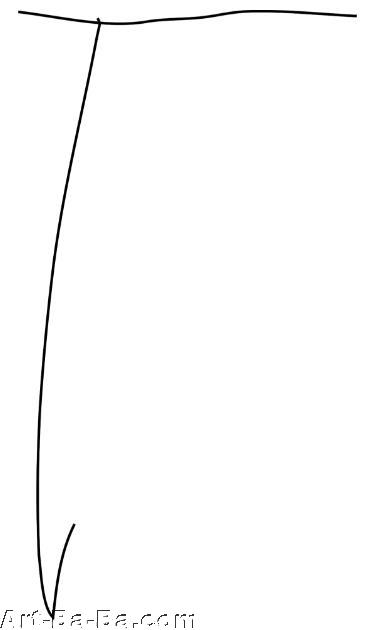来源:Trigger 触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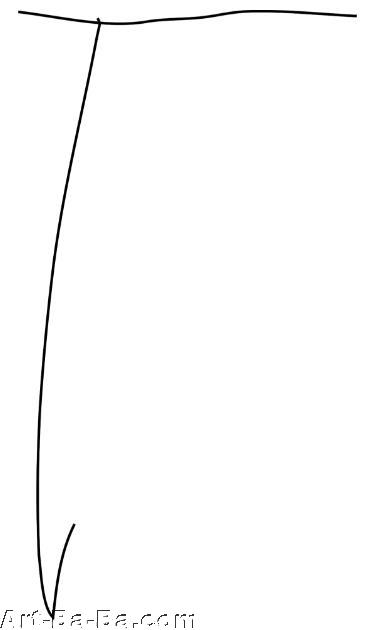

我大学就开始做影像了,因为我最早想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当时很想做综艺节目 ,可能因为小时候看《快乐大本营》看多了(笑)。但我的专业分考得有点高,老师认为我不选油画系可惜了,所以我上了油画系。后来我去北京,由于当时“学术热”的缘故,所有艺术家,哪怕是高中毕业的,好像都非要讲出一些大理来,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家。而我因为是油画系出身,没有很深厚的理论研究基础,也不是学习型的艺术家,对学术不感兴趣,所以如果非要逼自己去学,又觉得太残忍。当时我变得很焦虑,觉得自己可能没办法做艺术了。
隔了三四年后,我又尝试做了一些特别观念性的项目,但还是无法说服自己,总觉得它们不能够成立。后来,我跟大学老师聊天,他说:“你大学时的作品挺好的,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因此我开始按照我最喜欢的方式,做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影像作品。逐渐一些艺术家朋友或艺术从业者觉得好像这种形式还挺有意思的,我才慢慢地有了一些展示的机会。其实学油画有点像误入歧途,给了我特别大的空间。因为如果我真的去学电视或电影的话,在工业影视流程里,我肯定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也没别人做得好。但当代艺术就能给我一个空间,去做一些既像电视剧又不像电视剧的东西,让它们可以被称为作品。我通常在创作之初也没有太明确的观点,很多有关作品的解释更多是在作品完成后,一些评论人给了我一些他们的想法,在互相综合后,我发现好像是有那么回事,才放进作品简介里的。
我去上过一些表演的课程,模仿他们上课时的方式写了一些比较荒诞的剧本交给老师。老师在学生们都不知道剧本内容的情况下,根据剧本教他们做一些很夸张的表演。《演技教程》这个作品主要来自于我跟我妈妈的一次对话。她特别喜欢看电视剧,而且总是学电视剧里的东西,变得非常戏剧化。我很担心她,让她少看电视剧,不要再模仿了。然后她很生气地说:“谁模仿电视剧了,明明是电视剧在拍我!”我当时觉得她好像说得也挺有道理的,于是开始思考我们大众与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是我们在模仿它们,还是它们在记录我们?
这件影像作品叫《跳动的原子》。短视频社交越来越流行,甚至我的所有长辈都在使用。我当时也下载了抖音,花了很多时间看,发现很容易上瘾。我觉得这些时间花得特别不值得,一定要把它们赚回来,所以决定做一个作品。我在看抖音的过程中把一些很有意思的部分记录下来,写入我最初的脚本中,然后再找合适的人重新演绎它们。视频中坐在地上的女性是叙事的主体,我把自己比喻成她,通过她的叙述把所有碎片连接到一起,成为稍微有些叙事线索的片子,其中大多数内容是关于个体与社交短视频之间的关系。我在做这个作品时,想故意接近抖音和快手的视觉风格,为此我模仿了抖音的字体,影像使用了手机的竖屏形式。第一次在香港马凌画廊呈现时,我把投影墙的背面做成了手机金属后壳的感觉,从而让观众觉得它就是真的抖音视频。但所有内容其实都是我设计好后自己拍的,相对于直接使用抖音视频来说,我对这个作品的影像内容更有主导权。这个概念跟“后网络”(Post-Internet)不太一样,我并没有直接使用网络素材,只是借鉴网络上的形式作为材料进行再创作,它们并不能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
蔡星洋:这些文字和图像放在一起产生了某种尴尬、错位的美学,这是你刻意营造的吗?看多了这种类型的视频以后,观众能大概感受到它们的尴尬,但同时接收到特别多它们带来的碎片化信息。每个人将这些信息经过重组,会形成一个基于个人经验的东西。观众:你拍完这些短视频之后,有没有发到抖音或别的软件上?没有。我只是把这些软件作为作品的源头来使用,并不想让其最终成为一个抖音视频。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它会完全融入抖音的文化和世界观,而如果把它作为艺术作品,我也许还能加入一些批判的成分。
这个作品也特别大众、通俗,是个基于场域的创作。有一个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画廊,旁边是音乐学院和医院,很多来上海看病的人聚居在附近,因此周边有很多月租房。我找了一位台湾作曲人帮我写旋律,要求是一定要像流行歌一样,让观众听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我又找了一位法国女孩和一位中国女孩,一边唱一边讲一些我写的类似歌词的文字。我当时想把这个作品用喇叭对着社区播放,让住在附近的人产生一些感受,但后来被社区拒绝了,因为他们不希望听到这些声音,所以最后改为在画廊空间里展示。装置中间有一个全息的电风扇,它旋转的时候会显示一个鬼魂般的透明影像。但影像的嘴型和声音是完全对不上的,因为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影像,而是一个混合的、没有刻意指向性的东西。

南方戏剧史作家冷水花青年时代 No. 1,2018
南方戏剧史作家冷水花青年时代 No. 2,2018这是我在台北做的一个项目。它目前有三件作品,大概占到这个项目总预期的三分之一。我之前很想找一本书叫《南方戏剧史》的书,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并没有这样一本书,所以我自己虚构了一个叫冷水花的作家,她写了这本书。在《南方戏剧史作家冷水花青年时代 No.1》和《南方戏剧史作家冷水花青年时代 No. 2》两件作品中,我找了一位台湾演员来演绎这位虚构作家年轻时代的形象。
《南方戏剧史A幕》的部分则是一个机械的手写装置。它写的内容是《南方戏剧史》这本书里的一些部分。在这个虚构故事中,由于这个作家已经不在了,我还在她生前给她拍了一段采访的影像作为《南方戏剧史A幕》的一部分。我现在所完成的这三件作品相当于是塑造了这个作家。在剩下的部分的项目中,我可能会把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六部电影,拍成片段呈现。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故事、人物、事件立体地虚构出来。蔡星洋:为什么使用机械手臂,而不是一个更像人类身体的装置?你是否有意让人感觉到一种机械性?包括你的其他作品在选择使用显示媒介时,也使用了一些电子设备,这是一种刻意吗?这个机械手可以模仿不同人的字体,现场效果就像是真的有人在拿着笔写一样。我很喜欢通过一些设计,虚构一些不在场的人物,但又让观众感觉其鬼魂在那。

《多余的》是件特别戏剧化的作品,关于一个有六根手指的女孩。她的父母为了她多余的这根手指发生了争执,家里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当时我想模仿电视、电影里的那种表演方式,所以研究了一些不同类型影视作品中的表演,其中也涉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我先以电视剧的方式拍摄了我写的剧本,之后再把它作为材料,通过我自己的旁白分析了每个人物,从而建构出这个作品。画面中,我把所有背景和颜色都去掉了,只留下人物、一些能交待环境的道具和表演本身。在展览现场,影像的旁边有一个透明的播放器,里面藏了一根被烧焦的手指。这相当于是除了平面化展示外,衍生出来的实体,让观众觉得这不光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也许还有现实的延伸。


首尔现当代美术馆现场
这是我在首尔做的作品,也是我做创作以来最工业化的一件。韩国的影视制造业很发达,当时美术馆找了一个制作公司帮我做这件作品,走的全是工业影视的流程,就像真的拍韩剧一样。我是导演,下面有副导演和其他职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甚至还会给我写的剧本提一些建议,所以我自己能做的工作很少。在韩国,娱乐产业被当做一种政治手段,它映射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也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年有很多没办法复出的偶像明星面临很大的生活困境。在这个作品中,我虚构了一位已经去世的偶像明星,他回到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记者都跟着他。我做了两块同步的屏幕:右边的内容是记者们跟着他去他生前比较熟悉的地方,对他做有关娱乐产业的采访;左边的内容是一个教室里,老师在给学生上课,讲解采访里话语之下隐藏的一些含义。观众:您在对于播放形式的选择上,是非常具有主观性的。这个方面的选择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这更多是形式上的考量。因为我本来是学视觉艺术的,很多人觉得我拍的录像可能会受到绘画专业的影响,其实不光是那样的。我拍影像时,更多是直接挪用了一些现在大众媒体的方式,比如说电视剧,它们喜欢怎么拍,我就怎么拍。受到油画背景影响的反而更多的是在展示形式上。我把所有作品都看作我绘画中的某一个部分,而展厅的平面图或展示场域才是我的画布。假设我做了一个影像,我觉得还需要搭配一个另外的装置或某种播放形式去承载和连接这些琐碎的片段,从而达到平衡。因此我特别关注有关显示的技术,一旦发现有什么新的技术,肯定要试验一下,如果有合适的,就用在新作品上。观众:你的作品里有特别多的信息,包括声音的替换、给予屏幕里的人你自己的故事、在现实中暗示观众需要互动等等。你是如何把这么多信息层级组合到一个作品里的?你觉得能让作品很丰富,但又保持统一的要点和逻辑是什么?把这些信息整理到一起的逻辑是,我希望我的作品内容看上去比较大众化,然后通过一些新的叙事形式,让作品变得更丰富。艺术家除了把内容作为创作的核心,同时还是要做一些相对理性的设计,让作品更能与观众发生关系。作品的大方向通常来源于早期脚本的写作,而这些更为细节的设计则是来自后期拍摄时做的妥协或改变。

《德黑兰的黄昏》就是妥协的产物,是我第一次驻留时在伊朗做的作品。因为在伊朗拍东西有诸多限制,很多伊朗导演都是在车里完成拍摄的,我去了才发现这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既想在公共空间活动,又想自由拍摄的话,在车里是最安全、方便的。我找了一辆车,让一位伊朗女孩穿了一身伊朗的婚纱,演绎梅艳芳在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上穿着婚纱跟歌迷的对话内容。梅艳芳在之后就因乳腺癌去世了,当时她觉得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但是还没有结婚,她对婚姻是有向往的。我在伊朗跟一些女孩聊天时,发现她们对婚姻或恋爱也是特别有憧憬的。虽然是在两个完全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人们所憧憬的许多东西其实是很相似的,所以我让一个伊朗女孩来复述梅艳芳的这段对话。蔡星洋:你很多作品中都使用了虚构的叙事而并不是真相,通过错位感而呈现出批判性。你觉得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这种虚构是成功的?它该给人造成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感受该如何拿捏?提取出各种真实的片段,把它们拼贴到一起,好像是超越真实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虚构出来的东西比真实更真实。我觉得有时候要看观众的反馈。《Double Talk》拍完后,我自己其实不是很满意,因为制作公司在剪辑时把它当做一件商品在制作。但这个作品在韩国展出后,我收到了特别多偶像团体粉丝的邮件。虽然很多来信里的内容都是误读,但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一直希望我的作品能跟越来越多地大众发生联系。蔡星洋:在思考你的观众时,你是否会担心自己在其中想要强调或批判的部分,或是想要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消失或被误读?我做作品时,并不想制造一个观点让观众相信,而是希望呈现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和视角,所以批判和赞美的成分会同时存在。比如说,《跳动的原子》大部分讲的是我个人或其他人与社交短视频之间的关系,而《Double Talk》里也没有明确的观点表明娱乐产业是好的或坏的,而是把娱乐行业里产生的一些社会现象都一起呈现出来,所以误读就不存在或不太重要了。只要作品能让观众找到一个入口进入并与其发生关系,对于我来说,它就成立了。观众: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其实是在以你自己的方式,对当下热点的一些问题或讨论进行记录?对。有一些事件,在某一个时间段引发过比较火热的讨论,然后就被遗忘了。我做的事就像是把这些所有的讨论融合在一起,不会说我觉得哪一方是对的。我认为肯定没有一个完全客观的现实,每个创作者都会带有不一样的个人观念,但我所排斥的是,重复别人已经盖棺定论的东西,从既有的理论出发做创作。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在作品中带有明显的指向性,而是让观众从各种角度的观点中,根据自身经验,挖掘自己选择相信的那一部分。
Christoph Keller,Hito Steyerl,Tao Hui,2019
Esther Schipper,Berlin
© Andrea Rossetti
蔡星洋:我留意到你之前跟Hito Steyerl同时做过一个展览。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有比较喜欢的或是受其影响较深的艺术家?
Hito Steyerl那种艺术家其实不是我喜欢的路线,因为她太理论了。我比较喜欢的艺术家一定是视觉方面比较独特的,比如说Philippe Parreno。做影像的中国艺术家中,我喜欢杨福东和曹斐,特别是真正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后,会发现他们其实是特别有能力的艺术家。我很羡慕他们,因为很多艺术家在审美和想象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创作真的很考验执行能力。如果有好的想法,但无能力执行,是很难达成好作品的。蔡星洋:你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方式?这些作品和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关系?你如何处理作品中的叙事和情感?
我一般是基于场景进行写作。以录像为例,我先会选择拍摄的具体物理地点,再根据场域开始写作,最后拍摄。做其他类型的作品时,也一定要知道有关的现实成分后,才会开始实施。这样的方式比较节约成本,也更好控制。而文本的内容大多也好像是记录了一些碎片的东西,再做整合。如果真的要谈剧本的戏剧性,肯定是不足的。我也很想考虑剧本的完整性,但是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的创作周期特别短。比如说,我可能花一个星期把剧本写出来,花一两天就拍摄完了。在拍摄的阶段,可能要做很多妥协,现场操作起来会跟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在很多地方拍东西都像偷拍一样,总是有人在赶我们,经常随便拍一遍就走,没有特别严肃地对待。所以说,如果写得太具体,反而实施起来会比较困难。后期还有一部分创作可能是在剪辑阶段发生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外滩美术馆现场
能让大众感受到一些共鸣好像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事情,这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很喜欢做一些没有艺术背景的人也可以去感受到的作品。
观众:您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您本身就想让您的作品能更好地在公众之间流通,还是说只是因为您在生活当中与大众性流行文化相关的东西接触得比较多?我觉得都有,首先我倾向于创造这种东西,所以生活中肯定也会更多地接触到。因为我不太喜欢太精英化的东西,我自己也完全看不懂,除非给一叠很厚的作品叙述才能大概了解一些。但现在中国有这个背景理论知识的人太少了,包括很多艺术家也不见得就有,所以我倾向于创作一些能让更多人懂的东西。观众:您在把通俗文化转化成艺术作品的过程当中,思考逻辑是怎样的?您最想抓住的点是什么?我选择的内容一般是被一些人关注,但是好像又被更多人忽略了的东西。最开始我选择拍类似肥皂剧的作品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后来在北京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他们比较排斥国产电视剧,都喜欢看美剧。我住在中国,所有的亲人、高中和初中朋友都在关注这些,但艺术界却觉得这些我们身边的东西很垃圾,反而去关注更精英化的东西。所以后来我有冲动要对这些被很多人忽略的东西进行仔细观察,然后做一些作品将它们呈现出来。

蔡星洋:但是你说的这种去精英化的创作,最后反倒被放到了一个精英化的语境之下。国内很多艺术家现在都尝试做一些看起来接地气的作品,常常会显得有一点做作和故意。怎么避免这种状况?我觉得首先自己要喜欢和了解这些东西,才能去做。如果从小在一个跟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环境里成长,只是为了迎合大众,而非要做相关的作品,就肯定会显得很做作。艺术家的创作一定要能与其生长场域产生关系,才有可能成为好的作品。
观众:提到有关于商业化的部分,很多大众在把艺术当作一种娱乐和消遣前提下去看展,您在未来的创作中是否会排斥这种娱乐性和商业性?我不会特别介意,但会做一些选择。如果非要我刻意迎合商业,做一些创作,我觉得肯定没办法接受。但如果刚好跟我的作品有所契合,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艺术家和流量明星的合作以后,那些普通歌迷都开始去美术馆看展览,了解和学习艺术。这可能对整个行业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我对网红展本身是认同的。网红展本来就是给网红的展,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可以拒绝。虽然它不完全是艺术,但能让另外一些人更贴近艺术,至少对部分人产生影响,我觉得还是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