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蒲英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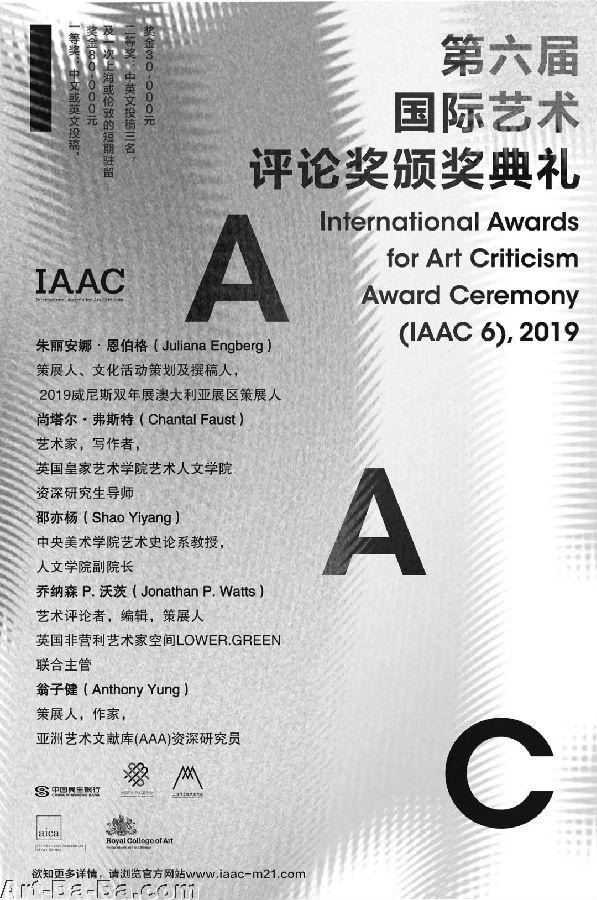
蒲英玮,艺术家,1989年出生,现工作、生活于中国北京。2013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8年毕业于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并获得评委会最高嘉奖。
为什么历史,
为什么现实,为什么政治?
蒲英玮:
如果说今天,或者在任何时刻,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与现实是被书写、改写、并重写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接收到的世界面貌是一种由某种力量所引导的“写作”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去“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真实,从来都是模糊的;是需要人们、并且需要不同身份背景和立场的人们,去不断地识别、描述、想象、并践行的一个未竟的志业。很难去设想在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浓度极高的社会语境中去生产一种“没有愤怒的审美”;总之,它不是我看到听到或者感知到的世界。政治,只是一个临时的词语。也许是文化、也许是生活、也许是其它别的什么,但在此时此刻,“政治”就是那个可以激起波澜,或者说让我们或许会感同身受的那颗石子。也许明天,所有人都有权利去写、去表达、去交流了,政治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
或许,“踱步”一词本身所折射出的蹒跚姿态就足以代表着新中国美术在其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坎坷与艰辛。回顾这姑且被命名的“70年新中国艺术发展历程”,在为我们今天的审美和语言梳理了无数条线索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种脉络还是不可避免地交汇于1942,不断地重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换言之,新中国美术的叙事之舟一直是被放置于政治与历史的洪流之中;时而乘风破浪,时而逆流而上,或奋进或欲坠飘摇。至此,艺术从未幸免。纵观这70年的走过,无疑是一部搅拌了家国、民族、记忆与阵营的共构史;而这种卷入式的「生命-历史」形态则是生活在这片疆域中每一个个体深陷其中的真实境况;就像在陈逸飞所描绘的《踱步》中那些半透明的灰色形象:也许卑微,也许曾经伟大,但今日我们都成为了无名者,所有悲伤的人都将失去名字。
同时,《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其平行于建国史的叙事方式无疑让新中国艺术史被牢牢地镶嵌在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结构之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机器”继而能够伴随着国家权力向外输出,但这种与权力的共舞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自省维度的丢失;因为权力不容置疑,但艺术的内在动力恰恰来自于其富有批判性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但纵使展览将观者面前的一切作品与形象都视为“新中国发展的图像史证”,我们也依旧能够在这种积极的叙事流中找到缝隙。例如,在陈烟桥绘制于1933的木刻版画《都市背后》中,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如古元在其《鞍钢的修复》中所展现出来的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热忱;《都市背后》悉心描绘了生活在“新城”外围的人民;描绘了他们的生存与劳作以及简陋房门之外所堆砌的杂物;陈烟桥似乎预言般地看到了中国在不断地向现代城市化进发的历程中(三个五年计划、或是改革开放以及现在的智能城市),人民,所为其付出的代价。而时至今日,无论是面对愈发严峻的房产经纪或是苛刻的户籍政策,那些在寒冬中被驱逐出城的一个个背影在提示着我们,提示着历史:这并非全然盛世。而这幅1933年的《都市背后》在今天也依旧应景。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中展出的1933年陈烟桥的版画《城市背后》,与出版于1978年《文艺报》中关于城市化所呈现的两种辩证视角。
诚然,历史总是被现实所无限地召回并又生成新的模样。曾经的红色叙述,与我们所正在历经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意志的增强不谋而合,而这种民族意识裹挟着国家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生成为一种极为强势帝国化世界主义思潮;如果说在60年代我们向世界输出了颠覆一切的抵抗因子,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困和饥饿。”则变成了我们通行于世界的漂亮姿态。在展览中,由恽圻苍与杨尧于1973年共同绘制的《国际歌》里,“亚非拉”人民共处于一间富有象征意味的列车车厢中,身着各式的服装,满载着各自的行李,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而在一位拉美裔的友人身旁,则放置着一份他刚刚读完的“北京周报”,似乎那是一份来自未来的指示。这份关切的、具有指引性目光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并不陌生,在肯尼亚、中非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等那些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中国的援助性建设方兴未艾且如火如荼。从新中国早期的建交到此刻的援建,中国与亚非拉阵营所组成了似乎坚实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其共同体内部的残酷与复杂性也被我们笼统地表述为一种:大国姿态与世界主义精神。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中展出的恽圻苍与杨尧在1973年共同绘制的《国际歌》中关于《北京周报》细节,与1965年出版的《世界知识》封面所刊登的毛泽东会见刚果妇女的照片。
那么,新中国美术真就的从此而始,又从此而终么?展览《踱步:七十年的走过》的最后一个章节“时代与步伐”终止于90年代初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那么之后至今的30年历史又去了哪里?断裂,这种断裂首先出现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斩钉截铁地拒绝,而第二次断裂则出现于新中国美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歧途。从无名画会到星星美展,再到之后的“89现代艺术大展”以及今天的一切,“中国当代艺术”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尚未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段历史。但无论官方的话语承认与否,中国当代艺术都无疑继承了这近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顽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且不消说,之后的“后感性”展览、社会介入式艺术的兴起以及近期的“档案转向”都与中国自身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身体、政治、土地、行动、人民,似乎就连时下的科幻热潮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由于话语空间的压缩而产生的“替代性方案”。而令人理解而又略带惋惜的是,种种这些实践都在70年这个节点,变成了展览中未曾呈现的声音,成为历史的幽灵穿梭、回响在整个由革命现实主义图像所构建起的单一语调之中。也许,这不是永远,只是尚未到来。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览手册影印与展览所呈现的六个章节
今天,我们也迎来了我们的国度,它坚信这将是属于它的时刻。这些诉说着它历史的图像为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留下了诸多线索,而那场发生于80年代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中所牵涉出的关于“真实”的论述与其背后的整个现实主义绘画历史则是有待我们重新去挖掘并构建的宝贵历史遗产。它可能能够成为去矫正这台吞噬一切的庞大机器的一个渺小参照;或至少,他让我们在这场浪潮中保持着卑微的清醒,孑孑而立,形影相吊,但或许,我们并不会孤单,并不会孤单。
图片资料致谢蒲英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