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
这是迄今为止,阐释现代艺术繁荣写得最好的一本书。这是一幅罗伯特阿尔特曼式的全景图,展现了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星期日泰晤士报》
《艺术世界中的七天》

内容简介
萨拉·桑顿花了五年的时间,走访六城五国,将其 280 次采访整理成7 篇故事,为大家探索艺术世界的秘密,是了解现代艺术的指南。在这一系列的叙述中,萨拉·桑顿带领我们参观了佳士得拍卖行上演的喜剧,村上隆工作室的艺术创作,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上的艺术精品,《艺术论坛》杂志的执着,透纳奖背后的竞争,尚未走入市场的加州艺术学院的艺术评论课,以及威尼斯双年展的仙境。
作者简介
萨拉·桑顿,作家,文化社会学家。出生于加拿大,目前定居伦敦,曾为《经济学人》当代艺术的首席撰稿记者。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取得艺术史专业的硕士学位,于格拉斯哥的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全职讲师,后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做访问学者。早期的作品主要围绕亚文化、媒介和文化传承,近作则聚焦于艺术世界和艺术市场。
经常以艺术史学者与社会学家的双重角色为文剖析艺术世界的人生百态与社会各种次文化中的现象。桑顿的《艺术世界中的七天》与《俱乐部文化》(Club Cultures)二书出版后甚受好评,并曾译成多种文字。她有关当代艺术世界与艺术市场的文章曾在《经济学人》、《艺术论坛》、《纽约客》刊出,她也是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电台(BBC)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撰稿人。
译者简介
何云朝,供职于央视,资深译者,译有《地球村里的喧嚣》《设计的魔力》《从柠檬到柠檬汁》。
书籍摘录
前言
《艺术世界中的七天》概括地描述了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我写这本书用了五年时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当代艺术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人丢掉自己的老本行,开始自称艺术家。艺术品市场不断扩大,越炒越热。五花八门的艺术品在赶超潮流的同时,价格屡创新高。
当代艺术界是一个松散的网络,由许多崇尚艺术的交叉的亚文化群组成。亚文化群遍布全球,主要集中在纽约、伦敦、洛杉矶、柏林等艺术中心。此外,格拉斯哥、温哥华及米兰等地的艺术群体也很活跃。这些地区远离艺术中心城市,但是那里的艺术家都愿意留在当地。 20 世纪,巴黎和纽约是绝对的艺术中心。进入 21 世纪,艺术品市场在更多的地区陆续发展起来。
艺术界存在六种占据支配地位的角色,分别是艺术家、艺术品交易商、策展人、评论家、收藏家和拍卖师。有些业内人士身兼二职,既是艺术家又是评论家,或者既是艺术品交易商又是收藏家。这些业内人士承认他们的这种双重身份不好把握,因为两种身份有时会出现矛盾,有时会互相影响。在艺术界,最难达到的是成功的艺术家,或者叫做可信任的艺术家的位置,但主宰艺术界的却是艺术品交易商,他们支配、引导着另外五种角色,控制着他们的步伐。本书中经常提到艺术品交易商杰夫·坡(Jeff Poe)说:“在艺术界,权力不重要,关键在于控制。动用权力,那是粗俗的表现;巧妙地控制,才是明智之举。控制,从艺术家开始,他们的作品是市场运作的对象,但他们在创作之前,必须跟艺术品交易商好好商量一下。艺术家与艺术品交易商互相信任,心照不宣。这才是艺术界的游戏规则。”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艺术界”的范畴远远大于“艺术品市场”。艺术品市场中的主角是买卖艺术品的人,包括艺术品交易商、收藏家和拍卖行的工作人员。通常,评论家、策展人以及艺术家本人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另外,艺术界内的许多人不但从事纯艺术方面的工作,而且将他们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跟艺术有关的活动上,可以说,他们整天都泡在艺术界里。艺术界是一种“符号经济”,人们在艺术界里交流思想,重视创意,普遍认为文化价值是值得被讨论的,认为艺术价值比赤裸裸的金钱更有意义。
人们经常将艺术界看做是没有阶级差别的领域,来自下层社会或中产阶级的艺术家可以跟身价千万的基金经理、文质彬彬的博物馆馆长、引领潮流的时尚设计师以及“创意天才”一起喝香槟。如果你被这种现象所迷惑,认为艺术界内是平等、民主、不分高低贵贱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正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说,当代艺术界是一个“名利场”。声望、信誉、臆想中的“历史意义”、所属机构、教育背景、表现出的才能、财富、藏品规模等方面决定着圈里人的社会地位。当我身处艺术圈的时候,我看到所有人都在追名逐利,所有人都在往上爬。其中最拼命的是艺术品交易商和收藏家,艺术品交易商费尽心机地想在艺术品交易会上搞到一个位置好的摊位,收藏家则为能否第一个得到某位艺术家的“杰作”而忧心忡忡。一位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约翰·巴尔德萨里(John Baldessari)讽刺道:“艺术家都很有个性,不同情况下能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硬要把简历塞给我,还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多么有才,我很反感。我一直在想,如果能佩戴臂章或者肩章,就不会这么烦了。大家去惠特尼双年展(Whitney Biennial)或者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的时候,这样别人也会一目了然。艺术家应该像军人那样戴上军衔肩章,这样别人一下子就能知道你的地位了。”

如果艺术界还存在一条规则的话,那么这条规则应该是:艺术本身最重要。有人坚信这一点,有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冠冕堂皇的幌子。不管怎样,总有一部分人认为艺术周围的社会是一个与艺术脱节的肮脏世界。
我在研究艺术史的时候,有幸接触到了许多近代作品,但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些作品是怎样流通的:为什么有些作品就受到了关注而频频曝光?为什么有些作品就一直蹲在冷宫里无人问津?那些受到关注的作品被出售、收藏、展览的过程是怎样的?如今,在世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教育中占着更大的比重,这就需要去弄清楚艺术的源头,艺术品的评价过程,以及艺术品从工作室到博物馆(博物馆,垃圾桶,拥有大量藏品的机构或个人都有可能是艺术品的永久栖息地)的流通过程。某公共艺术收藏机构的负责人罗伯特·斯托尔(Robert Storr)告诉我:“博物馆的作用就是毁灭艺术品的价值。博物馆从市场上把艺术作品请进来,把它们变成了公益性的东西。”经过研究,我发现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这些作品不单单是由艺术家及其助手共同创作的,同时也是由艺术品经纪人、策展人、评论家以及收藏家共同成就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再优秀的作品也无法“伟大”起来。这并不是说艺术品本身不伟大,也不是说艺术没有资格进入博物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艺术品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神秘。
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的一种信仰,这是本书的一个观点。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说过,当人认识到自己仅仅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时,他只能“超脱一小段时间”,很快他就会苏醒过来坠入尘世。培根说:“美术,或者说艺术,已经完全沦为人们的一种消遣方式……艺术家必须想方设法地取悦大众。”对于许多艺术圈内人以及狂热的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就是新奇的想法,有了新奇的想法,他们的存在才有意义。这种观念与宗教信仰存在一定的冲突,但符合因果论者的思路。教堂等宗教场所具有特定的社会作用,艺术活动也同样具有特定的社会作用,它使存在共同利益的人们产生一种归属感。当埃里克·班克斯(Eric Banks)离开一家艺术杂志社去编辑一份文学评论杂志的时候,他发现艺术圈里的社交行为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人们在观赏艺术作品的时候,确实会展开讨论。但如果我读书,比如读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 的小说,几乎就没有人跟我讨论。阅读不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整个阅读过程都是一个人进行的,而艺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催生出一个群体来。”所以,跟文学相比,艺术具有较强的社交功能。
艺术界是一个拥有虔诚追随者的社会群体。尽管艺术界的人士自命清高,但他们还是在乎大多数人的意见,仰仗某位名家的积极评价或某位批评家的评论。同时,尽管艺术界崇尚标新立异、颠覆传统,但艺术家的一些行为方式仍然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艺术家创作一些“看似艺术”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从不破坏规则,相反,他们维护、遵从着业内既定的规则。公共艺术收藏机构的管理人员始终迎合着同行和上司的口味。收藏家成帮结伙地购买时尚画家的作品。批评家不时地抬头看看“旗帜”飘动的方向,以便“与时俱进”。一部分人斗胆创新,但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得到回报。只有为艺术献身的人站出来,其他人才有了存在的理由。
本书写于艺术品市场空前繁荣的时期。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中,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如此迅猛?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先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艺术越来越热?书中好几个地方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妨在此直截了当地给出自己的答案。第一,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关注具有更多文化内涵的事物。艺术可以激发想象力,可以活跃人们的思维、陶冶人们的情操。由于文化领域中的部分产业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相当多的人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期望得到出乎意料的收获。第二,尽管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人们的阅读量却越来越低。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充斥着整个文化领域。尽管有些人悲观地将它们称为“次级口头表达形态”,但其他人还是热衷于“视觉文化”的说法。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不仅在感性上,而且在理性上都使自己得到了愉悦。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艺术跨越了国界,成了全球通用语言,将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艺术品越来越热的另一个原因是昂贵,或者说奢侈,这很有讽刺意味。天价吸引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于是舆论将艺术品定位为奢侈品,相应地抬高了某件艺术品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全球最富有的那部分人掌握了更多的财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全球著名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拍卖行的艾米·卡布拉佐(Amy Cappellazzo)说:“在拥有了几套房子,又穿上了名贵西装之后,你会干点什么?艺术品是个不错的选择,总得玩点儿高雅的吧。”如今,收藏、囤积艺术品的人数大幅增加。2007年,佳士得拍卖了793件艺术品,每件都在100万美元以上。在数字化时代,文化产品的复制十分简单。在这种技术背景下,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几乎就成了像房地产一样的不动产,不会说没就没,不会贬值到离谱的程度。以前,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拍卖行购买艺术品,现在艺术品拍卖会上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拍卖会加快了艺术品的“市场流通速度”,其火爆场面似乎在告诉人们,当代艺术品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投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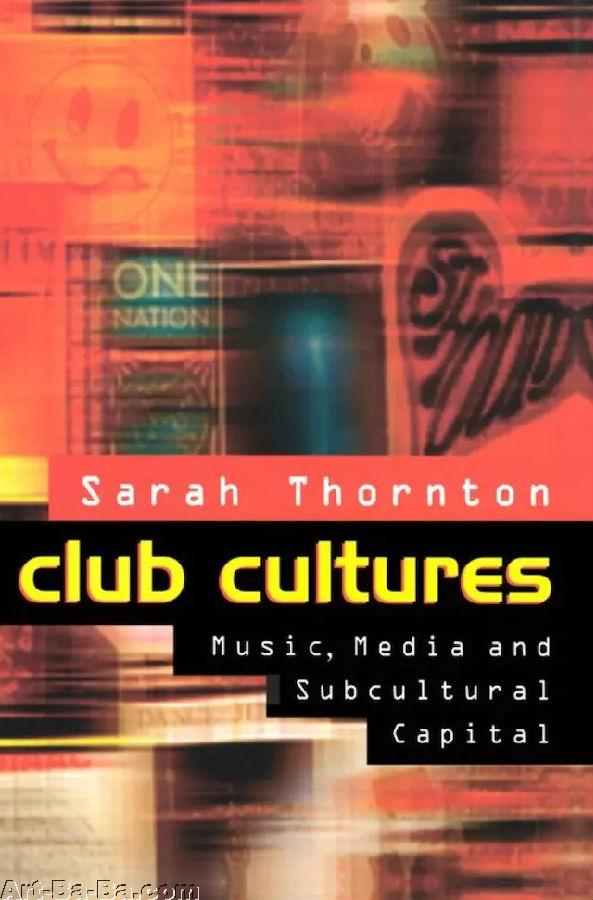
尽管有些收藏家对艺术品价格的暴涨叫苦连天,但艺术品市场表现依然强劲,许多艺术馆的营业面积也急剧扩大。更多艺术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少数艺术家的收入甚至已经超过了明星。批评家都在绞尽脑汁地用文字填满不断扩大的刊物版面,而博物馆的管理人员纷纷跳槽,在艺术圈寻求更高收入的职位。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也给一些人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市场定价会误导公众审美,从而掩盖了客观批评,艺术奖项及博物馆藏品选择对艺术品的评价作用,并希望人们不要一味地推高价格。就连务实的艺术品交易商也会告诉你,赚钱只是艺术的副产品,不是艺术的终极目标。艺术要想继续生存,要想保持其高于其它文化形式的地位,就需要找到一种动力,这种动力绝对不能是利益,而应该是比利益更有意义的东西。
由于艺术界的组成部分是多元化的,艺术圈内的活动又不透明,甚至有点神秘,因此很难概括艺术界的特征,也没有人能够彻底看透这个领域。此外,进入艺术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五个国家的六个城市进行了调查研究,把我的研究成果写进了本书的七个部分,试图描绘出艺术界的深度和广度。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是真实生活场景的描述,希望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知艺术界人士的生活方式,从而了解整个艺术界。我作为参与者,观察了艺术界很长时间,采访了许多人,书中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根据三四十个人的采访素材而写成的。通常,这种研究形式叫做“默不作声的观察者”,我则属于“亲身参与的观察者”。我在参与的同时,好奇地观察着艺术界。偶尔也会冒昧闯入艺术界人士的秘密领域想一探究竟,但我的行为从来没有对他人构成过威胁。
书中的前两章呈现出了对立的两极。“拍卖会”部分翔实地记录了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举行的一场拍卖会的过程。拍卖领域拒绝艺术家的参与,拍卖行为实际上是艺术作品的终结,有人说拍卖会就是艺术品的太平间。“艺术评论课”部分记录了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一场生动活泼的艺术研讨会。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是艺术家的摇篮,学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也会学习一下艺术界的业内基础知识。拍卖会与艺术院校相去甚远,拍卖大厅里的价格和竞争似乎远离财政吃紧的艺术院校。但要想弄清艺术界的运行机制,就必须了解艺术界中这组对立的两极。
同样,“博览会”与“工作室”也存在对立关系。前者是消费环节,后者是生产环节。工作室是了解艺术家创作过程的理想场所,博览会上拥挤的人群和令人目不暇接的展品足以让人们领略艺术界的繁荣。“博览会”部分描述了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开幕当天的盛况。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艺术界的重要活动,它推动了艺术的国际化发展,并确立了艺术界定期举办艺术活动的常规机制。“工作室”描述的主角是日本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他曾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雕塑的形象。村上隆在日本有三个工作室和一个制造厂,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工作室超过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工厂”。村上隆的工作室不仅是艺术家创作的场所,而且是他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同时,该工作室还是他同博物馆管理人员与艺术品交易商洽谈的地方。
“奖项”与“杂志”部分围绕辩论、判断和公众关注度展开叙述。“奖项”部分介绍了英国透纳奖(Turner Prize)颁奖典礼的现场情况。该奖项的评委会由泰特美术馆董事尼古拉斯·塞罗塔(Nicholas Serota)监督,评委会从四名最终确定的候选艺术家中选出一名优胜者,颁给他 2.5 万英镑的奖金,整个颁奖典礼通过电视进行现场直播。这一部分探讨了艺术家之间竞争的本质和荣誉在艺术家职业生涯中的作用,以及媒体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杂志”部分列举了针对文艺批评的不同见解。我观察了专业杂志《国际艺术论坛》(Artforum International)编辑们的工作状况,并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罗伯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进行了对话,还深入采访了一些艺术史学家。此外,这部分还分析了杂志封面和新闻评论是如何让艺术和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留下印记的。
最后一部分“双年展”叙述了我参加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的经历,这是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展会。威尼斯双年展似乎应该是一个度假场所,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忙碌的社交场合,以至于人们都无暇顾及艺术品。只有一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关注艺术品本身。在此,我要向这些工作人员表示敬意。记忆,给当代艺术赋予了意义,也给艺术品价值判断的后知后觉带来了灵感。这部分还着重思考了记忆在艺术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艺术世界中的七天》篇幅不长,但却耗费了我许多心血。在以往的民族志学(ethnographic)研究项目中,我假扮一个广告公司的“品牌策划师”进行研究工作,并沉浸在伦敦夜总会绚烂的夜生活中。坦率地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狂热地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但后来,我觉得有点累。在研究艺术界的过程中,尽管十分辛苦,可我还是觉得艺术世界很神奇。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有很强的诱惑力。一个原因是艺术界非常复杂,另一个原因是艺术模糊了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国家与国家的界限、文化与经济的界限。因此,我觉得艺术界就是未来社会组织的雏形。尽管许多艺术界人士以诋毁艺术界为乐,但我还是赞同《国际艺术论坛》发行人查尔斯·瓜里诺(Charles Guarino)的话:“我觉得艺术界的人同属于一个宗族的大家庭,成员中有许多天才、怪才,接受了太多的教育。他们似乎生不逢时,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们狂放不羁,有时甚至无法无天。我喜欢跟这群人待在一起。”最后即使人去楼空,房间里也到处弥漫着艺术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