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鲁明军

Leo Steinberg
本文选自即将出版的鲁明军艺术批评集《目光的诗学》(即将上市),为本书后记删节版。
2018年夏天在纽约时,曾半开玩笑地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艺术评论家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假如让您推荐一部20世纪最重要的当代艺术论著和文章,您会选择哪一部/篇?”博瓦略感为难,表示不好回答,但迟疑了不到一分钟后还是告诉我,如果非要选一部,那就选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的《另类准则》(Other Criteria)。开始以为他会推荐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或罗萨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的著作,没想到他选的是《另类准则》。约十年前,沈语冰教授组织翻译了这部同名论文集,记得当时读后留下较深印象、也是被讨论最多的是其中他关于毕加索、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等艺术家作品别具一格的分析和阐释,这篇同名文章及其重要性反而有些被忽视和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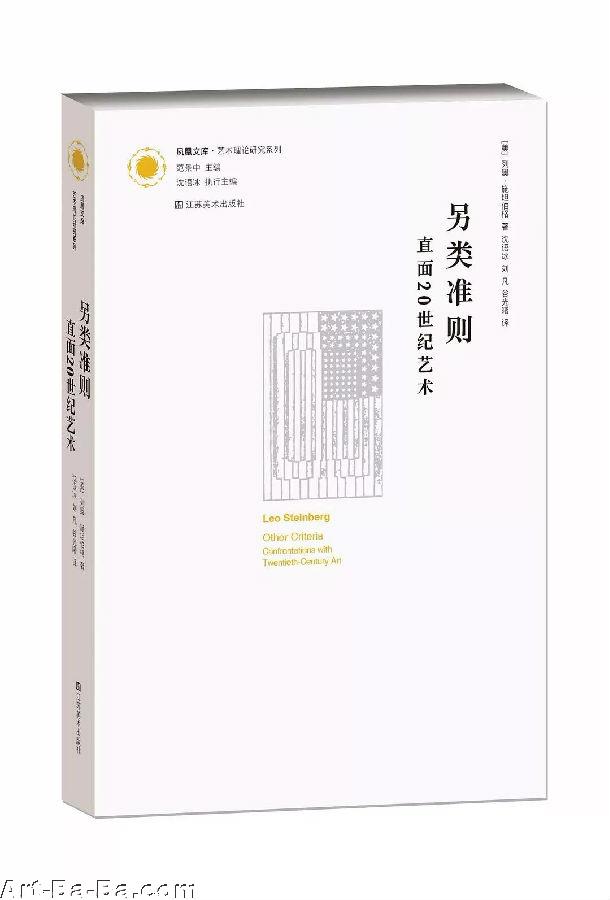
《另类准则》(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艺术评论界一度有“文化三伯格(三山)”一说,指的是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和施坦伯格三位享誉欧美的当代艺术评论家。比起前面两位,施坦伯格主要关注的领域其实并非当代艺术,他也不是职业的评论家,文艺复兴艺术史才是他研究的重心。兴许正是因此,比起格林伯格带有霸权色彩的形式主义和罗森伯格充满诗意的存在主义,他的评论少了过分的情绪和姿态,而处处泛着理性的智识和睿见。更重要的是,前面两位都是“美国绘画”或“纽约画派”的捍卫者,但他不是。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反形式主义者,在他的写作中,非但没有拒斥形式主义,其反而成了他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他甚至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形式主义”。
1968年3月,施坦伯格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做了题为“另类准则”的演讲,四年后,由演讲稿修订的同名文章发表在《艺术论坛》(Artforum)(1972年3月)上。文章系统地清理了形式主义这一理论模式,并对其予以了深刻的质询和批判。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但事实上,在他发表演讲之前,抽象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一解释模式就已经整体趋于式微。自1960年代初以来,“寻常物品的新绘画”(帕萨迪纳艺术博物馆,1962)、“六位画家和物品”(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1963)、“流行艺术”(堪萨斯城阿特金斯博物馆,1963)、“波普上架”(休斯顿当代艺术博物馆,1963)、“流行图像展”(华盛顿现代艺术博物馆,1963)以及“美国波普艺术”(奥克兰艺术博物馆,1963)等一系列展览的相继举办,标志着抽象表现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结束,与此同时,批评界也随之展开了对于形式主义的检讨和辩护。因此,对于形式主义而言,施坦伯格的这篇文章既不是最早的批评和质疑,也不是最终的盖棺定论,其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启了诸多新的问题面向。文章松散的结构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由演讲稿整理而成所致,另一方面不能否认,作者原本就不想将自己流动性的思考框在某个结构里面。
1967年,迈克尔·弗雷德发表了《艺术与物性》一文,通过“物性”和“剧场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批判了极简主义及其对于与观者关系的改变。这看似是为形式主义辩护,却由此打开了我们对于极简主义以及形式主义的新的认识,“物性”和“剧场性”反而成了我们进入极简主义重要的视角和路径之一。《另类准则》一文虽然关注点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与其说是反形式主义,不如说是透过格林伯格的眼睛对于形式主义以及极简主义、波普艺术等及其潜在的关联尝试予以重新认知和解释。几年后,罗萨琳·克劳斯将关于极简主义的认识投射到现代主义,进而将极简主义解读为现代主义的一个缩影——不过即便如此,二者依然是决裂的。这里且不论克劳斯是否受到前面两位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三位的解释在逻辑上的确不乏相似或暗合之处。
独辟蹊径的施坦伯格并没有从作品出发,而是选择从艺术市场开始谈起。他说,20世纪中叶以来,艺术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已经被美国化了的前卫艺术开始与赚大钱联系在了一起”。“艺术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以为的东西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就是硬通货”。在过去,艺术一直被美国人视为“狡猾”“故弄玄虚”“矫揉造作”的罪恶之根,现如今,他们则积极地要求改造艺术,试图按照本土的准则,同化它们。投资者们一开始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好在“拒绝的最初姿态”本身就是美国艺术文化的普遍性格。这就像那些曾经反学院派的先锋派一样,其实很快也被学院化了。所以,艺术家们其实并不担心艺术被改造、同化后会影响公众接受的程度。
在这之前的另一篇文章《当代艺术及其公众的困境》(1962)中,施坦伯格提到,1958年,贾斯珀·琼斯第一次个展的时候,别说是一般公众,连他这样的专业学者都“无法接受”。等他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才理解了琼斯绘画的真正意义。他渐渐意识到,琼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终结了传统的错觉绘画。而这不只是对人类主题的一种无视,就像抽象艺术一样,还暗示着人性的缺失。于是,只有物品——人造物的迹象被遗留下来,也是因为人类的缺席,这些迹象最终都成了物品。这一方面表明一种新的艺术创造曲折的受众过程,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种“物化”和“去人性”实则暗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篇文章构成了《另类准则》的基调,在此基础上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拓展。

《皮格马利翁与加拉泰娅》(1881)

《威廉·鲁什正在雕刻他的斯库基尔河的寓言人物》(1908)
施坦伯格智慧地选择两幅画作为引子,一幅是里昂·热罗姆(Leon Gerome)的《皮格马利翁与加拉泰娅》(1881),另一幅是热罗姆的学生托马斯·艾金斯(Thomas Eakins)的《威廉·鲁什正在雕刻他的斯库基尔河的寓言人物》(1908),两幅画都涉及绘画的自我投射,不同的是,前者中的雕塑是艺术(家)欲望的对象,而在后者中,模特儿的裸体并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出于科学观察的需要,画面中所有人物和对象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其更深的意义在于,它将艺术与裸体同化于工作伦理,从而化解了美国人对艺术与裸体的反对。施坦伯格敏锐地指出,艾金斯对于诚实工作的颂扬其实来自从事艺术中的清教主义,即一种作为绝对价值的职业纪律的理念。艺术家不再表达恐惧也不表达怜悯——甚至丧失了好奇与创造力,只是一个忙于干活,且干得非常有效率的工作者。就像约瑟夫·彭内尔(Joseph Pennell)所说的:“工作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艺术家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一观点无疑来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韦伯这样写道:“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而在施坦伯格看来,作为天职或职业,艺术就是“一种积极行动的人的形式主义——一种独立于内容的价值”。
尽管施坦伯格并没有明确提及,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洞悉其与形式主义之间隐伏的联系。换句话说,无论形式主义,还是后形式主义,抑或反形式主义,在施坦伯格这里,它们都具有一个形式主义的底色,而这原本就是美国文化精神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若由此再来回看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那种彻底的形式自足,不正是一种独立于内容的价值么?施坦伯格关注的是作为工作、职业或生产关系的形式主义,格林伯格的重心则在画面本身的形式主义,前者将人予以“物化”并赋予了它某种价值伦理,而在后者这里,他是将艺术彻底地“物化”——尽管格林伯格不承认物性及其空间属性,但画面作为一个自足的对象或“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格林伯格不认为形式主义承载着任何价值,但从“形式”的历史根源看,它本身又与19世纪的形而上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戴维·萨默斯(David Summers)曾极富洞见地指出:形式分析的源起与19世纪唯心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密切相关,也因此与贯穿了从离奇的到危险的全部范围的各种历史推论和归纳密切相关。所谓的形式,即非模仿的成分,但它并不是附带的或多余的,作为精神的表现,它是必要的。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是抽象的和普遍的,它所代表的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并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力量。然而,当“形式”演变成为更加彻底和极端的“形式主义”的时候,与其说形式是对立于内容的存在,不如说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进而言之,这里的唯心主义也不再是对立于唯物主义的存在。由此便可理解,萨默斯何以声称对立于形式分析的语境主义者潘诺夫斯基及其图像学研究被说成是唯心主义者的艺术史传统。反之,对于格林伯格而言,形式既是平面的纯粹之“物”,同时也是一种本质主义化的理性意志。
在《另类准则》一文中,施坦伯格虽然没有彻底否弃形式主义,但还是“觉得形式主义过于笃定,他不相信他们的定量手段,更不喜欢他们那种令行禁止的立场——一种告诉艺术家应当做什么,告诉观众不应当看什么的态度”。其试图将所有的绘画都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准则,而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党同伐异,可以说形式主义者之所以不接受极简主义、波普艺术,其实就是因为担心这样会逾越党派界限。于是,“对错”取代了“优劣”成了判断的准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形式主义脱离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就像前面所说的,其本身就是新教伦理这一价值体系的表征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其封闭性,所对应的正是当时美国封闭的工业系统。按施坦伯格的说法,“主宰过去50年的美国形式主义批评的描述性术语,与同一时期底特律汽车工业的演化相平行,这并非纯粹的巧合。”当然,这并不是说汽车看上去像绘画,而是说形式主义这一还原性术语与主宰美国发动机工业组装方式事实上处于同一个系统。
尽管如此,施坦伯格之所以反复强调艺术作为工作和艺术作为行动,终究还是为了走出形式主义的牢笼。这里的“行动”并非罗森伯格所谓的“行动绘画”(如波洛克、克莱因等)意义上的“行动”,施氏直言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眼中的作为艺术的行动并非停留在画面上,而是“指一个正在制作绘画的人如何在一个竞技场上行动,经历各种偶然,制造各种事件”。也即是说,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激发灵感的象征主义,也不是满足知觉上的愉悦”,而是如何构成一种“‘真正的社会政治力量’——大胆地发出艺术世界的声音,又重归艺术世界”。当然,他所谓的社会政治力量不是走向街头诉诸抗议,而是如何真正地进入社会运行系统和流通机制。这也是他一开始重申艺术市场、艺术工作以及艺术职业,甚至力挺波普艺术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这些已经成为绘画很重要的构成部分。
多年以后,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在讨论当代绘画的问题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说,所谓当代绘画,是指“在更广泛的社会、技术、经济网络的沟通中建立关系,而不是构成独立的实体”。这个时候,艺术作为一种职业,艺术家作为一种工作者早已成为普遍的事实。且不论乔斯利特是否受施坦伯格伦说的影响和启发,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乔斯利特之前,施坦伯格已经深刻地指出了波普以来的新艺术机制:当艺术作为工作或行动,进入传播、印刷以及资本等流通系统的时候,本身已经具有了某种社会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连形式主义都变得不再封闭了,它不仅带有新教伦理的价值底色,甚至还被视为美国这一时期工业系统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了“硬通货”。然而,这样一种解释意味着,一切似乎都有可能被合理化,乃至像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僵尸形式主义”(Zombie Formalism)这样的批评话语都会成为一个中性的表述。就此,施坦伯格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也不认为所有进入流通系统的艺术都是好艺术,相反,他在文中真正追问的还是到底什么是绘画本身,什么是艺术本身,因为只有通过自我指涉才可抵御一切被合理化的危险。
施坦伯格曾多次提到,他所针对的并非是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及其实践,而是作为艺术史描述方式的形式主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将绘画本身悬置起来。形式主义主张绘画的自足性或所谓的“回到绘画本身”,而在施坦伯格看来,其实所有的主流艺术,至少是过去600年中的主流艺术,都在坚持不懈地“提醒(或关注)艺术本身”。他说:“一切重要的艺术,至少是14世纪以来的艺术,都高度关注自我批判。无论艺术还关心些别的什么东西,它首先关心的总是艺术本身。所有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都在探索它的边界,而老大师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自我界定的事实,而是这种自我界定所采取的的方向。”基于此,他提出了“新老错觉主义”这一命题,而这则直接关系到格林伯格对于前现代艺术(pre-modern art)的处理,以及如何将自己与老大师们对立起来进而界定自己的。格氏认为:“写实主义、错觉主义艺术掩饰了媒介,运用艺术来掩盖艺术”,而“现代主义却运用艺术来提醒艺术本身的存在”。在他看来,这也正是现代主义的本质所在,即如何“以一个学科特有的方式批判学科本身,不是为了颠覆它,而是为了更加牢固地奠定它的范围”。可问题是,这一点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遭到贾德(DonaldJudd)的质疑,他发现纽约画派的平面性其实包含着“虚空”和“错觉主义空间”,他并不觉得罗斯科的绘画是纯粹的平面,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深度。这暗示我们,此时格林伯格的理论图式其实已经濒临崩溃了。后来,在迈克尔·莱杰(Michael Leja)的《重构抽象表现主义》中,形式主义这一理论模式则几乎被连根拔起。
事实上,回到绘画本身并不限于形式,施坦伯格提出主题也是其动因和要素之一,而且在前现代老大师们的绘画中,原本就不乏诸如这样的自我指涉意识和实践。他以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画家皮耶特罗·格里尼(Niccolòdi Pietro Gerini)(?)的《耶稣上十字架》为例,透过画面四角伸手的先知,提示观众它是如何跳出画面内容,而指向绘画本身的。接着又以伦勃朗的晚年作品《读书的女人》(1639-40)为例,提出其中笔触、水墨的物质性与他所刻画的形象之间所暗藏着紧张和拉扯,同样是绘画自我指涉的体现。然而,无论形式,还是主题,它们都限于画面内部,并未超出或脱离画布之外,而施坦伯格真正关心的显然不止于此。他在文章一开始提出艺术作为工作或职业,“形式主义”作为新教伦理的一部分的时候,就已经暗示我们,无论是绘画,还是艺术,其自我指涉不再停留在画布上,而已通向了画外。而且他已发现,“最近15到20年的绘画开始坚持一种激进的新方向,其中绘画表面不再是自然的视觉经验的类推,而是操作过程的相似物”。
就此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施坦伯格认为,到了劳森伯格(包括杜布菲)这里,尽管我们依然将他们的绘画挂在墙上,但这些画“不再模拟垂直区域,而是神秘的平台水平面”,它“象征性地暗指诸如桌面、工作室地板、航海图、公告板等坚硬的表面——暗示任何物体得以在其上分散开来、材料得以进入、信息得以收到、印刷、压痕的接受体表面——不管是井然有序的还是乱七八糟的”。因此,它标志着艺术主题的一次激进转移,即从图像作为框内风景的“大自然”范式,转向了图像作为信息网络的“文化”范式。施坦伯格将这一转向看作是后现代艺术创作的开端。不过,在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看来,这种从垂直到水平方向的转变仍然只是操作层面上的;它的社会维度要到波普中才得以发展起来。这里的波普不再将艺术“冻结在金字塔的一层层之上”,而是置于文化的“一种连续体当中”。可见,波普艺术的自我指涉不再是媒介的材料特性,要求回归绘画本质,参与情境变化,而是指向“画布内和画布外的通道”。
按照德·迪夫(Thierryde Duve)所言,这里已经不再是惯例意义上的绘画创作,而更像是“名义”上的艺术实践。面对如此混杂的信息,并不是说它丧失了自我指涉的可能,毋宁说是将艺术的路径再度变得非线性和不可说摸了。这意味着,它远不止是一种表面特征,如果它被理解为一种绘画中的变革,那么它改变的正是艺术家与图像、图像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在施坦伯格看来,“这是艺术震荡的一部分,它足以使艺术纯粹的范畴变得不纯粹”。据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连形式主义都已经变得不纯粹了,作为一种伦理形式,其自我指涉已不再限于画布内部。
贾斯伯·琼斯曾经感慨,劳森伯格是20世纪自毕加索以来发明了最多东西的人。而在施坦伯格看来,在劳森伯格的发明中,首先是使世界再度进入绘画的表面,它是为那些浸泡在城市大脑里的意识而创作的。也因此,它超越了“抽象”与“再现”、波普与现代主义这样的划分准则。不仅是他,也包括利希滕斯坦、沃霍尔等,他们不仅重新确认了艺术家或艺术家—技术人员的概念,并再度让艺术的路径变得非线性、不确定和不纯粹。借用乔斯利特的说法,它们像“病毒”一样,不断地反馈、干扰和侵蚀着非艺术的领地。既然如此,那还有建构唯一解释准则的可能吗?!数年后,围绕《十月》(OCTOBER)杂志的新的艺术评论范式,以及视觉文化和新艺术史的兴起,标志着又一个新的艺术史描述和艺术批评时代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十月》夏季刊(第25期)做了施坦伯格的专题,整本杂志都交给了施坦伯格,但刊发的并不是他的艺术评论,而是一组题为“文艺复兴艺术和现代无意识中的基督性取向”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罗萨琳·克劳斯和安尼特·迈克尔森(Annette Michelson)两位年轻主编的匠心所在。
施坦伯格的《另类准则》最初以演讲的方式发表于1968年3月,迄今过去已整整半个世纪。五十年来,艺术批评理论的几乎所有命题多多少少都可以在这篇演讲中找到蛛丝马迹,甚或说,这篇文章几乎涵盖了形式主义及其之后的所有艺术理论命题,包括形式主义的历史—社会机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W.J.T.米歇尔(W.J.T. Mitchell)的“元图像”和斯托伊奇塔(Victor I.Stoichita)的“元绘画”、克劳斯的“扩展的场域”、福斯特的“实在的回归”、乔斯利特的“反馈的干扰”、德·迪夫关于现成品和现代主义的知识考古学以及艺术作为工作/职业、行动的理论,等等。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史研究似乎依然笼罩在这些理论的阴影之下。这也表明,《另类准则》仍未过时,仍然常读常新,仍在为我们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提供着新的认知视角和解释路径。就像施坦伯格说的:“判断的一切既定标准都是暂时的,而另类准则却总是由于新形式和新思想的缘故而永久发挥作用。”
选自

《目光的诗学》
鲁明军 著
ISBN:978-7-5649-2357-0
即将上市
在《图像的生与死》一书中,雷吉斯• 德布雷沿着“图像—词语—宗教”“技术—艺术—媒介”及“视像—信息—观众”这一视角勾勒了古希腊以来目光的诗学史。本书以此为引子,透过十五位当代艺术家的个案实践,围绕“物与感知”“正义剧场”和“世纪幻影”三个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当代议题展开深入而开放的探讨。这些议题涉及艺术史认知、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逻辑、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动及其暴力,以及关于技术物的平等想象和对于未来的焦虑,等等。若循着德布雷的论述,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抽离出“感知—政治—时间”这一修辞机制,并不妨视其为当代目光的一种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