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卡塞尔“一无所知”的印尼团体,能否为文献展带来一针解毒剂?
来源:Hi艺术
唐泽慧
策展人
2019年年初,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Ruangrupa被任命为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这是这个有近七十年历史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际大展首次任命亚洲人为艺术总监,也是文献展首次将此职位委任一个团体而非个人。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在此之前印尼艺术家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可见度并不太高,以文献展自身为例,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印尼艺术家参加过展览。在被任命之前,Ruangrupa团队只有一个人曾经去过卡塞尔,他们的作品也几乎没有进入过市场。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很‘天真’,对文献展的神话一无所知。”

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Ruangrupa
主流国际大展模式的一针解毒剂
今年8月,通过澳洲艺术协会在印尼组织的国际文化项目,我有机会考察了包括Ruangrupa在内的雅加达和日惹的若干文化艺术机构。我感到Ruangrupa代表了一种在印尼被广泛实践、但还不太为我们所知的艺术创作和知识生产模式;也更理解文献展为何会选择他们——对于西方的艺术体制,他们是异质的存在,运行逻辑、社会语境和工作方式都如此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介入或许会给双年展、文献展这种在当代位居主流而又饱受争议的国际大展模式带来一针解毒剂。



Ruangrupa所在地
Ruangrupa是谁?
从雅加达市区出发向南大约40分钟车程,就来到Ruangrupa所在地,一个由学校、工作室、商店、图书馆、自制电台、餐厅、展厅组成的文化综合体。称之为文化综合体很可能是一种感官上的误导,事实上,它位于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旁,主体建筑是一个二层小楼,充满了DIY气息,柱子用汽油罐包裹,空间隔断是未经加工的木板和铝板,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涂鸦。小楼的旁边,是由集装箱搭建而成的二十多个工作室,租给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使用。我踩着轻微摇晃的铁架楼梯爬上集装箱二楼,只见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五六个人赤脚席地而坐,每人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烟味缭绕,四面墙壁的玻璃板上写满了各种图表,有人对我说:“欢迎来到文献展办公室。”

Ruangrupa所在地,创始人Ade介绍Ruangrupa商店里的T恤衫
Ruangrupa成立于2000年,是1998年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涌现的诸多艺术团体之一。艺术家Ade Darmawan是Ruangrupa的创始成员和总监,今天这个团队共有10位核心成员,分别来自于艺术、建筑、媒体、政治学等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实践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既作为艺术家创作作品,也组织和策划各类展览和活动;他们有一个社区电台,一个基于捐赠并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他们是二房东,工作室出租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他们还经营着艺术品装裱、包装业务,2018年以来他们重要的工作内容是“GUDSKUL”,一个基于参与者的个人项目,试图打破师生界限,通过“知识市集”等形式在交流与对话中实现自我教育的另类艺术学校。所有这些项目的收入都进入一个基金池,开销也从这里支出。他们将这种模式称之为“Lumbung”,一个基于“聚会”“协商”“共识”“集体抗议的权力”和“反对极权的权力”等民主原则的经济体。Ade Darmawan称他们有意识地“将机构建设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形式”。他们的实践既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发展出的生存策略,又带有浓厚的乌托邦实验性质。

Ade Darmawan(左二)、唐泽慧(左五)与澳洲艺术协会Arts Leaders 2019成员
这种多元、混生的状态并非Ruangrupa所独有,几乎我们去的所有文化艺术机构,无论名字叫画廊、基金会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特质。它们往往是画廊、咖啡店、餐厅、书店、工作室、客厅、礼品店、家具店甚至打印店等几种形式的组合。营利与非营利、公共与私人空间、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常常难于分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画廊的经典样式“白立方”在这里鲜能见到,它们在别的地方会被称为“替代性”空间,但在这里却成为主体,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经营逻辑和文化。
Ruangrupa在给文献展的提案中写道:“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文献展,它基于城市已有的系统并引入以下策略...... 这些策略包括但不限于,在文献展的常规场地举办规模适当的展览,在卡塞尔城市的学校、银行、医院等公共服务和公共项目中,展开1:1的真实的实践......以此激发不可预见的混生的艺术实践和形式。”




与Ruangrupa创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印尼艺术小组Kunci,由不同领域的学者组成,他们近期的研究课题是“非正当教育”。图为他们办公和聚会的地方
在与Ruangrupa接触的几天里,我就印尼当代艺术和他们正在为之工作的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与团队的几位成员断断续续进行了以下这些谈话。
隶属于团体的印尼艺术家个体
唐泽慧(以下简写为唐):Ruangrupa是印尼历史最长的当代艺术团体之一。在印尼几乎我们遇到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属于某个艺术团体,这种集体性似乎是印尼艺术家的一个显著特点,你觉得原因何在?跟印尼的艺术传统有关吗?
Ade Darmawan: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确定的答案,只能做一些猜测,对于不同年代的艺术家可能有不同的理由。对我个人而言,我的学生时代是在苏哈托“新秩序”下度过的,形成一个团体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是应对创伤的一种机制,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存活下来。
从艺术史上看,印尼最早的现代艺术团体Persagi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Drawers)成立于1938年,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他们的艺术宣言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试图确立一种有别于荷兰殖民者的属于印尼群岛的绘画传统。1975-1976年来自万隆和日惹的一些学生组成了“新艺术运动”(New Art Movement)重申艺术的社会责任。艺术团体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关。


Ruangrupa客厅
2010年,我们进行过一次调查,让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发几张最能代表他们实践的照片,结果在收到的20多份回复中,几乎没有例外,都包括了聚会的照片,漫长、混乱的聚会是我们的工作方式,非常低效,但所有的美也存在于此。“在一起”(togetherness),基于谈话的决策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唐:除了Ruangrupa小组的实践,你们每个人,作为艺术家或者建筑师,都还有自己的创作,你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如何平衡个人创作和团队合作?
Farid Rakun:对我而言,并没有确定的配方。我们在彼此身上浪费了很多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这对我们不太适用,时间几乎不值钱——至少对我们彼此的关系而言。我觉得二者是共生的,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的合作,我在这里浪费的时间影响了我个人的创作,反之亦是如此,我会把我个人的、别处的经验带到这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Ruangrupa还能存在至今。
游走在市场之外,不是因为“去不了”而是“选择了另外的路”
唐: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艺术近几年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很受关注,拍卖场上屡屡拍出高价,并且印尼拥有全亚洲除中国之外的第二大收藏群体。而我们所看到的你们的实践几乎不能被商品化,在印尼当代艺术的生态系统中,你们如何定位自己?
Farid Rakun: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角色。如果还我们还年轻,或许还会幻想其他的角色,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熟,如果不是变老,对这些都淡然处之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使命。
Iswanto Hartono:我们基本上是处在艺术市场之外,有时会有交集,但不是那种收藏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我们理解彼此,但出发点不一样,我们做这些是基于自己的信念。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去不了那里,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日惹版画艺术小组“Krack! ”和他们的集体工作室
我们对文献展的神话一无所知
唐:“文献展”这个全球性的艺术平台迄今为止仍然是非常欧洲中心的,作为“文献展”历史上第一个亚洲策展团队你们是否感受到某种压力和责任?印尼本地的艺术界是否也会对你们有某种期望?
Farid Rakun:我们并不会为了“文献展”而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提供的就是我们所知的,亚洲、东南亚、印尼是我们所知的一部分。我们避免令自己处于代表亚洲或者印尼的位置,欧洲的策展人似乎就不会被问到是否代表欧洲的问题。
Ade Darmawan:我们不希望陷入那种套路中。去到某地,艺术家展示他们的作品,策展人进行挑选,这不是我们工作的方式,我们希望挑战人们对于展览的认知。作为个人和作为团队,我们根植于特定的语境,这种语境会自然显现,不需要特别强调。


日惹艺术机构Cemeti- Institute for Art and Society
唐:你们如何把基于印尼社会和文化现实的本地经验移植到卡塞尔这个平台上?
Ade Darmawan:我们的联系总是通过现场的互动建立的。从今年10月份起,Farid会常驻卡塞尔,其他成员也会陆续去。你可以说去“做研究”,但其实就是做我们一贯在做的事情。我们依赖自身的敏感性和直觉,所有的联系归根到底是社会性的,是个人的。我们并不试图去理解文献展——这也不太可能,我们以“陌生人”的角度切入,去体验和感受,由此引发的反应和互动也很有意思。当然,作为艺术家,作为艺术从业者,那些宏大的全球性议题也会在我们的脑海中,但我们并不想强加在展览上,只是让它们自然地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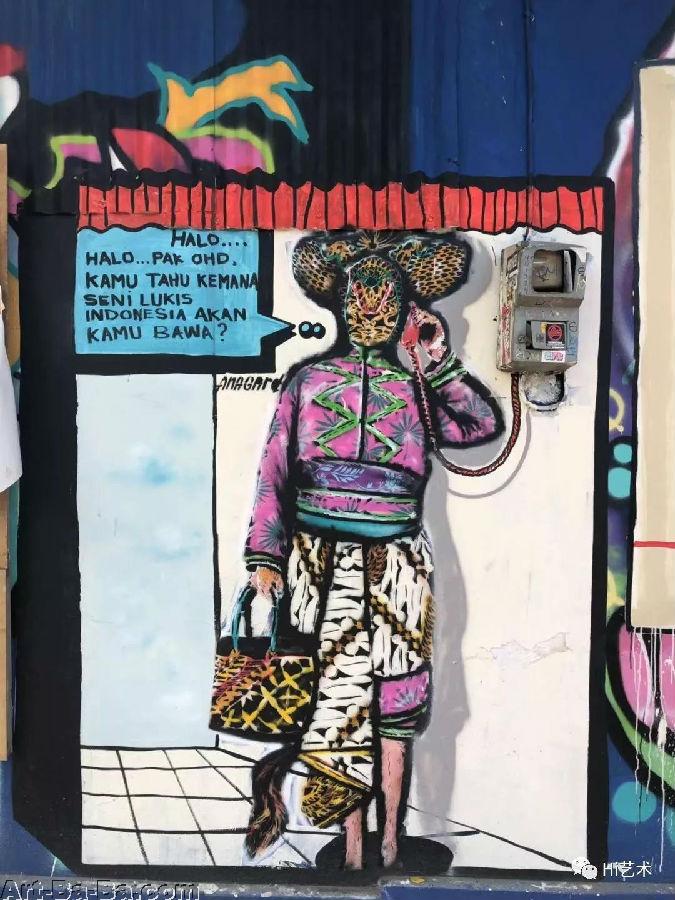
日惹艺术机构SURVIVE!Garage
唐:你们所说的“低效”“有机”“混沌”的工作模式根植于你们自己的实践,而你们以往项目和活动规模都是比较小的。这种基于中小型实践的模式如何能被顺利地应用到文献展这个当代艺术世界最为鸿篇巨制的展览上?
Ade Darmawan:我们不从规模上着眼。以这个杯子为例,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比这个更大的杯子,而是做无数个像这样的小杯子,并把它们联结起来。所以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把每个小单元联结起来,使它们相互呼应,产生更大的意义,而不是把个体的规模做大。我们的策略是解析而非强化。
Farid Rakun: 我觉得关于“文献展”的既定认知也应该被改变——文献是巨大的、神圣的、体制化的——我们应该对这些标签保持警惕,这是一个被塑造的神话。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既定想法,就有可能尝试新的可能性。文献展并没有为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它?从来没有一个印尼艺术家在文献展上展出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之前我们整个团队只有一个人曾经去过卡塞尔,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很“天真”,对文献展的神话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