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Artcoco 马玲玲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凭借地理和政策优势迅速进入一个生猛年代。相对宽松、包容的氛围,本土文化生产和港台、日本、欧美流行文化、艺术的混合交错,致使这里产生了丰富而多元的艺术实验。但在随后的历史脉络梳理、撰写中,饱满的真实现场、多向度的社会走向,和它们后面隐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早已被书写着的筛选机制清除干净,成为了几个干燥的节点。想要更加接近客观现实,我们所能借助的除了当时的文献、文档资料,口述史亦是一个有效途径。除此之外,被北方当代艺术实践夺去太多关注的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南方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也需要被倾听。

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展表演准备现场
为此,我们拜访了胡斌、杨青、钟刚、董超媚这四位有着策展、研究、媒体等多重经历、视角的广东当代艺术参与者、观察者,并试图在他们叙述的个人经验和历史中观看到一个前进与消逝并进的广东双城图景。

胡斌
典藏:作为在场者,你对在众多展览现场所感知、记忆的和媒体报道、出版物中展览现场、历史脉络有何差异?能否为我们讲几个例子?文本、个人经验下储藏的艺术实践历史、个人史是否真的值得当代人追忆?
胡斌:媒体对展览的报道、记录是多样且广泛的,很难有人能够全部知晓,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我也可以就我参与过的两届广州三年展谈一点感想。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名为“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主策划巫鸿先生有感于国内外的种种误读,希望提出源自内部却又具有全球眼光的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合理看法。展览图录中所集合的中外学者的多篇论文从艺术史性质层面来审视90年代的中国实验艺术,比如纵向和横向的渊源与语境讨论,自身演变逻辑的揭示以及对与周边世界的关系的质疑等。这本图录现在成为我们回顾中国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文献。在当时的专业媒体上,我们看到,展览因强调本土性视角和艺术史叙事为学界所称道,但也有人质疑“重新解读”的成效以及对当代艺术体制化和话语权力反省的缺乏。而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所体现的全球本土化,抑或另类现代性理论底下的策展思路在后来同样遭遇到有些学者的质疑。

第三届广州三年展展览现场,2018
现在翻看三年展的图录和三角洲实验室的读本,其实有很多议题值得讨论,包括策展的思路、展陈以及学理上的争议等等。但是印象中当时大众媒体所热衷的话题是,当代艺术让人看不懂,而这一说法出现在各种当代艺术展览的报道中。很多时候,展览都是喧嚣一时,现在尤其是这样,大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浮光掠影式的照本宣科或者追逐一些浅层次的话题,甚至学界也来不及来仔细辨析内在的问题和关系,一闪而过。喧嚣过后,真正进行学术清理的时候,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才会浮出水面,文本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有些关节是很难体现在文本上的,这个时候,某些经历者的个人史可能能够弥补这种缺憾,或者抵抗历史中单向度的叙事。
说到这里,我想起并非自身经历而是做过研究的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1992年广州双年展上的“消毒”行为。因为这届广州双年展被视作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商业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而针对双年展的“消毒”行为在一般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叙事中便被认为是对艺术商品化、媚俗化的批判。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翻阅他们当时的资料以及采用当事人和观察这个团体的动向,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他们批判的内容包括政治、商业和传统等很多方面,而就商业而言,他们并非反对商业化,而是希望提倡一种不囿于既有的艺术流通系统的、健康、纯粹、开放的市场与操作方式。但是,在传播系统,事件往往以单一化的解读形式而被引爆。而简单的历史书写则容易变成对于这种传播效应的追认。新的话语力量出现时,历史或许会被改写,但是这种重构经常离不开当下的某些权力结构的左右。所以,我觉得个人史、个人经验尽管无不带有强烈的个人诉求,但是如果具有一定多元性的话,可能能够丰富那些符号化的历史书写。再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因为当初文本资料保存的问题有不少缺漏,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不失为一种补正。
典藏:在你的记忆中,有哪些曾经活跃的艺术项目、媒体或机构已经关闭或消逝?这些项目的终结是否是一种必然?
胡斌:广州的机构大多很有韧性,一些重要的机构、项目或许体量不大,但大都持续存活了下来。比如博尔赫斯书店,从1993年开设以来,虽然一直保持着较小的体量,但它一直都在,并且创办者陈侗又拓展了录像局和本来画廊等新的机构。而广东美术馆创办的广州三年展、广州摄影双年展(中断后,现在又以广州影像三年展的形式继续进行)等虽然也曾遇到波折,但延续至今。广东时代美术馆持续举办了“泛策展”和“榕树头”等系列项目,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辟了“珠三角艺术单位观察”等。近些年,像观察社、腾挪空间、扉美术馆等小型机构还在继续发力,又有很多新的空间或项目产生,比如上阳台、顶上空间、你我空间等。当然,也有空间消逝,比如Loft345,因为租赁问题,艺术家都搬走了。艺术媒体方面,《画廊》杂志在90年代曾经有较大影响,几经周折,现如今仍然在持续;而新的自媒体“打边炉”成为珠三角非常活跃的艺术发声平台。深圳的机构情况,我不是那么清楚,何香凝美术馆创办的“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划”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已经停办了,何馆和OCAT先后主导的深圳雕塑双年展目前似乎暂停了。但是,华侨城园区又有新的项目,比如动画双年展的持续举办。而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机构或项目的终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经济、政策、主管者以及艺术环境等,而依据新的条件又会产生新的事物,此起彼伏,总体上还是越来越多元和活跃。

杨青
典藏:在你2018年创立的“城市艺向”中,曾策划过一个展览“来处”以思索城市、家和精神来处的问题。作为广州人的新客家人、广州当代艺术发展诸多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你的来处是什么?你个人经验中的广州当代艺术的来处又是哪里?
杨青:对于我个人经验在广东当代艺术中发育出的“来处”,可能最重要的起点是广州三年展。我对广东当代艺术的认知构建是和同时期的广州三年展密不可分的。那时由王璜生馆长等人推动的广州三年展自2002年首届举办以来,因为开放和实验的氛围让当时的广州迅速成为了当代艺术界眼中的一片乐土,南方(或广州)更多呈现了一个先锋者、实验者的状条件又会产生新的事物,此起彼伏,总体上还是越来越多元和活跃。
典藏:在你2018年创立的“城市艺向”中,曾策划过一个展览“来处”以思索城市、家和精神来处的问题。作为广州人的新客家人、广州当代艺术发展诸多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你的来处是什么?你个人经验中的广州当代艺术的来处又是哪里?
杨青:对于我个人经验在广东当代艺术中发育出的“来处”,可能最重要的起点是广州三年展。我对广东当代艺术的认知构建是和同时期的广州三年展密不可分的。那时由王璜生馆长等人推动的广州三年展自2002年首届举办以来,因为开放和实验的氛围让当时的广州迅速成为了当代艺术界眼中的一片乐土,南方(或广州)更多呈现了一个先锋者、实验者的状态,而同时期北方的当代艺术实践还未被官方承认。另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维他命艺术空间,它是我2005年进入《VISION青年视觉》杂志工作后拜访的第一个当代艺术机构。那时维他命还在客村的一个菜市场里,我记得去拜访时充满疑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直到穿过一条特别市井的市场,爬上一座工厂车间大楼的顶层,才到达维他命艺术空间。空间里面的实验性和外部的市井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次“亲密接触”。
典藏:在你的个人记忆中,有哪些重要的当代艺术机构消失了?你又如何看待它们在广东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价值?
杨青:广州的当代艺术机构不多,几个重要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机构还是一直在的,没有结构性坍塌。在当代艺术发展的进程中,肯定会有一些项目、机构结束,但我觉得这是机构和环境的双向选择,开始和消失都是正常的。毕竟除了消失,还有各种新的生长。商业画廊的沉浮,主要和市场有直接关系;而美术馆或非营利空间的生命周期,可能背后的原因更复杂一些。商业画廊对收藏的经营,令更多艺术家获得合理收入,得以继续创作,艺术品在流通中也在发挥更多的公共价值。非营利机构对艺术的推动,让具有实验精神和批判思考的创作得以生长,如果没有这些异质性的角度,社会就会变得只有一个声音,单一、僵硬和乏味。广州近几年的画廊和美术馆、艺术中心都在增加,从面对公众的层面来说,它们共同都起到了艺术普及教育的作用。同时,无论是对艺术收藏还是资助,它们面对的也是同一批争取对象,没有收藏家就没有更多的艺术资助人出现。所以,无论是商业画廊还是非营利机构,它们共同构成了艺术生态的各个环节,彼此是互相依存和促进的。
典藏:做为曾经的广东媒体人,你如何看待南方系媒体的现状、现代传播等大型传媒集团发展重心的北移并设立自己的画廊、艺术机构等现象?
杨青:广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媒体的大本营,可以说很多广州本土媒体都是携带着南方基因的。媒体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南方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比较强烈。媒体都需要通过多平台的经营来打破原来内容生产的单一模式——可能去做内容的上下游,打通形成文化产业链,也可能把经营重心转移到资源中心城市。但媒体的主要优势毕竟在内容生产,它是思想的提炼者、信息的过滤者、资讯的采集者,这才是媒体的强项。离开这个强项去做别的,能不能做得好,都需要时间去检验。

钟刚
典藏:在你的个人经验中,有哪些广州、深圳的当代艺术项目、媒体或机构让你印象深刻?这其中是否有对你创立“打边炉”有影响,或对标、参照的?
钟刚:陈侗的博尔赫斯书店和胡昉的维他命空间的长期存在以及他们持续的工作,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点事情有基本的信心。他们做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己负责,在私有制范畴下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机构非常动荡的根源,就在于没有一个人对它负责任,他们所做的事情属于一个单位,或者某个集团,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的、长久的责任人。为什么博尔赫斯书店和维他命空间能够不断积累他们的工作成果和声誉,就在于我们说到这些机构,知道它背后是谁,而这个“谁”就是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在乎自己声誉的人,所以当很多机构进行人事更替和品牌破产时,这两个机构还能持续去积累,持续去发展。
我做“打边炉”的初衷,首先就是想去做点自己的事情,这个事情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它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应该是私有的,这个事情的所有权全部在我这里,甚至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开会讨论,想到就去做。后来我发现这样去行事,工作效率比过去高多了。
至于“打边炉”的空间为什么要那么小,这一点还是受到陈侗和珠三角的整体氛围影响,把空间往小做,尽可能地降低工作的消耗,将注意力放到内容上,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的,才是美好的”原则吗?当我经历了大媒体和大企业的工作后,我对把事情做大一点兴趣都没有,太多大而虚空的事情,我希望去做一点“小而有力”,同时又完全属于我的工作,慢慢去积累,持续去工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叠加,我脑海中曾经闪现过的那些模糊的构想,一定能实施和实现。
做“打边炉”没有对标物,但媒体的死亡案例给我很多启发,我不希望成为这类死亡物中的一员。也许正是“打边炉”没有对标物,这份工作才能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新鲜感和成就感。我们在创造一些事情,当我们周围太多确定性的事物时,我们能够发明一些事情去持续做,我觉得这个工作挺酷的。
典藏:这些艺术项目、媒体或机构中是否有已经关闭或消逝的?你如何看待这些已经不存在的艺术实践、观察机构对珠三角艺术史的意义?
钟刚:我曾经写过一篇《广东慢车:珠三角艺术坎坷史》的文章。写这篇文章源于我自己对失败的关注,我很担心自己希望去持续做的事情,哪一天会失败,会破产,相比对成功的追求,我更关注我所做的事情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样就自然会去留意珠三角有哪些失败的尝试,比如媒体的失败,比如美术馆的无疾而终,这些失败的实践和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些艺术系统中的“原理”,比如这个系统并不支持那些做起来很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影响力并不能支撑一个机构的长久生存。生存问题还是得自己来解决,它是一个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
典藏:“打边炉”一直很重视对文本和个人史的记录。你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媒体报道、出版物中展览现场、历史脉络和文本、个人史下的有何差异?在大历史的重压下,文本、个人经验下储藏的艺术实践历史、个人史是否真的值得当代人追忆?
钟刚:这样做首先源于我对现场报道的厌倦,在社交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重复的信息已经严重过剩了。并且我始终认为媒体工作不是现场的附庸,它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尊严以及自成线索和系统的工作原理。所以“打边炉”一开始就放弃了现场报道,甚至用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建立“打边炉”的内容线索,“旧文重读”就是用至少十年前的旧文章来回应当下的问题,这段编辑经历对我影响很深,我非常关注我们的实践在一个历史线索中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的行动不是向前的,而是进入到低质量的“燃烧”当中。“打边炉”对现场文本的处理(也就是和你交流时说到的风干)以及建立文本进入档案系统的路径和结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工作价值留存得时间更长一些,我们不是为现场服务,而是为支撑现场运转的一个思想系统工作。我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最终是否能够成为值得追忆的一部分,但我确定不去做这些工作,我们很快就会遗忘它,我们在当中的“燃烧”,也会很快转为灰烬,被掩埋,被遗忘,最后我们就像没有什么都没做一样。
典藏:在这些年的珠三角艺术观察、文本整理中,你觉得广州、深圳的艺术实践有哪些关键词?它的艺术发展是否始终是向前的?
钟刚:去中心化,主体建构,游击性,独立意识。它的发展是迂回的,到底是否向前,我并不是很乐观。有时我会担心自己不小心滑入到这个系统的消耗循环当中,耗尽生命,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做”以及对“做”本身的琢磨,比最终一个目标的实现更重要。也许它是否始终向前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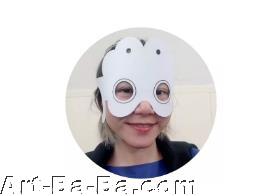
董超媚
典藏:你个人所累积的广东经验主要是由什么构成的?在累积过程中,有哪些令你影响深刻的当代艺术项目、媒体?它们中是否有已经关闭或消逝的?你如何看待这些已经消逝、不存在的项目、媒体、机构对珠三角艺术实践的意义?
董超媚:回答这个可能得回到一个大环境中来。因为我是广东人,TVB、明珠台、《YES!》杂志等香港媒体和当时的哈日氛围几乎影响了我们一代人。随后我到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读大学,碰巧又是打口碟、盗版碟文化和学校BBS(华南木棉BBS)活跃的时代,学校附近岗顶一带书店和音像店比如六月书屋、乐评人丘大力开的店是我们这拨文艺理工青年、也可能是广州打口一代的重要的回忆。当时很多音乐现场我们是一起去的,包括已经消逝的酒吧solo(后叫碟瓦)、办了两届办不下去的现代音乐节等。
2005年,我进入《周末画报》工作。那时《城市画报》《书城》等本土媒体已经崛起,广州的媒体在那时也经历着一个跃进时代,现代传播集团收购了香港的《号外》杂志,把一批香港的杂志“师傅”请到了广州。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媒体精英,后来《生活月刊》的创刊就是许知远、令狐磊等人共同创办的。那时候广州的书店、报刊亭中的杂志也很多样,我当时常去天河购书中心三楼的必得书店,我买到了许知远早期创立、只出版了三期的《大视野》等杂志,也关注起一个城市读本《城市中国》(没想到会有后续)。而位于海珠区的博尔赫斯、学而优等书店,我有时候也会坐个一个小时的巴士去逛逛。
在2000年左右吧,独立、文艺电影主要是通过录像带或者刻录碟来播放的,广州当时有一个观影组织“缘影会”经常组织观影活动。策展人欧宁当时还编辑制作了会刊等,记得也请过贾樟柯来到学而优书店播放了《任逍遥》。这个群体还促成了实验纪录片《三元里》(欧宁、曹斐)的诞生,后来这些主要的参与者、艺术家也都与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广州快车”密切相关。

欧宁、曹斐,《三元里》(片段),实验纪录片,2003
随着校园网络的开通,ftp下载电影、购买盗版D9也让影像变得容易传播。观影组织式微,“南都”策划的“先锋光芒电影节”让很多优秀的独立电影、文艺片有更为广泛的受众。与这类文艺团体同样消逝的,还有一些“意见领袖”的博客,如李如一的“文艺青年集散地”和欧宁的“别馆”。面对这种几乎无迹可寻的消逝,纸媒、出版物的价值是值得被深思的。

欧宁、曹斐,《三元里》(片段),实验纪录片,2003
在艺术项目上,主要是2002年和2005年的广州三年展、曹斐2006年的西门子艺术项目。我当时采访曹斐的文章,后转载到《城市中国》“隐蔽的珠三角”这一期,而这是我后来到《城市中国》工作后才发现的。而在这一期中,亦有库哈斯与哈佛GSD对珠三角的观察《大跃进》的后续。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中侯瀚如在“珠三角实验室”项目中请来了库哈斯,在当时的建筑设计界也引起了轰动。有趣的是,这届广州三年展的视觉设计团队是王序设计公司。2011年我到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深双、UABB)组委会工作的时候,那届视觉设计团队也是他们。其实,兜兜转转,你能够观察到一种“吸引力法则”,彼时分岔小径此时终将会合。

欧宁、曹斐,《三元里》(片段),实验纪录片,2003
在微信公众号等之前的网络时代,广州的文艺生活可以说是生猛、多元的。多样化的角度、流动的资讯为广州造成了相对自由的氛围,现在看来虽然资讯有限,反而给到了沉淀和准备期。这是只注重结果的后网络时代所不具备的。

欧宁、曹斐,《三元里》(片段),实验纪录片,2003
典藏:作为广州、深圳两地大型双年展、展览和媒体的参与者,媒体报道、出版物中所呈现的展览现场和你经验、记忆中的状态是否存有一些差异?能否就一些个案为我们讲一讲?
董超媚:差异是绝对存在的。比如,在我的印象中,2005年我作为《周末画报》记者第一次来深圳采访是因为首届深双,但后来才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在去深双开幕前的一两周,我其实已经在深圳参与了“GDC平面设计在中国”的报道,而那次的深双开幕现场是我同事负责的。这个例子或许并非那么恰当,但恰巧也说明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都是混乱、交错的,而且,常常下意识地拒绝修正。但这些混乱、交错,又是不可避免的。对广州三年展等在固定展馆举办、作品收藏、文献记录明确的展览而言,或许引发的问题并不会太大。但是,对于常在城市内游牧且结束后展品几乎完全撤出、不留痕迹的展览(如深双)则不是,记忆、经验带来的问题、线索的交叉,因为缺少参照物,往往会让事实变得难以辨析。
典藏:在广州、深圳的当代实践发展、消逝和历史梳理中,你怎样看待媒体的工作所担任的角色?这种看法,是否有影响你现在所做的相关杂志内容策划和出版、书店项目?
董超媚:除了报道功能,媒体是需要一些批评能力的。然而,批判力常常缺位。像生活方式类媒体,着重点是流行文化、视觉呈现和生活美学等,对批判力并不执着。它的角色,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帮他们提取展览或活动信息,是一个辅助者、信息串联者,而不是专业媒体更强调的批评者,或者日报等社会深度的调查者。虽然如此,它还是部分呈现了历史,不失为一种档案。说到档案,其实我2017年参展深双(UABB)的文献库项目,就是为了构建城中村研究的档案及展示文献的状态。
最近关注深圳的美籍人类学家马立安开始进行城中村口述史的工作,相对以往的以研究者、作者观点主导、强调批判性的方式相比,我更倾向这种更加关注人的访谈(或口述史)的形式。我越来越喜欢人物的访谈、口述史,它们显然更具可读性、更纪实且有场景感。同时,Q&A的直观方式也更能还原真实对话,像是素材一样。我时常翻阅的《与中国有关:domus19个访谈》,就是史建策划、编辑的,包括了张永和、马清运等策展人、建筑师的访谈文本。
采访 | 马玲玲
图 | 本刊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