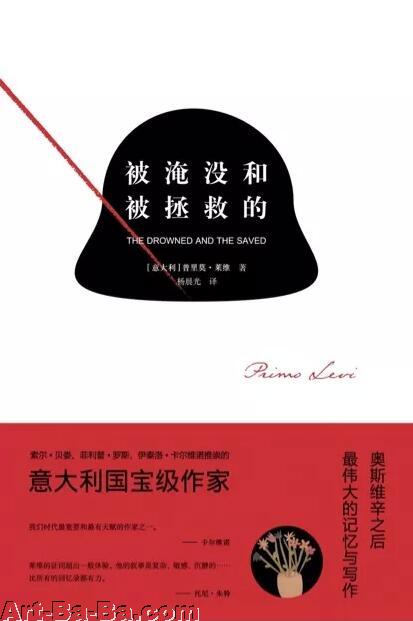来源:凤凰艺术
近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忆所》。波尔坦斯基始终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存人类的记忆? 本次展览将借助装置、影像、声音、影子剧场,引发参观者从视觉、听觉到心理的情感联系,对个体在日常和历史事件中不可预测的际遇进行追问,而其作品中所使用的衣服、图片与肖像,皆体现了每个个体独一无二的记忆。

▲ 《忆所》海报
暴力的记忆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场馆外景 (图片来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一楼的大展厅,被两件大型装置作品占满。第一件是波尔坦斯基创作于2010年的《无人》(Personnes,2010),它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成吨的旧衣物所堆砌而成的一座小山丘,十几米高,旁边是散落一地的衣物池;另一部分是一台抓钩起重机,它每隔两分钟自动下降,抓取衣物升至半空,而后突然停顿抛下衣物;第三部分是展厅昏暗的灯光和起重机启动时的机械声。观众仰望巨大的山丘绕行,当他们得知眼前这些全都是死人的衣物时,更加默不作声。远观之,还觉得整件作品像一件夹娃娃机,波尔坦斯基一定不会否认这种感受。因为夹娃娃机本身就像这件作品一样是“命运”的巨大隐喻。当我们用夹娃娃机的视角来联想这件作品,没错,在夹娃娃时,我们充满期待、惊喜或失落,我们好歹还可以扮演那些娃娃的操纵者。可是,我们自己的期待、惊喜或失落,却受到另一个巨大未知者的操纵。我们自己的哀乐喜怒跟命运,比那些娃娃更无常,也更惊险,因为我们毕竟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只是一场游戏,或者一场游戏的受害者。

▲ 《无人》,2010 法国大皇宫
绕着山丘前行,右面是两片衣物池,散落着牛仔裤、皮夹克和布衬裙,一座小桥将它们分开。在意大利大文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地狱之门上写着:“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抛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由此而入的人”。要到达地狱的第一环,必须经过一条叫Acheronete的河,而在名为“林勃”的第一环中,挤满了生前有功德的异教徒。这些散落一地的死人衣物,却更像是纳粹集中营中那些堆积成山的犹太人衣物。矛盾的是,犹太人绝不会视自己为异教徒;更矛盾的是,那只抓取衣物的抓钩,在二战中挑选出来并抛弃、乃至毁灭之的,恰恰是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这显然不是犹太人的神在挑选,也不该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在选,因为这群施暴者,他们自己就身处地狱的第七环之中。那么又是什么在选?

▲ 《无人》,2010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同样的疑问,也由旁边的第二件作品《机遇·命运之轮》(Chance-the Wheel of Fortune,2011)提了出来。这也是一件巨大的装置作品,脚手架上的传送带,陈列着新生婴儿的黑白照片。传送带不断运作,每隔几分钟随机停止,右侧的显示屏上将会出现停顿时的一张婴儿照片,照片是从波兰的一本杂志上收集而来。照片和摄影一直是波尔坦斯基创作时的主要媒介,而二战结束后,波兰人口减少了近20%。这些婴儿照,既是那些亡故的婴儿照,也是每个新生者的照片。原本可以把距离拉长到一辈子的生与死,却在一瞬间相遇。是什么挑选了即生即死的命?又是什么主宰着死后复生的运?没人知道,艺术家只告诉我们,能让生与死这对矛盾在一瞬间相遇的,必定在时间之外。


▲ 《机遇·命运之轮》, 2011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两件大型装置作品,展现出波尔坦斯基在媒介选择上的转变,从原来主要以摄影和照片的小型装置为主,拓宽到包括衣物和起重机这类日常物的大型空间装置。为此次上海个展所委约创作的《心》(Coeur,2018)同样如此,它陈列在PSA的大烟囱内部,一枚灯泡与波尔坦斯基的心跳声同频闪烁。从母题来看,这次展览很大部分集中了波尔坦斯基最关注的记忆、历史和死亡问题。

▲ 《心》,2018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记忆的暴力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是法国最为知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1944年他生于法国,有一个犹太人父亲和一个离异了的天主教徒母亲。二战期间,他的父亲曾躲在家里的地板下,而波尔坦斯基在二战的战后效应下长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

▲ 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
此次展览中,被视为代表作的《纪念碑》(Monuments,1986)、《祭台》(Autel,1987),是波尔坦斯基作品中受二战影响的重要表现。两件作品都以摄影为主,黑白的人物肖像,经过二次加工而成的装置作品,这些人物像都是死者。分明已经死去的人,却通过摄影重新出现在观者眼前,换言之,这些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却通过摄影出现在世界上。这些照片,由于技术原因,原本面容模糊,而艺术家却将这些照片放大,造成面容更加模糊。这种模糊的技术处理,是为了模糊照片与片中人的意义关系(模糊能指与所指的同一性)。因为分不清具体是谁,观者就不是在看某一个人的照片,而是在看每一个人,在看自己。这种模糊性也使得照片表现的不仅仅是大屠杀的某个具体受难者,而是数不清的男女老幼。用刻意抹去照片的具体所指,正是因为这可以使所有主体性荡然无存,“消灭所有主体性”,这是在指控大屠杀的大规模毁灭和种族灭绝。


▲《纪念碑》,1986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对观众来说,照片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或主体),变成一件作品和客体。如果说,当我们看自己的照片时(比如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拍),我们还如罗兰·巴特所言,“在照片中,我既非主体亦非客体,我感到自己是正在变成客体的主体:这使我体验到了轻微的‘死’,我真的变成了幽灵”,那么这倒还能理解为,嗯,照片中彼时的我已经死了,或者照片中在彼时彼地跟我合影的朋友也“死”了,但现实的我们毕竟还活着。可是,当我们看到波尔坦斯基经过模糊化处理的死者照片时,死者就不只代表某一个死者了,它代表所有活着却行将死去的人。这才是罗兰·巴特那句“我感到自己是正在变成客体的主体”的含义:是的,我还活着,我活着迈向死亡。这也是本雅明所谓的,死亡必须有其处所,如果它不在宗教那里,就必须在其他地方。通过摄影表达记忆和历史的庄重、将饼干盒陈列在肖像照下,形成宗教祭台,产生宗教感,这既盖过了摄影这种人工制品的平庸,更赋予饼干盒新的意义。

▲《祭台》,1987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波尔坦斯基关注“大屠杀”和二战,不单是用艺术来承载或见证历史,尽管这确实跟艺术家的经历有关。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言:“我们的记忆所保存的并不是对往昔经验毫无判断的快速复制,而要以这些经验为我们提供的意义和情感为中心。”波尔坦斯基作品中呈现出的“大屠杀效应”,绝不仅仅是想复制一遍历史经验。这些“大屠杀效应”最终发酵成对生存、死亡、道德、消逝、哀伤以及偶然性的质问和表达,并最终通过艺术媒介呈现为眼前的事实。近年来,波尔坦斯基用更丰富的语言和媒介来表达这些主题。《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的人生》(La Vie de C.B.,2005)《最后一秒》(The Last Second,2014)《离去、到达》(Depart,Arrivee,2015),都是用电子媒介来表达人的生与死;《秘语》(Misterios,2017)是三部连续影像,用来记录未知,它是所有参展作品中灯光最亮的一件,即便如此,第一部影像中原本鱼跃的鲸,到第三部中也成了一堆空守海岸的残骸,就算作品在色彩、光影和展览空间上变得更明亮了,也没能改变艺术家在意义和情感表达上的哀伤和冷静。这是一种记忆的暴力,用Ernst van Alphen的话说,波尔坦斯基的作品中的那种“大屠杀效应”(Holocaust-effects):“更少被束缚在记忆图像的惯例之上,却使艺术家更习惯于一种长期参与其中的创作,这引出了历史上的暴力时期,跟历史施暴于智识之间的冲突。”波尔坦斯基自己也认为,他和基弗(Anselm Kiefer)、波兰艺术家坎托尔(Tadeusz Kantor)在与战争和犹太文化的关联上,有共同点。

▲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的人生》,2005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到达》,2015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秘语》,2017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二战”和“大屠杀”施暴于二十世纪的精神生活。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到德国诗人保罗·策兰从莱茵河上一跃而下,从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自绝于世,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者张纯如用一颗子弹结束生命;从波兰诗人米沃什、到德国画家基弗;从哲学家阿伦特的艾希曼报告,到实验心理学家米尔格伦的“服从权威试验”,无不体现二战所带来的哀伤与抑郁。晚年弗洛伊德区分了“哀伤”与“抑郁”。处于哀伤中的人,是因为丧失了拥有的对象(无论是人、国家或理想),但他们终究能克服丧失的失落感;而抑郁者,无法达到任何成就,他们自责和贬低自己,希望自己受罚,抑郁者把对对象的内疚感,转移到自己身上。弗洛伊德认为,他们表面上谴责自己,其实是在谴责失去的对象,但随着内疚感转移到自己身上,对谴责对象的敌视态度,变成了对自己的敌视态度。

▲ 德国艺术家,基弗的作品

▲ 波兰艺术家,坎托尔的戏剧

▲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受害者的鞋子
被淹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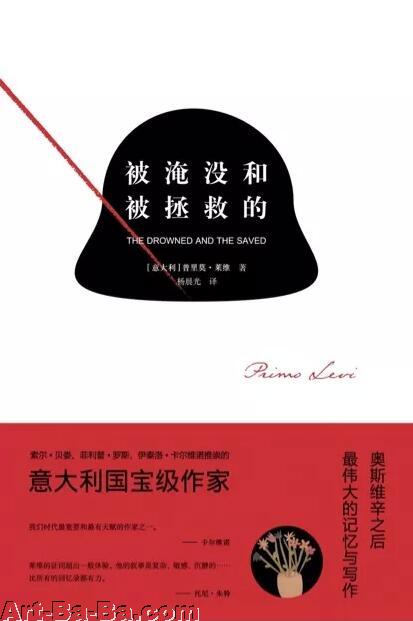
▲ 意大利作家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波尔坦斯基运用大量现代技术手段呈现艺术作品,这次展览也通过营造氛围,带来一种哀伤乃至恐惧感。迈克尔·弗雷德这样的艺术批评家严厉批判这类源自极简主义艺术的氛围营造(剧场性)。波尔坦斯基不仅接受了极简主义的氛围营造,而且还在作品中运用极简主义的作品。他自言不是一个知识型艺术家,而是在描述寻常物,要与大众情绪相关,让大众融入情感。认知科学早已表明,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单纯回想和复制,而是必须与当前的意象和感知相关。所以波尔坦斯基动用这些氛围和技术手段,为观者提供了双重信息,一个是记忆中的,一个是眼前的。如波尔坦斯基的法国前驱普鲁斯特认为的,“记忆产生于当前意象和过去意象的比较”,仅仅记住某件事没有意义,除非它跟眼前的事实相结合。换言之,观者与自己之外的他者或事实相交织和接触,是唤起记忆的对话机制,也是产生意义的对话机制。所以在大型装置作品中,波尔坦斯基通过三维实物和氛围,将观者的情感带入其中。而非看似与艺术家对话、其实是与自己对话的静默欣赏。

▲ 艺术批评家,迈克尔·弗雷德
哲学家阿多诺对技术抱有偏见,固守传统,抵制大众艺术。本雅明则从新的技术手段(如摄影术)中看到审美上新的事物,他认为大众可以借助新技术参与艺术。阿多诺想为艺术保存一片自留地,从而形成一种审美乌托邦(价值理性),来抵抗产生了“大屠杀”的现代性,抵抗现代性内在逻辑中的同一性、系统性和一致性,而且他认为唯有前卫艺术还能担此重任。阿多诺的艺术自律,原本是想呈现被现代性所淹没了的价值理性,却拒绝乃至淹没了艺术与大众相关联的一面。

▲ 哲学家,阿多诺
波尔坦斯基的作品和布展恰恰呈现出一些被淹没之物:理性之外的感性、感性之外更阴郁的感性、白立方之外的黑立方、乐观之外的哀伤、个人成长之外的集体灾难。无论是阿多诺还是弗雷德,都将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相对立,但如果像波尔坦斯基这样,借助技术手段让大众体验和沉浸在艺术和审美中,可以阐述艺术对大众的影响,并重新进入生活,那么上述对立恰恰淹没了很多东西。观众更深入参与艺术作品,才更可能阐述和沟通他们的感受。艺术作品此时即便成为社会对话的媒介,也仍可保留了它们的自留地(自律)。艺术通过这种体验重新进入生活,不仅揭开了艺术被淹没的一面,也揭开了生活中被淹没之物。

▲ 哲学家,阿多诺
波尔坦斯基的作品和布展恰恰呈现出一些被淹没之物:理性之外的感性、感性之外更阴郁的感性、白立方之外的黑立方、乐观之外的哀伤、个人成长之外的集体灾难。无论是阿多诺还是弗雷德,都将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相对立,但如果像波尔坦斯基这样,借助技术手段让大众体验和沉浸在艺术和审美中,可以阐述艺术对大众的影响,并重新进入生活,那么上述对立恰恰淹没了很多东西。观众更深入参与艺术作品,才更可能阐述和沟通他们的感受。艺术作品此时即便成为社会对话的媒介,也仍可保留了它们的自留地(自律)。艺术通过这种体验重新进入生活,不仅揭开了艺术被淹没的一面,也揭开了生活中被淹没之物。

▲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在制作小型泥球,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