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艺术家在敦煌,1982
栾志超|采访整理
李津|图片提供
ArtWorld: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去的西北?
李津:最早应该是1982年,当时还在上美院,学校正好有一个去敦煌临摹的任务。因为机会很难得,所以就去了。后来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每天不做别的,就是临摹。而且,我们当时的条件不错,不像现在有很多的游人。而且当时的洞窟都是开放的,没有护栏和玻璃之类的。基本上一个窟就一到两个人在里面临摹。这种绝对零距离接触壁画的条件现在肯定是不存在的。
当时火车一坐就是几十个小时,两天的路程。到了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风土人情跟天津完全不是一回事。主要是宗教感,莫名地就有点想哭。我在这之前对宗教也并没有兴趣,也没有做什么研究。但是,那里就是有一种气场。我第一次进到石窟看到壁画之后就总感觉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冥冥之中以前在这里呆过。光线和气息都似曾相识。
我有的时候还是有点迷信的,相信前世有一个渊源。当时是学校的很多高年级同学去临摹。我当时还在二年级,就被派去了。所以,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每天通过画画的方式特别投入地和佛教故事交流。所以,天天就跟诵经一样,只不过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图像,在宗教的氛围里洗刷自己。这就等于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那里闭关了一段时间。这个经历是十分重要的。包括我后来去西藏和西北的其他地方,起因也都是这次敦煌之行,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对话空间是无古无今的。

李津,《萨埵哪太子舍身饲虎》,水粉、高丽纸、挂轴,161.7 x 113.5cm,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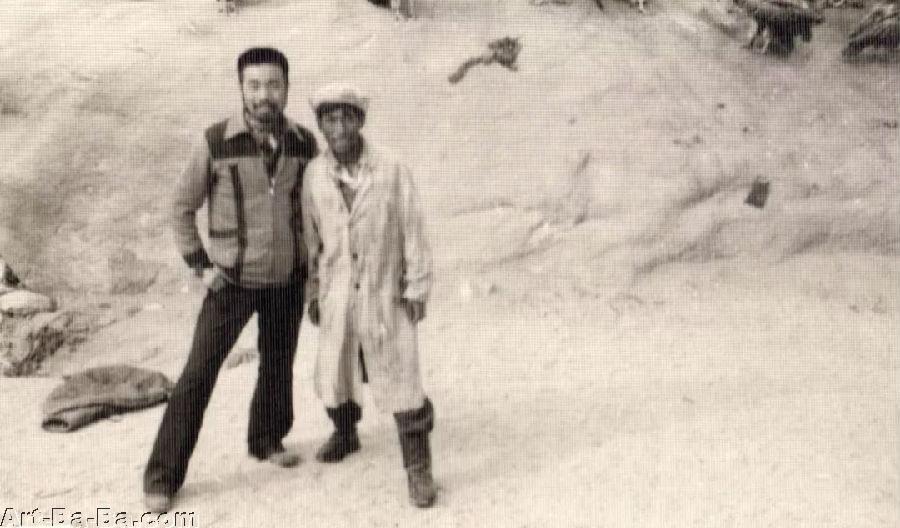
李津和天葬师在天葬场
ArtWorld:临摹敦煌石窟是当时美院的教学任务吗?
李津:是给学校资料室临摹,每个人有非常明确的分工,把重点作品临摹下来。同时也是一种课程,了解传统的同时也学习一些方法。当时,一些美术杂志已经在讨论敦煌石窟了。但只有浙美(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天津美术学院在做这件事情。当时大多数的时间都沉浸在壁画里,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临摹上,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做自己的创作。我当时的主要兴趣都在北魏和更早一些的壁画。
当时有几个北魏的窟保存的还是不错的,但当时的敦煌连护网都没有。我记得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敦煌保卫处有一位守窟人,他因为涉嫌监守自盗被抓起来了。我们去敦煌的时候,他是当时的保卫科科长。但他是个瘸子,会两下子三节棍。就这样一个人,掌控着所有的钥匙,担任着保卫石窟的重任。当时大家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概念,宗教气息又很浓,很多藏族去朝圣的时候,都会抚摸石像。所以,很多像的边缘都被酥油蹭得锃亮锃亮的,莲花座上的壁画就都被蹭掉了。
后来,逐渐地有了保护的意识。我们去临摹的时候不能使用直射光,而是使用反光板。好在那个地方没有阴天,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由于每天浸染在宗教的氛围里,也没有了各种计较,比如今天画了多少个小时,画的充分不充分等等。所以,当时就是全身心的客观临摹,没用使用敦煌的壁画方法,等于是像写生一样把面前的图像临摹下来。敦煌的壁画是有一套方法技术的,我们当时就是生画,看到什么画什么。

李津,《净水菩萨》,纸本,155cm x 80cm,1982

李津,《临摹敦煌壁画》,70cm × 34cm,1982
ArtWorld:你后来还去了麦积山石窟?
李津:对,去麦积山石窟那次也是很棒的体验。因为当时正好内部装修,不对外开放。当天还在下雨,连个看洞窟的人都没有。我就自己在里面转,特别泥泞。但是,这种时候的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像故宫在白天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故宫一样。我一个人在里面看着石窟,外面飘着小雨,感觉到的气场太不一样了。当时,我站在那里想到的都是刻工们在里面工作时的感受。
和敦煌石窟比起来,麦积山石窟的形象要更汉化一些。这就跟在云冈会发现大同人长得特别像云冈石窟一样,到了龙门石窟就是很周正的汉人形象了。石窟是很现实的,以周围人的形象作为载体。敦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山洞里的壁画和用四梁八柱盖起来的庙宇壁画不是一个感觉。我觉得,能去敦煌做壁画的都是苦行僧,要么是修身到了一定程度的高僧画家,或者是供养人花了很大的钱请过来的人。但是,我有时候更愿意看一些小耳洞,而不是重点洞。小耳洞里的创作非常自由,我觉得可能都是野和尚画的。
ArtWorld: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李津:我觉得西北是我的第一个出发点,敦煌是我的第一口奶。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们内在的审美里有这种大厚和大自在。我的审美还是想回归这种气度。年轻的时候,敦煌作为一种气场,一种文化的震撼,那种多个朝代的规模带给我的体验太多了。在那里走一趟可以看到整个历史的变迁。后来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张大千会在那里花功夫,因为没有敦煌这一页就没有后来的他。他本身能力很强,画什么都行,在哪儿都能活得不错。他那个年纪在敦煌呆几年所储备起来的东西,后来需要的气场和心量就都有了。他后来的很多东西就是把敦煌变化一下。如果他没去敦煌,那他的创作可能就会像唐寅。而且,他大红大绿的色彩也是从敦煌来的。所以,应该趁着年轻在敦煌多呆一呆。
ArtWorld:在去敦煌之前,你有看这样一些前辈艺术家去敦煌或者去西北其他地区的创作吗?
李津:严格来讲,我是从敦煌回来之后才开始关注之前去西北创作的艺术家。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有情感的,不像以前只是觉得风光很异域风情。包括黄胄的画很招人喜欢,但他只画少数民族,很少画汉人。所以就给人感觉很西洋,很欧洲。后来开始喜欢石鲁这波艺术家,因为开始对黄土有感情了。而且,黄土的感觉跟太行山很不一样,跟青藏高原也不一样。在那样的风景中,一定要有骆驼在走,感觉才是对的。我在甘肃兰州看到马家窑的彩陶,图式上类似最早的岩画,很原始。我的审美一度受到了影响,画了很多彩陶图式。

李津,《牛头》,纸本设色, 91cm x 53cm,1983
ArtWorld:你觉得他们当时的关注点是什么?有什么一脉相承的东西吗?
李津:我觉得,首先整个那代人的传统积淀要比我们厚很多。他们有很多国学的底子,而我们的积累实际上是断层的。解放之后很多东西也不被推崇,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主动地去看。那代人的文化底蕴,对美术史的了解,对东方史造型的了解,和我们也不一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西画的介入。好的一点是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活跃,整体的社会环境都想要往前走,觉得人终于打开了。当时这个气息是一种国家的整体力量,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所以,开始重新看以前一些被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再加上当时都是往外看,觉得国门之外的吸引力更大,视觉图式差别很大。但是来了敦煌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大陆。那时候就意识到这里的张力、造型和色彩是我们不能失去的。
我记得当时袁运生也在那边,我们在一起交流,他讲到他考虑到的就是中国造型的张力,其次就是色彩。后来我们谈起来民族和本土,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作为艺术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结构中,战争中人的那种刚烈和硬度是能够在西北找到对应的。他们当时是真地感到国难当头、民族灭亡了,所以是在一个大的气浪里,强调黄河、长城和敦煌。我觉得也是因为西北跟整个国家的命运是相关的。这种关联在上海、苏州是不存在的。
从艺术家的角度简单来讲,黄胄一定是一方面觉得那边适合他,另一方面想摆脱一般内陆文化人的创作。他自己想要占据一个高点,这里的图式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语言,和叶浅予的创作区别了开来。包括石鲁一定也是本能地寻找适合自己,同时又远离圈子集体束缚的视野。至少我当时去西藏也有这样的一层想法。我去西藏不是因为我要去做当代艺术,而是我在学校憋太久了,总有一种压力想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去野了,从生活到创作,远离那些计较。在那里泡了一些时间,回来后作品就带着那边的气质。

艺术家和三舅于确的通信,1983
ArtWorld:像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尚扬、丁方,以及周春芽都去过那边。你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吗?
李津:丁方一直都在找寻很厚,很有宗教气味的土地。他对土地的这种眷恋是在南京得不到的。他在西北能找到这种浑厚和苍劲。周春芽和丁方不是一个类型,他是四川人。四川实际上是个混搭的区域,不完全是汉人的天下,有很多少数民族。所以,他从小对苗族、藏族都有些感觉。因此,他的作品里既有西南的感觉又有高原的感觉。尚扬是湖北人,生长在楚汉文化之中。所以,他有长江这样的大情怀。他跟丁方更像,但要比丁方灵活一些。丁方是一根筋,但幸好他是一根筋,才有这样的创作。尚扬是在寻找自己的语言建设。对艺术家来说,最后的丰收都是要有自己的创作语言。在他有了自己的创作语言之后,他画什么都行,哪怕是小桥流水也可以是大漠孤烟直的感觉。所以,他去那边吸收自己所需的养料,建构自己的语言和态度,到最后,他画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ArtWorld:你怎么评价你自己的出生地和你去西北之间的关联?
李津:我是一个无远虑的人。天津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所谓的市井幽默感也是因为天津。其实就是马三立的逗你玩之前先逗自己玩,把无聊单调的东西趣味化,给没有意义的事情赋予意义。但是,这种东西过于技巧,这种趣味需要对接大一点的东西,让幽默成为大幽默。这种气是要去大地方养的,小环境养不出这种东西。一直在天津的话,我肯定画不出这种东西;但是到了西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感觉系统的苍白是最要命的,所以需要借助外力去除麻木。某种程度上也是接地气,去各种不同的地方。我不赞同一个人喜欢黄土就一生都扑在黄土上。有这种艺术家,但我不是。我觉得要在地球上来回地走,积累到最后,你能用上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压缩出来的信息。
ArtWorld:现在时隔三十多年,你仍然觉得西北是一个必要的参照点吗?如果再去的话,你会做些什么?
李津:特别有必要,文化的根还是要找到起点。前几年我去过一次敦煌,我在房间里看着石窟,安静地回想我当时临摹的感觉,画了一些记忆里的敦煌。因为我现在去那里不会再临摹了,而是回头体会对我影响最大的声色感、体量感。当时,这些东西打开了我对形的意识,整个的把造型和度都撑开了。这些年我经常画市井,把市井拘泥在现实和细节里。回到那边之后,我觉得细节不是生活的细节。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之后,我可能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里找到了感觉,找到了大的空间思考和大的姿态。
这种姿态也是很细微的。其实哪怕是很离谱的敦煌壁画,都是极其讲究的。大的东西不等于里面是空洞的,而是那种向外的延伸太厉害了,所有的量和气场都是向外的。所以,我觉得回头是必要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到直觉打动你的东西,比如色彩和表情,或者是构图。年轻的时候直觉好,但是有了一些经历之后,还会看到更里面的。
ArtWorld:能具体谈谈敦煌壁画引发你所做的绘画的思考吗?
李津:在敦煌的三个月里,我们其实都是在和敦煌壁画做交流。我发现环境对绘画形式有直接的影响。壁画里的风景和山水完全是沙漠的曲线和韵律。后来我去了新疆,我发现我们大多数时候认为的中华文化的起点是长安。我觉得这种对汉文化的认识应该要转换了,如果追不到源头的话,肯定就是不对的。从克孜尔怎么来的敦煌,北魏怎么会有波斯的东西,包括当时的丝绸之路上有很多拜占庭的典型图示。但今天的美术史并不这样写。如果宋没有南移,仍然守在西北的话,那今天中国的艺术形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当自然环境里有了那么多曲径通幽的东西和遮蔽之后,整个人的思维、审美都会发生变化。你会在环境中找相同的趣味。那种天地人的现实在江浙是一种幻想。但审美是要穿透遮挡的。而西北是不存在遮挡的,一切都是一览无遗的。太阳这边升起那边落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参照,开车是奔着一个地平线去的。所以,人们思考问题也不会那么琐碎,没有那么多故事可以思考,只有寂寞。回到起点实际上需要的是这个气度。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视觉化的时代,图式的辨识更需要一些横平竖直的东西。

李津(右)和李彦平,背后为参加1984年前进中的中国美术展览的作品《月亮河》
ArtWorld:你谈到你喜欢在地球上来回走,每个地方给艺术家能提供不同的东西。西北能给艺术家提供的是什么?
李津: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我们总是要奔着源头走的。这个源头是深埋在那片土地的,是我们今天必须去接壤的。不管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都需要去找到这种根源性的东西,找到气场。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往那边走。那片土地的朴厚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不仅仅是在风景里,包括在人身上,在文化里都有很多原生态的东西。这些保留下来的朴素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多么贫瘠和苍凉,不管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多少故事和悲歌,他们内心始终都有所仰仗和支撑。对当地人来讲,不管是贫困也好,还是单调也好,精神上的依赖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生存,但居然有世世代代的人生存了下来。这其中一定有非常强大的理由,他们的基因里一定有这种勇敢和忍耐。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落后,反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这不存在先进或落后,而是人的踏实。他不惧生死,很踏实,安静。
ArtWorld: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和地方的生态,如果写生和采风只是把它当作是景观的话,怎样的切入是合理和有效的?
李津:写生是一个手段,关键是你通过写生要找到什么。很多早期的艺术家都写生,但是他们的写生包裹着一个时代的审美。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人的素质和文化底蕴。所以,写生,包括课堂作业都得画成创作。创作要求把自己的感觉和景观融在一起,把自己的态度介入进去。所以,西北的画家和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审美上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优势。我觉得他们现在更多地是从彩陶、石刻、壁画中找自己的审美方式。外来户只是在借鉴,而他们是这块土地所养育出来的人。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自己是谁,这样哪怕你到了其他地方也会保护自己的本钱,不会伤害自己。如何找到自己,找到血液里、基因里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这些是不可代替、不能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