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螺社区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一度默默无闻的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和大学教授乔丹·彼得森的大火,证明了自由主义-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彼得森,这个说白人特权这个观念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谎言”,并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不谈论沙特对人权的侵犯,是因为“她们无意识地希望男人来残酷地支配他们”——的家伙,很快成为一名主流评论家。
与之前反对LGBT+的明星,米罗·雅诺波鲁斯(Milo Yiannopoulos)相比,彼得森的优势是明显的。雅诺波鲁斯风趣、语速快、段子和讽语多,并且公开出了柜——在许多特征上,他和他攻击的那种文化很像。彼得森则是他的反面:他结合了一种“常识”的进路,和(表面上的)冷静的科学论证,论证中又带有一点苦涩的愤怒,愤怒于我们社会的自由主义基础受到了威胁——他的立场是:“够了!我不能再忍了!”

米罗·雅诺波鲁斯(Milo Yiannopoulos)
他鼓吹的,用冷静的事实来反对“政治正确”的破绽,是很容易察觉的:他不仅经常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而且,他的大问题,在于他用来诠释他所谓的事实的那种偏执的建构。“事实就是事实”,他喜欢这么说,但接着他又会说“那种认为女性在历史上饱受压迫的想法是一种骇人的理论”,以及,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就和声称世界是平的一样糟糕”。
雅克·拉康曾经写到过,就算嫉妒的丈夫所说的关于他的妻子的话(她到处和别人睡觉)都是真话,他的嫉妒也依然是病态的:病态之处在于,这个丈夫对嫉妒的需要,他需要嫉妒,嫉妒是他维持自己的尊严、甚至是认同的唯一方式。按此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哪怕纳粹关于犹太人的大多数说法都是真的(他们剥削德国人、他们引诱德国姑娘,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并不真实——他们的反犹主义,也依然是(并且实际上也是)一个病态的现象,因为它压抑了纳粹为什么需要反犹主义来维持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理由。在纳粹的想象中,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和谐合作的有机整体,所以,他们也就需要外来的入侵者,来为分裂和对抗负责。
今天,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也是这样处理难民“问题”的:他们是在恐怖的氛围、是在即将到来的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斗争的氛围中切入难民问题的,而且,他们陷入了一系列显而易见的荒谬之中。对他们来说,逃离恐怖的难民,被等同于他们所逃避的那些恐怖主义者,但显而易见到不言自明的事实却是,尽管难民里很可能也真有恐怖主义者、强奸犯、罪犯等等,但绝大多数难民依然是寻求更好生活的,绝望的人民。
换言之,这些问题的原本内在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原因,被投射到一个外来的入侵者头上了。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并不危险,因为它谎话连篇;只有在它的谎言以(部分的)事实真相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才最危险。

乔丹·彼得森
来源:jordanbpeterson.com
不幸的是,自由派、左翼对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民粹主义和左佬的“政治正确”实践了两种互补的谎言,二者刚好符合歇斯底里与强迫性官能症之间的经典区分:一个歇斯底里的人会在谎言的伪装下把真相说出来(他说的话严格来说并不真实,但这个谎言却以假话的形式,表达出真实的抱怨);而一个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则会说出严格来说真实的话,但这个真话却服务于谎言。
民粹主义者和政治正确的自由派同时诉诸这两种策略。首先,民粹主义者在为他们认为是他们的事业的更高真理的理想服务的时候,就会诉诸事实性的谎言。宗教的基要主义者也提倡“为基督而说谎”——比如说,为防止“堕胎这种可怕的罪行”,你可以宣传关于胎儿生命、和堕胎在医学上的危害的伪科学的“真相”;为支持母乳哺育,你也可以把不用母乳哺育就会导致乳癌等包装为科学的事实。
常见的反移民民粹主义者也为使他们的“洞见”——难民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威胁——显得更加可信,而无耻地传播关于难民犯下的强奸和其他罪行的,未经验证的故事。而太过于经常地,政治正确的自由派,也在以类似的方式行事:他们对难民与欧洲人之间的“生活方式”的实际差异避而不谈,因为谈论这些差异,看起来有提倡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想想罗塞兰的性侵丑闻吧,人们为避免被诠释为种族主义,而对施害者的种族轻描淡写。
相反的策略——在真相的伪装下说谎——在这对立的两拨人那里也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如果说,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不仅宣传事实性的谎言,也狡诈地使用带有真实性灵光的事实性真理的碎片,来包装他们的种族主义谎言的话,那么,政治正确党也在实践这种在“用真相来撒谎”的把戏:在反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斗争中,政治正确党大多会引用一些至关重要的事实,但他们又经常会对这些事实做一些错误的扭曲。民粹主义者的抗议把真实的挫败和损失感移置到外部的敌人头上,而政治正确的左翼则用其这些真实的点(在语言中发现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来重申它的道德优越性,并因此而阻碍真正的社会变革。

#MeToo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彼得森的爆发会有这样的效果。他的疯狂的阴谋论——他认为,LGBT+权利和#MeToo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者毁灭西方的计划的最后支流——当然是荒谬的。这种阴谋论完全没有看到自由主义计划本身内部的对抗与不一致:那些已经做好为言论自由而宽容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笑话的自由派,和那些想要把这些笑话当作妨害其受害者的自由与尊严的障碍来审查的政治正确的管制者之间的张力,和真正的左派没有半毛钱关系。
彼得森说出了我们许多人觉得在政治正确的过度管制的宇宙中不对的地方——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的理论,而在于他用来维持他的理论的部分的真相。如果左派不能正视自己计划的这些局限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打一场已经输掉了的战争。
译自Slavoj Zizek, “Why do people find Jordan Peterson so convincing? Because the Left doesn’t have its own house in order”, 原载The Independent, 13 Feb, 2018. 见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jordan-peterson-clinical-psychologist-canada-popularity-convincing-why-left-wing-alt-right-cathy-a8208301.html。
来源:海螺社区
齐泽克丨关于与乔丹•彼得森的交火,对我的批评者的一些回应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下面这些评论,是对人们对我在《独立报》上发表的关于乔丹·彼得森的评论的诸多批评的回应。
我的批评者在提到彼得森与另类右派之间的关联的时候,要表达的主旨是,在展示我不熟悉我所批评的对象的同时,证明我错了:他们认为,其实,彼得森是激进的自由派(他支持福利国家等等),他担心政治正确、认同政治、LGBT+等对言论自由及其他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提出的威胁。在把彼得森定位到另类右派那边的时候,我像政治正确、和后现代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一样,忽视了基本的事实。
我发现这条思路很奇怪。无论你怎么看我的理论,我的理论中的一个常量,始终是批判地拒绝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和那种把现代科学贬斥为另一种“话语实践”(这样的话语实践的“真理-效果”又是历史地相对化了的)的做法。而且,大约在一年前,在我质疑政治正确和LGBT+运动的一些方面(和今天的“激进左派”的其他一些成问题的方面,比如说对难民的主流立场)的时候,我不仅遭到了一系列非常残酷的攻击,更是被逐渐排除到公共媒体之外。所以,如今,还能接受我的英文媒体只有下面三家数字媒体了:《独立报》、《今日俄国》和《洛杉矶书评》的一个频道(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途径也够我发表这篇回应了,我没能把它发在《独立网》的网站上,因为作为评论,它太长了)。我还能在《卫报》,有时甚至还可以不时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甚至《当今时代》也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所有这一切,喜剧的一面是,我经常因为同一个文本遭到多方的攻击,一方认为我是欧洲中心的种族主义者,而对立的一方又认为,我仇恨西方传统……这出喜剧的一部分,是《独立报》上对我的文本的诸多回应:阅读这些回帖,你会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我只是在攻击一方,却没有指出双方都在诉诸同样的策略——在真相的伪装下撒谎。

乔丹·彼得森
这就把话题引回到彼得森。在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两个层面。首先,是他对PC, LGBT+等的自由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关于何以它们对我们的自由提出挑战,尽管在这层面上彼得森那里也有我不同意的东西,但我也在其中看到一些有价值的评论。我和他的差异在于,在批判政治正确的诸多立场和政治实践的同时,我也在这些立场和实践中看到了一种对非常真实切迫切的问题的经常是不充分的、扭曲的表达。你不可能通过引述《五十度灰》,那个关于一个享受被支配的女人的故事(就像我的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说跨性人的苦难太过于真实,等等,就把认为女性受压迫的主张给打发过去。在发达的自由主义社会中,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压迫的作用方式,比直接粗暴的那种,要更精致得多(但也这样的压迫也同样地有效),而最危险的错误,莫过于把女性的低下地位,归结为她们的自由选择了。
但在彼得森进入阴谋论领域的时候,我是真心地不同意他。在我看来,真正成问题的是,他把政治正确(和他的其他攻击目标),诠释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阵营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认同政治、性别与酷儿理论等等)的极端的副产物。他看起来是在暗示,“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策略中的一次蓄意转向的结果;在共产主义输掉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战(徒劳地等待革命来到发达的西方世界)后,其领袖决定把领土向文化斗争的方向(性、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宗教……)转移,以系统地侵蚀我们的自由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在最后几十年里,事实证明,这种新进路格外地有效:今天,我们的社会陷入了自我毁灭的罪责循环,而不能在保卫自己的积极的遗产了……
我并没有在这个思路,和自由主义之间看到任何必然的关联。一些秘密的共产主义骨干为摧毁西方的自由而操纵“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想法,纯属另类右派的阴谋论。而这个想法居然可以被动员起来,作为自由派对我们的自由的捍卫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自由主义计划内在的缺陷。首先,不存在统一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域:今天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本就是“法国思想”的最恶毒的诋毁者;许多“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剧烈批判认同政治等等。其次,任何对法兰克福学派或对“法国思想”的正面评价,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被禁止的,在那里,当局更倾向于接受盎格鲁-萨克森的分析思想(我自己青年时候的记忆就是这样的),所以,那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及“文化”版的马克思主义不知怎地为同一个中央施动者所控制的主张,不得不把其真实性建立在那种非常可疑的,认为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操纵傀儡的提线大师的想法的基础之上。最终,尽管我承认政治正确和一些跨性取向(这些取向见证了一种古怪的合法化、禁止和管制的意志)的所谓的“极权主义的”过度,但我并没有在这一倾向中看到任何“激进左派”的痕迹,相反,我倒是看到了一种在努力保护、保障自由时误入歧途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永远是一个不一致的计划,它充满了对抗和张力。
如果非要让我来进行偏执的揣测的话,那么,我更倾向于说,政治正确的强迫性的管制(就像要求用不同的代词来称呼不同的性别认同,不然就诉诸法律那样)毋宁说是左翼-自由派为破坏一切真正激进的左翼运动而搞的阴谋。在这点上,只要想想一些LGBT+和女性主义圈子对伯尼·桑德斯的仇恨就够了,这些圈子里的人,可是觉得支持他们的那些大公司老板没什么问题呢。政治正确和#MeToo运动对“文化”的专注,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来说,是一种避免面对实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把女性的压迫和种族主义放到它们的社会-经济语境中去看——的,绝望的尝试。你一提到这些问题,你就会被指控为庸俗的“阶级化约论者”。瓦尔特·本·迈克尔和其他人已经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在欧洲,罗伯特·普法勒也写过好几本批判政治正确居高临下的姿态的书,并已经发起了一场“为成人而成人”的运动。自由派将不得不注意到,来自激进左派的,对政治正确、认同政治和#MeToo运动的批判是越来越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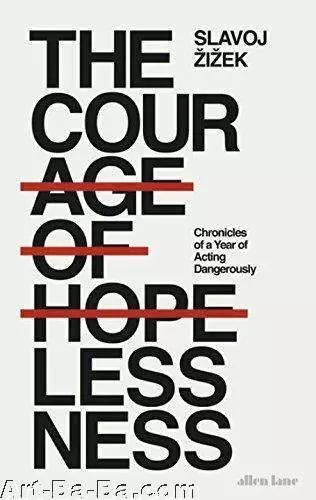
《无望的勇气》
这里不是全面展开我的观点的地方。对于有兴趣的人,我推荐你们去看看我刚刚在美国出版的《无望的勇气》。最后再说一句。我既不玩脸书,也不发推特,但我得知,许多匿名人士在这两个媒体上以我的名义活动。这些都是冒牌货。所以,在得知彼得森在回应一条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推特时,激我与他辩论时,我大吃一惊。但如果他真想辩论,我准备在下次,也就是明年十月到美国的时候跟他来一场。
译自Slavoj Zizek, “A Reply to My Critics Concerning an Engagement with Jordan Peterson”, 原载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reply-to-my-critics-concerning-an-engagement-with-jordan-pet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