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引言]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既可能在改造,也可能在破坏生态。精英职业人士霸占了那些创造性的、关怀的、自治式的工作岗位,使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去做一些鸡零狗碎或半官僚式工作,然后国家再将找不到像样工作的穷人当宠物来养着,这就破坏了全国的工作生态。职业精英们在其中受罪的同时,还口口声声要去改造社会环境之外的生态。那他们既然号称要改造生态,也许首先就应该从阻止他们自己为了守住手上这份所谓的创造性的、有精神性的工作,而对社会的生态加以破坏这一点开始。你想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手头的工作都不能够成为自治的行动,不能使我们自己通过劳动融入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之中,那么,外面的生态又怎能搞好?贝特森说,做生态工作应该从改善我们的脑中的观念之间的生态开始,那么,我们也应该从改善我们自己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改善每一个人的劳动与他人之间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来开始我们的生态工作,甚至先要从设计我们自己的工作与他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或生态开始。不光设计我们各自的工作之间的生态,设计师更必须同时设计自己的工作:自我设计(self-design),而这是先锋派艺术家马列维奇式的工作了。
1-设计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
今天,越来越多门类的劳动带上了非物质性。非物质劳动有点像设计劳动了。今天的劳动者经常像设计师那样,是一个开发自我的企业家,付出的是一份自治的劳动,得到的却是一种含有集体价值的社会性收入,也就是,作品和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社会共享的,无法全归劳动者本人,成了社会的共同物,为一切人所用。但同时,,正如设计师个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也都被当作固定资本投资在了其设计工作之中,也就是说,资本家除了从设计师的劳动中,还从设计师对自己的“主体性”的生产中抽取利润,那么,今天的非物质劳动者的主体性,也正在被这样开发和剥削。设计师的被剥削,非物质劳动者的被剥削,在今天的后-福特主义劳动场所中,比纯体力劳动者的被剥削还更多了一层。
根据Maurizio Lazzarato,非物质劳动除了生产出产品,还同时生产出了其中的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labour3.htm)。非物质劳动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数码技术应用、性别角色牵入的社会劳动和家庭和学校的劳动组织之中。这些劳动具有情感性和认知内容,是生物政治式劳动,内含劳动者个人的主观价值,有点像妓女的劳动,情感劳动和身体劳动正是其卖点,另如瑜伽或健身教练,都是如此,其劳动的价值很难独立估算。另外,今天我们在网上和屏幕上所从事的数码劳动,也基于对共同物的同侪生产和针对用户的内容生产,包括了开源、自由软件、众筹和灵活的执照协议下的内容挪用,也包括在普遍的分享中的版权瓦解后的内容共享和进一步的集体内容开发,生产本身带上了社会性,必然是免费共享的。我们的劳动具有了更大的社会性后,劳动成果也更被全社会分享,实际劳动成果的大部分,也被归入社会的集体财富之中,尽管后者现在正被淘宝和脸书们侵吞。在未来,数码看护、全球教育中的群组劳动和在数码和知识经济中由其它的社会介入所生产出的对社会的关注和关怀,也仍将被大网站和资本巨头当作“活劳动”来剥削,我们得想想办法了。总之,我们的非物质劳动正在成为被寄生和剥削的对象,而它本来应该是今天的诸众的自我创造的动力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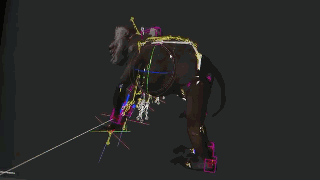
同时,在今天,普遍和随时随地的人和物之间的分离,也使艺术家和设计师越难确认其作者追溯权。由此创造出的留在各种网络平台上的集体参与所留下的大数据,是典型的共同物,目前却落入阿里巴巴们手中。个人作品在今天很难独立出来,去与大公司的产品竞争。这是一种很难堪的局面:我们本该欢迎共享时代的到来的,但这种共享总是先落入大资本的手中。
以非物质劳动这一眼光看,设计中的劳动和生态建设中的劳动之间就有了某种共通的东西。设计师对于自己的设计工作所处的环境的敏感,迫使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设计成为一种负责、保护和守护遗产的劳动、关怀他人的劳动和为达到个人自我实现的劳动,这些都通向每一个人的自治的劳动。这种自治的劳动涉及劳动者在系统内对自己的工作的控制论式调节,横向是在同事和同行之间进行联合,纵向是在管理和社会交往上下功夫,来造成新的团结。在这种情势下,设计师应该成为新劳动的社会开发方面的楷模,而不应被束缚在传统的设计师角色上。
这时,设计工作更显示出它在定义和确立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趣味、消费准则和更主要的,也就是对于公众舆论的把控方面的强势。设计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定夺这些标准、趣味和准则时所付出的主体劳动。正如做小吃的老板的劳动,比如他们在熬汤时的品尝,就是在为我们食客定夺口味。这种预先品尝是在为用户服务,与设计劳动那样,都算是非物质劳动。
这种广泛参与的非物质劳动中正形成一种群众智性(massintellectuality)(同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对个体生产中的个人自我价值化的要求强逼出来的,但客观上它也就造就了一种集体智性的共同平台,与那个大数据对立。这种群众智性,在内格里和哈特看来,是引领我们的未来的新君王:我们不能靠一个领袖来指出我们的未来的政治道路,这种群众智性才能够(内格里、哈特,《集合》,231ff)。
每一个非物质劳动者也都是在某个界面上工作。这个界面打通了各个不同的功能部门、工作团队和不同等级层面。他们的每一个都形成了自己的平面。而设计劳动不就是从来都处于这样一个界面上?它既是艺术,也是教育,更是一种道德示范,在今天也应该是对生态教学法的一种现身说法。设计师的传统角色在今天受到挑战,这就不难理解的。
现代主义设计在出现之初就必须回应那个拉斯金-莫里斯问题:设计到底是不是一种手工劳动?或者说,设计是否应该单立,成为身体劳动之外的另一种身体劳动?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激进在于,他们认为设计就应该隐含在手工劳动之中。在包豪斯的建造哲学中,身体劳动也被认为是粘合科学与艺术的媒介。设计师被认为应该去教会大众做出自己的身体劳动,不要成为独立的一门技术或艺术。今天的很多设计师要强调自己有多么原创,包括对包豪斯精神的推崇,也仍是想要回到这一手工劳动的本真性上。
但是,在今天,由于在这个时代里,非物质劳动正成为普遍实践,我们就必须重新来问了:设计到底是手工劳动,还是艺术劳动,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数码界面上的集体、诸众式、社会性劳动?动用设计软件的设计工作还可能是纯手工劳动吗?
很明显,拉斯金和莫里斯关于设计是手工劳动的这一定位,在今天是过不了关的。
今天,我们遭遇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性协同的激烈自治”。不光设计师,连一般大众的劳动,也都这样地自治了。这其中,设计也只不过是多型的自我雇佣的自治工作(polymorphous self-employedautonomous work)罢了(Lazzarato,同上。)。在非物质劳动中,这种工作渐趋主导,劳动者也成了智性工作者(intellectualworker),与设计师一样了。他或她自己经常就是一个开发自我的企业家,不得不将自己插进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变移的市场和网络之中。设计师这时应该如何跟进?
总之,非物质劳动迫使我们重思我们过去对工作和劳动的古典定义,因为它是很多种技术的社会协同的结果,是智性技巧、体办技巧和开发技巧的有机结合。它通过网络和算法,也将设计和管理纳入自身之中了。网上或开源设计时,非物质劳动立刻以集体形式来构成,总是立刻以网络和流动来存在的集体形式:是人力、知识和行动的交叉产物。这其中,设计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生产出了现实的新的层级,为产品和品牌附加生产出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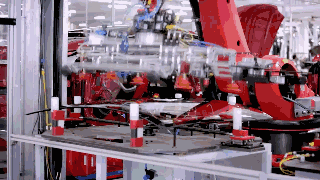
特斯拉生产线
二、
非物质劳动具有了更大的社会性,而全球资本主义装置正通过大数据经济,抽取由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出的共同的社会财富,夺取本来就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今天的数码状态下的非物质劳动的社会价值所创造的财富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反对私有财产本身,反对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这对这种共同财富的占有,是我们的新政治目标了(内格里和哈特,《集合》,94-95)。
今天我们须讨论的另一个关于工作和劳动的面向,是:人工智能加入后,工作的稀少将给社会生态带来的压力后,我们应该拿出怎样的对策?我们应该如何来迎接工作将越来越少这一局面?如何通过设计社会内的工作本身,在新的技术条件,来分离工作和收入?
社会学家Gorz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与今天大家普遍担心的不同,如果我们以改造社会生态这一大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工作岗位的日趋稀少,反而会给我们打开通向另外一种社会的视野。为经济目的而做的工作的正走向终结,而这同时也将使个人的自治活动在社会中变得更有压倒性。这时,自由时间会多过劳动时间。这一自由时间将激励大家创造更多的共同价值(《经济理性批判》,183)。这时,如果创造性、凑趣,美学和游戏压倒了工作中涉及的效率和利润率,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大变样(同上,184)。所以,我们必须批判目前的经济理性,用另一种理性来看待这种新局面,帮助一个新社会的早日到来。这相当于要逼我们自己去发明出一种新的关于活着的艺术,去更社会的自我创造的诸形式。
实际上,在目前的现状下,如果我们不对收入和工作进行分享,那么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只会给我们带来社会的隔离、贫穷和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也只会加剧“所有人对所有人之间的战争(霍布斯)。而反观今天,通过娱乐工业和休闲工业来剥削大众,是今天添加到人民头上的又一苦难品种。而相反,在工作之外多出来的这些时间里,为自己做的工作,如建房、园艺、关怀直接周边的环境和社会地介入互助活动,不光会创造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激发出个人的能力和渴望,而付工资的劳动却只会使这两者同时枯萎。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旦人们有了自由的时间来做公共事业,那些维护公共物品或遗产的工作,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会带上新的价值;很多临时的军事式帮助,都可由这一部分劳动来完成。艺术和文化生产最终也可以依赖业余爱好者来做了。而且这还能推动和倡导各种微型文化,后者更利于为社会生产出新的意义,比目前这些由大众媒体弄出来的标准化的材料更有积极的作用。
相反,如果最近的技术发展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不能为每一个人的工作省下时间,不能帮我们每天从中解放出几个小时来,如果这一被解放出来的时间也不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服务,那么这省下来的时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8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为每一个人带来福祉,后者可能并不表现为更多的财富,而更可能是得到更多的自由时间,有更大的余地去做自己的更自治的劳动。
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地问下面这个问题了: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要改变目前的这种工作的被垄断,首先就要求我们拿出一种职业觉悟:必须审视技术、经济和商业决策对社会和这个文明造成的后果,认真考虑进退之间所涉及的赌注。为什么我们得坚持目前的这种工作伦理?这样的坚持会有什么消极后果吗?
Gorz提醒,我们必须小心,别中了下面这种工作伦理的毒:为努力工作而努力工作,努力工作成为目的本身;为生产而生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一定会导向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里的场景:大胆妈妈很愿意让独裁者发动战争,让大儿子阵亡,小儿子残废,这样自己的小生意就会红火,女儿在兵工厂里也能每天干十小时,多挣半份工资。
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将不再能给每一个担保工作的机会了。所以,只有重新安排能养活每一个人的工作时间,人人的工作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而且还必须给每一个人到经济之外去工作的权利。社会也必须将这样的工作看作是正常的。
那些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的工作和自治活动,由此发动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工作者的深入社会,会使他们更对这个文化有归属感,这些也应该被算作工作。
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场地和空间,使人们能在其中发展他们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能力,能对他们的社会关系作自我管理:业余大学、社区学校、社区中心,服务合作中心、互助组、合作修理和自我生产车间、讨论组、技术转让中介、艺术和手工艺组等等,都可算作是工作,尽管不是目前的这种经济体系里的工作。
这样,如果大规模失业真的到来了,我们也将不用担心,因为,吸纳整个人的失业人中的到来,这时也将不是像当前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所担心的那样的灾难,而是改造社会生态的良机了。
在Gorz看来,这种由工作的平等分享开始的社会改造,出乎意外地,将左派的传统目标也就是人的解放与对生态的捍卫结合起来了。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生境里,反抗我们的生命的被资本职业化、技术化和货币化,也成了对我们的环境问题的改善的一部分!生态工作须以人人的被从劳动分工和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为前提了。两个事情可以一起做了!
现实地看,如果每周的工作时间缩短到25或30小时,我们的很多活动就不用与经济效率挂钩。这会使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更丰富。我们的文化和审美活动就会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多的快乐,并且提高和培育出新环境。社会的帮助、关怀和互助活动也会在邻里之间和本地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团结形式。每一个人会更注重对友谊和感性关系的培养,和教育和艺术活动的展开。诸如对物品的修理和生产,自足的食物生产和供应,为了获得自己耕作这一快乐,为了保存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将它们带给下一代所带来的快乐,服务-交换式的合作组织,都会根本地改变我们的劳动的性质(234)。
Gorz的核心关注是,工作时间的减少必须使我们使自己的更多的活动摆脱经济理性的专制,增加我们自己的创造性、互助和自娱的活动。而每一个人都会因此而将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将做得满意,当作目标本身。
一年一千小时的工作可被划到每星期二十小时,可在每周的两天半内完成,或每月工作十天,或一年工作二十五星期,或两年里工作十个月。这样,一生只要工作两万到三万个小时(236)。我们甚至可以由每一个人在五十年的活跃期里挑时段来工作,可以在任何时段,不论有没有在这期间上班都得到目前每年1,600个小时下的工资待遇。
总之,在Gorz看来,今天的工作的稀少,不是因为人们缺乏才能,不能够找到工作,而是因为创造性的、负重要责任的、有技能的工作都被少数职业精英垄断了,后者总是拼命捍卫其公司职位和阶级特权和权力位置,大学也为此而将职业搞得像是军训。正是他们逼社会中的其他人去做那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使后者在社会中感到自己是废物。分享工作,就意味着不让职业精英霸占那些工作,这些重要的工作必须纵向地被分享。一个外科大夫或大学的系主任的工作必须与一个普通人分享,因为这是国家的工作,不是他们个人的特权。
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总是希望他们的子女去成为教师医生银行人士,他们所以总要国家去捍卫这些职业的稳固性,来为他们的子女开路和保障。今天的教育的父母从幼儿园开始的就打破头往前挤,就是出于这种特权争夺。人工智能普及,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后,工作和收入的全民分享必须以打破这种中产阶级及其子女的工作特权为第一目标,倡导真正的社会平等,鼓励人人成为负责的公民,使所有人都愿意为所有无工作的人兜底,让人人都有自主的活动来服务社会,获得奉献式地付出而生的满足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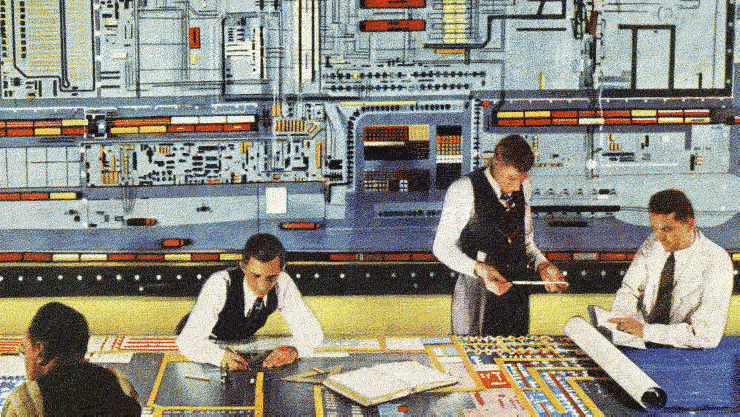
三、总是为着那个老问题!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配比!
1962年到1982年间的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中的那种劳动主义,自下而上的社会设计和改革,堪比中国的文革时“上海公社”和工农兵的又红又专道路。从今天看去,它是人历史上对于贡献式经济的极其重要实践,是对社会的总体生态设计的一次伟大尝试,尤其是在对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之间的自我管理下的公平分配上说。
这种工人自我组织式的“劳动主义”帮助工人们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惊天搏斗中,漂亮地扳回了一局。
1968年4月,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厂的工会被工人们抛弃。工人开始自我组织。每一个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参与了组织动员,每一个人身上的非物质劳动和工作的社会价值创造突现,使得在这一新共同体里,共同物终于压倒性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年青人是最善于利用共同物的群体,所以青年学生也被看作劳动者。今天的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APP的熟练利用,也正是他们对于共同物的利用的高出一筹之证明。
1968年4月,在都灵,菲亚特的工人向雇主施加压力,要求把工作时间压缩到每周40小时,取消义务性的加班制度。从此,工人拒绝把日常的罢工组织委托给工会的官员,相反,他们以当时学生集会的模式为蓝本,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集会制度。至1969年春,菲亚特汽车厂已成为暴动的中心。刚好在那一年,菲亚特被迫招募了大量的新工人,当地的警察和神职人员事先又没有对这些工人做持久的调查。结果,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及那些和西德工会有过接触的工人,在来自梅佐乔尔诺的非熟练工人群体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场激变持续了将近一年,彻底改变了菲亚特的形势。米拉费奥里厂的工人拒绝接受加速生产的管理条例。4月,菲亚特全体工人举行罢工。50天的持续斗争在1969年7月3日到达了顶点。那时,工会号召在都灵举行总罢工,以抗议该城市过高的地租——结果引发了工人和警察之间大规模的街头械斗。这样的冲突在都灵始于菲亚特,在米兰始于马尔盖拉和比雷里,从1969年9月起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现象。卷入那年秋季罢工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了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达5亿2千万个工作时,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惊人的数字。1969年11月,2000万意大利人加入的总罢工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养老金制度。
1969年和1970年初赢得的协定,代表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可观的胜利。100万以上的冶金工人和机械工人所签订的工业联合会条约开创了先例。它包括:在两三年内将周工作时间减少到40小时;限制加班,承认加班只能是偶然的而不能是正常的周工作时间;在雇员15人以上的工厂,工人每年有权在工作时间内召开10个小时的集会;承认工会代表的合法地位,他们为工会工作,每个月有8小时是支薪的,其他时间则不支薪;工会合同的基层批准制度;在培训活动中工人有权保护自己;平等主义的工资增长必须超过通货膨胀率等。传统上,意大利工厂传统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黑名单、政治监控、在生产流水线上因交谈或由于午餐时间浏览报纸而被立刻解雇时有发生。工厂还成立所谓“流亡部门”以便把那些偏激分子和其他工人隔绝开来,而这些政策变动无疑代表了生产第一线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这些还仅仅是开始。
劳动时间的划定是这场斗争的标的,双方卯足了劲,要在这个领域展开拉锯战。菲亚特当时如果真的要想削减劳动力人数,管理部门只需接受联合会的轮换解雇的提议就可以了。因为菲亚特本身就有每年自动裁减12000名工人的计划,这对管理部门来说应该是够了。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重新收回1969年失去的对劳工及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从工厂开除出去的23000名工人并非随意指定的:他们之中有数量非常不成比例的政治积极分子、妇女、年轻人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选择有失常规。对于留下来的幸存者来说,厂里的气氛立刻就彻底地改变了。在1981年的罢工斗争中,菲亚特损失的仅仅是100万个工作时,而上一年它们的损失则高达1350万个工作时。工人们再次害怕成为冗员,对监工也是胆战心惊。在新的工厂纪律下,消极怠工这一著名的社会现象即刻消失了。罢工之前,旷工率一度高达14%-18%,现在降低到了3%-5%之间——甚至低于以屈从而闻名于世的日本汽车工人,他们的平均旷工率高达约8%。产量一年内增长了20个百分点,公司回到了令人满意的赢利状态。在罢工后的最初18个月内,菲亚特本部施加压力,关闭了几个分厂,继续临时解雇工人,短时期裁员经常一次就多达4万人。生产线上越来越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人。到80年代中期,菲亚特已经可以夸耀它们是欧洲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汽车生产厂,在国际市场上阔别多年的份额又被他们夺了回来。意大利权势集团的这场胜利的代价是由意大利全体工人阶级来支付的。都灵工人在1980年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是整个意大利劳动者的一个转折点。菲亚特发生的事件为后来定下了不祥的基调。也是今天我们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的新切割时所要考虑的前景。这一拔河比赛接下来不得进行。
四、小结
设计我们的各自的工作岗位之间的新生态,要求我们改造社会目前的劳动-工作生态。这将会将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拉到一起。个人获得解放,与活到一个更好的生态之中,相通了。这并没有给我们的改造社会的任务加大份量,而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说的那种新的组合,是我们走向爱的新世界的一条快乐之路。但它开始于我们每一个人审视自己手上的工作和岗位,从改善它们与其他人的工作和岗位之间的生态关系开始。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