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98艺术 李旭辉


恩里科·巴赫个展“如果·但是”偏锋新艺术空间展览现场
谈论恩里科·巴赫的创作我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巴洛克传统的颤变,其中涉及到尼德兰地区对信仰的变动和科学地位的变化;第二是克里恩·巴赫本身所在地莱比锡画派一直以来的绘画传统,这种偏重写实和表现于一体,之后不断综合其他艺术的大荟萃与巴赫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三是19世纪抽象表现主义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在强调秩序的冷抽象和强调表现的热抽象之间一些辩证关系。
所有事物都是从简单开始,恩里科·巴赫早期创作也是这样。从一张伦勃朗的《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的变体开始,艺术家回到17世纪那个资本主义的前夜,神学逐渐消去其魅影的时代里,也是荷兰人最为艰苦的时期。荷兰持续80年的独立战争战火正酣,26岁的伦勃朗创作了这件作品,以尼德兰地区最为流行的祭坛画形式,描绘了一群人文主义者对生命和宗教的思考。加尔文教在荷兰的传播间接影响到荷兰这个建构在沼泽和风车上的人群,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富饶的土地,唯一好的收益在于其精打细算的本领和周旋于欧洲各国的商业船只。

恩里科·巴赫个展“如果·但是”偏锋新艺术空间展览现场

ESW 250×200cm 布面油画 2017年
对于这样的生存条件,任何高规格祈祷仪式和奢靡的造型方式都是耗时耗力的,加尔文教对基督教的简化和实用化不仅表现在对巴洛克时期所崇拜的偶像方式进行破除,也表现在对教会仪式的简化。对世俗生活的肯定更加使得荷兰本有的重商形社会结构得到巩固,同时更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哲学与艺术的思考。更务实的思考也扭转了人们对宗教幻觉的寻找,转而走向更加实在的客体。
当然,世俗生存被当作一种宗教行为这种说法本身也是极具欺骗性的。就像20世纪以来,宗教建筑逐渐被世俗建筑取代,包豪斯式的平面化设计在只是注重功能和基本审美后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繁殖,但其本身依然继承了巴洛克以来对崇高、伟岸等要素的基因。明亮的玻璃墙继承了哥特建筑彩色玻璃墙,巨大的水泥柱继承了罗马建筑和埃及古庙巨型石柱的精神。事实上逐渐成熟的商品世界作为宗教的替代品其本身已经构筑了新的社会生存模型,但这种生存是人类纵欲的模范还是日常宗教践行,可能就很难分辨。19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很多,但事实上所有宗教和哲学都不可能带来古代那样将个体完全脱离世俗化进程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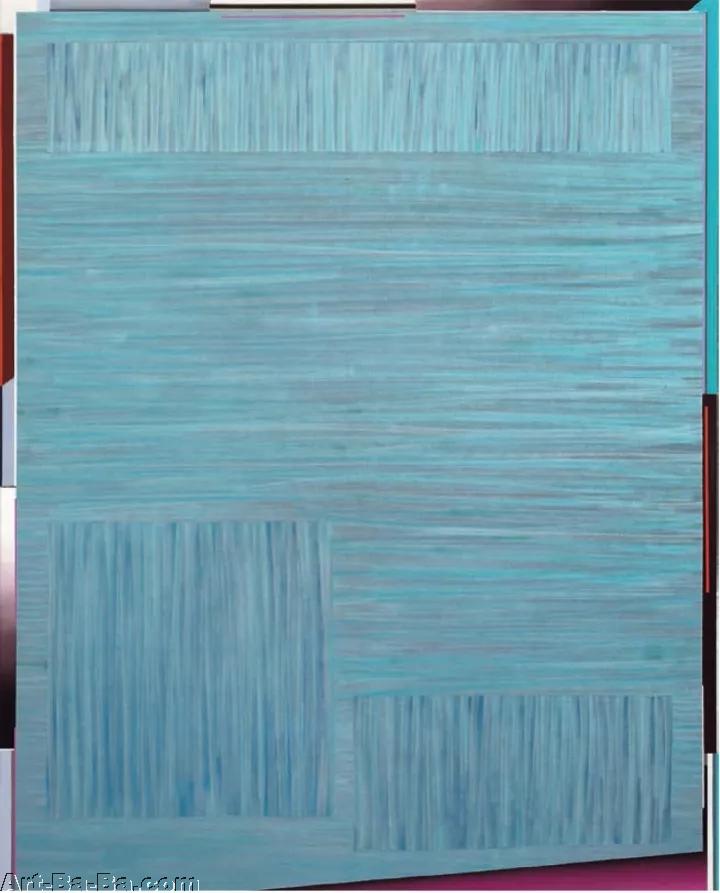
ZSMB 145×115cm 布面油画 2017年
但是从世俗时代的精神萎靡的角度来看待,以往的宗教绘画又是怎样的存在呢?没有人再去满腹热情地绘制英雄和圣人的肖像,除去极少数宗教化的国家,像阿拉伯和北韩,神权退隐背后的世界也并非令人乐观。从这点上看伦勃朗的《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仿佛是一个交叉口,以描绘英雄和修士的方式描绘一群世俗的科学家,被挑起经脉的尸体仿佛是一种丧失神性的现代人的寓言。当然这些在现代人那里早已不会有多少反应,悲剧被卡通化的时代就像恩里科·巴赫作品一样,一切都被早起的世俗生存抹平。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恩里科·巴赫出生在德国60年代会怎样,无疑此时的德国还陷在东西德的危机当中,西德建国后近30年完全不讨论任何政治话题,所有人关心的只是经济复苏,而此时东德却从开始的高歌猛进逐渐耗尽人力物力而陷入红色恐怖当中。此时艺术家所处的莱比锡正处于东德境内,为东德第二大工业城市。莱比锡画派早期为了与苏式绘画保持距离,而强调本土性的绘画传统,提倡技术至上,当然在经历三代莱比锡画家的演变之后,创作中逐渐融合了超现实和抽象元素,成为一种综合化的视觉艺术。在早期莱比锡绘画主要以描绘英雄、历史及战争为主,在后期逐渐走向日常,偏向平民阶层,逐渐向波普化演变。90年代新莱比锡画派的艺术创作里开始呈现出碎裂、空间交错,同时也呈现出一种精神的糜烂,或反映权力阶层的僵化和冷酷。这些事物琐碎,但却并置在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的90年代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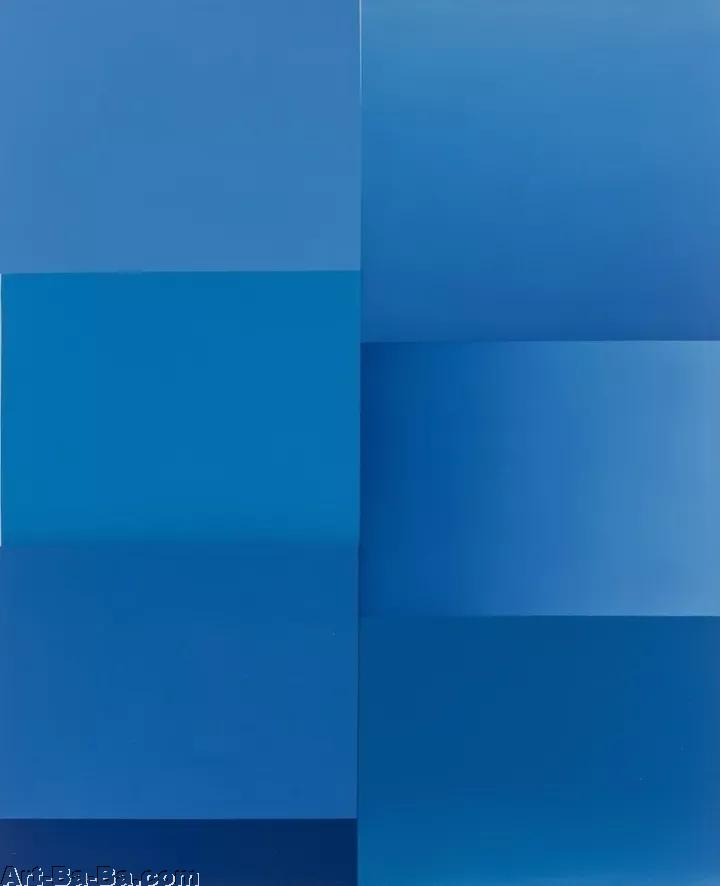
无题 195×160cm 布面油画 2015年
从琐碎到一体化,恩里科·巴赫同样经历这样的过程,在中国的展览中这个过程常常被人为删减,仿佛是不存在。当然在他一体化画面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过往的混乱和碎片化的结构,如此我们对照抽象绘画发展,可以看到在二战之前未来主义在抽象中的演绎。像马列维奇的创作中,对世界的宗教历史寻根溯源导致其创作一列超越于宗教题材的创作,如其创作的圆形系列中我们会发现与马格丽特超现实主义的圆形创作有某些方面的契合点,可知的是在科学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同化已经变得不再是梦想,一个没有纷争同质化的时代。
但事实上随着全球化地域性不平等,商业和科学促成的副作用在呈现,污染、宗教导致的恐怖主义,文化的扁平化也在逐渐显露其病症。对于文明而言总有其两面性的呈现,一方面呈现其希望和机遇,另一方面呈现的是现实的问题。马格丽特的创作无疑有着法西斯的专制社会的内容,而马列维奇在苏联时代的境遇证明了在专制体制下,对艺术家超越于政治意识之外的一体化思考必然也是局限的。战后出现的色域绘画有着希伯来复国主义的影响,而极简主义的出现也回应着未来主义19世纪初的思考。

KM 布面油画 195×160cm 2013年
所以任何艺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抽象绘画里艺术家开始用另一种语言在彼此交流,恩里科·巴赫创作里的硬边材料虽然经过激光般精准的修饰,但彼此却扭曲地拼合在一起,这种矛盾给予其艺术悲剧性张力,一种新即是旧,表层的掩盖既是现在也是历史背景的,分裂既是组合的逻辑隐射出前人对现代性乌托邦的想象的荒谬,这与未来主义和极简主义对未来张望形成时空的对话。艺术家善于抓住平面图形上那些迷人的机理,同样也善于制造废墟般的迷局,这二者之间的张力给予人们一直观看的徒劳感,从而我们会反思假如世界只是利用物质的方式就能连接和沟通,那么又如何面对以往生命的崇高、正义的永恒,又要如何言说生命无法承受的隔离和脆弱。假如现代人只是用娱乐和消费来添补其越来越大的沟壑,而为了安全不断将悬崖的边缘筑上五彩的安全之墙,那么也许能够迷惑自己一时,而最终依然需要偿还所有的欠债。(文:李旭辉 图:偏锋新艺术空间及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