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鲁明军
鲁明军说:
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沈莘是一名工作、生活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写作者。她常用的媒介是影像(装置),作品看上去也像是一种生产性的文本实验。
2015年下半年参加华宇青年艺术奖初评时,第一次看到了沈莘的相关资料,在诸多艺术家资料中她显得比较突出,于是很快联系她,确定了去年9月份在剩余空间的个展项目。而她的出现也的确让很多人眼前一亮。和许多同龄的艺术家不同,我觉得她很“强硬”,也有足够的能量。她的作品常常包含了很多的议题,内容涉及身份、性别、阶层、宗教等,纪录片的质感,加上图像、文本、表演、声音等各种语言手段交织在一起,看上去它更像是一种流动性的、生产性的写作。对于既有的审美习惯和认知经验而言,在我看来她这样一种带有强烈压迫感的复杂叙事和美学结构无异于一种“暴力”,本身就具有某种挑衅性和批判性。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她的评论和报道,但我希望借此访谈,就相关问题做一更深入的了解和探讨。

▲ 鲁明军与沈莘
纪实是沈莘常用的语言手段,与之并行的还有各种相应的文学、历史及理论文本的线索,有时还会附着一重“另外”的图像线索。作品的素材有的来自艺术家的个人生活经验,有的源于网上的社会政治事件(如反复出现的藏传佛教问题),有的则借鉴自她所关注和感兴趣的文本。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透过一种复杂的、不确定的流动性叙事铺陈她的想象和思考。当然,流动性本身并不是她的目的在;她看来,真正的生产和介入恰恰体现在流动过程中持续再生的各个节点。这也使得她的叙事极具开放性,而观者的主动性参与本身亦是她所预期的政治之一。
不同于上一代海外华人艺术家的是,像沈莘这样的在海外的年轻艺术家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遭遇身份问题。但她的自觉明显不同于上一代,它不再是如何超越简单的二元框架,也不再是“廉价”地对抗/认同西方中心主义或某种普遍性,而是尝试将更为复杂的、矛盾的、辩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境况带入她的实践中。因此,她的叙述并不受限于某个既有的观念和自我认同,而仿佛是一个能动的机体,野蛮又不失审慎地介入有关情感与物、权力与异化、个体与公共,以及有关身份、性别、宗教、社会伦理、地缘政治以及被裹挟在其中的艺术体制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讨,以此尝试一种不同的影像(装置)句法和修辞机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带入感与拒斥感、确切性与模糊性、临时性与永恒性之间,影像常常充满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但她真正想揭示的是暗藏在背后的政治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暴力,包括暴力本身。此时,作为她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复杂性”本身业已构成了一种具有挑衅性和批判性的“暴力”。借用哈特(Michael Hardt)、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话说,它是一种智性的、感情化的、关系化的和有关语言的歧异性的劳动,是一种全新的抵抗力量。面对新的世界变局,我相信这样一种言语方式和美学结构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动能。
在国内外不同的艺术生态中
鲁明军: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你一直在国外度过的,在你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哪些艺术形态和艺术家比较吸引你?为什么?
沈莘:我比较关注以不同的形式去参与社会问题的艺术形态,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从认知上对于“产生关联”和人事物之间的联系有着强烈的需要。关注的实践者来自很多不同的领域:导演、小说家、诗人、理论家、艺术家都有,但欣赏的程度通过个别的作品和时间段又有所区别。
鲁明军:去年是你第一次在国内集中曝光、做了在国内的第一个个展、首度和国内画廊合作、群展也参加了几个,还获得了华宇青年艺术奖提名等等,感觉是一不小心就被带进了另一个系统中。我们姑且将它看作一种生态。联系你在国外的经历,你觉得这种生态和伦敦有什么根本的异同?
沈莘:身份上的认同可能更自然,有如在英国知名艺术学院受教育的英国艺术家,在本地发展会比外国艺术家和没有进入艺术主流圈的艺术家有更多的优势。也许作为相对处于局外的人,如果能做到不去追求在名利和事业上与他人比较,在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在伦敦可能由于艺术家太多,所以有实践意义的机会很少,比较能够提供平台的机构也会对年轻艺术家有一个观察期吧,而且会相对比较长久。对于年龄段也有比较明显的要求,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度消费引起的后果。机构对于艺术家劳动力的肯定也有区别,比如在国内一般没有惯例付给艺术家为一个群展、个展或者事件准备的时间和劳力的报酬,但在伦敦的主流艺术机构这是比较忌讳的。就算是再少,从50英镑的学生电影放映费,到300英镑的一小时以内事件的艺术家费用,再到2000英镑做个展的艺术家费用,都是需要去做的事。只通过销售,能够真正创造生存和实践系统的艺术家是极少数,有家人的支持的人也有别的优势,但这并不有益于更多样的艺术家和创作形式的兴起,或者去支撑艺术实践者们作为一个群体的长期发展。如果展览的邀请很多,而年轻艺术家觉得必须去撑起这个压力并且没有劳动力的意识,会在时间和精力上被消耗,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义而且紧迫地需要去改变的事,从机构和艺术家两方面去争取。也许国内的氛围由于市场和阶段的影响,对于作品本身的关注度会显得片面。虽然有大量有能力的作者和评论人,但展览的生产模式似乎比作品的内容和意义的流动更迫切。如果从观众给予作品的时间和讨论的程度上来看,在伦敦和欧洲其他一些主流城市里会慷慨和多样很多。年轻艺术家聚在一起可能更愿意讨论的是作品的意义、带来的感受、创作的方式,和从彼此身上能够学到的东西。

▲ 沈莘《夜莺的挑衅》四屏影像静帧,2016-2017年
鲁明军:前不久,英国 BALTIC 当代艺术中心公布了今年的获奖名单,作为四位获奖者之一,你觉得这个奖——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他三位获奖艺术家你熟悉吗?放一起看,你觉得今年的评选有没有一个学术上的倾向?
沈莘:对我而言,它意味着有一笔经济来源去支持已有的作品的完善和新作品的创作,并且通过 BALTIC 有大量的观众能够看到作品,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联系。这次能得奖也来源于与艺术家麦克·奈尔森在我韩国驻留期间的交流。我们做了工作室访问,聊天的内容当时让我特别有感触,触及了他人和自我在内容产出和意义给予上的模糊界限。这个奖项也让我更相信每个艺术家所遇到的人事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展览,驻留,以及环境有关,每一次得到的支持都是值得珍惜和为之努力的。其他三位我不认识,这次的评选也是这个奖项设立的第一次。由艺术家评选艺术家这一点,加上经济上的支持,以及 BALTIC 作为英国当代艺术的一个主流平台,也许能保证这种对艺术家支持的纯粹性和价值的设立。
鲁明军: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除了6月份的“BALTIC 艺术家奖”的展览以外,还有哪些计划?可以的话,谈谈初步的制订和实施方案。
沈莘:去年对我而言算是比较有压力的一年,所以今年上半年都会集中精力来消化之前做的作品,为之后的作品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构思。下半年会开始主要的新作品的研究和制作,以及经费上的筹划。想用3年的时间制作5至7部短片,会类似于电视剧的结构,但仅仅是结构不是叙事逻辑。
写作与影像的“复杂性”美学
鲁明军:你说过,“并非所有的创作和输出者都对复杂性感兴趣,或都愿意效忠于复杂性,无论是社会政治的、抽象感官的或是努力不去区分这两者的。”很多人看了你的作品以后,会觉得你的作品容纳了太多的图像信息和文本知识,其中交织着很多线索,这种复杂性是一种有意使然,还是本身就是你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种习惯?或者说,复杂性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性的叙事方式?而它往往带给观众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拒斥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同时也带有某种挑衅性?
沈莘:可能是我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种习惯,像之前所说是对于人事物之间的联系的需求。但也是具有生产性的,因为复杂性不是说教式的,它便需要一种主动式的介入。所谓的挑衅也可以看作是对主动形式的带入吧。当纪录片语言开始被当作艺术语言讨论时,很多艺术家把自己代入作品,比如 Renzo Martens 的 Enjoy Poverty 就是当时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艺术家自己当靶心,让观众通过攻击、排斥和被压抑,迫切地生产跟个体所处的社会政治位置有关的感受。但那样的作品把对于同谋的普遍性认知作为最终目的,也算是对于复杂性的一种妥协吧。
鲁明军:我们也可以把这样一种写作和影像方式视为一种美学结构,而这样一种美学结构对于既有的普遍的审美习惯、认知经验而言,同样具有某种“杀伤力”和“摧毁性”,可不可以说它同样是一种暴力?
沈莘:可以,但这种暴力形式可能是无限制循环的,以此避免生产出的受害者和施暴者得到的权力可以再次形成系统性的暴力。
鲁明军:你同时也是一名写作者,在写作与影像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当然也看得出来,无论是你的影像还是写作,都是流动性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内部会不会构成一种抵消,会不会导致对判断的回避,或者是有意对任何结论的消解?它会不会成为另一种讨巧的方式呢?记得阿甘本似乎对这样一种流动性、关系性和生产性有所质疑,他强调的是一种悬置和去功用化,他认为悬置本身也是一种开启。那么,他所谓的这种“悬置”、“隔离”与你的这种关系性、流动性的叙述矛盾吗?还是异曲同工的?
沈莘:文字的生产对于我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在影像作品中与文字有关联的地方也许是解读方式的交错吧。我觉得在实践中无论是对来自别人的还是自己的,甚至是设想的判断都是包容的,并且判断的姿态是肯定式的存在。对于流动性的理解可能并不是一个公认的模拟资本流动的方式,而是对于各节点的肯定与包容。所以任何结论都是存在的,和被赋予权力的,但不具有统治性。流动性的目的是对压迫和统治的消解,关系性和生产性不具有占统治地位的功能,所以这样的结构在理想的状态下会比所谓资本流动的方式更强调速度和范畴。在讨巧的方式中,被“悬置”和“隔离”的也许恰是对于这些方式的绝对服从和反叛,能在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权力构建的过程,和结构外围正在被建造的结构。
宗教与性别的权力认知
- ▬ -

▲ 沈莘《据点》单屏影像静帧,2016年
鲁明军: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在涉及相关素材的几件作品中,它扮演着什么角色?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本身就是一个敏感话题,另一方面,也似乎涉及你一直比较敏感和关注的身份问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可否联系《细数祝福》、《形态逃脱·序》、《据点》等相关的几件作品,谈谈在不同作品中你是怎么处理这个素材的?
沈莘:对于宗教我感兴趣的是它如何被社会政治的权力系统所影响。正如您所说,话题本身存在于很多层面上,对于身份、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言都是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我会对它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它处于夹缝中。这个夹缝本身也许是不易被观察到的,但可能是它运作的逻辑,也可能是认知和理解的夹缝。《细数祝福》描述了对他者的欲望和表现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产生经济效应的,是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内观察到的一个具体的循环系统。《形态逃脱·序》是由一个地理范围即“伦敦的藏传佛教徒”扩散到三个影像里的各种痛苦的形式,这个扩散本身是不平衡的。《据点》通过剧本和记录的结合,使虚构的叙事介入一个具体的地点来探讨和影像有关的,可以放宽范围观察的一些话题。

▲ 沈莘《细数祝福》单屏影像静帧,2014年
鲁明军:说到身份问题,你似乎一直是有意地避免陷入“霸权”和“反霸权”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通过身份认同争取知识和权利同样是需要被抗拒的”。比如在《形态逃脱·序》中,三位的身份角色(德意志银行总监、初创顾问和俄罗斯籍英文老师)的设定是有意的,还是随机的?另外,新的世界变局(比如难民、英国脱欧、包括右翼势力的上台等)使得种族、宗教、身份以及阶层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复杂,包括国内的社会环境也一直在变化中,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这一新的世界变局会成为一个紧急状态,或是一个新的艺术时刻吗?当然,我也比较好奇的是,在你的真实经验与艺术实践之间是否有紧张或冲突的一面,还是说,你其实是把自己的认同暗地带入艺术和写作中?
沈莘:《形态逃脱·序》中的三位的角色算是在预料范围内的机遇。当时在伦敦各个藏传佛教机构里发出了邀请,这几个人是在不同机构里回应的人,但他们的角色和在伦敦对于藏传佛教感兴趣且积极的主要人群有关。英国脱欧和右翼势力的上台后大众意识到的矛盾的尖锐或者早就存在于时间上的前因后果和一些群体的生活体验中了。例如英国在脱欧前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并不是由于戏剧化的政治事件登台导致的直接后果。对于社会政治的权力结构导致的现实变局,很多时候感觉像是戏剧对于发生过的事情的诠释。也许艺术语言很容易和表演性挂上钩,但这并不意味着会生产出新的语言,或者生产出的东西是无法被资本和权力所消化的。我的实践方式是不排斥他者的介入的,所以通常被当作一种可以去深入研究,去探讨以及分享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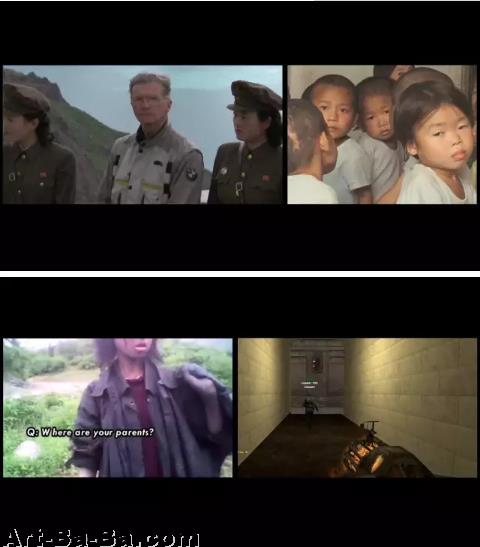
▲ 沈莘《形态逃脱·序》三屏影像静帧,2016年
鲁明军:性别也是一个你比较敏感和关注的问题,但显然有别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或平权运动,如在《付出式批评》中,通过大量的图像资源、声音信息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酷儿美学”的认知系统,但你认为“酷儿美学”是一个桥梁式的批评方式,最终目的是在“观念的聚集和语言的共享”,这里的“桥梁”如何理解?是不是说,性别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媒介?
沈莘:桥梁的意义在于它本身是有它所占据的实际位置的。正是因为如此,对它的理解可以与对其他事物的理解产生关联。这也许是基于女权和平权运动改变了对待他者的态度的标准,但仍有它未被解决的脆弱性。从而在公共范畴内这种缺乏讨论的脆弱性可以通过阶级的代入,左右翼势力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学上有关自我映射的语言来衍生出可以被分享的理解方式。

▲ 沈莘《付出式批评》单屏影像静帧,2015年
不妥协,艺术家的社会角色
鲁明军:你的作品往往是通过图像、声音、“表演”以及文本等多个言语手段展开叙述的,从计划、编排到拍摄、剪辑,它依赖于一个混杂的、反复的思考、推敲和制作过程。这些言语手段之间有时候是一种强硬的搭接,有时候又是一种巧妙的衔续,有时候又极具冲突感和断裂感,制造了很多的间隙,而这些间隙可能是最具生产性的。比如《巨人的肩膀》,它看似是一个体制批判的实践,但这里面你质疑、批判的不是体制,而是“批判体制”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权力增殖与欲望过剩?亦如你所说的,这里所生产的主体性及其交流变化实际上又形成了一种巩固性,那么这种巩固性是不是意味着又将批判性悬置起来?它与你所使用的《山海经》以及对这个动画形象被滥用的质疑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沈莘:随着批判主体的消失,到来的是对于批判作为手法的质疑。如《付出式批评》的“桥梁”,通过建造关系来进行对于阶级系统和劳动力的反思,或许是更具有生产力的“批评”方式。《山海经》无数次地被再生产、被当作文化符号和集体知识的象征,国内外的投机者都欲从一个看似固定的客体上谋利。将《山海经》中的人物再次激活也是在思考其作为象征的本质和再生的意义,从而反省集体性知识的形成方式。会议中激进的思辨和批判的回响具有被再生的重复性,和动画能传达的观感一起,挑战彼此的存在所依赖的体制。

▲ 沈莘《巨人的肩膀》实时生成动画静帧,2015年
鲁明军:你的作品中也同时借助了大量网络资源和信息,但似乎很少看到你对网络本身直接的反思和检讨?或者说,在你多次提到的物化的暴力中已经包括了这样一种非物质化的宰制性?
沈莘:可能在我的实践中很少会把某一主体单独列出作为探讨对象。主体的存在方式更像是为了通过和他者产生联系,从而有效地被激活。网络和科技是我关注的个群体表达的形式,比如在《据点》中,屏幕表面的文字就是网络论坛上人们向藏传佛教咨询的问题和答复,它们与影像中情侣之间的矛盾、和喇嘛的访问都是有关联的。
鲁明军: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有什么变化?艺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因应今天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冲突,你认为艺术(家)能做什么呢?
沈莘:对于言语权与行动权的区别的理解,是对言语和行动在社会影响上强弱判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铺垫。比如我自身对于激进主义行为的参与和研究都很少,但这不影响我认为可以通过“自我”这个媒介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对社会产生影响。可能艺术家或者任何“文化输出者”能做的是去平衡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开放性,或许是很基本的工作,但在思维方式上能够开拓出不去妥协的生产方式。
*本文图片均来自对谈者本人
关于两位对谈者

沈莘
沈莘,1990年生于成都,工作生活于伦敦。沈莘的创作通过探索影像及事件来实现,同时运用虚构和真实的信息与手法。她的作品检验着情感、价值判断和伦理在个体及群体层面的循环运动的效应与技术。她的实践专注于人与人间的复杂关系和政治的叙事,影像往往致力于创造反身性,以此解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其近期个人项目包括《半说半唱》,蛇形画廊展亭,2017;《据点》,荔枝一号,伦敦(2017);《原本包容》,CFCCA,曼彻斯特(2016);《在家》,剩余空间,武汉(2016);《形态脱逃:序》,Chisenhale 画廊,伦敦(2016);《巨人的肩膀》,伦敦议会大楼(2015)。其近期参与的群展包括《BALTIC 艺术家奖》,BALTIC 当代艺术中心,纽卡索(2017);《例外状态》,UCCA,北京(2017);《龙肝凤脑》,OCAT,上海(2016);《好景不常在》,235光复路,上海(2016)。沈莘于2017年被授予“BALTIC艺术家奖”,并将在2018-19年参与荷兰皇家视觉艺术学院的艺术家驻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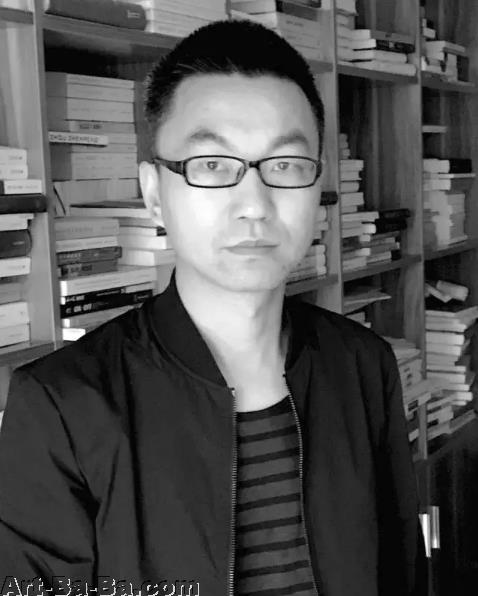
鲁明军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近期策划展览包括“解放的皮肤”、“力的能见度”、“Talk,Talk”等。论文见于《文艺研究》、《美术研究》、《二十一世纪》等刊物。近著有《视觉认知与艺术史:福柯、达弥施、克拉里》、《论绘画的绘画:一种艺术机制与普遍性认知》、《目光的诗学:视觉文化、艺术史与当代》等。 2015年起兼任剩余空间艺术总监,2015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年获得 YiShu 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
鲁明军近期的研究方向和关注议题
“近期主要工作是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奖助金项目关于‘后感性’和‘超市’的研究,4月份提交了所有资料,接下来还有出版的事宜。另外,剩余空间今年会有一个大的项目‘复活’计划。我们特意选择了七部影片、七位艺术家和七位学者(艺术家),通过‘据点的再生’、‘幽灵的面容’和‘将临的风暴’三个单元,将先后以放映、展览和集体阅读三种不同的方式,共同指向‘复活’这一主题,召唤一种新的主体。起因是,去年以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以及 ISIS 的肆虐、深陷泥潭的中东局势等各种事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时刻或被清零,它意味着一切旧有的意识形态之争和价值冲突可能将面临着彻底失效。对此,全世界(尤其是欧美)各艺术机构、艺术家、写作者及相关从业者已经集体付诸行动,发出抗议的声音。但我们也须承认,一直以来,无论是对体制和系统的不满和麻木,还是对于创造力和意志力的焦虑和召唤,都提示我们,新自由主义阴影下的众神狂欢无法掩饰集体感觉的匮乏和心智的贫瘠。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复活’既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艺术宣言,也是一次响应新的世界时刻和未来变局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