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空白艺论KONGBAI 旷之 译
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搞到了施杰尔达的这篇“Festivalism”,于是,硬着头皮翻译了一下。说实话,施杰尔达的文字不好翻,他的文章虽然是写给《纽约客》的中产阶级读者,用词看似很简单,但文风却颇为老辣,观点犀利,富有洞见,且不失幽默和讽刺。
去威尼斯看当代艺术是最令人不自在的一件事,那么最好的理由就是告诉自己,去威尼斯做什么都是一件乐事。确切说,我真的不爱威尼斯。但这会让人觉得我太自以为是,好像威尼斯在乎别人对它的感受一样!威尼斯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它当真是一座城市吗?——这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消散的、梦幻般的沉静。在圣马可,就算有再多的游客和鸽子嬉戏,也无法打破这份宁静。这种冷漠和超然就像延时摄影中抖动的模糊画面。威尼斯只关注光线在闪烁的空气和青瓷般的水面上划过的轨迹,日复一日,从清晨推向悠长夜晚的高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夜晚。
我觉得自己既幸运又愚蠢,我加入了大约三万名带着邀请函的艺术界人士,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再次开幕。让我们看看另一番景象吧!身处威尼斯的国际艺术圈完全像是活在另一个尴尬的世界里,这些人倒着时差、神态慌忙,还有的偷偷在自助天堂里白吃白喝。(一位意大利朋友冷淡地告诉我,依赖旅游业的威尼斯人讨厌那些双年展吝啬鬼们。)这些人略带着些许相互蔑视的姿态,各自溜达半小时后——也许是在一个安静的教堂里欣赏最受欢迎的乔万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一幅祭坛画)——重新聚集在一起开始称赞某人的影像装置。“你看到了什么?”,毫无音调的短语与双年展的视觉艺术大杂烩相呼应,从每个人的喉咙里挤出来,就像在忏悔精神的荒芜,好像我们喝的是喷妥撒(一种麻醉剂)而不是葡萄酒。但是,嘿,我们是在威尼斯。有什么会不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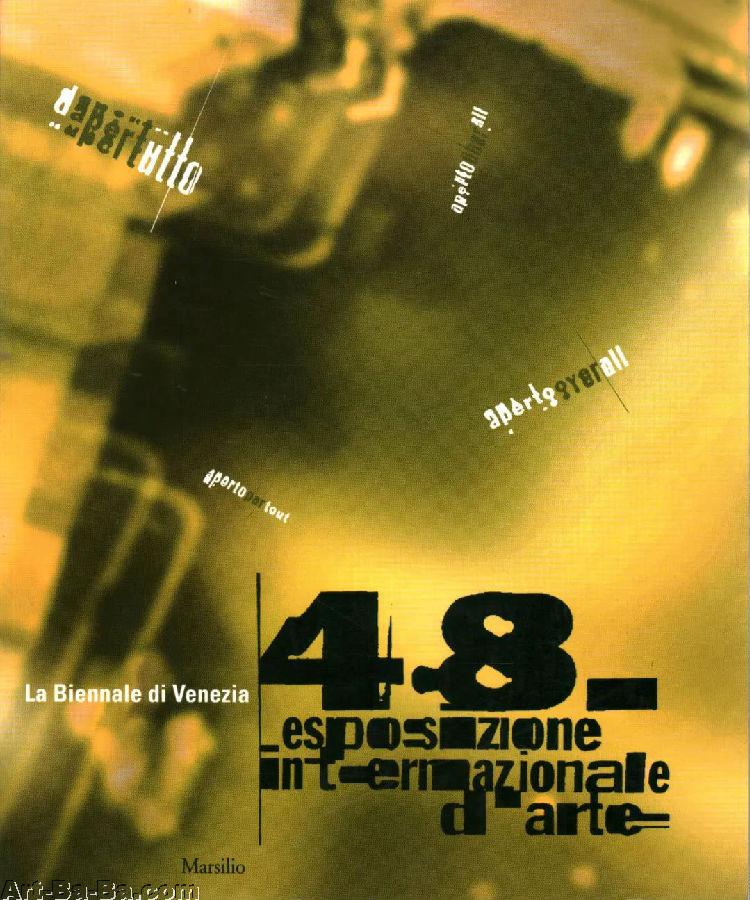
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海报
事实上,目前的第48届双年展(展期至11月7日)一点都不差。它是我参加过的几个双年展中最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除了绿园城堡(Giardini)巨树下那些历来无甚起色、令人尴尬的国家馆。今天,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代表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是否已经超越了以往的神秘感?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会让大多数管理展馆的公共机构人员感到不快。主导双年展的声音仍然是对陈旧的、盲目乐观的民族主义的虔信,并以此来抵制全球资本主义——要么是零散的商业赞助的刺耳声调——即使本土英雄被推上世界舞台。请注意,几乎没有一个英雄展出的是商业艺术品,比如绘画。[英国的加里·休姆(Gary Hume)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外;他别致的铝制搪瓷画似乎放错了地方。]本届双年展凸显了全球范围内疯狂追捧装置艺术的机构的观念立场。
我称之为节庆艺术:一种环境产物,只存在于展览中,把策展人的位置于画廊主之上,把公众的位置似乎抬得比艺术专家还高。热爱生活的女巫安·汉密尔顿(Ann Hamilton)以积攒令人着迷的人工制品而闻名,她在美国馆的墙面上让亮紫色的粉末时断时续地滑落下来。这导致墙面上凸起的盲文字母得以显现,据说文字摘录于已故的查尔斯·雷兹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的诗歌,这些诗歌是关于美国中心地区谋杀、混乱和其他事故的法庭记录。如果尝试去解析汉密尔顿的政治神秘符号学,你会感到头晕目眩。或者,像我一样,你可以简单地看一下这首漂亮的曲子,隐约感觉到一种美德,然后继续前行。顺便说一句,在最近的双年展上,美国一贯的政策就是选择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的艺术家。这源自一个超级大国从艺术炮舰外交中退缩后的羞涩内疚。

Myein , The United States P**ilion, 48th Venice Biennale·Venice, Italy
和我交谈的大多数人对汉密尔顿的努力表示了适度冷淡的认可。我的对话者对比利时馆赞不绝口,不过那里的艺术很难被看到,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建筑里弥漫着浓浓的白雾。然后是丹麦馆,丹麦人彼得·邦德(Peter Bonde)和美国人杰森·罗德斯(Jason Rhoades)制作的赛车装置,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震耳欲聋的马达声。芬兰艺术家埃亚·利亚斯·阿赫蒂拉(Eija-Liisa Ahtila)在北欧三国馆拍摄的一部精彩视频作品也受到了欢迎。作为节庆艺术的理想选择,视频投影显示出一种迹象,它将演变为不同于电影、戏剧、音乐和雕塑的纯艺术形式。其诀窍在于将电视固有的单调性转化为令人放松的内容。你不是在看视频影像;你只是和它共处了一段时间。在不经意地看了阿赫蒂拉的23分钟、双屏半纪录片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是一则道德寓言,让人联想到了高度凝练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阿赫蒂拉关注的是:公共场合里发生在人们身上紧张而亲密的故事——一种与陌生人分享私密经验的生活经历。录像艺术家,或者说使用录像的艺术家,在本届双年展导演,瑞士老牌艺术家哈罗德·泽曼(Harald Szeemann)组织的大型群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是泽曼发明了节庆主义,他在1969年策划了极富前卫的展览《当态度成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作为一种改变,不仅军械库(Corderie)——威尼斯古老军用船厂的前绳索工厂,摆满了不太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连其他翻新的船厂和拥有多个房间的意大利馆也充斥着这样的艺术。泽曼心照不宣地提出了当代的新典范,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么,什么是节庆艺术?它是任何能够操控一特定空间的东西,它能够立即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但绝不会引人入胜。它是反沉思的。观众不会忘记他们身处人群之中。人群也不会在任何时候停留太长时间。这是一种流动的消费:一点儿这个,一点儿那个,谢谢你,再见(arrivederci)。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展览现场照片
这足以伤害一个专业艺术批评家的感情。泽曼的展览似乎和威尼斯一样,并不在乎我的意见。这是因为他看重的是一种量的而不是质的回应,就像观众敲击中国艺术家陈箴制作的那上百个铺着兽皮的床和椅所发出的噪音,它们在远处听上去就像轰鸣的雷声一般。顺便说一句,在这场盛会上涌现出不少中国艺术家。他们中很多人对刚刚解禁的性和玩世不恭表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思考。(在这届双年展中,明确的性和政治出乎意料的少,于是人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挑逗性。)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代表都在节庆主义华丽的辞藻和富有感染力的美学方面表现出无可挑剔的天赋。几年后,如果趋势不变,中国艺术家将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与此同时,在陈的鼓房里,我也拿起了鼓棒,和其他人一起敲打起来。为什么我要特立独行呢?享乐有什么不好的呢?

陈箴,絕唱 - 舞身擂魂
装置艺术创始人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曾经培养了一种对“商品资本主义”的准政治敌意。但那已经成为过去。不可销售的艺术和可销售的艺术之间的战线演变为一道深切的鸿沟,一边是令群众陶醉的节庆艺术,另一边是人类所看重的永恒的商业。(顺带一提,市场化的艺术品不是商品;从经济上讲,它们更像是手工货币)现在,艺术游戏的合理化正在全球上演。一种艺术家选择呆在工作室里,而另一种则穿梭于各大机场。在威尼斯,游牧型艺术家可能看起来很强大,但事实上,他们的安全感更低。政府、公司和其他机构会继续支持这种艺术吗?除非有普通观众自愿前来,并且愉快地做回头客。就像今天的许多事情一样,票房女神代表着盲目的正义,用她冷漠的天平衡量着艺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