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 Ba Ba 刘化童、李亭葳

图片致谢艺术家、弥金画廊、几点艺术中心、姚纯纯、姜晔
最初,人与世界接触的目光方式不外乎三种。农耕的人俯视大地,征服者和商人眺望远方,而还有一类人选择仰望天空。其中,云乃是天上最为虚无缥缈与变化万千之物,引得诗人、画家、隐士,以及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总在凝望。历史上著名的观云者不在少数,尤其是画家。据于贝尔·达弥施 (Hubert Damisch) 的研究,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蔓延至19世纪末,西方绘画的天空始终被云笼罩着。不论是作为图像学的主题,抑或是符号学的表征,云都是绘画技法和人文精神达成平衡后凝结的产物。
平心而论,云在绘画中的大规模隐退与现代主义的崛起,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几乎保持着同步性。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当代艺术大行其道的时代,由于环保主题、数码技术以及互联网社会的思考日渐走俏,“云”再度在艺术中复辟——只不过,这一次它并不作为形象,而是以观念和概念的姿态被植入艺术。
颇为巧合的是,环保、数码与互联网这三大议题,正是青年艺术家李亭葳所关注的。这似乎也冥冥中把她推向了这场以“云”的概念为主题的展览。近期,在上海弥金画廊开幕的个展“云落石出”中,李亭葳一改以往创作数码与影像作品的形象,极为罕见地展示着以云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并且搭配有手稿、装置和影像等不同语言媒介的作品。作为当代意识催生出的观云者,她的“云”与其说是回溯和重现古典绘画的主题,毋宁说是对互联网时代“云”的关联物进行观察与思考;并非是对古典绘画技法运用的复习,而是在演练数码拼贴缔造的美学如何应用于传统题材。

李亭葳,《巨石云》,2021,单屏幕视频,4K,7分钟8秒,视频静帧

LHT:此次展出的作品都是你在瑞士驻地的时候创作的?你画了很多的云,这是写生的产物?
LTW:我在瑞士驻留的住所正好有一扇大窗,正对着广场。那里空空荡荡,没有行人,只有天上的云飘过。艺术家每天都面临的课题就是如何应对日常,以此进入工作状态,获得某种工作方法。当时,几乎是百无聊赖,我就干脆写生,画云。不过,如今完成的作品却不仅仅是写生。我很喜欢把图像学研究作为创作方法,就去研究比对了古典油画中的云,尤其是17、18世纪的创作,例如约翰·康斯特勃 (John Constable) 。在巴塞尔美术馆看展览时,我看到瑞士风景画家亚历山大·卡拉梅 (Alexandre Calame) 画的《乌里湖畔》,还特意跑到实地去看了山、湖和云的视觉关系。

巴塞尔Atelier Mondial工作室窗外的Freilager Platz,图片来自李亭葳2020年12月

李亭葳,《Petting the cloud》,马克笔、铅笔、十二幅纸上作品和最初的三幅写生草稿《擦天空板》在工作室

Alexandre Calame (1810-1864),《乌里湖畔》“Am Urnersee” (By the Lake of Uri),布面油画,1849,巴塞尔美术馆中的一幅收藏于1950年的藏品,图片来自李亭葳
LHT:在看展时,我脑子里忽然一闪而过觉得可能跟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画有关,尤其是弗雷德里希的《云端漫游者》。但是,不管是作为艺术史里的形象也好,或者“云”仅仅作为意象也罢,它本身并不当代。你的创作思路是对于当下“云端世界”的思考,而那是互联网时代的“云”。你试图在展览中衔接两者,仅仅因为文字上的相同?
LTW:其实,跟我热衷于图像学研究类似的,还有对于词源学研究的兴趣。在本杰明·彼得斯 (Benjamin Peters) 的《数码关键词》(Digital Keywords) 一书里,他梳理了网络时代的很多词汇是如何从它们的本义里衍生而来的。再比如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 的《奇云》(The Marvelous Clouds) 和詹姆斯·布莱德尔 (James Bridle) 的《新黑暗时代》(New Dark Age: Technology and the End of the Future) 也对此有所探究。本杰明·彼得斯说,cloud最初和clod (岩石、山丘) 有关,而cloud在13世纪出现在古英语中,最初的意思是从地球到天体的一个投影,是漂浮在天上的岩石或者山丘。这两者关系特别巧妙,我就以此为切入口,展开思考和创作。展览名“云落石出”正是由此而来。而英语标题“Air Drop”正好有空中的物掉落在地,并同时双关语指向苹果电脑系统里的一个“隔空投送”。

李亭葳,《巨石云》,2021,单屏幕视频,4K,7分钟8秒,视频静帧
LHT:从“云”的词源学入手是一种路径,我记得你此前的创作经常关注到气候问题。这应该是另一种路径吧?
LTW:我最早关注气候问题大约是在2018年。确切地说,我关心在气候与环境问题之中人的生存处境。于是,就做了《敏感人群不宜外出》。当时雾霾很严重,天气预报建议“敏感人群不宜外出”。那么,究竟谁是“敏感人群”呢?我对这个关于如何界定“敏感”很敏感,就据此创作了;而我想探究的是不宜外出之后,人被迫自我隔离,又会产生怎样的心境和状态。此外,《新黑暗时代》提及烧煤和用电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影响新的积云类别的形成——很多云的形态是直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同时,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研究19世纪的风暴云,我又去研究云是如何得以进入绘画作品的,包括气候气象、古典美学,以及人类对于云在形态上的认知和分类。

2017年,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一期《国际云图》(International Cloud Atlas) 中加入了一种新的云型类别:人造云 (homogenitus) ,图片来自于:https://cloudatlas.wmo.int/en/homogenitus.html
LHT:换言之,你把这些绘画当作对云的研究的视觉成果?
LTW:通过创作,我希望提供一种对云的思考。无论如何去描述,云都是随处可见,它是我们头顶上的一个现象,一种物。这个跟我们现在到处都是的所谓“数据云”并无差异。就像我们受制于作为天气现象的云那样,我们同样受制于数据云的储存、监视和控制。

李亭葳,《乌云恐惧症吗?》,2021,布面油画,丙烯绘画,50 × 60 cm

李亭葳,《上风之眼》,2021,布面油画、丙烯,50 × 60 cm
LHT:在你看来,古典时代的云和当代的“云”其实在本质上具有某种同构性。而这也是你去并列呈现两者的原因?
LTW:古典和当代被并置在一起所形成的对比与思考,对我而言,它提供着某种类似于考古学的认知路径。尤其是现在的数码时代,笼罩在数据云之下,一切都太快了,完全没有时间去反思。就比如,短短几年时间里,电子通讯设备不知道更迭了多少代了,只留下一堆不同插口型号、无法兼容通用的充电线和数据线,而我们却几乎忘记了曾经还有座机、电话拨号……当代的“云”造成了记忆断层,而我们就身陷其中,被恍如隔世的感觉包围着。这太奇怪了,但它就是我们的生活。因此,我就希望在创作中呈现这种今昔对比。

李亭葳,《巨石云》,2021,单屏幕视频,4K,7分钟8秒,动画静帧
LHT:数码物是信息的载体。就像你提到的,我们总是因为数码物迭代产生的数码废物而困扰。我想还有另一种疑惑,那就是关于它是否意味着永恒。这个跟古典时代的云和石头相似。石头作为载体,不管实际上是否能永恒(巴米扬大佛也能被炸掉),至少人类把它当作永恒的象征物;而云跟石头的意思却相反,它意味着易逝性。两者正好意味着两极。你对当代的“云端”也持这种两极看法?既倏忽即逝,又永恒?
LTW:对,任何物都能困住我们。我们每天都跟很多东西打交道,实际的,或者虚拟的。困住,既意味着困惑,同时也存在某种安全感——我们会感到,那些东西还在,并且愿意相信它们一直会在,就像永恒。尤其是现在的云端技术,特别值得探讨和分析。就像网盘,你储存进去的东西会永恒保留吗?不,你需要购买会员,一旦不续费,那些你原先储存的东西,就连你自己都下载不了。从中,我体会到的是,每当技术往前发展一步,我们应对它而产生的心理与精神状况也会产生一些困扰,甚至就连这些困扰都不是一尘不变的,它永远都是崭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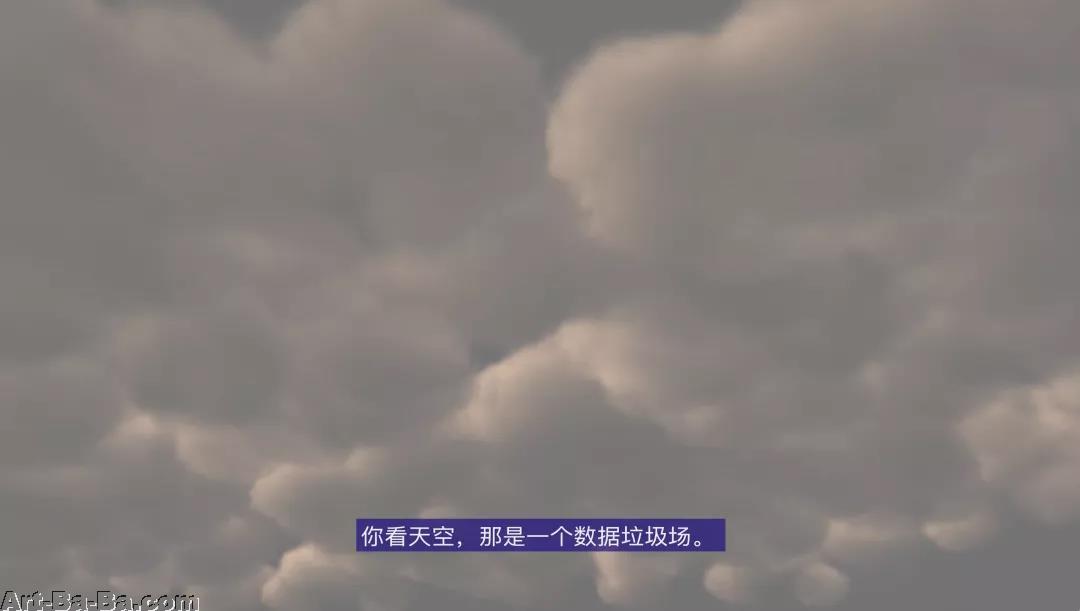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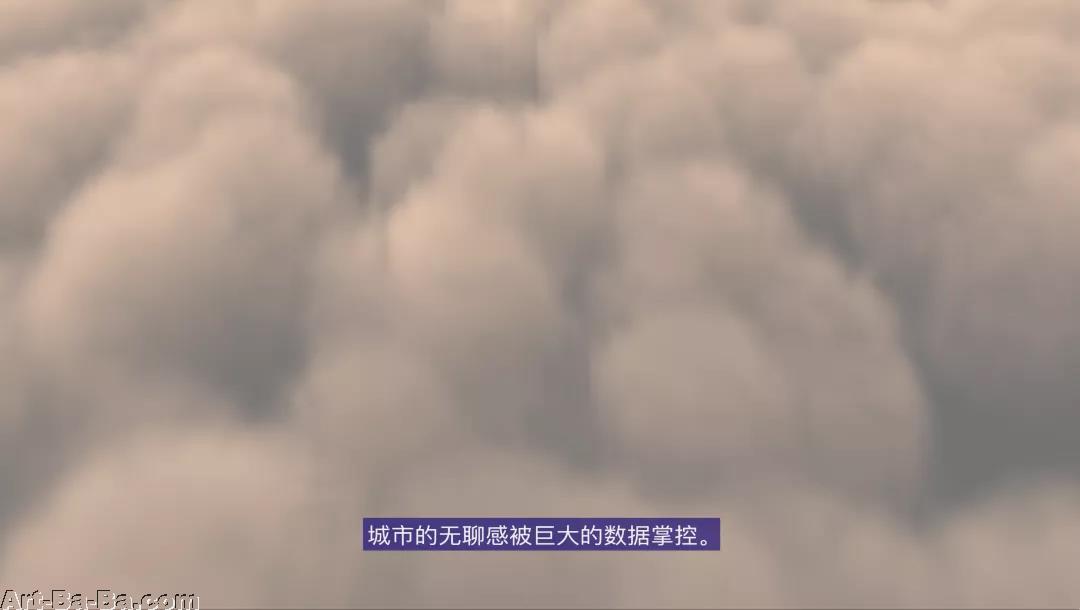
李亭葳,《巨石云》,2021,单屏幕视频,4K,7分钟8秒,动画静帧
LHT:我们刚才聊到的主要是触动你去创作这些作品的心理、感性和认知上的动因,以及探究的路径。我深感好奇的是,你用古典时代的云来思考当代的“云”,那么仅就内容和艺术语言来说,匹配度更高的不是用影像或者数码技术去表现嘛?为何选择用完全属于古典的绘画的方式?并且,跟你以前的创作相比,绘画也并不是你主要的艺术语言,为何在这次会产生这种变化?
LTW:我更多选择影像和数码的方式去创作,同时也会尝试其他媒介。这次展览上就有绘画、影像和雕塑。我正式尝试用绘画的方式去创作,应该是从几点艺术中心的驻留项目开始的。那时正处于思考期,我创作完一些小石膏雕塑,就想着是否能把它们再画一遍。从此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写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我感到写生拯救了我的创作之路,尤其是自己特别干枯和不爽的时候,写生给予我很强烈的愉悦感。随后,我就开始对着自己创作的雕塑或者数码图像进行描绘。对我而言,创作影像、数码和装置,整个过程其实没有太多的反馈给予自身,很少存在太多出乎意料的惊喜。然而,绘画让我体验到这种差别,渐渐迷恋上这种工作方法。

李亭葳,《圣骨》,布面丙烯6幅,每件20 x 30 cm,树脂、镜面不锈钢、亚克力外壳。李亭葳个人项目“Grasp, Kneel, Hold, Count, Pray” ,展览于几点艺术中心,2020
LHT:你选择绘画,更多是基于愉悦原则,以及它能更方便的让你对于艺术史上那些经典图像的迷恋、临摹与改写。
LTW:绘画这件事对于艺术家来说有多重要,就好比你去做瑜伽,回来跟别人说感觉特别好,但是听你说的那个人没有去做,体会不到你的感觉有多好。绘画也是如此,没去实践的人无法体会它的好。事实上,虽然我一直以视频为媒介,却并非从这批作品才开始绘画。我只是中断了很多年。早在念大学时,我一度觉得自己不想画画了,因为不知道要画什么。尤其更加了解艺术史之后,就会形成巨大的包袱,主题、绘画性、媒介,什么都显得很重要,可当时的我却迷茫着不知道如何再去用绘画表达我个人的情感。

李亭葳,《补天》,2021,布面油画,80 x 80cm
LHT:难怪我看你的画有一种奇怪的感受,不像是艺术史里对于绘画的理解。确切地说,在你的画面中有一种拼贴感——并非超现实主义崇尚的那种“拼贴”,而是有着很浓的PS的拼贴痕迹。虽然它实际上是画的,但更像是用画去模拟数码图像的感觉。这也是你说的对着数码成品再临摹的产物?
LTW:拼贴既是我的习惯,也是创作方法。就是从用PS开始,然后是动画制作软件,或者是剪辑视频时处理的很多叠层,于是就慢慢养成这种用拼贴来制图的习惯。图片是平面性的,可我总想让它具有厚度,那就再叠加一个图层。当不同图层的内容在相同平面内呈现时,就会产生拼贴感。当然,两者存在本质差别。绘画的动手性和创造性体现在完全“手做”,其他二维图像或移动图像需要基于电脑和工具,以及在选取图像时手指的机械性点击。所以,涂抹描绘是区别于选取的,这也是绘画有趣的部分。对我来说,图像即记忆。在生活中,我总在通过手机相册里的图像去记忆。或许是生活习惯形成创作习惯,我也总是在作品中把构成记忆的不同图像以拼贴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李亭葳,“云落石出”艺术家手册内页
LHT:在你作品的画面构成里,云和石头,是展览名字中就有的,又拼贴了一只手是出于什么想法?
LTW:我是手机重度用户。天天就是这只手拿着手机,经常觉得要残废,还由此衍生出很多自我批判和忧虑。至于为何把它拼贴到绘画之中,似乎也没有单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去年做《数码手指》时留下了印象。手持手机是单手,拍摄自己的手也是单手。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去年画了一幅叫“multitasking”的小画,那是多面手。还有两件作品(《补天》和《探病》)中的手,它的原型是我爷爷的手。老人的手总是显得令人伤感。

(左)李亭葳,《多任务处理》,2020, 布面丙烯,40 x 50 cm
(右)李亭葳,《爷爷》,2020,布面丙烯,60 x 90 cm

李亭葳,《探病》,2020,布面丙烯,60 x 80 cm
LHT:从视觉表现上来看,拼贴的手法能制造出某种蒙太奇、隐喻等效果;同时,它也会让视觉形象的表意变得含混,不够直接而清晰。通俗点说,就是想表现的东西太多了,反而显得芜杂。对此,你怎么看?
LTW:对,我同意。要谨慎。创作中我也会自我批判和反思,在“跳脱”出好的效果和出现“语义不明”中反复判断一下。最近几年,尤其是做视频的时候,特别是这次展出的视频,逻辑滤清很多。之前两年有几个作品我觉得是太想到哪做哪了。然后每一个作品都学着“收一些”,保留好的,去掉那些失败的尝试结果。其实,视频里面的拼贴性很难,要处理大量的素材,排序、攒、挑在一个文件夹里。就算只有7分钟,还要脚本,时间线,还是要写,画个表,一口气粗剪才能又保持那种感觉和节奏,又不漏掉什么。当然,我也不知道对于拼贴的执迷还要多久。因为我不喜欢自己出现在画面里,似乎有手出现就够了,这种拼贴强调这个“主角”和主体性了。

李亭葳,《巨石云》,2021,单屏幕视频,4K,7分钟8秒,视频静帧
LHT:在我看来,“云落石出”展览至少成全了你一种尝试在不同媒介上实现拼贴性的创作方式。相比过去,这次有手稿、绘画、装置以及视频,完成了同一主题的不同媒介语言切换。
LTW:这也正是我最近在尝试的,就是视觉艺术里的各种媒介能怎么综合起来用于表达。比如,这次我尝试了纸本、油画、视频、砂型打印。这里既有我自己创作使然,也有根据弥金画廊空间大小、地板和灯光的情况才做的决定。下次可能不会有速写了,换个别的气质的空间,不合适了。





李亭葳,“云落石出”展览现场,2021,弥金画廊


作品“护身符”细节。《护身符(圆柱)》,高150cm,直径50cm,砂型3D打印;《护身符(方柱)》,150 x 54 x 54 cm,砂型3D打印,图片来自姚纯纯

作品《天气是时间的易碎品,石头是时间的载体》,3D砂型打印、摄影拼贴、树脂、艺术家手册,图片来自姜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