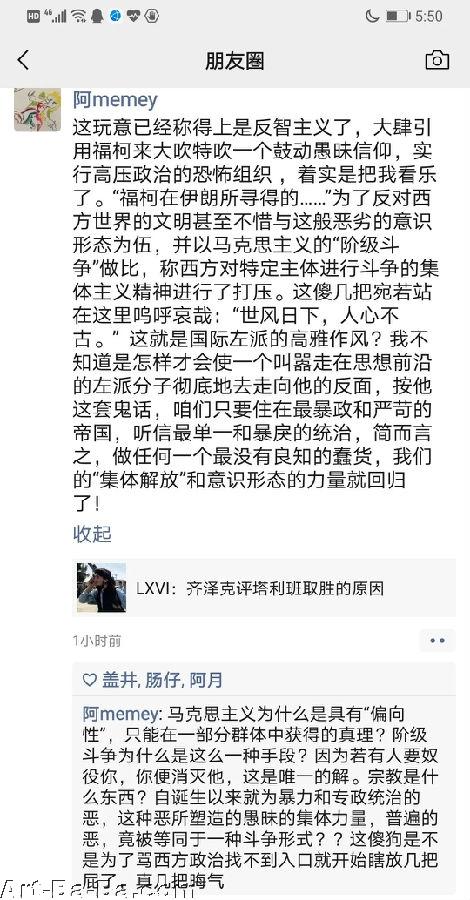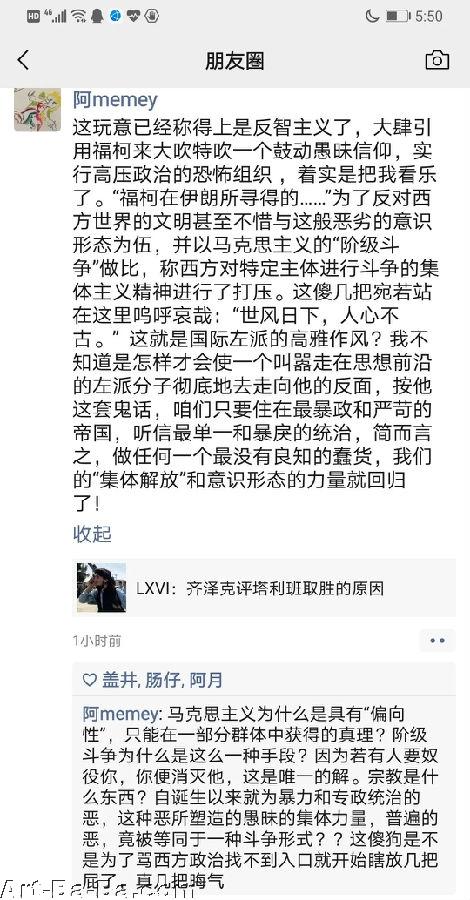又一座让·努维尔设计的美术馆落地青岛,西海美术馆以开馆展“超越”带动艺术新浪潮
发帖: 1090
威望: 点
注册时间:2012-05-30
最后登录:2021-10-20
|
[楼主]
点蚊香
2021-08-23 11:24:48
来源:后现代主义哲学 阿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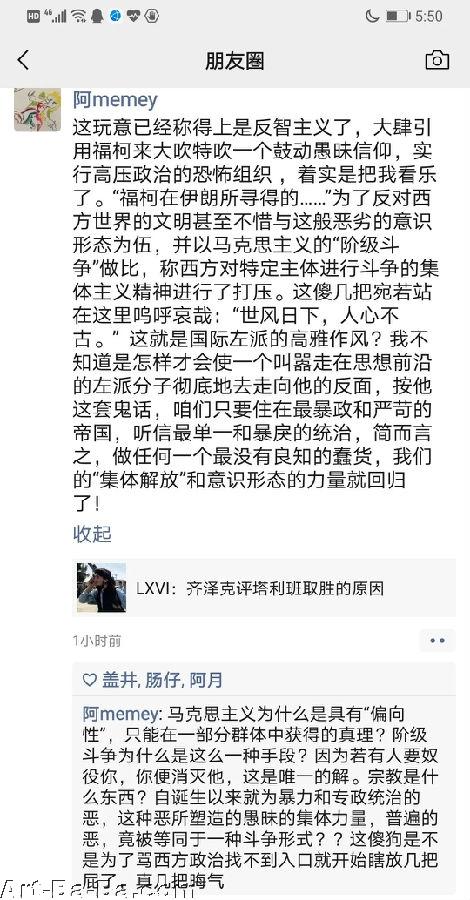

在上次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里,齐泽克揶揄了列宁,迎来国内苏联威权体制爱好者的一片谩骂;这次,齐泽克则因为他对前现代神圣主人的组织形式的某种赞扬而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当然我们对《前现代神圣主人为何能光速重夺阿富汗》这篇齐泽克新写小散文的指责绝不会仅限于齐泽克已经老年痴呆了他现在说的全是胡话,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他的论述本身上——纵观全文,齐泽克最核心的叙事其实很简单,他对比了两种“真理”,一是卢卡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建立在对偏向性的排斥之上,而恰恰是因为它具有偏向性,无产阶级才能先被建构成一个特定的革命主体,再从此位置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二是资本主义的真理,它们理性、客观、中立,它们是缺失偏向性的真理,因此人民无法被这种真理组织起来,被此类言辞规训之后,人民便只能被动地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在面对前现代神圣主人时显得不堪一击。这里,齐泽克认为无产阶级需要偏向性的真理来引导,并终将以集体的形式卷土重来,现在的环保主义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具有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一些近乎殉道的个人生存样态,并且它还要求我们牺牲掉当前已经习惯的许多资本主义之下的乐趣,这代表着环保主义具有着类似前现代神圣主人的模式,我们可以借助它(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以对抗资本主义和前现代神圣主人的入侵(齐泽克全文在原文链接里)。这个观点问题很多,我们先从最表面上来说,齐泽克实际提倡的正是一种政治姿态上的右翼保守主义,一个人获得了偏向性之后便不需要再向其他的维度敞开(因这种敞开反而使得偏向性难以为继,不断革命只会有损齐泽克“革命”主体的“革命性”),最终形成了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又决定屁股的奇谈,类似的话语诸如“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当然永远站在自己的同胞这边啊”,此处的主体便只需要当好一个傻瓜,无限地保守在自己内部的偏向性里就完事了。进一步而言,为了达成这个效果,主体必须被困死在一个笼罩了他一切可能的思维运动形式并深刻内化在他心灵深处的信息茧房牢狱里,才能保证其偏向性不受到外界其他话语内容的捕获,因而此类主体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认知,都将有赖于其内在偏向性抹除所有差异,并使其通通转化为偏向性真理的再复制与再生产,这样单向度的人民,入眼所见入耳所听皆为有待于被偏向性真理重构之客体,他们盲目得根本连他人都看不到,又怎么可能真正被纳入一个集体呢?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都于无数个维度被连接在一起,而偏向性既然不是普遍的,那它必然只能依靠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不断寻找敌人—斩断连接来确立它自己,由此可知,越纯粹的偏向性就越是需要将更多层面的人民和外部连接抛射出虚构共同体才能成立,在此构成了一个大写的“自绝于人民”,前现代神圣主人的偏向性纯粹到无以复加,简直是一群pure big sb,但这对集体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严酷的前现代神圣法以主人的姿态凌驾于一切之上,只会减缓、停滞、甚至摧毁集体的运转罢了。不要谈什么教育、建设、经济和科技发展了,前现代神圣主人连最基本的种植和粮食生产都搞不定,面对他们自己闹出来的大饥荒,神圣主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把脸贴地上求现代性威权联合体要粮不成,便只能废物似的对着压根不会反抗的巴米扬大佛气急败坏满地打滚口吐白沫无能狂怒,这下真是反动派炸了反动派遗址宛如大水冲了龙王庙(虽然这大佛也只是另一波前现代神圣主人奴役老百姓造的狗东西,但我完全支持对其妥善保存,以便于让后来的人民看看历史上的反动派们对待无产阶级到底有多么黑暗和残忍,很有教育意义的),总的来说,前现代神圣主人没有生成集体,反而其一切行动都不过是对集体的摧残和戮害,这帮货色入主了个威权中心怎么能叫前现代神圣主人的胜利呢?这只是当地人民的失败罢了。
谈完了齐泽克的叙事问题,我们再谈一下齐泽克这篇短文的两处错误,第一,诚然,前现代神圣主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偏向性,但前现代神圣主人的偏向性是唯心主义的偏向性,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唯物主义的偏向性,这么显而易见的根本性断裂齐泽克居然没有看到,最终导致了齐泽克的第二个更荒谬的错误,实际上,前现代神圣主人的组织形式绝非齐泽克认定的是集体主义的,而正相反,前现代神圣主人恰恰是绝对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他们思想的时候,一些人会说“你们马教徒又来传教了”,这么理解当然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和传教混为一谈。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前现代神圣主人传播前现代神圣法却只是为自己死后可以升入天堂而积攒福报,前者才是目的,后者只是手段而已。简单来说,唯物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才去传播偏向性真理,而唯心主义者却认为,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他者—安那其拉拉神在审视和评判着自己一切行为和思想的价值,以衡量自己作为个人死后将会受到怎样的待遇。传教?那只是大主人的任务罢了,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在死后得到大主人的奖赏。马克思主义者散播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有所帮助的,但对于真正的唯心主义教徒来说,在他们的认知里大他者—安那其拉拉神或耶和华神全知全视全能,祂已经无敌了,传教压根不是为了帮助祂让祂变得更强,也不是为了教会作为“人群—信仰—聚集”的集体利益,而是因为神的大审判终将来临,那一刻所有的死人都会被神复活,并按照生前所作所为升入天堂或永坠地狱,因此前现代神圣主人传教、发动惊骇猪突、杀死唱歌者、跳舞者和通奸者压根就无关集体的福祉,而恰恰相反,这些行为均是出于绝对的自私自利,是为了自己在死后天堂里可以享受更多的处女。可以说,前现代神圣主人在面对现实秩序时展现出的充沛的武德,正是来自他们唯心主义的对现实秩序意义的直接否定,如果非要在左派里生拉硬拽出一个和他们类似的群体,那也不应该是将意义存放在现实之中且费拉不堪的环保主义者(现实主义是像拖拉机一样没有力量的),而应该是俄国虚无党这种人,这些安那其—虚无主义超人在二十世纪发动了大量的惊骇猪突事件,正如鲁迅所言,人们一听到俄国虚无党的名字就会被吓得屁滚尿流。
进一步来说,前现代神圣主人式的惊骇猪突是绝对个人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因为在他们的意识结构里,总有一个被臆想出来的无所不能的崇高客体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他们,迫使其个人完全闭合成绝对原子化主体,并且整个生存样态都要朝向他内在精神的唯一单向度通路,这样的个体当然不“存在”于此岸的集体,而是仅能“存在”于其反动颅内对彼岸的纯粹个人化意淫里——仅能“存在”于那个个体内向性臆想之中有七十二个处女在等待着他的精神神国里。这恰恰意味着前现代神圣主人完完全全是集体主义的反面,每个愿意发动自我回归实在界式惊骇猪突的前现代神圣主人,对自己此刻生命身处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前现代集体之中的存续均是毫无留恋的。齐泽克能管这个叫做集体主义实在是太搞笑了,我当场变成流汗黄豆。
对齐泽克文章的批判已经到此为止,但这篇文章仍然尚未结束,因为左翼不应该给自己先在地预设一个偏向性立场再去理解事物(不过这就属于我个人观点的范畴了)。依我之见,在996、福报、打工人和反躺平的日常语言的压迫里,才有了阶级斗争作为左翼哲学的生成;在马子,婊子,守贞和荡妇的日常语言的压迫里,才有了女权主义作为左翼思想的迸发;在黑鬼,棒子,鬼子,白皮猪和黄皮猴子的日常语言的压迫里,才有了后殖民主义作为左翼理论的涌现。左翼哲学的来源不应该是某些理论家的知识、书本或视频所规定的偏向性,恰恰相反,它就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秩序的直接性反抗,准确来说,左翼哲学是日常压迫性话语语系之下的裂缝,它理当具备一种愤怒的情感力量,只有依靠撕开日常话语致密的压迫性,才能使被遮蔽的自身得以作出一个破坏性地显现。因此,左翼话语不在过去(过去符号秩序上的裂隙早已发生变化,强求历史不过是象征层意义上的刻舟求剑);不在现在(“现在”是一个创伤性的场所,它正是左翼哲学被遮蔽被压抑被暴政的地方);而只在未来——左翼哲学永远是一种尚未到来的新事物,它是未来充盈的激荡的不可能性赠予当下的礼物。很多所谓的“左翼理论”的使用者,使用拉康精神分析/德勒兹分裂分析/阿甘本政治神学或者别的什么去理解世界,现实秩序里异质化的事件一形成,他们就拿着源源不断的“左翼术语”铺天盖地地覆盖了上去,这是一种对压迫性事件捕获、遮蔽和再压抑的叙事态度,无法走向对事件—裂隙和直面和遭遇,他们说出来的话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只是早已被提前写入他们先在被规定的偏向性里的旧事物罢了。对这些人来说,总是先有了一个左翼的话语体系—偏向性真理的到场,再有这一系统对具体事件的分析,我无法接受这样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我这儿,整个结构必须被全部颠倒过来——一定是左翼先把自己一切预设的立场和话语全部清空,再去直面那个具体的事件,让这个事件内部被压抑和被暴政的裂隙,反过来借助我的知性和灵感,去创造、生产乃至迸发出新的左翼理论。不是拿着现成的理论去侵入性书写现实事件,而是在现实事件这里直接将尚未到来的崭新的左翼理论创造出来。这里需要注意,我不是说我在反对学习,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学习更多的哲学家(就我目前读过的东西来说,只有《千高原》是唯一不需要被“学习—知识”的姿态所进入的读物,重点只在于对《千高原》的阅读于何种程度上启发了我们自己的灵感和思考,这当然不代表《千高原》比其他哲学书更好,我的意思只是《千高原》和其他哲学书不一样),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差异性是个人思路的逃逸线涌现的地方,而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则是哲学史生成的地方,我们要在更多异质化的哲学系统里穿梭,而不是困守在一个单一话语体系的偏向性里——后者意味着一种非常危险的面对一切事物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什么是精华?人只能从自己理性的偏向性里出发去判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人只能从自己理性的偏向性里出发去判断什么是糟粕。认可了这个,这人就在他自己的偏向性里完成了绝对的原子化式闭合。现在,面对这些保守派喂给我们的狗屎,这些“黑鬼”,“婊子”和“996的福报”,你们不愤怒吗?你们的愤怒难道没有生成一种灵感吗?你的灵感难道没有产生将整个反动的外部现实秩序和你精神内在秩序颠倒或撕裂的力量与冲动吗?你们的灵魂里难道没有这些不断涌现的、流溢的、喷薄的、迸发的、就连直面事件之后临时预设的大纲也无法限制的写作的磅礴气势、激情与美吗?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总是,看,事件出来了,吴亦凡被逮捕了,那么,拉康会怎么看?德勒兹会怎么看?阿甘本会怎么看?以及最闭合最单向度的,我自己的偏向性会怎么看?这人就好像把脑子交给了一个外部的秩序(自我就是一个他人),任由这一外部秩序将其复读的话语投射和倾泻到现实的事件上去,这道覆盖了对象裂痕的幻象天幕,除了能压抑和遮蔽他自己涌动的灵感之外,我不知道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的写作来说还有什么好处——这样复读机式的写作是不能唤起主体的差异与强度的。其实哲学并不复杂,它只需要你具备足够多的激情与叛逆,以至于你有足够多的勇气能说出这样的话语——思考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